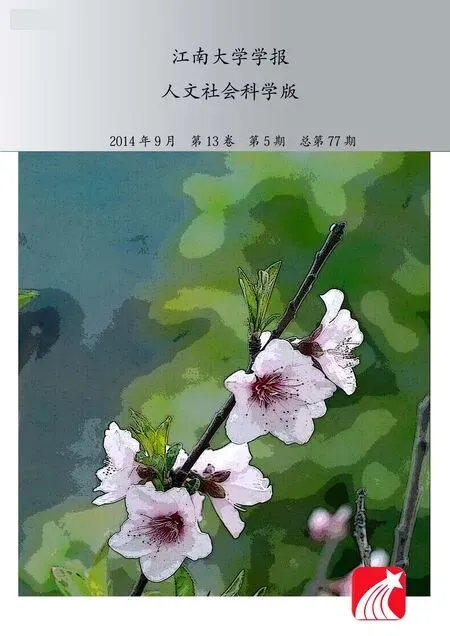明代于都“何黃语录”解义
2014-04-15蔡仁厚
蔡仁厚
( 台湾东海大学 哲学系,台湾 台中 40704)
一、黃宏纲“洛村语录”解义
黃宏纲(1492-1561)字正之,号洛村,江西于都人。洛村从学阳明,与善山相先后,同在阳明巡抚南赣之时。当时阳明一面平寇乱,一面讲良知学。南赣各县从游者,于都士子独多于他邑。阳明教法,士子初学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后与之接谈。洛村列于高第,后又随阳明入越,不离师门者四五年,接引后学一如南赣。阳明卒后,更居守师宅共三年。据此可知,洛村在王门亲炙之日特久。阳明既逝,妻弱子幼,而朝议多歧,且有削爵、禁伪学之逆施。洛村居守师宅,与同门共相护持,其行谊有足多者。
《明儒学案》本传,说他任刑部主事时,因为不愿刻深(对嫌犯深文周纳,刻意求刑)以逢迎上意,乃致仕(辞官)而归。先后与邹东廓、聂双江、罗念庵、欧阳南野等相聚讲学,流连旬月。“士子有所讲质,先生不遽发言,瞠目注听,待其意尽词毕,徐以一二言中其窍会,莫不融然。”他这种简言解疑的教法,可以证见他的学养深厚,文理明通。本传又说,洛村之学再变:“始者,持守甚坚,其后以不致纤毫之力,一顺自然为主。其生平‘厚于自信而薄迎合,长于持重而短机械(不会耍弄心机)’,盖望而知其为有道者也。”
(一)自先师提揭致良知,莫不知有良知之说,亦莫不以意念之善者为良知。以意念之善为良知,终非天然自有之良。知为有意之知,觉为有意之觉,胎骨未净,卒成凡体。(《洛村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王阳明的良知学,首先在赣州开讲,五十岁时又在南昌揭示“致良知”三字为口诀。从此以后,世人“莫不知有良知之说,亦莫不以意念之善者为良知”。这大概是当时的情形。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黃宏纲特为指出,甚是切当。
阳明所讲的“良知”,乃是天理明觉,是至善的心体。绝不可落在“意念”上而“以意念之善者为良知”。如果以意念之善者为良知,便表示你讲的良知不是“天然之良”,而只是后天偶发的意念。凡是偶发都沒有定准。而良知乃是定然如此,不是偶发。所以“知善知恶”的良知,才是判断是非善恶的定盘针。
如果所谓良知只是“有意之知”,明觉只是“有意之觉”,便表示此人夹杂意念,胎骨不纯不净,到头来只是个凡俗之辈,成不了圣贤君子。
(二)治病之药,利在去病,苟无病,臭腐神奇同为元气。本领既是知觉,意念莫非良知,更无二本。(《洛村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这一条说“意念莫非良知”,和上一条“以意念之善者为良知”,意旨相同。黃宏纲既批评上一条,何以又肯定这一句?我本乎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言,不敢强为之说,敬待能者解之。
(三)喜怒哀乐之未发,且不论其有时与否。但子思子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曾谓天下之本,可以“时”言乎?未发非时,则道体之功,似不专于归寂而已也。故子思子曰:“致中和”,盖合寂感以为功者也。(《洛村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中庸》首章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条语录指出,喜怒哀乐之发虽然有“时”,而未发则不论有时无时。因为未发之“中”,是天下之大本,大本超越时空,所以不以“时”论。未发之中相当于《易传》之“寂然不动”,已发之和相当于“感而遂通”。良知发用,通合“动、静、寂、感”,亦通贯于“未发、已发”。所以语录末句说“致中和”是“合寂感以为功”。若寂与感分隔不合,便不能“天地位,万物育”。
其实,阳明讲“致良知”和《中庸》讲“致中和”,在义理上是相互印合的。依阳明,良知即是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宜,皆得其成。中与和是原则。推致“中”的原则,可使天地正其位,推致“和”的原则,可使万物得其化育而生生不息。可见“致良知”与“致中和”,二者皆可创造价值和成就价值。
宏纲又指出“体道之功,不专于归寂而已”。这是针对聂双江和罗念庵二人说“知善知恶”的良知不是真良知,必须致虛守寂,回归良知寂体(归寂)才是真良知。宏纲守护师说,认定“知善知恶”之良知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的良知独体,皆是真良知,皆是良知真体。而聂双江的说法,实非谛当。
(四)或疑慈湖之学,只道一光明境界而已,稍涉用力,则为著意。恐未尽慈湖。精于用力者,莫慈湖若也。所谓不起意者,其用力处也。绝四记中云云,慈湖之用力精且密矣。明道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善用其力者,固若是。慈湖千言万语,只从至灵至明、广大圣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中提掇出来,使人于此有省,不患其无用力处,不患不能善用其力矣。徒见其喋喋于此也,遂谓其未尝用力焉,恐未尽慈湖意也。(《洛村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杨慈湖,名简,南宋陆象山之大弟子。他顺承象山之“明本心”的脉络,提出“不起意”三字为讲学宗旨。大意是说,人之为善,若顺仁义本心自然而为,其中沒有一丝一毫私意杂念。这样行善,就是纯粹的善。如果另起私意,私心私欲便乘机而入。这时候,人之行善便不纯净,而有了各种私意私念之夹缠。所以慈湖特别标举“不起意”以为学的。
如此一来,学者便误以为慈湖之学,只是讲说一种光明的境界,全不致力于圣贤工夫。人若稍涉用力,便被判为“著意”(起意执著)。黃宏纲认为,如此理解慈湖,是不妥切相应的。事实上,慈湖的“不起意”,便正是他用力之处。他不是不用力,而是顺乎本心而“不助长”。(若起意,便正是助长)。
孟子有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长也。”程明道特为指点,说孟子必有事焉,勿忘勿助,是自然顺适,由仁义行。既然自然而然,当然“未尝致纤毫之力”。这就是所谓“不起意”。
宏纲于此,深有体会。他看出慈湖千言万语,只从至灵至明、广大圣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中提掇出来(抓住要领,反身而诚),使人于此有省(省察觉悟)。如此一来,还怕“无用力处”吗?还怕“不能善用其力”吗?世人不解慈湖之意,所以胡乱揣测,喋喋不休。
其实,慈湖“不起意”,实与象山“明本心”意旨相同。“明本心”是要彰显仁义本心,是从正面积极地说。“不起意”是要克除私意杂念,这是从负面消极地说。总之,象山阳明是心学,慈湖也是心学(当然,心即理,心学也仍然是理学)。宏纲是阳明高徒,所以也能深知慈湖之意。
(五)存主之明,何尝离照?流行之照,何尝离明?是则天然良知,无体用、先后、內外、深浅、精粗、上下,一以贯之者也。(《洛村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存、主于內(存养本体),照、显于外(本体发用,光照万物)。存主在心的“明”不离“照”。明是体,是本性;照是用,是功能。体用不二,不相离析。同理,流行于事物的“照”(照察事物之理),也不离“明”。由体起用,离了体则不能承体起用。反之,离了用也无从见体。(必须即用以见体)。
宏纲称阳明所讲的良知为“天然良知”,表示良知是先天如此,不是后天寻求得来。因此必须“一以贯之”,不容许分隔间断。所以宏纲说:“天然良知,无体用、先后、內外、深浅、精粗、上下,一以贯之者也。”
凡是分离“体与用、先与后、內与外、深与浅、精与粗、上与下”,都只是事物表相的分别。在形上本体(良知本体)那里,是不容许离析分化的,是通而为一“一以贯之”的。
(六)人心只此独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视听喜怒诸物,舍此更别无著力处矣。谓天下之物,触于前者有正有不正,又谓知、意、心、身,无能离天下、国、家而独立。是以物为身之所接,而非所谓备于我者,虽视听喜怒未尝不在其中,而本末宾主则大有间。后世格物之学所以異于圣人者,正惟差认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不容不补。主敬存养以摄归身心,而內外动静不得不为二矣。(《洛村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这条语录,首先标举“人心只此独知”。盖“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知,即是“知善知恶”的良知。良知发用,“出乎身而加乎民”的具体行为,又是通过“目之视、耳之听、口之言、四肢之动”以及“喜怒哀乐”之情而表达。而视听言动、喜怒哀乐,便正是工夫著力之处。(视、听、言、动,皆合礼。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这就是工夫得力之证明。)
但也有人说,在人面前出现的“物”有正有不正。又说《大学》八条目中的“知、意、心、身”不能离开“天下、国、家”而独立。这样的说法,正好是以“物”为身之所接,而不是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如此看人,人只是与物相对的“小我”,而不是与物为一体的“大我”。大我的生命才能与万物为一体,也才能与天合德。
语录后半,评判程朱格物之说。程伊川有云:“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以穷理,正好将“物”与“人”置于相对之两端。如此看物,便是黃宏纲所谓“差认(错认)此一物字”。于是,又补上一段“主敬、存养”工夫,想要摄归身心。如此,乃使內外动静对立为二,而与圣人“物我一体”之义不合。
今按:关于《大学》格物致知的诠释,朱子的重点在“格物”(即物穷理),阳明的重点在“致知”(致良知)。二家之说,各成系统,而又未必是《大学》之本义。对这二个系统,我们只讲明义理,而不必投入门派之争。
(七)往岁读先师书,有惑而未通处,即反求自心,密察精进,便见得自己惑所从来:或是碍著旧闻,或是自己工夫犹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义上比拟,与后儒作用处相似,是以有惑。细玩先师之言,真是直从本心上发出,非徒闻见知识轮转。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乃知笃信圣人者,必反求诸己。反求诸己,然后能笃信圣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训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则相与滋惑也已。(《洛村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这一条语录,先说惑之所从来:或是碍于旧闻而生惑,或是自己工夫未透(未免在事迹上揣量、在文句上比拟)而生惑。等到自己细细体会,从容玩味之后,方知阳明所言,都是直从本心发出,并非从闻见知识上轮转。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正须各归自己以深造自得。
反求诸己,是自信自肯;笃信圣人,是服善信道。二者(指反求与笃信)相需为用:笃信圣人者必反求诸己,反求诸己而后能笃信圣人。如此而后乃能判定古人训诂解说上的是非,以解蔽辨惑(解我蔽塞,辨我疑惑)。否则,滞于事迹、文义,便不免相互牵扯而滋惑(滋生疑惑)而已,又有何益!
宏纲此条所说,诚直信实,不可作泛语错过。
(八)谓谢子曰:“太古无为,中古无私;太古至道,中古至德。吾将与子由至德而观至道,由无私而游无为乎?”谢子曰:“古道辽矣,孰从而观之,孰从而游之?”曰:“子不见耳目口鼻视听言臭乎?今之人耳目口鼻之于视听言臭也,犹古之人耳目口鼻之于视听言臭也,吾何疑焉?则吾心之于是非诚伪,无古今之殊焉,吾又何疑焉?日往而月来,寒往而暑来,今之日月寒暑,犹古之日月寒暑也,则又何爽焉?吾心至德,吾心至道,吾心无私,吾心无为,而奚观乎?而奚游乎?苟有志于希古者,反而求之吾心,将无往而非古也已。”(《洛村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这一条语录,宏纲发挥“心外无道,心通古今”之义,说来颇为亲切。
首先,他提出二句话:“太古无为,中古无私;太古至道,中古至德。”同时邀约谢子(名不详,当是宏纲门人弟子)由至德而观至道,由无私而游无为。谢子回答说:“古道辽(辽远)矣”,何从而观,何从而游?宏纲之答,分为二点:(1)今之人的耳目口鼻视听言臭,与古之人的耳目口鼻视听言臭,完全一样。同理,我心对于是非诚伪的判别,也同样是古今相同,沒有殊异。(2)日往而月来,寒往而暑来,这是时序使然。今天的日月寒暑与古时候的日月寒暑也完全一样。同理,至德至道,无私无为,也同为古人今人所共同向往,实无差别。
然而世人不察,以为“至德至道、无私无道”,必须求之于外,乃有所谓“观”,乃有所谓“游”。其实,至德至道,无私无为,皆在吾心,何必向外而观?何必往外而游?只要有志希古(希慕古圣先贤),返而求之吾心,自然通今通古,古今不二,而至德至道、无私无为,也全在吾心。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世人皆属万物之灵,亦知“欲至德、欲至道、欲无私、欲无为”乎?(试一思之,即得正解。)
(九)先师之学,虽顿悟于居常之日,而历艰备险,动心忍性,积之岁月,验诸事履,乃始脫然有悟于良知。虽至易至简,而心则独苦矣。何学者闻之之易,而信之之难耶?(《洛村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阳明曾经表示,他的良知学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一口说与学者。而学者沒有经过事上磨练,不知艰苦。因而便把良知学看得太轻易了。如此,自然无所得力。于是“知之而不能行”或“行而不得其道”的情形,所在多有。
宏纲关心师门之学,也察觉到一般学者对于良知学“闻之甚易”而“信从卻难”。他和阳明同其感受,所以也发出这无可奈何的感慨。
今按:阳明良知学,是一套“即知即行、知行一贯”的道德实践学。落在《大学》上说,可以简约为“心、意、知、物”四句: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拙著《王阳明哲学》(台北、三民书局)第七章第二节“四句教释义”,有详尽之说明,请参阅。在这里,只能述其大要:
第一句讲“心体”。心体是理,不是事。这是第一点。第二、事有相而理无相。第三、心体是理,不显善恶之相,故曰“无善无恶”。阳明有云:无善无恶是谓至善。据此可知,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和说“至善无恶心之体”,意指是一样的。若问:只说“至善无恶”不就好了,何必再说“无善无恶”添麻烦?对!你这一问正说出了大家的疑团。不过,所谓“大家”,是指一般人或一般学者。至于讲良知学的人,则必须把道理说透。不可因为怕麻烦便不深究。所谓“至善无恶”是正面的表,“无善无恶”是反面的遮。“表诠”与“遮诠”皆须顾到而不宜偏废。这样讲义理,才显得能探根究柢,周全透彻。所以,凡讲义理,都必须说到究竟处。
第二句讲“意之动”。心体至善,沒有善恶之相。但心所发出的意念,便不免有善恶的分化。顺心体而发的意念是善的,不顺心体而发的意念便善恶混杂而有善有恶了。谁能辨知意念的善恶呢?当然是良知了。
第三句讲“良知”。意念发动,是善?是恶?只有良知能夠觉知。这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的地方。所以说“知善知恶是良知”。
第四句讲“格物”。良知知善知恶,再由知善而好善,由知恶而恶恶。格物之物,事也。从视听言动到生活行为,都是“物”(事物)。善的事物要好而为之,恶的事物要恶而去之。“为善”是做好事,“去恶”是不做坏事,如此便是“格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便是格物。这是阳明的格物说。
(十)有迁官而较远近劳逸者。曰:“不然。责望于人者,谓之远;求尽于己者,谓之近。较计于远近者,谓之劳;相忘于远近之外者,谓之逸。苟有以尽吾心,远、近、劳、逸,吾何择焉?吾惟尽吾心而已矣。”(《洛村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迁官、升官也。世人为官,通常都会计较任所之远近与职事之劳逸。宏纲于此,提出一番“尽吾之心”的议论。他说:
“责望于人”者,自己不能做主,所以事事物物,都觉得远不可及。“求尽于心”者,操之在我,只要自己尽心致力,即可有得有成。
人若时时计较远近,便不免朝夕忧虑,心劳日绌。反之,若能相忘于远近之外,便可以心平气和,无所牵挂。由此可见,人只要“尽我之心”,便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又何必计较远近劳逸呢?
二、何廷仁“善山语录”解义
何廷仁(1486-1551),字性之,善山是他的号,江西于都人。他奉派为广东新会县令时,內心非常感奋。他说:我虽不及白沙之门,如今有幸到他家乡任官,怎敢以俗吏临其子弟呢?(按、陈白沙(献章)是明代大理学家,广东新会人,从学于江西吴康斋(与弼),归而发扬孟子之学,声名甚显。)于是,先谒白沙祠堂行礼致祭,而后入县衙视事。
后来,阳明巡抚南赣,讲良知之学。善山慨然曰:吾恨不得为白沙弟子,今又可失之耶?乃专程见阳明于南康(属赣州府),遂为高第。当时,阳明忙于平乱,难得亲讲席,四方来学士子,多由高第接引,疏通大义。善山年长,而又心诚气和,不厌详细,学者益发亲近。
《明儒学案》善山学案中有云:阳明卒后,善山与洛村约同志会讲于南都(南京),诸生往来者常数百人。故一时为之语曰:
浙有钱王,江有何黃。
钱绪山、王龙溪,是阳明晚年二大弟子。钱绪山完成《王阳明年谱》,功劳特显。王龙溪弘扬师门良知之学,影响最大。二人是浙中王门的代表人物,而江右王门则人物最多,何黃二人同列高第,在南都会讲时,声光特显,故时论举二人与钱王相提并论。
(一) 圣人所谓无意无情者,非真无也,不起私意,自然无意无情耳。若果无意,孰从而诚?若果无情,孰从而精?是尧舜不必惟精,孔子不必徙义改过矣。吾故曰:“学务无情,断灭天性;学务有情,纵情起衅;不识本心,二者皆病。”(《善山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圣人也是人,当然有意有情。但世人之意常是私意,世人之情也常是私情。所谓不起意、不留情,正是就“私意私情”而言。
《大学》讲“诚意”,如果无意,如何能诚?尧舜“惟精惟一”的工夫,和孔子“徙义、改过”的德行,都是针对意与情而道之成德、引之成善。何廷仁有见于此,所以拟为三句以述心得:
(1)为学若致力于无情,便将断灭天性。(无情无意,何以为人?)
(2)为学若致力于有情,又将随情意而泛滥,甚至引发闲隙而爭斗。
(3)为学若不能识得本心,无论“学务无情”或“学务有情”,二者皆将成为弊病之缘由。
(二)有意固谓之意见,而必欲求为无意,是亦不可谓非意见也。是故,论学不必太高,但须识本领耳。苟识本领,虽曰用意,自吾留情;苟不识本领,虽曰欲无意,只是影响。(《善山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此条与上一条相通。“有意”固然是意见,力求“无意”也是一种意见。论学要平实,不必过高。但要识得“本领”。所谓本领,是指良知原本领摄(领有)的实践功能。譬如“知善知恶”、“好善恶恶”、“为善去恶”皆是。
只要识得(体悟、体证)本领,虽然顺意起用,也不会为私情私意牵绊。如果不识本领,虽然说是“无意”,其实他的所知所见,都只是影响之谈。(影子、声响,皆非本根,只是一些闻见之知、世俗之见。)
(三)或谓:“求之于心,全无所得,日用云为,茫无定守。”夫良知在人为易晓,诚不在于过求也。如知“无所得,无所定守”,即良知也。就于知无所得者,安心以为无得,知无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岂非入门下手之实功乎?況心性既无形声,何从而得?既无定体,何从而守?但知无所得,即有所悟矣,岂真无所得耶?知无定守,即有定主矣,岂能无定守耶?(《善山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日用云为”,“日用”指日常生活,“云”指言语,“为”指行为。有人说,求之于心,全无所得,反而使得日常生活言行,茫茫然不知所定与所守。
何廷仁在此指出,人人皆有良知,这个道理很平常易晓,的确不必过于深求。譬如此人能夠知道自己“无所得,无所定守”,这就是他的良知。顺就他知道“无所得”,而即安心以为无得。顺就他觉知“无定守”,而即安心以守之。这不正是入门下手的实工夫吗?
何況心性既无形声,何从而得?心性既无定体,又何从而守?只要他真知自己无所得,便当下可以有所悟;既有所悟,又怎麼会无所得呢?他知道自己无定守,便当下可以有定主,既有定主,怎麼会无定守呢?
这一条宛转开道,经过层层反问,使话语渐次落实。由此可知,良知随时而在,就看我们是否能反躬自省,一念警觉,使良知当下呈现。
(四)后世儒者,不能至于圣人,其毫釐之差,只不信此。使果真知,即刻一了百当,自是了得终身。见在此心,合下圆成,合下具足,更有何意可起?何理可思?苟有所思虑,盖不过殊途同归,一致百虑而已。(《善山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儒家的经典,都说人皆可以成圣成贤。但除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外,后世的儒者为什麼不能到达圣人的境地呢?何廷仁说,其中毫厘的差别,只在人“不信此”。
今按:这个“此”字,指人成圣成贤的根据,像“仁、本心、良知、四端”等等。总起来说,“此”字就指人的良知本体。人人都有良知本体。但你如果不能“笃信”自己真有良知,你就不可能真心诚意地“致良知”。你的良知不能通到自己的生活行为上,也不能通到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和家、国、天下上面,便不会有“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可能。这就是后世人不能成圣成贤的关键所在。
如果人果真明白这个道理,便当下肯定自己有良知,并时时警觉,不断做致良知的工夫,自然就可以事事物物一了百当,直到终身都能事事合乎天理。
“见在此心”,见音现,指现前当下的良知本心。我们的良知本心“合下圆成、合下具足”,是说良知是人人生而即有的,而且是完完整整,十足圆满的。和圣贤的良知完全一样,分毫不差。这时候,天理良知做主,便不会有私意杂念,也不会思前想后,强词夺理了。如果说,人总是各有思虑,也不过是“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而已。
(五)有欲绝感以求静者,曰:非也。君子亦惟致其良知而已矣。知至则视无不明,听无不聪,言无不中,动无不敬。是知应物之心非动也,有欲故谓之动耳。苟有欲焉,虽闭关习静,心斋坐忘,而其心未尝不动也。苟无欲焉,虽纷华杂扰,酬酢万变,而其心未尝不静也。动而无欲,故动而无动,而其动也自定。静而无欲,故静而无静,而其静也常精。动定静定庶矣。(《善山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寂与感,动与静,是理学家做工夫时常用的字眼。第一句“有欲绝感以求静者”,是说有人想要断绝“感”以求“静”。何廷仁指出,这样是不对的。
一个为学君子,只要正面“致良知”就可以了,不必在动静寂感上多作计较。良知真能推致到“视、听、言、动”,便自然可以视无不明、听无不聪、言无不中(中理、合理)、动无不敬(敬谨不失礼)。由此可知,人之应事接物乃是顺理而行,这不是“动”(有私欲才是浮动)。同理,人为了求静而绝感,这也不是“静”(无私欲之纷扰才是真静。)
一个人如果有私欲,虽然闭关静坐而达到“心斋”“坐忘”的境地,他的心也“未尝不动”而算不得真清静。反之,如果人无私欲,虽在纷华杂扰中应酬不断,他的心也“未尝不静”而实无浮动。
总之,“动而无欲”,故“动而无动”。虽有动的形相,实无动的纷扰。所以虽在动中而能静(心能贞定)。同理,“静而无欲”,故“静而无静”。虽在静中也能无适无莫,心入精妙。如此,便庶几是程明道所谓“动亦定、静亦定”的境界了。
按、程明道的“定性书”,我在《宋明理学?北宋篇》(台北、学生书局)第十二章三四两节有完全之论述,可参阅。
(六)所论“个中拟议差毫发,就里光明障几重。肯信良知无适莫,何须事后费磨砻。”即此知直造先天。夫本来面目,岂特无容拟议,虽光明亦何所有!诚知本体无容用其力,则凡从前著意寻求,要皆敲门瓦砾耳,门开则瓦砾诚无所施。虽太虛中何物不有,门戶瓦砾,色色具列,而不能染于太虛。思而无思,拟议而无拟议,道本如是耳。是故戒慎恐惧,格物致知,虽为眾人设法,在圣人惟精亦不废。不然,孔子尝谓“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而又忧“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以上达不离下学中得之,则磨砻改过,正见圣人洁净精微。(《善山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首先引对方一首歌诀:
个中拟议差毫发 就里光明障几重
肯信良知无适莫 何须事后费磨砻
第一句“个中”犹言此中,指为学这件事。人在为学之时多方拟议猜测,便显示他胸中无主,虽差之只毫釐,而谬以千里。第二句“就里”,承上句“拟议差毫发”而作指点,指出人若常拟议描绘,他胸中的光明便不免被一重一重的乌云障蔽了。第三句“适莫”,适音滴,犹言肯定,莫、犹言否定。人对事物若只一味肯定或否定,便表示他有成见,偏离中道。人只有肯定并信从良知天理,才能“知善知恶”、“为善去恶”而无适莫。如此的话,便进到第四句,而无须“事后费磨砻”了。(磨米、脫谷,都是后天的加工。)如果事事依良知天理而行,便一切都可以合理合宜,而无须加工补救了。
这首歌诀虽然言之俚俗,却亦意思贴切。何廷仁指出,若依此四句而行,可以直达先天心体。本来面目(良知天理)不容拟议,到究竟处,连良知本体的“光明相”也要化掉(直造化境)。
本体发用,乃自然而行(由仁义行),所以本体上是无须另外用力的。而一切的“著意寻求”,都只是敲门砖瓦。门开了,砖瓦便用不著了。“太虛”指本体世界。本体呈现的空阔世界,涵容万物,色色俱全,无所不有。但太虛虽涵容万物,而万物不会沾染太虛。道之功能作用无限无穷,它有思之用而无思之形迹(思而无思),它可以拟议一切而卻沒有拟议中的偏见成见。因为“道”本来就是这样的。
因此,“戒慎恐惧”、“格物致知”的实践工夫,虽是为眾人设立的规矩法度,而圣人“惟精惟一”,卻也并不废弃“戒慎恐惧”和“格物致知”的工夫。不然的话,孔子既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而又担心“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圣人之道,本就落实而平平常常(故谓之常理常道)。“上达”与天合德,也仍然要有“下学”的工夫。从不断地磨砻改过,正可看出圣人生命的“洁净精微”。
(七)天下之事,原无善恶。学者不可拣择去取,只要自审主意。若主意是个真心,随所处皆是矣;若主意是个私心,纵拣好事为之,卻皆非矣。譬如戏谑是不好事,但本根是个与人为善之心,虽说几句笑话,动人机括,自揣亦是真心。但本根是个好名之心,则虽孝亲敬长,溫凊定省,自揣还是欺心。(《善山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天下事物的本来面目,原是不分善恶的。学者要自家守住原则,拿定主意,不可随自己的私意而去做“去、取”的拣择。若自己的主意是个“真心”,则处处随真心而行就可以了。反之,若自己的主意是个“私心”,纵然你选择一件好事来做,也还是利害计较,说不上是善的行为。
譬如戏谑本非好事,但你本根上是个“与人为善”之心,虽然说了几句笑话,可能触动别人內心的机括(机括、意指机心),但你自己知道是一番真心,并无歹意。
反之,如果你本根上是个“好名之心”,则你表面上虽然“孝亲敬长,溫凊定省”,但你內心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真心,而是“欺心”之行。
(八) 此学是日用寻常事,自知自足,无事旁求。习之则悅,顺之则裕,真天下之至乐也。今之同志,负高明之志者,嘉虛玄之说;励敦确之行者,乐绳墨之趋。意各有所用,而不能忘所见,此君子之道所以为鲜。(《善山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这一条指出,良知学乃是日常生活中的事,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知自足”,不必求之于外。学而时习之,自然可得悅乐。时时顺之而行,自然宽裕心安。所以良知之教实为天下之“至乐”。
但何廷仁又感觉到,如今有志向学的人,不免各有所偏:(1)具有高明之志的人,往往嘉尚虛玄之说;(2)砥砺敦笃的人,则往往趋于株守绳墨规矩。二者各有所用,且皆不能跳脫一己之所知所见。于是或“过”或“不及”,这就是“君子之道鲜矣”的原因了。
(九)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者,如或动于客气,梏于物欲,觉得胸中劳耗错乱,天地即已翻覆,亲而父子兄弟,近而童仆,远而天下之人,皆见得不好。至于山川草木,雞犬椅桌,若无相干,也自不好。天下虽大,我自不得其平矣。少则平其心,易其气,良知精察无有私意,便觉得与天地相似矣。不惟父子兄弟童仆自无不好,天下之人亦无不好,以至雞犬椅桌,山川草木,亦无不好,真见万物皆有春意。至于中间有不得其所者,自恻然相关,必思处之而后安。故尽天下之性,只是自尽其性。位育之理确然。(《善山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中庸》首章结句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说中而不偏倚,则天地可以正位;和而不流荡,则万物可以化育。如果良知不能做主,而为外来之客气所牵动,为物欲所桎梏,觉得胸中劳耗错乱。这时候,便是翻天覆地,于是父子之亲,与远近之童仆路人,皆似形成一种矛盾,看在眼里,只觉得他人之不好。至于山川草木,雞犬桌椅,更与自己不相干,看来也自不好。如此,则天下虽大,皆与我相隔对立,我将如何平天下!
稍后,我平其心,易其气,良知呈现而可以精察,始觉我与天地相似相亲,实非相隔对立。于是,不但父子兄弟童仆无有不好,且能证见万物也生机活泼,皆有春意(春生之意)。如果发现其中有不得其所者,也恻然关心,并设法使他得到安置。如此,则所谓“尽天下之性”也实是尽自己之性。而所谓“天地位,万物育”的道理,也确然可以信从了。
(十)天地万物与吾原同一体,知吾与天地万物既同一体,则知人情物理要皆良知之用也,故除卻人情物理,则良知无从可致矣。是知人情物理,虽曰常感,要之感而顺应者,皆为应迹,实则感而无感。良知无欲,虽曰常寂,要之原无声臭者,恆神应无方,实则寂而无寂。此致知所以在于格物,而格物乃所以实致其良知也。明道以穷理尽性至命,一下便了,于此可见。(《善山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这一条的前段,讲天地万物与我同为一体,故人情物理也都是良知之用(呈现起用,落实表现)。离开人情物理,则良知之致也无从具体落实,而不免成为空谈。
后段又指出,人情物理虽然常在感应之中,但那只是良知顺应事理之宜,为了应迹(应事接物)而感,而良知本体未尝逐物。是谓感而无感,感而常寂。凡应迹而感者,有感应之功能,而无感应之纷扰。故良知之感应,乃属神感神应(神妙不可测)。
儒家言体用,基本上都是承体起用。用从体来,即用见体,体必起用。故良知天理之起用,实乃自然而然者。偶或落于有为,也只是为了顺世俗而应迹,良知本体并未蒙尘而受拖累。
良知无欲,所以常寂。良知是无声无臭的寂体,但它虽“寂然不动”,却能“感而遂通”。所以良知又是寂感真几,自能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其神感神应,无有方所之囿限。寂而能感,是谓寂而无寂。
何廷仁这条语录,以良知寂感与致知格物关联起来。(1)寂而无寂(寂而能感),故致知工夫必落实于格物。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正,皆得其成。(2)感而无感(感而常寂),故格物正所以致其良知。事事物物皆得其正,皆得其成,岂不是良知已致?知既致矣,事事得其宜,万物得其所,自然归于无事。程明道所谓“穷理、尽性、至命,三事一时并了”(一时完成),亦可于此而得到印证。
(十一)象山云:“老夫无所能,只是识病。”可见圣贤不贵无病,而贵识病,不贵无过,而贵改过。今之学者,乃不虑知病即改,卻只虑有病。岂知今之学者,要皆半路修行者也。习染既深,焉能无病?況有病何伤?过而能改,虽曰有病,皆是本来不染,而功夫亦为精一实学耳。(《善山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此条先引陆象山的话,证实圣贤不以无病为贵,而贵“知病”以治之。所以不贵无过,而贵改过。
善山指出,今之学者,不去思虑“知病即改”,卻只担心“有病”。看来都是一些半路修行的人。他们习染已深,怎能无病?其实,有病何妨?过而能改,自然恢复本来面目。此中工夫,亦仍然是尧舜“惟精惟一”的精一工夫。
(十二)今日论学,只当辨良知本领果与慎独工夫同与不同,不当论其行事标末,律之古人出处異与不異。使其本领既同,而行事或过,自可速改而进神明之域;使其本领已失,而操履无过,虽贤如诸葛、韩、范、明道,尚惜其不著不察,而有未闻道之叹!(《善山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此条指出,今日论学,当以辨识良知本领最为优先。致良知的工夫究竟与慎独工夫相同不相同?这才是必须用力之处。不必去计较行事上的细微末节,只看与古人郑重出处相异不相异。如果成德的本领同于圣人之慎独,虽然行事偶或有过,也可以即时改正以进于诚明之地。反之,如果良知本领已经亡失,即使你的操持践履沒有过失,也难以成为有道之人。就如诸葛亮、韩琦、范仲淹、程明道之贤能,也还不免“行之而不著,习焉而不察”,而有未闻大道之叹。(按:诸葛等人当然是大贤。但理学家论人,必以圣人之道为准则。理境既高,论人必严。)
(十三)谓“近来勉强体究,凡动私意,一觉便欲放下。”如是岂不是切实工夫?但说得似易,恐放下甚难。若私意已尝挂根,虽欲放下,卻不能矣。须有好仁无以尚之之心,然后私意始不挂根。如此一觉放下,便就是洁净精微之学。(《善山语录》,《明儒学案》之《江右学案四》)
此条言及“私意挂根”之问题。何廷仁说到“近来勉强体究”,凡是私意萌动,只要一旦察觉,便想即时放下。这样当然是切实工夫。但说得很容易,真要做到“放下”二字,卻很难。其中的关键,在于你的私意是否已经“挂根”(生根)。如已挂根便难以除去。必须“好仁”之心放在第一位(无以尚之),然后私意方能从根消除。这是何廷仁切己自反的真切心得。必须如此,才是“洁净精微”的成德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