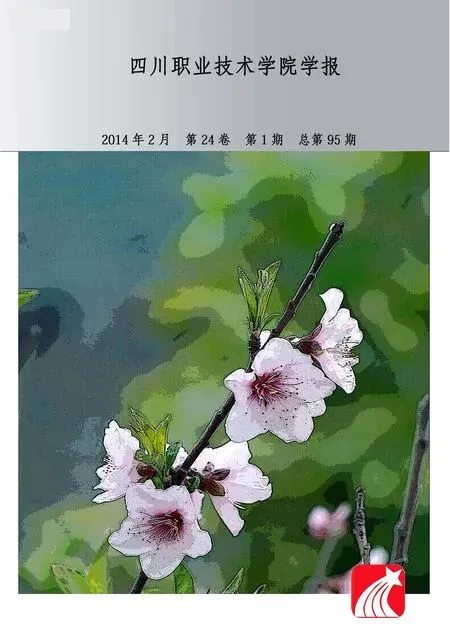论先秦道家的境界与修养
2014-04-11任明艳
任明艳,李 凯
(西南大学哲学系,重庆 北碚 400715)
论先秦道家的境界与修养
任明艳,李 凯
(西南大学哲学系,重庆 北碚 400715)
先秦道家依其觉解程度的不同可划分为冯友兰先生所谓“人生四境界”:老子、庄子皆追求与超世俗的大道相融合,属天地境界,达致这样的境界须通过“为道日损”、“心斋”、“坐忘”等修养工夫;宋钘、尹文汲汲救世,志在社会和谐,属道德境界,“情欲寡浅”是其修养工夫;杨朱营营谋求养生小利,属功利境界;《列子·杨朱篇》的作者以及田骈、慎到丧失精神追求,成为只剩生理欲望的动物性存在,属自然境界;自杨朱而下的人生境界不需修养而成,而是堕落而致的。
先秦道家;境界;修养
“境”与“界”二语源出于佛家,二语连用构成“境界”一词,意指人的心灵所能达到的界域或境地。人的境界有高有低,境界之高低会在心灵观照外部世界时呈显。近代思想家谭嗣同有“智慧深,则山河大地,立成金色;罪孽重,则食到口边,都化猛火”[1]之说,意谓对于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外部世界,不同的人会对其产生不同的感受,这感受的不同实际就取决于个人境界的高低。人要达到相应的境界,往往需要进行相应的自我修养,所谓修养,就是指个人为了实现某种境界所付出的努力、所作的自我调整。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依据不同的人“觉解”[2]程度的不同来划分人生境界。“觉解”的“觉”,指个人内在的觉悟,“解”,指个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解释,有什么样的内在觉悟,对世界就会作出什么样的解释,这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借助冯先生的“觉解”概念,我们便可发现,中国的先秦道家各派在境界上有极大之差异,决非铁板一块。
1.老子、庄子属先秦道家之主流,学界一般认为,庄子的思想是对老子思想的直接继承与发展,而在实际上,老庄的境界也确实大体一致。老子的境界可以被简要地概括为“观复”[3]。观复是一种极高的境界,观就是直观,就是身心合一的体验,复就是回归到本根,返回到道。老子把道视为天地万物的本源,所以,观复二字合起来讲,就是指,在至虚至静的状态下,个体就能全身心地体验到万物都要返回到道这一本源。老子认为,能够做到观复的人,就可以称得上“明”[3],从字面上讲,明只是明智或者聪明,但对老子而言,这个明是一种大觉悟、大智慧,因为通过这个明就可以洞见到宇宙的根本和生命的根本,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达到澄明的境界,对于宇宙、人生,做到明的人就不再有困惑和烦恼了。因此,观复的境界也就是一种与宇宙本源融合为一的境界。为了达到这一境界,老子提出了如下的相应修养方法,这就是“为道日损”[3](243)、“涤除玄鉴”[3](93)与“致虚守静”[3]。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是认为,获得知识靠积累,要用加法或者乘法,相反地,体验道靠减损,要用减法或者除法。“损”就是老子的修养工夫,损的对象包括了外在的知识和人自身的欲望等等。只有不断地减损知识和欲望,大道才能逐渐地澄明,逐渐地向我们呈现。显然,老子的这种修养方法的方向不是向外的,而是向内的。因为老子主张向内修养自身,所以,老子又提倡把人类向外观察的门户关闭起来。他说,“塞其兑,闭其门”[3](272),即关闭感官的通道,堵塞欲望的门洞。不过,仅仅闭目塞听还是不够的,不看不听只是不再接受新的知识,不再产生新的欲望,要想修道,还要在这一基础上,把已经获得的知识和已经产生的欲望逐渐排除掉,也就是要为道日损。除了“为道日损”,老子又主张“涤除玄鉴”。“涤除玄鉴”的字面意是洗去内心的尘垢。这里的尘垢又包括了人对于权势、利益、美色等的欲望和对于外界事物的知识。所以,涤除玄鉴也就是为道日损的另一种说法,涤除就是损。至于“致虚守静”,仍与为道日损、涤除玄鉴等方法同属一类,致虚也就是让头脑中已有的知识、规范、技巧以及对于利害关系的权衡等等内容被强行排除出去,从而解放自己的大脑,守静也就是保持内心的平和,不让情感和欲望扰动自己的心灵。老子关于修养方法的范畴和名词虽多,但它们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它们都是要求人们摒除内心的欲望、抛弃头脑中的世俗知识,从而让心灵恢复到空虚和澄明的状态。
庄子虽继承老子思想,却又不像老子那样关心现实的政治,老子还寄希望于统治者采取他的“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而庄子对政治彻底地不感兴趣,庄子只关心个体的自由,关注个人的心灵解放。在内在精神生命的追求上,庄子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并且正是在这方面发展了老子的哲学。《庄子》的境界可以“同于大通”[4]四字概括。所谓“同于大通”,也就是与大道合一、与大道融为一体。庄子的所谓道与老子不同,老子把道视为世界的起源,而庄子则认为世界起源的问题不可知。道对庄子而言,不具有实体性,它只是一种精神体验,不过,道这种精神体验具有超越性,换言之,有了道这样一种精神体验,人就可以俯瞰天下万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4](1342)。因此,对于庄子而言,与大道相合一,同样意味着老子的所谓“明”,在这种境界中,人完全恢复了自然本性,达到了精神绝对自由的状态。庄子用于达到这一精神状态的方法是“坐忘”[4]和“心斋”[4](130)。“坐忘”的关键在于“忘”,从忘仁义、忘礼乐,到忘肢体、忘聪明,忘的内容由外及内、步步深入。人的心灵不会仅仅因为身体静坐不动就一念不生,反倒有可能更加心猿意马、心神不宁,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坐驰”[4](134),所以,“坐忘”就必然要求姿势的调整和心态的转换的相互配合,而心态的转换显然是更加重要的。忘掉一切之后,人便可以“同于大通”了。“心斋”即心灵上的斋戒。庄子指出,“心斋”的方法要求人意念精诚专一,要求人关闭耳目等感官的通道并且断绝一切思虑。处于“心斋”状态下的心是空灵的,这个时候的人会连自我都忘掉,人的心灵既不排斥外界事物,也不执著于外界事物;总之,此时的心具有“虚而待物”[4](130)的特质。此外,这里所说的虚并不等同于绝对的虚无,用庄子的话说,它是“虚室生白”[4](134),“虚室生白”的字面意是空虚的房子里自然会产生白亮,庄子以此比喻空灵中会生发出无限的智慧,这智慧就是道,道就含藏在这空明的心境里——“唯道集虚”[4](130)。由此可见,“心斋”就是大道的本源。
综观老子与庄子,在修养的层面上,庄子沿着老子的思路,发展了其修养方法,从而使得悟道、体道的过程更具有可操作性;而在境界的层面上,无论观复,还是同于大通,都是指谓一种个人与大道融为一体的状态,因此,老子与庄子对于宇宙人生都有着最高的觉解,他们都实现了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当然,此“天人合一”实为“道”、人合一。总之,在境界层面上,老子与庄子难分伯仲。
2.关于宋钘、尹文所属的学派,历来受到学界争议,但多数学者依据班固“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5]之言,推定宋尹学派属先秦道家支流之一。宋尹学派的观点散见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概而言之,其要点有六:一、“接万物以别宥为始”[4](1318),二、“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4](1318),三、“情欲寡浅”[4](1318),四、“见侮不辱,救民之斗”[4](1318),五、“禁攻寝兵,救民之战”[4](1318),六、“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4](1317-1318)。通观以上六要点,最能展现宋尹学派的精神境界者当属“见侮不辱”一语。“见侮不辱”指在遭受别人欺侮时,内心里不把那视作一种侮辱,从而对对方的羞辱行为予以宽容。从反面来讲,“见侮不辱”有逆来顺受、不思反抗的消极意义,但从正面来看,“见侮不辱”却是心量广大的一种体现。笔者以为,宋尹学派的觉解不为不高,但却拘限于社会层面,因为宋尹学派的一切主张都是为了“救民之斗”、“救世之战”、“愿天下之安宁”,而缺少对于道这种超越存在者的感悟。至于宋尹学派的修养工夫,则应为“情欲寡浅”。“情欲寡浅”意指人生来就情感淡泊、欲望稀少,它是指称人的本然的存在状态,却非实然的状态。人在后天的成长、发展中,受到来自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的熏染,情欲已不寡浅,倘能恢复到“情欲寡浅”的本然状态,那么人们自然就能够“见侮不辱”。宋尹学派对世人大讲“情欲寡浅”,正是希望人们能够认清生命的本来面目,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情感、欲望,从而回复到生命的本然状态,显然,“情欲寡浅”之说具有修养论的意义。
关于杨朱,孟子曾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6],这说明,在先秦时期,杨朱之学曾与儒、墨并称显学。杨朱的思想散见于《孟子》、《吕氏春秋》及《淮南子》等。孟子说“杨氏为我”[6],又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6](313);《吕氏春秋》评价杨朱说,“阳生贵己”[7];《淮南子》则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8]。由此可以推知,杨朱的生命境界可概括为“为我”或“贵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以及“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则是杨朱“为我”的具体表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一句堪称杨朱的“名言”,意为假使只拔掉他身上的一根汗毛,就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不肯干,古人常据此判定杨朱为极端自私、利己之徒。实际上,杨朱的“一毛不拔”只能表明他反对为他人而付出,另一方面,杨朱也反对自身对他人的攫取。换言之,杨朱既不会舍己为人,也不会损人利己,他只是以自我的生命为中心,重视个体生命的保存、追求感性欲望的适当满足,这与极端的自私、利己之辈明显不同。依笔者愚见,杨朱的这种觉解并未使其丧失人的社会属性,但却已经不具备利他的道德特征,因此,杨朱的生命境界并不玄妙和高尚,并非难以企及,要达致这样的境界,人们也并不需要经过特殊的修养,只需接受他的思想即可。
3.依照徐复观先生的观点,《列子》的《杨朱篇》所反映的是道家末流的思想[9]。列子是战国前期的道家思想家。古本《列子》很早就已亡佚,今本《列子》八卷,是东晋学者张湛依据其先人藏书,以及在战乱后收集到的残卷拼凑而成的。今本《列子》中的《杨朱篇》所展示的并非杨朱本人的思想,因为它不仅继承了杨朱“为我”的观念,反对任何自我牺牲,而且力言人生短暂,鼓吹及时行乐。《杨朱篇》把个体感官的享受和欲望的满足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提倡“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10],这显然属于极端的纵欲思想。张湛生当东晋时期,《杨朱篇》一文难免掺杂他本人的思想,体现魏晋玄学末流的放纵情欲、肆意胡为等特点,不过,针对《杨朱篇》,徐复观先生曾指出,“当战国末期,由持久战争的彻底破坏,使许多人感到时代及人生的绝望;于是由杨氏为我而再向下堕落,便否定了为我的理想性的一面,即全性葆真的一面;而完全把人的生命,集注于当下的现实享受追求之上”[9](381)。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列子·杨朱篇》也反映出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观念。《列子》的《杨朱篇》所体现的思想境界可以文中的“且趣当生,奚遑死后”[10](221)来进行概括,即姑且把生前的日子过好就行了,哪有功夫去管死后的事情,这正是把享乐视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比较杨朱的思想与《列子·杨朱篇》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出,二者皆重视人的肉体生命,而缺乏超越的精神追求,不过,肉体欲望的价值在《列子》的《杨朱篇》中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伸张,相较于杨朱本人的思想,《杨朱篇》的思想更为堕落,觉解更显不足。显而易见,这样的人生境界也不需修养而至,而是随波逐流、堕落而成的。
田骈、慎到通常被学界谓之“道法家”,他们的思想主张主要体现在《庄子·天下篇》和《荀子·非十二子篇》之中,其中,《庄子·天下篇》的叙述偏重于他们道家性格的一面,而《荀子·非十二子篇》的叙述则偏重于他们法家性格的一面。在《庄子》和《荀子》中,表达田骈、慎到的思想境界的文字有“块不失道”、“魏然而已”、“謑髁无任”、“椎拍輐断,与物宛转”[4](1329)、“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11]以及“有见于后,无见于先”[11](330)等等。“块不失道”、“魏然而已”皆形容顽钝无知的状貌;“謑髁无任”、“椎拍輐断,与物宛转”、“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及“有见于后,无见于先”皆指毫无主见、一切被动、万事跟从他人的麻木不仁的处世态度。田骈、慎到的这种人生态度,可谓毫无觉解,故而《天下篇》的作者将他们的理论称之为“死人之理”[4](1329)。普通人要获得这种虽生犹死的状态并不容易,因而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修养”,只不过这种“修养”是一种强行让自己堕落的工夫,这种工夫也就是《天下篇》所谓的“弃知去己”[4](1328)。当然,老子、庄子也力倡“弃知”和“去己”,然而,慎到的“弃知去己”与老庄有根本之区别:老庄“弃知”,只是要抛弃世俗知识这种“小知”,“去小知而大知明”[4](1065),“小知”摒除了,道这种大智慧才能呈现出来,而慎到的“弃知”却是要达到绝对无知的状态;老庄“去己”,是为了去除对小我的执著,从而开显出感通万物、融于宇宙的精神体验,慎到的“去己”,则是压制自我的一切思想、见解,使自我还原为只具有原始生理欲望的动物性存在。由此可见,田骈、慎到的修养工夫与老庄虽有类似之处,但二者的觉解程度却有天壤之别。
冯友兰先生根据人的觉解程度的不同将人生境界划分为四大类,分别为天地境界、道德境界、功利境界与自然境界[2](390)。笔者以为,中国先秦道家各派的思想境界也可据此被划分为四类:老子、庄子能够跳出现实人生、俯瞰世界万物,他们毋庸置疑地具有最高的觉解程度,为天地境界;宋尹学派胸怀悲情救世,以天下安宁为己任,倡导宽以待人,容人之过,堪为道德境界;杨朱特重对自我的肉体生命的养护,养生虽非向外谋求名利,但亦属私利之一种,故而当属功利境界;《杨朱篇》的作者所阐发的思想属杨朱思想的堕落,这种人的生命任由生理欲望摆布,完全不能由精神主宰,因此,相较于杨朱,境界又低一层,属自然境界,至于田骈、慎到,他们虽不追逐欲望、放纵肉体,但“弃知去己”之后的人,社会性荡然无存,也只剩下一点生理欲望,因而也可将其视为处于自然境界之中的人。
[1]谭嗣同.谭嗣同文选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208.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389.
[3]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21.
[4]王叔岷.庄子校诠[M].北京:中华书局,2007.266.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44.
[6]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155.
[7]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七)[M].北京:中国书店,1985.31.
[8]刘康德.淮南子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682.
[9]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三联书店,2001.371.
[10]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222.
[11]杨柳桥.荀子诂译[M].济南:齐鲁书社,2009.82.
On the State of Being and Cultivation of the Taoist School in the Pre-Qin Period
REN Mingyan; LI Kai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nan University, Beibei Chongqing 400715 )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degree, the states of being of the Pre-Qin Period could be divided into alleged four types which Mr Feng Youlan called "the four realms of life".Lao Zi and Zhuang Zi both pursue the amalgamation with the sacred tao. So their state of being belongs to cosmic state of being, which could be reached by these training methods such as“Weidaorisun”,“Xinzhai”and “Zuowang”. Song Xing and Yin Wen are anxious to save common people and aim at social harmony. So their state of being belongs to moral state of being, which could be reached by“Qingyuguaqian”. Yang Zhu is anxious to strive for the wealth of health maintenance and his state of being belongs to utilitarian state of being. The author of Yang Zhu in Lieh-tzu, Tian Pian and Shen Dao lose mental seeking and they become beings of animality who only have physiological appetite. So their state of being belongs to natural state of being. Descent from Yang Zhu,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ir state of being need not cultivate and due to degeneration.
the Taoist School in the Pre-Qin Period; State of Being; Cultivation
G122
A
1672-2094(2014)01-0046-04
责任编辑:邓荣华
2013-12-17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孟子伦理思想与列维纳斯伦理学之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2C ZX057)的阶级性成果。
任明艳(1981-),女,山东临沂人,西南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伦理思想史。
李 凯(1980-),男,山东淄博人,西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