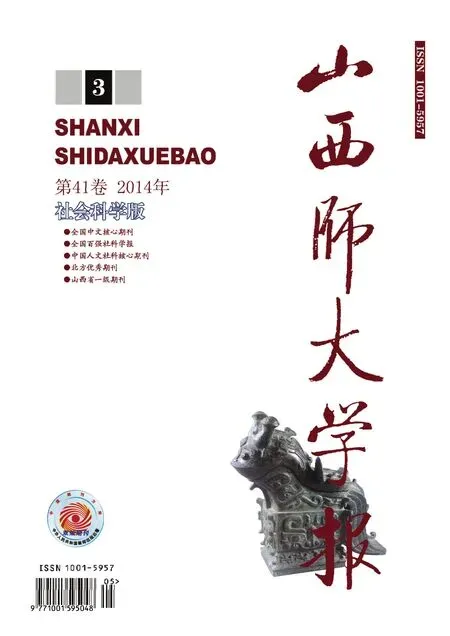论《蝴蝶君》文化产业幻象的实质
2014-04-11范煜辉邓玉芬
范煜辉,邓玉芬
(1.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2.广西民族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南宁 530006)
黄哲伦的《蝴蝶君》在美国亚裔戏剧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剧作在美国百老汇成功上演,改变了美国戏剧版图的格局,使黄哲伦成为了“首个在一代人里就成为世界性现象的美国剧作家”[1]。评论界对《蝴蝶君》的解读向来是把其放置在美国经典戏剧的文本序列中进行考察的,有人认为它彻底颠覆了东西方两元对立的模式,对原有的东西方关系中潜在运作的文化霸权与权力关系进行了一次惊人的倒置。[2]然而,这种误读的产生是由于未能认清《蝴蝶君》本质上是大众文化产业的幻象。本文将从大众文化产业和运作的角度,论述《蝴蝶君》在“东方理想妻子想象”的产业链中如何反讽西方/东方固有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黄哲伦迎合观众审美期待的创作理念使得这种批判不可能具有彻底性,进而纠正对《蝴蝶君》的误读。
一
自首演之日起,《蝴蝶君》就被纳入了大众文化运作的程序。1988年1月第一次彩排引发关注,到3月剧组移师美国商业剧演出重镇百老汇剧院,并获得商业演出的成功,上演多达777场。詹姆逊在批判商品化的文艺作品时指出,商品化的文化产品业已受到资本主义的收编和利用,丧失了批判与颠覆的勇气,失去了对意识形态幻象发起攻势的距离,不可能完成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幻象的任务。《蝴蝶君》的题材与西方对异国姻缘中东方理想妻子的想象有重要的关联,这其中隐现着一条从菊子夫人到蝴蝶夫人,最后变异出蝴蝶君的文化产业链,在这一脉络赓续涉及的体裁形式包括小说、歌剧、音乐剧、话剧等,西方社会利用它强大的文化产业不断调节、修正和深化殖民活动所需要的意识形态。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说:“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系和殖民风格等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3]2东方学提供给了西方人想象东方问题的先见构架,这些先见在文化产品序列里反复铭写,形成强大的叙述原型模式,故而在创造新的文本,解释特定主题时,西方人会无意识地参照、对应、协作这一叙述模式,所生产的新文本也会与已有传统形成互文,最终再次蹈入具有特定原则性和程式化的刻板知识体系。
西方对东方理想妻子形象的想象与西方殖民扩张同步,首先出现在1887年出版的小说《菊子夫人》中。小说作者是法国的皮埃尔·洛蒂,他年轻时曾长期在海军服役,随舰到过亚洲许多地方。《菊子夫人》是日记体小说,讲述了19世纪初法国军官“我”随舰来到日本长崎,按当地习俗相中了少女菊子当作“临时妻子”。小说是描写“我”两个多月租妻生活的见闻及感受。这部小说的出版,因其富有东方的异国情调,特别是满足了对东方女性的猎奇心理受到了读者欢迎,一度成为热门畅销书。从此这一形象开始进入了商业化运作,不断得到重写,在重写过程中逐渐修正丰富了这一形象,以此迎合资本市场的需求。菊子夫人的独立意识与她恬不知耻地出卖肉体,使她仍然不失完美的东方女性。1898年美国约翰·朗发表短篇小说《蝴蝶夫人》,把女主人公取名为“蝴蝶夫人”乔乔桑,男主人公换做头脑粗鄙、极端自私的美国海军中尉平克顿。但小说《蝴蝶夫人》不是普契尼同名歌剧的脚本,蝴蝶夫人殉情结局首次出现在大卫·贝拉斯科的独幕剧《蝴蝶夫人》里。在伦敦首演时,普契尼碰巧观看了演出,之后普契尼创作出了对东方女性幻象的经典之作——歌剧《蝴蝶夫人》(1904年)。剧中情节也被黄哲伦的《蝴蝶君》移用:年轻的日本姑娘乔乔桑爱上了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被他戏称为“蝴蝶夫人”。两人相恋后,蝴蝶夫人很快有了身孕。不久平克顿随海军舰队返回了美国,将已有身孕的蝴蝶夫人留在了日本,并向她做出承诺,说等来年知更鸟啼叫时,他一定会回到蝴蝶夫人身边。蝴蝶夫人忠贞不渝地苦等了平克顿三年,期间她拒绝了日本皇室成员的求婚。然而平克顿回来时,却带来了他金发的白人妻子,他们来是想要蝴蝶夫人的孩子。爱情幻灭的蝴蝶夫人拿起短剑,毅然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东方理想妻子的形象出现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产业链。这些不同文本所表述的内在的意识形态结构与文本当时产生的文化历史语境的需要是一致的。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在今天,文化给一切事物都贴上了同样的标签。电影、广播、杂志制造了一个系统。不仅各个部分之间能够取得一致,各个部分在整体上也能取得一致。”[4]134在蝴蝶夫人的文化产业链中,各种表达渠道捕捉、框限、存储、传输和再复制生产着同一均质的意识形态幻象。东方属于西方之外的异在的世界,在殖民过程中西方自认永远是施动者,而东方则是被动接受者,东方这块神秘顺从的大陆静候着西方用洋枪大炮和它们的商业文明去征服和开发。在类同性思维的作用下,建立起了一系列复杂的二元对立关系,西方/东方、主人/奴仆、男人/女人、白种人/黄种人、残酷/柔顺,等等。这种通过文化产业运作的意识形态在黄哲伦《蝴蝶君》上演时,在西方已经深入人心了。
二
《蝴蝶君》创作灵感来自于1986年震惊世界的间谍案。据《纽约时报》披露,法国外交官博思考特先生被指控犯泄露国家机密罪。据传,博思考特爱上了有着京剧旦角与中国间谍双重身份的施佩普后,把国家安全机密泄露给了他。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博思考特20年来一直认为施先生是个女人。黄哲伦对这个间谍案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他把已经为西方人所熟识的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内置于这个间谍案,创作了戏剧《蝴蝶君》。黄哲伦说:“《蝴蝶君》为他提供了表达对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和帝国主义看法的机会,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与《蝴蝶夫人》之间的互文获得实现的。”[5]1579《蝴蝶君》与《蝴蝶夫人》的互文关系,主要表现在《蝴蝶君》反讽了“蝴蝶夫人”中对西方男子气概的程式化叙述。这种反讽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即被嘲讽者嘉礼玛与自我镜像、被嘲讽者与意识形态幻梦、观众和意识形态幻象。通过反讽戏拟,黄哲伦意图颠覆蝴蝶夫人叙述中的东西方固有二元对立模式,揭露叙述中白人体现着阳刚男子气概话语的虚幻性。
自《菊子夫人》以降,在东方理想妻子的想象中西方男人始终是主动者,身上体现了阳刚的男子气概。而黄哲伦《蝴蝶君》中,男子气概缺失的嘉礼玛却成为了反讽受嘲弄的对象。米克在《论反讽》中,谈到“反讽的受嘲弄者常常是傲慢的、任性的盲目者;他仅仅是通过言语或行动,暴露出他丝毫也没料到事情完全出于他天真的设想之外”,“反讽的基本因素是掺杂着不同程度的傲慢、自负、自满、天真或单纯的那种安然而笃信的无知无觉。受嘲弄者愈盲目,反讽的效果愈明显”。[6]42嘉礼玛一直天真地执迷于普契尼《蝴蝶夫人》中西方男性神话的幻象之中,平克顿是嘉礼玛心中的“镜像”,但他的现实身份与理想人格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造成了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分裂,但天真的嘉礼玛意识中对这种分裂却浑然不知,这就成了反讽效果的来源。
嘉礼玛竭力想周旋于女人之间,展示他作为阳刚男人的魅力,握有对女人的绝对控制权。但事与愿违,在与四个白人女性的恋爱交往中,嘉礼玛皆以失败告终,毫无男子气概可言,这一切他似乎浑然不知,他继续寻找新的猎逐目标,幻想能在下次获得成功。他第一次性经历就充满了惊恐和痛苦,在这男女性别权力倒转的关系中充满了嘉礼玛被去势的意象。在和伊莎贝尔发生关系时,嘉礼玛“被强行按倒在灌木丛的污地里,只能两眼无助地抬望着女人在他的腰间上下郁动”[5]1558。第一次性经历,嘉礼玛并没有主动攻击,反而处于被动接受的尴尬境地,从象征意义上,性爱中的伊莎贝尔阉割了嘉礼玛的菲勒斯。嘉礼玛成年之后,在性经历上也同样充满胆怯和颤抖,弗洛伊德宣扬的男性菲勒斯欲望支配女性,在嘉礼玛与另外三个白人的性爱关系里也没有表现出来。
怀揣着强烈征服女人欲望的嘉礼玛遇到“蝴蝶夫人”宋丽玲时,他立即被“她”柔弱的女性气质征服了。嘉礼玛竭力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幻境,他与宋丽玲交往时,按照情节剧《蝴蝶夫人》的交往方式来安排,像蝴蝶夫人这样的文化符号将大男子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角色施加于西方男人身上:嘉礼玛相信他可以成为“真正的男人”,他能向气质优雅和低眉顺眼的女人展开他男人的攻势,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容易被宋丽玲怯弱的蝴蝶夫人的外表所蛊惑。嘉礼玛在与西方女性交往中表现的文弱,甚至男子/女人性关系的被颠倒,使他成为了西方女人控制的对象,他终于在宋丽玲身上找到了他施展男性权力的空间,宋丽玲就是他这位骑士怜惜的美丽脆弱的蝴蝶。
嘉礼玛猎捕他的“蝴蝶”,观众看到他自认掌控着与宋丽玲的感情,却浑然不知他已陷入了自己幻象的泥沼。这就形成了《蝴蝶君》第二个层面上对《蝴蝶夫人》的反讽,即对《蝴蝶夫人》中西方男人/亚洲女人二元对立关系的意识形态幻象的反讽。在“蝴蝶夫人”叙述中,西方白人男性掌控着东方女性的命运,东方女性为西方男性做出牺牲。这种关系在《蝴蝶君》中被颠倒了,在嘉礼玛与宋丽玲的第一次见面谈话中,宋丽玲就揭示了自己并不实践嘉礼玛理想的屈从的东方女性的角色。在宋丽玲离场之后,嘉礼玛对观众让步“用我强壮的西方臂膀保护她的想法只好作罢”。在嘉礼玛与宋丽玲的交往过程中,是由宋丽玲来确定会面的时间、地点、两人相处多久,她还驳斥了嘉礼玛幻想的“东方女人”形象。当宋丽玲与他心目中的形象冲突时,嘉礼玛就自我宽慰,他辩护说:“她外表上冒失和坦率,但是她的心是害羞和害怕的。这是她身上的东方性在与她的西方教育交战。”嘉礼玛自认战胜了他的“蝴蝶”:“我不再去看京剧了,我不给她打电话,也不写信……我恶毒地拒绝这样做,我第一次觉察到了这股奔涌的权力——绝对的男人的权力。”[5]1558嘉礼玛完全被西方“蝴蝶夫人”的意识形态幻象捕获了。
嘉礼玛因叛国罪被捕入狱,在法庭上宋丽玲脱去衣服,裸露身体,彻底砸碎了嘉礼玛的幻梦。嘉礼玛打发他,“你走吧!我与我的蝴蝶还有个约会”。嘉礼玛解释:“我爱那个由男人创造出来的女人。所有的,总之……在今晚,我最终从真实中学会了谈论幻象。而且认清了不同,我选择幻象。”[5]1574嘉礼玛至死都追逐着他虚幻的男子气概和他的理想爱人,他领悟到唯一真正能维护尊严的是像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一样“带着荣誉赴死胜于苟延残喘”。当嘉礼玛自杀时,他完成了黄哲伦预设的对西方平克顿角色的反讽。黄哲伦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一个法国男人自认是平克顿,他在中国探寻到了漂亮的蝴蝶夫人。到了剧终时,他有点醒悟到他,法国男人已经为爱情牺牲了,而那个间谍才是真正事实上猎获了他爱情的平克顿。”[7]
嘉礼玛的悲剧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幻象所致,反讽戏剧中的“笑”能转换“所指”,即从对人物的嘲笑转向对观众的嘲笑。通过这“艺术的笑”既讽刺丑恶又净化灵魂,期望观众从或辛辣尖刻或温和幽默的反讽“他者”的语境欣赏中,顿悟出自身在无形之中受到了嘲讽,从而达到用真实去纠正幻象的目的,这是《蝴蝶君》里第三个层面上的反讽。黄哲伦的《蝴蝶君》设置的时代背景是1960年到1966年,正是朝鲜战争之后、越南战争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美国在亚洲战场的接连失利,东西方权力关系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东方不再是西方殖民扩张时期的东方,东方不再是柔顺的女性形象,而是潜藏着反抗的力量,因而黄哲伦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讽希望能形成对西方处理东方问题期待模式的挑战。
三
黄哲伦《蝴蝶君》的反讽层层推进,从对强势白人男性,到白人男性/亚洲女性的二元关系,推进隐射至西方/东方的权力关系,意图颠覆传统东方学色彩的思维定式。黄哲伦的反讽递进模式与美国在亚洲影响力衰退的时局相勾连,但这一递进模式是建立在解构蝴蝶夫人的幻象之上的,在我看来,他对这一幻象的反讽批判虽有成效,但由于黄哲伦践行大众文化运作策略,使得他的反讽基石——对蝴蝶夫人幻象的批判仍留有待解构的痕迹。
《蝴蝶君》批判的不彻底性应归咎于黄哲伦对观众审美趣味的迎合上,这个致命的弱点使得《蝴蝶君》丧失了经典的气质。在谈论《蝴蝶君》粉碎刻板幻象的策略时黄哲伦说:“我打算给观众他们所期望看到的,与此同时试着准确地探讨为什么观众会对这些材料感兴趣,然后用这种方式颠覆它,到那时他们就会被吸引住了。”[8]117从中可知黄哲伦对西方二元模式的反讽是建立在对观众审美心理狡黠的把握上,与其说是为了戳破幻象确立真实,不如说是为了迎合观众继续书写大众文化新的神话,这暴露了黄哲伦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其实不过是一种商业化经营的故作姿态。
黄哲伦的创作意图先天地决定了《蝴蝶君》中反讽西方对异国姻缘中东方理想妻子的程式化幻象,并没有为塑造新的亚洲女人提供契机。怯弱的黄哲伦努力揣度观众的欣赏心理,使得他的创作意识不可避免地与具有东方学先见的集体意识相缠绕,使得黄哲伦在摆脱了蝴蝶夫人幻象后,不由自主陷入到了另个虚幻的桎梏——“龙女”(Dragon Lady)幻象。龙女这一幻象体系始于米尔顿·卡尼夫创作的连环漫画《特瑞与海盗》(Terry and the Pirates,1934—1973年)。漫画里塑造的龙女,后来作为文化原型被延伸指称残暴、傲慢专横、富有魅力、神秘的亚洲女性。龙女也受到西方大众文化产业的支撑,仅仅在1985年塑造龙女的大众文本就有电影史泰龙的《兰博》Ⅱ、电影西米诺的《龙年》、小说克拉维尔的《幕府将军》等,足见其影响力之大。这些形象都有龙女的三个基本表征:东方神秘风情、白人男性的泄欲工具、天性狡诈。
《蝴蝶君》中的宋丽玲也是“龙女”型的人物,黄哲伦通过宋丽玲的易装将她的社会/生理性别神秘化,她/他开始以一个受欺凌污辱的“女伶”角色登场,到了剧终却揭露了他是个男性,另重身份是中国间谍,他驾驭着嘉礼玛,享受着性欲倒错的生活。在剧中宋丽玲的社会性别认同神秘,他的性别更准确地说应是介于男/女两元分法之间或者之外的“雌雄同体”。雌雄同体的宋丽玲对东西两元对立模式的抗争,并没有通过他亚洲男人的男子气概颠覆西方对东方宰制的权力话语,象征着宋丽玲男子气概的菲勒斯欲望从未在剧中显露,一直处于缺失抑或被阉割的状态,她/他用带有东方风情旦角的形象进行易装表演,用欺诈的手段去主动迎合西方男人的性想象。这种屈就迎合的抗争策略在《蝴蝶君》中虽说是胜利了,但这一形象再次确证和铭刻了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亚洲女人在《蝴蝶君》中被塑造成了狡诈的、精明的、操控人的和具有欺骗性的龙女形象,而西方男人像嘉礼玛则是值得信任的,有着骑士的气度,至死不渝地追求着理想的爱情,只不过偏信狡诈的东方女人而已。黄哲伦意图戳穿西方对东方陈词滥调的意图失败了,他在《蝴蝶君》中用一种虚幻去反讽纠偏另一种虚幻时,虽然摧毁了原有的对蝴蝶夫人的刻板印象,却又提供了另一个性质更为恶劣的玷污了的亚洲形象。
黄哲伦的《蝴蝶君》虽存有解构东西方二元对立模式的意图,颠覆强势西方男性和柔弱东方女性的程式化形象,但黄哲伦对幻象的颠覆并不是出于他重塑亚洲形象的欲望,他在潜意识里惯用文化产业操作策略屈从迎合观众的审美心理,反而又确认了对亚洲他者的恶毒想象。黄哲伦塑造的龙女宋丽玲作为文化原型在影射东方神秘不可捉摸的表象背后包藏着奸诈且有恶毒功利心的本质。这位易装的东方男性的阳刚气质被阉割,根本无力对西方构成任何威胁,只是增强了西方人的道德优越感和戒备心理。这一邪恶的文化想象也必然无助于西方正确处理与东方的关系。
[1] David Henry Hwang.Contemporary Authors Online. Thomson Gale,2005.
[2] 卢俊.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黄哲伦的文化策略初探[J].外国文学研究,2003,(3).
[3] 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4]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 David Henry Hwang.M. Butterfly,From Lee A. Jacobus.The Bedford Introduction to Drama.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 ST. Martin's,2001.
[6] D.C米克.论反讽[M].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7] David Henry Hwang.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0, 1988. December 10,1988.
[8] David Savran. In Their Own Words. 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