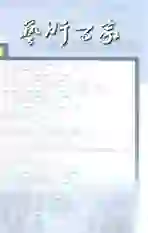回归还是利用:乔伊斯流亡美学批评
2014-04-10赫云
赫云
摘 要:[JP2]流亡虽然有可利用的价值,但流亡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流亡者无路可退时,宗主国就会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美国人借《尤利西斯》向温文尔雅、矫揉造作的英国人发起了挑战,挑战英国的文学传统和文化霸权。庞德作为《利己者》杂志编辑,也同样为颠覆英国文学的传统、创造文学艺术的新语言而奋斗着。为了这一共同的理想,他和乔伊斯走到了一起。庞德对乔伊斯文学实验的过度夸张和渲染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想借乔伊斯之手摧毁老牌的英帝国的文化殖民主义,故此,挖掘和培养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代言人的任务就被强加到了乔伊斯的身上,而乔伊斯本人也乐于扮演颠覆英国文学、重建文学新秩序的角色。
关键词:[HTK]艺术作品;乔伊斯;流亡美学;回归;利用;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HK]
流亡者的离乡情结中始终萦绕着还乡的渴望。乔伊斯选择流亡作为他的美学之后,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关于爱尔兰。离开爱尔兰之前,史蒂芬在最后的日记中展示了对母亲深刻的依恋。斯坦雷·苏坦(Stanley Sultan)认为,“史蒂芬的母亲象征着他的家庭(‘家);以都柏林湾为同一体,她象征着爱尔兰。”[1]这表明史蒂芬与爱尔兰之间将有着永不能割裂的联系。流亡者的流亡之路看起来像是一条还乡路,离故乡越远,也就越亲近它。流亡者更喜欢在远方,在一定距离之外,欣赏他的故乡。乔伊斯与爱尔兰之间的联系与其说是为了思乡,不如说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以便获得经济上的援助。流亡并没有让乔伊斯像巴黎中产阶级那样富裕,他需要来自依然挣扎在贫困边缘上的故乡的经济援助,以维持他孤独的流亡者的英雄形象。他同样需要来自故乡的消息作为他创造艺术的原材料,加工起来也得心应手。欧洲的阳光与香风并不是爱尔兰人的,体味起来也并不深刻。“所以,回来了。想想,你在逃,然后遇到了你自己。绕了最远的路是回家最近的路”(Ulysses, 13.1109-1110)。乔伊斯在都柏林憧憬着欧洲,在欧洲遥想着都柏林,因为除了都柏林,他一无所有。这种情感的倒错也许是流亡者特有的症候。乔伊斯在欧洲大陆上流亡了将近四十年,但在他的作品中却丝毫没有给罗马、苏黎世或者巴黎留下半点展示的空间,也顽固地拒绝表现欧洲的风情和人文景观。面对风雅、尊贵、世故的欧洲,乔伊斯这位来自殖民地的流亡艺术家显然是不知所措,也无能为力,尽管在流亡之前,他是那么地崇拜欧洲,甚至主张把爱尔兰欧洲化。可是从乔伊斯一生的结局看,他最终也没有成为“欧洲人”。这种被排斥、被疏离的现实导致乔伊斯根本无法融入欧洲社会,也无法获取创作的来源。似乎一离开都柏林,乔伊斯的所有故事就结束了,可那恰恰是流亡的真正开始,但乔伊斯从来没有让它开始过,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关于爱尔兰人在国外的描写,流亡的背景永远是都柏林。乔伊斯和他的流亡艺术家永远是在自己的国家里流浪。“乔伊斯,一个流亡国外的爱尔兰前一天主教徒,因此他对于英国文化和欧洲大陆思想来说是个异己分子。我们从莫尔那里看到的文体变化,在乔伊斯身上同样出现,从发出甜蜜微笑的《一分钱一首诗》到粗暴的《进行中的作品》;文体的改变是与出现同样的问题相联系的。乔伊斯放弃了观察他所定居的地方那异己的大陆文化的一切企图;相反,他只关心被他抛弃的都柏林生活。”[2]除了都柏林,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让乔伊斯这样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地加以利用。1904年就开始流亡的乔伊斯,直到1941年离开人世,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只字不提欧洲,也丝毫没有流露出对欧洲的感激之情。这多少惹怒了欧洲人,所以,乔伊斯才会与美国人建立起流亡联盟。由威拉德·珀茨(Willard Potts)编辑的《流亡艺术家的肖像:欧洲人的乔伊斯回忆录》(Portraits of the Artist in Exile: Recollections of James Joyce by Europeans)(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9),是一部记录“外国人眼里的乔伊斯”的专辑。乔伊斯一向自认“欧洲”为他的“精神父亲”,并以“欧洲传统”来装饰他的生活和艺术。该书为了解欧洲人如何看待乔伊斯,欧洲精神的义子,一位异乡人,和他的作品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非常难得的第一手材料和依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人认为“他的作品太受局限、太具地方性,而难以激起爱尔兰之外的人的兴趣,也难以被非爱尔兰人所理解。[3]实际上,乔伊斯与他的欧洲是格格不入的,他除了爱尔兰也别无选择。乔伊斯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爱尔兰的关注并不是为了偿还与感恩,也不是为了宣扬一种回归的理想,而是为了艺术创作的需要,为了建立一个流亡与回归的循环模式,也是现实的流亡生活所导致的一种与宗主国疏离的必然结果。乔伊斯对爱尔兰的憎恨和恐惧足以证明他的回归是假的,仅仅是文本形式的需要,而彻底地逃离它才是现实中的乔伊斯的真正迫切要求。乔伊斯1907年在《爱尔兰,圣徒和圣人之岛》(“Ireland, Island of Saints and Sages”)一文中就指出,“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不会留在爱尔兰。”[4]乔伊斯曾表示过,除了他家里的人,他谁也不爱。一个本已孤立、孤独的人,又缺少爱,也就免不了有人戏称他为不过是一名“文字搬运工”。从乔伊斯的书信中,也可以准确地捕捉到他对爱尔兰的厌恶之情。他在1909年8月22日写给诺拉的信中,迫不及待地、毫无保留地展示了他对都柏林的厌恶。“多么令人厌恶,厌恶啊,我对都柏林厌恶到了极点!它是失败之城,仇恨之城,灾难之城。我渴望逃离它”;1909年9月2日的信中,他又说,“都柏林是一座令人讨厌的城市,我对来说,这里的人最遭人讨厌。”[5]乔伊斯1912年12月9日在给舅妈(Mrs. William Murray)的信上说,“我讨厌看到都柏林的邮戳,因为所有这些信封都封存着死亡、贫穷或失败等这一类的坏消息。”。[6](p.72)在史蒂芬·迪达勒斯的眼里,都柏林也到处充满了腐败(corruption)和死亡的味道(mortal odour)(Portrait, 184)。乔伊斯的心中由于充满了对爱尔兰的厌恶和仇恨,结果导致他患上了严重的被害妄想症。他总以为爱尔兰人会报复他。乔伊斯在1913年的复活节写给埃尔金·马修斯(Elkin Mathews)的信中说,在爱尔兰,各种力量都蓄意合谋起来打击他;并在1914年3月4日写给格兰特·理查德(Grant Richards)的信中重申了这一想法,即某些人别有用心地怀有想拖垮他,甚至置他于死地的企图。[6](p.73、75)乔伊斯的这一症状在《尤利西斯》出版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他不敢回国,是因为他知道,他借作品对都柏林人实施的报复行为,反过来必然会遭致自己被攻击和被报复。他确信,爱尔兰人不会原谅他,或者说,从1912年起,乔伊斯就根本没打算要再回都柏林。与祖国的决裂,也并不能促成他与欧洲大陆的联姻。像乔伊斯这样的流亡作家在宗主国人的心目中并非如想象的那般有尊严。不管乔伊斯怎样一厢情愿地把欧洲大陆当作自己的精神之父,但这一父亲却好像从不站出来保护他这个来路不明、血统不纯的局外人。与乔伊斯同年生、同年死的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在1922年8月16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写到:《尤利西斯》的最初两三章还有趣,但从此书两百页的地方开始就令人失望、烦躁不安,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她认为此书的作者“既没有语言素养,也没有必要的审美趣味,倒像个刚学会写作的搬运工。我很知道这类人,粗俗不堪,还自以为是,简直令人作呕。”[7]像乔伊斯“这类人”是很难进入主流社会的,他们不得不在边缘处自哀自怜,而这类人的作品有时候在“主人们”看起来也是相当的无聊。“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表现的猥亵是故意谋划的,好像一个人在忍无可忍之中,为了呼吸而打破窗子。有时候,当窗子被打破的时候,他是光彩夺目的。但这是何等的精力浪费啊。何况,猥亵的表现是多么无聊,当它不是精力过剩或野性难驯而只是一个需要新鲜空气的人的义举的时候。”[8](p.360)在伍尔夫眼里,那些像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之流的作家毕竟是外国人,是附庸风雅的势利者。伍尔夫是看不起“最后通过合法的步骤成了英王乔治陛下的臣民”的那些漂洋过海而来的艺术家的,“难道他们不是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些外国人吗?”[8](p.418、496)流亡者永远是一名外国人。对于这一点,乔伊斯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兴高采烈地利用起这个“流亡者”的身份。由于是站在主流之外,流亡者会持有一种超然独立的态度,并时时刻保持一种特殊的敏锐性。流亡提供了一种微妙的生存状态:缺席的,边缘的,无所属的。正如塞谬·迪恩(Seamus Deane)指出的,“爱尔兰为乔伊斯提供了一种缺席的感觉,这也是他的作品努力要满足的。”[9]站在边缘成就了一种观察现实的特殊方式,并占据了一个轮廓清晰的观察角度,看到了站在中心所看不到的一切。流亡者不但可以从不同位置和角度观察、感觉和体验世界,而且他们本身也是双重的。乔伊斯聪明地游离于主流之外,不参与任何团体和组织,使自己可以自由地思索,以便更全面、更客观地批评他的都柏林。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最佳生存状态就是流亡。流亡最好地诠释了知识分子作为他者的范式。[10]流亡让流亡者实现了超越空间、征服土地的梦想。即便他们不在真实的路途上行走,但他们的精神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征服。跨越时空与国界让流亡者在流亡的帝国里成为一个统治时间与空间的主宰,在边缘与中心、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流亡让乔伊斯摆脱了各式各样的责任和义务,他不必再听家长,师长,教务长的名目繁多的召唤和指引了。他奉行一条自我至上主义原则,迷醉于孤芳自赏中。[JP2]而流亡最迷人、最实用之处就在于可以去任何地方却免于罪责。来自家庭的,学校的,国家的,教会的各种责难和非议都可以抛洒在路上。一度是殖民地的受压迫者也摇身一变成超级大国里的自由人。乔伊斯可以不再为他的叛逆与不忠遭受谴责与惩罚。他可以更自由、更客观地揭露和批评都柏林的麻痹与无能,更轻松地向欧洲展示爱尔兰曾经如何压迫他的肉体和精神,而不再担心有来自个人的和官方的攻击与迫害。这种种便利之处让乔伊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流亡之路。流亡虽然有可利用之处,但它不仅仅意味着收获,同时它也损失、消耗着流亡者的能量与热情。他们在旅程上一边欢笑,一边流泪;一边遗弃,一边追思,忍受着种种意想不到的酸楚与悲哀。首先遭遇的就是孤独与寂寞,甚至没有一个朋友。乔伊斯曾在信中袒露:他太幼稚,他冲动,以至不能一个人生活。[11](p.195)经历过流亡之后的史蒂芬也在心中呐喊;快来用温柔的手触摸我,我在这里是如此的寂寞,悲伤(Ulysses,)。不安与骚动是另一种折磨。乔伊斯不但在意大利,即便是在艺术家的天堂──巴黎,他也时常感到不安。史蒂芬也像一只飞来飞去的燕子,不得不离开自己亲手搭建的窝,然后去流浪。而最让流亡者感到伤心的是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而被冠以“爱尔兰人”,“外国人”,或者“异教徒”,以区别于本地人。比起流亡者的智慧、品德与人格,那些本地人更关心他们是从哪来的、他们的社会制度怎样、他们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那种不一样的社会体制和生活习俗会让本地人更加欢喜、更加充满好奇心,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乔伊斯一心想成为欧洲人,但当他一踏上欧洲大陆,他立刻还原成爱尔兰人。当他在都柏林时,他叫詹姆斯·乔伊斯;而在殖民者的国度里,人们更习惯叫他外国人,爱尔兰人。他极力摆脱的“爱尔兰性”,此时却被刻进他的骨髓里。温森特·陈指出:有些人在他身上贴上种族差别的标签,用他们特别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布阵使他被视而不见;尽管他能像本地人一样去适应每一个特殊的文化和语言,他却反复地被标记为一个“外国人”。[12]当马尔科姆·考利,一个在欧洲大陆上寻寻觅觅的美国人,第一次去采访乔伊斯时,他以“主人”的口吻这样描述到:“他是一个外国人,身无分文,脆弱不堪。”[13] [JP]流亡虽然有可利用的价值,但流亡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一个女孩嘲笑他贫穷的祖国爱尔兰时,乔伊斯感觉受到了侮辱。[11](p.111)1932年11月11日乔伊斯在写给韦弗小姐的信中透露,他曾给女儿露西亚(Lucia Anna Joyce)四千法郎只为了买一件裘皮大衣,以此来减轻她的劣等感(inferiority complex)。[6](p.327)乔伊斯认为裘皮大衣比看心理医生对女儿的劣等感更有好处。很显然,《肖像》中的史蒂芬的那些二手衣服也只会暴露他的爱尔兰气质,加深他的劣等感。正如威尔登·桑顿(WelDon Thornton)所指出的,爱尔兰情结(Irish Complex)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史蒂芬的潜意识里,由于无法正视与面对它,会导致史蒂芬退回到原始、野蛮的状态。[14][JP2]当流亡者无路可退时,宗主国就会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面对主人的好客与大度,流亡者变得相对文雅,也更温顺,尽管他们批评自己的祖国时是那么的冷酷无情,那么的激进与激烈。史蒂芬对爱尔兰的解剖与批评满足了殖民者的好奇心。乔伊斯对英帝国主义的猛烈抨击也同样受到了某个新兴大国的欢迎。这也说明了乔伊斯产业在美国的发达与旺盛远远胜于在英国的原因。但是,这些流亡作者的作品畅销以后,他们的声音便销声匿迹了。在媒体上频频登场的是好客的主人,而不是客人。宗主国的专家们很专业,很权威地重述着流亡者的故事。乔伊斯对这套殖民者的规则是早有领教的。早在1907年,乔伊斯就在《审判台上的爱尔兰》(“Ireland at thebar”)一文中,敏感而深刻地感受到了爱尔兰无力表达自己、言说自己,进而任意被人歪曲、丑化的尴尬境地。从伦敦发出的关于爱尔兰的报道被国外的新闻记者们转载,或者进行再生产、再编辑,以致使爱尔兰面目全非。被殖民者言说自己的权力依然掌握在殖民者的手里。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爱尔兰,永远没有可能言说它自己。然而,乔伊斯利用流亡的特殊身份,却获得了言说爱尔兰的权力和机会。他以兜售这些言说来博得主人的好感,对于这种利益交易,陆建德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然而部分‘流亡到海外的人士却要把美国当做文化联合国的所在地,自己到了那里就可以做被抛在身后的祖国的代表。他们甚至会利用西方对自己祖国的偏见来谋取这样那样的同情、资助和好处……看重的未必是故土文化本身,而是故土文化在新环境下的使用价值。”[15]在宗主国的温柔款待下,和本地人相比,这些流亡者变得更加顺从,更加乖巧,他们以流亡为筹码,与主人们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并不是只有宗主国才是自由的、和平的;而是流亡者在策略上放弃了斗争和攻击。[JP]endprint
从一开始,美国人就借《尤利西斯》向温文尔雅、矫揉造作的英国人发起了挑战,挑战英国的文学传统和文化霸权。这一野心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得以实现。美国的纽约成为现代艺术的中心。美国人依仗坚挺的美元,在欧洲大陆开始重新确立美国的文化地位。英国在现代主义运动中不但保守、迟钝,而且明显地是不知所措。美国对《尤利西斯》的推崇一方面借以抒发叛逆者被压抑的情感,一方面也是颠覆殖民者的陈规戒律。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激进的《利己者》杂志的文学编辑,也同样为颠覆英国文学的传统、创造文学艺术的新语言而奋斗着。为了这一共同的理想,他和乔伊斯走到了一起。自1914年起,庞德慷慨提携乔伊斯。庞德是现代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乔伊斯除了可以为他倡导的文学实验效力之外,也是美国期刊国际化运动中塑造出的国际化人物的典型代表。庞德对乔伊斯文学实验的过度夸张和渲染显然是别有用心的。那就是决心借乔伊斯之手摧毁老牌的英帝国的文化殖民主义。美国显然有取代英国成为英语世界的新的文化教父的野心。挖掘和培养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代言人的任务就被强加到了乔伊斯的身上,而乔伊斯本人也乐于扮演颠覆英国文学、重建文学新秩序的角色。 (责任编辑:徐智本)
参考文献:
[1]Stanley Sultan. The Argument of Ulysses [M]. Ohio: Ohio State UP, 1964: 174.
[2][美]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著,薛鸿时译.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对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的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88:112.
[3]Willard Potts, ed. Portraits of the Artist in Exile: Recollections of James Joyce by Europeans [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9: 47.
[4]James Joyce. 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M]. Ellsworth Mason and Richard Ellmann, ed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9: 171.
[5]James Joyce. Letters of James Joyce [M]. vol. II. Richard Ellmann, ed.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6: 239, 243.
[6]James Joyce. Letters of James Joyce [M]. Stuart Gilbert, ed.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7.
[7][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读书随笔[M].刘文荣,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232.
[8]李乃坤.伍尔夫作品精粹[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9]Seamus Deane. Celtic Revivals: Essays in Modern Irish Literature 1800-1980 [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5: 123.
[10]Edward W.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M]. New York: Vintage, 1996: 53.
[11]James Joyce. 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M]. Richard Ellmann, e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5.
[12]Vincent J. Cheng. Joyce, Race, and Empir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3.
[13]Malcolm Cowley. Exile's Return: A Literary Odyssey of the 1920s [M]. London: Penguin, 1994: 117.
[14]WelDon Thornton. The Anti-modernism of Joyce's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M]. New York: Syracuse UP, 1994: 146.
[15]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32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