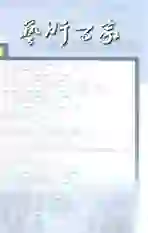论李开先旧藏与元刊杂剧之关系
2014-04-10杜海军
摘 要:李开先藏书甚多,其中富有元杂剧作品,因邀门人选刊成了《改定元贤传奇》,也促成自作《词谑》等书。从这些书中我们看到有多种元杂剧整剧或单折,如《陈抟高卧》、《萧何月夜追韩信》、《李太白贬夜郎》、《王粲登楼》等可与今传元刊本作比较。经研究发现,凡李开先藏书无论剧或曲,其内容与今存元刊本录曲比较,数量、曲牌的名称以及排列先后等皆无差别,由此,基本可以断定,今传《元刊杂剧三十种》与李开先所录曲词的杂剧应是出于一个版本系统,即是说今传《元刊杂剧三十种》本出自李开先旧藏。
关键词:戏曲艺术;李开先;元刊杂剧;词谑;改定元贤传奇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元刊杂剧三十种》为如今仅存的刊于元代的元人杂剧,对人们正确理解元杂剧发展的成就,推进元杂剧研究的深化,有着特别的意义,于是其出处流传也受到人们的关注。或以为出自李开先旧藏,如孙楷第等人引脉望馆杂剧《单刀会》、《看钱奴》、《范张鸡黍》、《魔合罗》所附的何煌跋语立论①;或怀疑非李开先旧藏②。也难怪,因孙楷第等人所说从来未作深入分析。今笔者于《单刀会》、《看钱奴》、《范张鸡黍》、《魔合罗》之外,研读《词谑》、《改定元贤传奇》、脉望馆杂剧何煌校《王粲登楼》等文献,发现李开先采用材料多可与元刊本印证,可以揭秘元刊杂剧与李开先旧藏的关系,因成此篇。
[HS2][HT5,5”H] 一、从《改定元贤传奇》看元刊杂剧与李开先旧藏关系
李开先藏书甚富,其中元杂剧是重要的构成部分,号称词山曲海,他自己《南北插科词序》说:“予少时综理文翰之余,颇究心金元词曲,凡《芙蓉》、《双题》、《多月》(杜按:或云即《拜月》)、《倩女》等千七百五十余杂剧,靡不辨其品类,识其当行。”[1](p.320)这中间大概包括了不少元明杂剧作品。于是“取其辞意高古,音调协和,与人心风教俱有激劝感移之功。尤以天分高而学力到,悟入深而题裁正者”的杂剧为本,率门人高笔峰、弭少庵、张畏独(自慎)等先选得五十种,因财力不逮,遂又减为十六种,刊成《改定元贤传奇》[1](p.316-317),是为今所见元杂剧传本明版中最早的刊本,约在1556年前(因李开先的《闲居集》已收入《改定元贤传奇》序),也是仅次于元刊的元杂剧刊本。今残存六种,《续修四库全书》收录最易見。六种中有《陈抟高卧》元刊本犹存,正可比较以探索元刊本与李开先的关系,虽然李开先在收入集子的过程中“删繁归约,改韵正音,调有不协,句有不稳,白有不切及太泛者,悉更正之,且有代作者”,这是说李开先对所选杂剧作品做了大量的更正甚至再创作。但是,若李开先本与元刊杂剧本存渊源关系,二者之间关键的字句必会有相通或者相同之处,如果细加比较,关系的蛛丝马迹会被发现。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先须讲明元杂剧版本的流传系统。仅就《陈抟高卧》而言,今存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改定元贤传奇》(1556年以前)、《杂剧选》(万历戊戌,1598年)、《古名家杂剧》(1588年)、《阳春奏》(1609年)、《元曲选》(1615年)六种版本。《改定元贤传奇》作为元代以后现存最早的元杂剧版本,研究发现,《阳春奏》、《古名家杂剧》等与其曲、科、白全同,结构布置、角色称谓等无差别,应该属于一个版本系统。主要标志性特点有第一折出场元本为外末,《改定元贤传奇》本改作“冲末扮赵大舍引郑恩上”,以下人物演员,以角色名目如末、色旦、外末、净等标识。题目正名元本无,《改定元贤传奇》同《杂剧选》无,《古名家杂剧》、《阳春奏》等本皆作“识真主买卦汴梁,醉故知征贤敕佐。寅宾馆敕使遮留,西华山陈抟高卧”。《元刊杂剧三十种》本第四折最后曲牌“离亭煞”,《改定元贤传奇》等皆作“离亭宴带歇拍煞”。“拍煞”显系错误,通常作“指煞”,若非一源岂能同错。《元曲选》或是来自另一版本系统,与《改定元贤传奇》等不同处在于,第一折出场作“冲末扮赵大舍引净扮郑恩上”,以下末、色旦、外末、净等皆以角色所扮人物名字标识,如第一折正末扮陈抟,外扮赵大舍,净扮郑恩。第二折外扮使臣党继恩。第三折赵太祖改扮驾。第四折郑恩扮汝南王。演员出场皆以人物名字标识。题目正名作“识真主汴梁卖课,念故知征贤敕佐。寅宾馆天使遮留,西华山陈抟高卧”。“离亭煞”与他本不同,作“离亭宴带歇指煞”。当然,《元曲选》虽与《改定元贤传奇》等本不同,但是由于晚出,虽有不同,也不排除可能本出于《改定元贤传奇》而自己作了大的修改,只是我们也无法否定其来自于另一版本系统的可能,因此,权且说是独立的一个版本系统。再加上《元刊杂剧三十种》,这样《陈抟高卧》今天就可以看作流传有三种系统的版本:元刊本一种即《元刊杂剧三十种》,明刊本两种:《改定元贤传奇》(下称李本)和《元曲选》(下称臧本)。我们将两种明刊本与元刊本比较,因三本的问世时间前后次序非常清楚且相距较远,可认定先后顺序即元本、李本、臧本。设若三本中或有全同,我们便说他们来自于一个版本系统。或李本同元本而与臧本异,我们就可以说李本来自于元本;或臧本同元本而李本不同元本,我们就会认为李本与今存元本无关系,而与臧本所属的版本系统有关系。因为元杂剧的版本据本人研究,其来历并不复杂,这样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叙述简略,我们且不论三本基本相同之处,因为他们的最始原本应该是一样的,也不论李本、臧本相同而不同元本者,因为后出者都可能有自行删改,我们仅校李本与元本同与臧本异或臧本与元本同而与李本异,以确定《改定元贤传奇》本与《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渊源如何。为了叙述简洁,我们这里主要从曲词方面取两个典型例子将三者比较,如元刊本第四折[七弟兄]“这场斯央不寻常,粉白黛绿妆宫样。茜裙罗袜缕金裳,绣帏中取乐崔身丧”,李本全同。而臧本作“这场斯央不相当,你便有粉白黛绿妆宫样。茜裙罗袜缕金裳,则我这铁卧单有甚风流况。”这里元刊本与李本表达的意思是,第就普遍道理上说男女渲欲将会丧身的道理,而臧本所说的是道士陈抟的土木形骸状况,显示的是道士的特质与操守。又如第四折[太平令]元刊本作“见如今山鬼吹灯显样,野猿伦笔题墙。子怕腐烂了芒鞋竹杖,尘昧了蒲团纸帐。尘世上勾当顿忘,枉交盹睡了都堂里宰相”,李本全同。臧本作“现如今山鬼吹灯显像,野猿抡笔题墙。怕腐烂了芒鞋竹杖,尘没了蒲团纸帐。纵有那女娘,艳妆洞房,早盹睡了都堂里宰相。”臧本这里是为结合剧情将元刊本与李本的“尘世上勾当顿忘”改作了“纵有那女娘,艳妆洞房”,句意场景完全不同。以上所云虽是仅举两例,实是笔者将两本所有曲词比较后得出的结果,反映了两本的基本状况,可见李本同元本处。而臧本虽然多有同李本处,却并无超出李本而与元本相同的内容,因此说,李本只能来自于元刊本,应与臧本系统无大关联。我们说李本来自于元刊本,不只是简单的观察二本之间的同异,而是也注意到他们字句有时相同,这种相同从校勘角度说毫无道理。如元刊本第一折[点绛唇]“定死知生,指迷归正,皆神应。蓍插方瓶,香爇罍文鼎”一曲李本完全相同,其间有“香爇罍文鼎”一句值得一说。“罍文鼎”本当作“雷文鼎”,因为雷文鼎是历史名鼎,又名孝成鼎,据云是王褒所造,金石类著述多有记载,属于常识,一般文人都应该知道,所以,臧懋循《元曲选》便改作了雷文鼎。又如元刊本第四折[离亭煞](他本作[离亭宴带歇拍煞])陈抟称“大王加官赐赏,交臣头顶紫金冠”,称呼皇帝赵匡胤为“大王”,称自己为“臣”,以大王称皇帝显然是大不敬,也不合常理,《改定元贤传奇》本若非从元本抄来,李开先应当不会有如此疏忽,《元曲选》后起便将“大王”改作了“你”字。“你”字呼皇帝对俗人而言不合常理,对于蔑视富贵的道士而言还是可接受的。似此种浅显错误的发生,若非来自于同一版本,这样的一致当不会发生。另外,李本的科白与元刊本的科白也是可以比较的指标。元刊本的科白虽然简略,也明显隐含一些李本与元刊本科白表述用字承启的痕迹。如元刊本第一折开场白陈抟有“五代间朝梁暮晋,尘世纷纷”,李本作“五代间世路干戈,生民涂炭,朝梁暮晋,天下纷纷”,只是将元刊本文字做了扩写。又如[醉中天]后正末陈抟宾白“不须酬谢”,《改定元贤传奇》作“无须酬谢”,至《元曲选》则改作“无烦酬谢”,李本改不作无,保留了“须”字,臧本将须方一并改去。第二折陈抟上场白形容自己为赵匡胤算卦回到华山后的生活情景说“倒大清闲快活”,《改定元贤传奇》与元刊本同,《元曲选》作“倒大快活清闲”,颠倒了字序。其间这一二字差别,有实质意义,也可想见李本与元刊本的直接关系。endprint
二、从《词谑》载曲看元刊杂剧与李开先旧藏关系
《词谑》一书是李开先晚年未完成的专录词曲的著作③,多收套曲、小令以及元明杂剧中曲词,其间选录有十多种元杂剧全折套曲,还有些零曲,赵景深钩沉元杂剧以及校勘元杂剧的学者多借其功,包含了元刊本同目同折者《萧何月夜追韩信》(《词谑》作《夜月追韩信》)、《李太白贬夜郎》,与明刊本同目同折者更多。从词曲看,《词谑》内容多与元刊本同,而与明刊本有着十分明显的差距。我们将其比较,亦是探索李开先旧藏与今存元刊杂剧关系之一途。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自二者本无相通之处设想,从曲词相异处先将《词谑》录曲与《元刊杂剧三十种》作比较。因李开先在《词谑》中说《萧何月夜追韩信》的《新水令》“此套元刻有《水仙子》、《夜行舡》,亦只平常;有《尾声》,他刻皆不载。予为之删其前而存其尾”,已经肯定了《萧何月夜追韩信》属于元本④,我们且以《李太白贬夜郎》为例,二本同处不说,其不同处主要是字词互异与元刊本多出《词谑》一些词句。
1.元刊本与《词谑》字句互异者,如:[混江龙]“决恋花市清香”,《词谑》作“偏恋花市清香”。“欧阳浩气”,《词谑》作“浩然真气”。“羨尘世苍苍”,《词谑》作“羨尘世茫茫”。[油葫芦]“蒲葡酿”,《词谑》作“葡萄酿”。“汗杀江湖量”,《词谑》作“干杀江湖量”。 [天下乐]“御手亲调”,《词谑》作“玉手亲调”。 [那吒令]“这酒曾散漫却云烟浩荡”,《词谑》作“这酒曾散浸了云烟浩荡”。“这酒曾眇小了风雷势况”,《词谑》作“这酒曾眇视了风雷势况”。“这酒曾混沌了乾坤气像”,《词谑》作“这酒曾混沌了乾坤气象”。“得运子有十年旺”,《词谑》作“得运只十年旺”。 [鹊踏枝]“祸起肖墙”,《词谑》作“祸起萧墙”。 [寄生草]“通厅炕”,《词谑》作“通鞓炕”。[六么序]“酒债寻常,粜尽黄粮”,《词谑》作“粜尽黄粱”。 [么篇]“教这厮横枝儿泄理阴阳!肚岚躭吃得惹来胖”,《词谑》作“教这厮横身躯燮理阴阳!肚瓓躭吃得偌来胖”。 [金盏兒]“子管里开宴出红庄”,《词谑》作“只管里开宴出红妆”。“锦屋闭鸾凰”,《词谑》作“金屋闭鸾凰”。 [后庭花]“我若沾危邦”,《词谑》作“我若站危邦”。“不合将足下央”,《词谑》作“不合将足下殃”。[尾]“子信着被窝儿里顿首城隍”,《词谑》作“只信着被窝儿里顿首诚惶”。“尽交谗臣每数量,至尊把我屈央,休想楚三闾肯跳泪罗江”,《词谑》作“尽教谗臣每数量,至尊把我屈殃,休想楚三闾肯跳汨罗江。”我们试分析元刊本与《词谑》这些字句互异者情景,一类是元刊本中的替代字,也可以说是错别字,《词谑》因更正而异,如“蒲葡”,《词谑》作“葡萄”;“气像”,《词谑》作“气象”;“祸起肖墙”,《词谑》作“祸起萧墙”;“泄理阴阳”,《词谑》作“燮理阴阳”;“惹来胖”,《词谑》作“偌来胖”;“红庄”,《词谑》作“红妆”;“顿首城隍”,《词谑》作“顿首诚惶”;“交”,《词谑》作“教”;“屈央”,《词谑》作“屈殃”;“泪罗江”,《词谑》作“汨罗江”类。二是元刊本用字《词谑》因理解不同更正而异,其实从李开先本人而言可能与第一类情形相同,以为元刊本也是用错了,如“决恋”《词谑》作“偏恋”,“欧阳浩气”《词谑》作“浩然真气”,“尘世苍苍”《词谑》作“尘世茫茫”,“汗杀”《词谑》作“干杀”,“御手”《词谑》为“玉手”,“眇小了”《词谑》作“眇视了”,“子”《词谑》作“只”,“通厅炕”《词谑》作“通鞓炕”,“黄粮”《词谑》作“黄粱”,“锦屋”《词谑》作“金屋”,“沾危邦”《词谑》作“站危邦”等。以上两类,第一类《词谑》是对的,第二类可能会有些不同看法,也就是说元刊本用字未必错,是可通的,如“通厅炕”实际就是大炕,主人可以在上面睡得很自在,如果改作“通鞓炕”(鞓,此处当指人体躯干)就失去原有的意义。又如将“锦屋”改为“金屋”,可能是李开先想到了金屋藏娇的典故,但联系剧情,却也是不符合李白追求的。只是不管这两种情况是对还是错,考虑到字词之间的不同都是一对一的关系,我们以为,《词谑》的不同是在对元刊本做校勘工作。众所周知,元刊本中的错别字替代字是非常普遍的,李开先编纂一种属于自己的著作,改正文献的错误是完全必须的,他自己也屡次说到更改词曲。这种改动的特点是不改变曲词的主干,仅仅改动一些作者认为的错误的或不恰当的词句。
2.元刊本多出《词谑》字句者,如:[混江龙]“似一竿风外酒旗忙……我舞袖拂开三岛路,……虽一箪食,一瓢饮,我比颜回隐迹只争个无深巷”,《词谑》作“一竿风外酒旗忙……舞袖拂开三岛路,……一箪食,一瓢饮,我比颜回隐迹只争无深巷”。 [油葫芦]“常是不记蒙恩出建章”,《词谑》作“不记蒙恩出建章”。 [天下乐]“官里御手亲调醒酒汤”,《词谑》作“玉手亲调醒酒汤”。 [醉扶归]“子一句道得他小鹿儿心头撞”,《词谑》作“道他是小鹿儿心头撞”。[金盏兒]“不争玉楼巢翡翠,便蚤锦屋闭鸾凰,如今宮墙围野鹿,却是金殿锁鸳鸯”,《词谑》作“玉楼巢翡翠,金屋闭鸾凰,宮墙围野鹿,金殿锁鸳鸯”。考察元刊本多出《词谑》的这些字句,诸如“似”、“我”、“虽”、“个”、“常是”、“官里”、“子一句”、“不争”、“便蚤”、“如今”、“却是”等,不难发现,曲词中这些字多属于衬字,于曲本身并无实质性语意。这些字的有或无不影响或改变作者意思的表达。《词谑》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从其以“谑”字的命名就很容易看出。再加上李开先录的是“词”,因此,在对待曲的取舍方面当然是以清曲为标准,是将戏曲的元杂剧一样作为清曲看待,从《词谑》标题可以看出,这与元明人论元杂剧重曲的态度是一致的,并不考虑情节的问题,因此录元杂剧时所重在曲,多以曲格录文,会有意裁剪去元刊杂剧曲中的衬字,或者李开先本人以为元刊杂剧中的字句不合曲格者。从上面两种情况看,《李太白贬夜郎》较《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同一支曲并无多出一些特殊字句,看不出版本的区别之处,再加上《词谑》录曲与今存元刊本录曲的数量、曲牌的名称、前后排列次序等皆是一样无二,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今传李开先《词谑》所录曲词的杂剧与今存元刊杂剧应是出于一个版本系统,或者就是李开先所用底本。endprint
[HS(3][HT5H][JZ(]三、从何煌校《王粲登楼》看元抄本杂剧与李开先旧藏关系[JZ)][HS)]
赵琦美脉望馆杂剧《古名家杂剧》有郑光祖《王粲登楼》一种,其字里行间,天头地脚有许多校勘批语,结尾有清人何仲子(何煌)校跋一则这样说:“雍正三年乙巳八月十八日,用李中麓抄本校,改正数百字,此又脱曲廿二昭昭,倒曲二,悉据抄本改正补入。抄本不具全白,白之缪陋不堪,更倍于曲,无从勘正。冀世有好事通人,为之依科添白,更有真知真好之客,力足致名优演唱之,亦一快事。书以俟之。小山何仲子记。”[2])这则跋文有两个问题尚需要深究,一是何煌依据抄本的时代问题,二是此本《王粲登楼》与李开先所藏的关系如何,虽然有何煌说“用李中麓抄本校”,但是确凿无疑吗?我们先说抄本的时代问题。断定抄本时代问题的首先是建国初期的孙楷第。孙楷第作《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据何煌跋文断定为元抄,说:“煌所据旧抄本见新安徐氏刊本《王粲登楼》跋……据此知抄本亦李开先旧藏……据煌跋称‘抄本不具全白,缪陋不堪,则其本与今所见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正同,以此知开先所藏抄本必为元人抄本,否则自元刊本抄出。”[3](p.168-170)。日后郑蹇又据元刊本形式,结合《古名家杂剧》以及何煌校勘语言整理成新本《王粲登楼》,又有《抄本<王粲登楼>跋》简单阐述了何煌校抄本的元抄性质,文云:“元刊三十种即李旧藏。细观此一抄本,不谨与三十种同出李氏,其体裁形式亦完全相同。一,只有正末之白,且甚简略质俚,其他角色之白皆谨以‘某云或‘某云了代之,又多‘某人一折了或‘某上开住等语。二,各曲文字简劲,所用衬字远较《古名家》及《元曲选》二本为少。三,曲数多于上述二本。全剧合计,较《古名家》多十七曲(何校云多二十二曲,计数错误。杜海军按:实多十八曲),较《元曲选》多十二曲,又有数曲文字与《元曲选》完全不同,凡此三者,皆为元刊本杂剧与一切明人刊本之主要区别。可知此钞本若非元钞,即是自元刊或元钞传录,盖与元刊三十种可以等量齐观者。其文字胜于《古名家》及《元曲选》甚多,不仅多出若干曲为可贵,洵善本也。”[4](p.457)郑蹇后宁希元也赞成何煌所据李开先本为元抄说,他在肯定了孙楷第、郑蹇意见后说:“我所补充的只有一点,即何煌的过录是非常忠实于原本的。原抄本许多待补的缺字,甚至明显的错字,都一仍其旧,末作改动。又,本剧第三折全套,亦见于李开先另一重要戏曲论著《词谑》内,两相比勘,除个别文字略有出入外,基本全同。可见,何煌所录确为李氏原本。”[5](p.257)诸家断定李开先抄本属元人抄本应该说是不错的,但是多为推论甚至是揣测,许多文献没能得到利用,笔者今日此文试做详论。《王粲登楼》今存刊本有脉望馆《古名家杂剧》、《元曲选》、《酹江集》诸本。《元曲选》、《酹江集》是一个版本系统,曲词相近;《古名家杂剧》是一个系统;李开先抄本是又一系统。另外,何煌校《王粲登楼》最后还说到第四折“一本[水仙子]下有[殿前欢]、 [乔牌儿]、 [挂玉钩]、 [沽美酒]、 [太平令]五曲”,这里的“一本”,与我们看到的诸本皆不同,今未见。也就是说《王粲登楼》共有过四个不同系统的版本,今存只有三个。我们将这三个版本系统的《王粲登楼》比较,发现李开先抄本有比他本不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正与《元刊杂剧三十种》相近。诸如不分折,科白少,交代提示情节过程简单,所用字词以“子”代“只”,以“恁”为“您”,以“得”为“的”,提示动作以角色不以人名等。李开先抄本最明显的元本特点,与明本较,在于一是曲多二是叙事逻辑两点。曲多,是元刊元杂剧最明显的特点⑤。《王粲登楼》全剧李开先抄本54曲,较《古名家杂剧》36曲多出18曲(第一折多[么]、[金盏儿]、[醉扶归]、[尾声],第三折多[喜春天]、 [哨遍]、[耍孩儿]、[么]、[三煞]、[二煞],第四折多[驻马听]、[甜水令]、[折桂令]、 [川拨棹]、[七兄弟(杜按:当作[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央煞]);较《元曲选》42曲多出12曲(第一折多[么]、[醉扶归],第四折多[驻马听]、[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元曲选》多出抄本[沉醉东风]),《酹江集》本同《元曲选》不论。将同一剧目元杂剧元明刊本作比较,元刊本曲都要比明刊本多,如《看钱奴》元刊本共有曲子57首,而《元曲选》刊本只有41首。这个差距中《元曲选》刊本径删去的有23首,几近原剧的一半。这样,似乎单从曲词的数量多少已经可以断定李开先抄本只能来自于元。再说曲的多少看似是数量的不同,实际是体现了剧本形成时代的不同。从元杂剧体裁的形成历史说,元杂剧形成在诸宫调与散曲之后,因此叙事形式多受诸宫调与散套叙事形式的影响,学界对此有共识,郑振铎已说的明确:“诸宫调的伟大影响,却在元代杂剧里……或者可以说,如果没有‘诸宫调的一个文体的产生,为元人一代光荣的‘杂剧,究竟能否出现,却还是一个不可知之数呢。”[6](p.332)郑振铎所说诸宫调对元杂剧的影响主要就是“专一人”念唱的形式,就普遍情况而言,通常一套曲叙事到结尾。我们看到的元刊杂剧曲通常多于明刊本,明刊元杂剧曲少,是由于明人已经认识到杂剧是戏曲,应以表演为主,也就更注重科白部分。
李开先抄本的叙事完整,前后照应,合乎逻辑。一是第一折首[仙侣·点绛唇]曲前有“驾一折”,也就是皇帝出场,从剧情推测应该是皇帝号召朝臣举荐贤能,这样,蔡邕荐举王粲入京便合情合理。作为照应,第四折首[双调·新水令]前又有“驾一折”,并于[驻马听]后有“太保送宣”科白,写王粲上万言书后得到皇帝封赠,完成照应,使得《王粲登楼》成为一个圆满的故事。二是李开先抄本开场有卜儿(王粲母亲)出场,第四折结尾卜儿、旦儿上场作为照应,推测情节应该是在王粲赴荆州后,蔡邕将王粲母亲接到自己家中赡养,最后又将自己女儿嫁与王粲,这使得王粲的母亲归宿以及王粲的亲事都有了交代,舞台活动也显得丰富。各个明本删去了剧中皇帝角色,也删去了太保送宣这场戏,卜儿、旦儿上场明本中改编作曹之建叙述,削弱了舞台表演部分。三是李开先抄本的第四折曲子主要描写王粲接受使臣授命后取得的战功,以展示王粲的治国理想与才能,如[七兄弟]“振雷霆势况,动关山响亮,珂珮韵锵锵。七重围里元戎将,五方旗号合堪傍,一轮皂盖飞头上”,明《古名家杂剧》本将此类原本十三支曲删至五支曲,《元曲选》六支,改写作曹子建叙述蔡邕多年对王粲私下帮助,以化解王粲因对蔡邕的误解产生的矛盾,变动了剧情,于剧于理皆不合。从全剧结尾曲看李开先抄本作“张仪若不是当时一度怀愁怅,苏秦怎能够今朝六国知名望。填还了万里驱驰,报答了十载寒窗。唱道执着百万军权,三台印掌,卧雪眠霜,雄赳赳驱兵将,再不对楼外斜阳,望断天涯旧乡党”,紧扣剧情,强调的是王粲有艰难的经历方有出色的成就,也说出了艰难困苦与汝玉成的人生成长之路。这样的曲词从故事发展逻辑看正可涵盖全剧,也具有普遍的人生指导意义。而明刊《古名家杂剧》本以[得胜令]结尾,显然是情节不完全,可不论,《元曲选》结尾曲作“你元来为咱气锐加涵养,须不是忌人才大遭魔障……早匹配了青春女一生欢,稳情取白头亲百年享”,从情节发展的逻辑看,这只能算是第四折的一个结尾,表现的是王粲对蔡邕的理解及其王粲成功后欢喜场面,于全剧却是缺乏照应,就作文章的角度看,显然是忘记了文章的整体思路或者说要表达的主旨,不及李开先本叙事的完满,优秀的作家叙事必不会有如此的疏漏,从这一角度看可见李开先本的早出。以上我们是以内证论述李开先抄本的元抄性质,以下从他证我们再将李开先抄《王粲登楼》与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引曲作比较。李开先抄本有 [仙侣·醉扶归]“论文呵笔描云烟散,论武呵箭射射斗牛寒,扫荡妖氛不足难。折末待掌帅府居文翰夕,不消我羽扇纶巾坐间,敢破强虏三十万”,《太和正音谱》有同曲与较,只最后一句“敢破强虏三十万”,少一衬字“敢”。[7](p.107)因朱权是明代早期人,所见曲本还保留有元人的本色,此一曲所有的明本皆缺载,所以,拙见以为也可以为《王粲登楼》李开先抄本属于元抄说助力。这样看来,李开先抄本《王粲登楼》属于元本无疑,那么,它与李开先藏书的关系如何呢?李开先十分看重《王粲登楼》,他说:“郑德辉作《王粲登楼》杂剧,四折俱优,浑成慷慨,苍老雄奇。”[8](p.297)这与李开先对元杂剧的整体评价是一致的,因此,在其《词谑》中屡有曲入录,涉及曲文包括第三折与第四折。特别是第三折全折入录,这让我们可以有个比较,看李开先在《词谑》中录曲与元抄本的一致,也为李开先藏元杂剧元人版本说一证。首先我们肯定李开先《词谑》所录曲与何煌校曲属于同一种抄本,试将何煌校录的元抄杂剧第三折与《词谑》所录第三折曲词比较可见,一是曲目皆为一十九曲,⑦在这一十九曲中,曲牌名除了笔误 [喜春天]《词谑》作[喜春来],[哨遍]《词谑》误作[哨篇],或同曲异名[么]《词谑》作 [四煞],[尾声]《词谑》作[尾]外,其他全同。联系其他元明刊本的差异可见,虽然间有不同,但若非来自同一版本便不会有如此高度的一致。《词谑·词尾》录[鸳鸯煞尾]来自于《王粲登楼》的第四折,与何煌校曲《王粲登楼》第四折尾曲也相同,他本皆不具备此曲又可为一证。二是我们将《词谑》录曲、《古名家杂剧》、元抄本杂剧三种作比较,见《词谑》同元抄本处,显示了与元抄本的关系。如[尾声]“看我事君王如腹心”,《词谑》作“事君王如腹心”,《古名家杂剧》作“你看我待君王如腹心”,三种版本的不同主要在于“事君王”与“待君王”,当然是“事君王”于意为胜。“事”为以下奉上,是王粲表明对汉帝的态度,而《古名家杂剧》“待”则是以上对下,此处的确不通。当然,我们也看到李开先《词谑》对元抄本有校改,但也仅是对个别字句的校改,是校勘性改动。如改[二煞],何煌校本为“我治的花生解倒悬”,《词谑》为“我治的苍生解倒悬”,实际情况可能是何煌因字形误辨,误将抄本“苍”(元人多写简体字,因是抄本,或“蒼”简写作“苍”)作俗体“芲”,所以辨作“花”。说到李开先《词谑》对元抄本校改,以上我们论到各剧本来自于李开先旧藏问题时,所举李开先所藏剧本的例子与我们见到的元代刊本或抄本杂剧在词句上多少都有些差异,这确实是我们理解元刊或者抄本元杂剧来自于李开先说的一大困惑,因为从传统的版本学观点而言,同一系统的版本通常是无多少字句差异的。但作为杂剧也就是戏曲这种文学文本,我们是不能以传统的版本学观点相视的。杂剧是一种活的文学,其文字是时刻会随着所有人(包括演员、观众)的需要而发生变化的,李开先多方说明他自己录入曲词时的改动⑧,所以我们只能从大方面的一致判断其与元刊杂剧的关系。这样我们若将《元曲选》等明刊本与元刊本比较所显现出来的不同与李开先本与元刊(抄)本之间的不同作个比较,会看到李开先所录词曲与各种元本的不同是很少的,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李开先本来自李开先旧藏即所藏元人版本这个问题了。李开先各本与元刊本、抄本间的不同仅仅是曲中错别字、异体字的不同,再就是有无衬字的不同,而所有李开先后其他系统明本与元刊(抄)本的不同涉及曲词的增减,上已有论,更主要的是往往涉及到剧情主题、曲词风格等多方面的质的不同。如体裁形式的改变,《赵氏孤儿》本为四折,《元曲选》改为五折;剧作结局的改变《疏者下船》元刊本为悲剧结尾,《元曲选》改为喜剧结尾;剧情主题改变《赵氏孤儿》本写复赵氏之仇,《元曲选》改为忠奸斗争等。这种大的改变甚至让人将同一种作品误解为他作,比如严敦易批评《元曲选》本《楚昭王疏者下船》是另一种剧作说:“元刊本《疏者下船》无问题是属于郑廷玉所作的。至于这另一本(《元曲选》本)《疏者下船》,他和元刊本的题名,以楚昭‘王和‘公为分野,所有的本子,应皆同出一源,似委实无庸再把他列在郑氏名下。严格地讲,认做是改订本,重编本,或‘别本,都觉不免牵强;最合适的说法,是同名另撰的一本杂剧,但其间剽窃了郑作的若干曲文,以及重复抒写了主要的情节罢了。”[9](p.395)。两相比较,李开先所藏各种元杂剧版本来自于元代版本这个问题就不难判定了。endprint
总的说来,我们从《改定元贤传奇》收录的《李太白贬夜郎》、《萧何月夜追韩信》,从《词谑》收录的元杂剧套曲,从何煌以李开先抄本校《王粲登楼》等,多方面探讨了李开先旧藏与元刊杂剧的关系,我以为元刊杂剧中多篇出自李开先旧藏基本可以定谳,至如三十种中其他元刊杂剧因无他人收藏记录,也可作如是观。加上《王粲登楼》抄本,即是说李开先所藏元本杂剧至少有三十一种。还有《词谑》收录王实甫的《芙蓉亭》、范子安的《范蠡归湖》(《录鬼簿》著录为赵明道)等的整折佚曲也见于《词谑》,或也为元代版本。《词谑》中所载元杂剧套曲多与明本不同,甚至完全不同,如元无名氏《郑月莲秋夜云窗梦》[仙侣·那吒令]《词谑》:“见一面半面,弃茶船米船;着一拳半拳,毁山田水田;不一年半年,卖南园北园;白玉妆了翡翠楼,黄金垒起鸳鸯殿,珍珠砌就了流水桃源。”[8](p.335),脉望馆抄本:“那等村的肚皮里无一联半联,那等村的酒席上不言语强言,那等村的俺根前无钱说有钱。村的是彻胆村,动不动村筋现,甚的是品竹调弦。”[2]且从《太和正音谱》看,《词谑》载曲更合谱,所以如此推论。李开先称自己“书藏古刻三千卷”,有藏曲一千七百多种,其间包括几十种元刊杂剧当不稀奇。在元刊(抄)杂剧存世不多的情况下,对于元代戏曲研究是有极大意义的。 最后,或疑李开先之本何来?我做了粗浅思考。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二在李开先小传中曾说李开先藏书涉及到文渊阁书允许外借事:“中麓撰述潦倒粗疏,然最为好事,藏书之富甲于齐东,诗所云‘岂但三车富,还过万卷余;又云‘借抄先馆阁,博览及瞿昙是也。……噫嘻!文渊阁藏书例许抄览,先具领状,以时缴纳,世所称读中秘书,盖谓是己。奈典籍微员收掌不慎,岁久攘窃抵换,已鲜完书,可为浩叹。闻中麓后人尚余残书数十部,巡抚丹徒张公物色之,中有陆司农《礼象》一编,张公殁后访之不能得矣。”[10](p.332)因此我们可想,李开先藏曲或多来自内府,或自己收藏,或手自抄录。我曾试将李开先藏曲与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引曲作比较,发现二者之间更有相同之处,如上举例何煌校抄《王粲登楼》[仙侣·醉扶归]曲,这一曲所有明刊本是没有的。朱权是王爷,其曲来自内府应该是没问题的。李开先在《张小山小令后序》又曾说到过大家熟知的明初亲王之国多以词曲相赠,可见李开先对明代内府藏曲事是比较熟悉的,且说到自己与曲词图书得来的关系:“予自游乡校,读书或有余力,则以毕词。……当时苦无书……既登仕籍,书可广求也”[1](p.369),也就是说李开先为官后接触上层人物或内阁成了得书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再考查《太和正音谱》载曲与《元刊杂剧三十种》之间的关系,发现他们之间同样有密切关系,即朱权的藏书中应该有不少元代杂剧抄、刻本,如《贬夜郎》,《太和正音谱》有[中吕·迎仙客]。《陈抟高卧》,《太和正音谱》有[南吕]曲[牧羊关][菩萨梁州][哭皇天][乌夜啼] [红芍药]。《竹叶舟》,《太和正音谱》有[南吕·三煞](太和正音谱)作[煞],[双调·新水令],[梅花酒],所载曲词两两之间,除了极个别衬字或有或无的差异,正曲之间无丝毫不同。又《太和正音谱》与《中原音韵》所载曲词也多相同,《中原音韵》所载自然是元本无疑问。据此我们似乎可以对元刊(抄)本杂剧从元代末期到嘉靖之间的流传有一个描述,如果再结合孙楷第对元刊杂剧李开先及其以后流传路径的研究,就可对元本至今的流传过程做如下推测:元本→明内府(朱权)→李开先。如果再向下说就是李开先→钱谦益(钱曾)→何煌→元和试饮堂顾氏→黄丕烈→顾麟士→罗振玉→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罗振玉,[11]( p.28、168)今藏国图。以上是对李开先藏元人版本杂剧的探讨,望方家指正。 (责任编辑:陈娟娟)[HT]
① [ZK(#]孙楷第以为元刊杂剧出自李开先旧藏,他说:“四跋《单刀会》不署名,审其字实系何煌笔。其跋《单刀会》、《看钱奴》,俱在雍正三年八月。跋《范张鸡黍》则已至雍正七年七月。前后相距,凡五年之久。似书即煌所自有,非假之他人。《魔合罗》跋不署年月,然煌校曲记所据本却以此跋为详。据此跋知煌所据为元刊本,其书乃明李开先旧藏。”(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杂出版社,1957年版,第168-169页。)持此说的又见今苗怀明《戏曲艺术》,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包建强、胡成选《〈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版本及其校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44-49页。脉望馆杂剧中有何煌校过的杂剧五种,所谓“四跋”,包括《单刀会》、《看钱奴》、《范张鸡黍》、《魔合罗》。每校有跋语,分别是《单刀会》:“雍正乙巳八月十日,用元刊本校。”《看钱奴》:“雍正乙巳八月廿六日灯下用元刻校勘。仲子。”《范张鸡黍》:“雍正已酉秋七夕后一日,元椠本较。中缺十二调,容补录。耐中。”《魔合罗》:“用李中麓所藏元椠本校讫了,清常一校为枉废也。仲子。”
② 复旦大学博士甄炜旎说“现存元刊杂剧三十种并不一定都是李开先的旧藏”。见《〈元刊杂剧三十种〉研究——以元、明版本比较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11页。
③ 路工在《李开先的生平及著作》中引述说李开先临终前手书遗嘱说:“惟苏、杭未得一游,普济新修园未得一到,《词谑》一书未成,尤可惜也。”见李开先著,路工辑校《李开先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36页。
④ 李开先《词谑》《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第321页。《词谑》此说意义有二,一是《词谑》所录《萧何月夜追韩信》是来自元刊本,其二是说,当时李开先所见除了元刻本再无他本,以此《词谑》中所录《萧何月夜追韩信》曲词来自于元刻本就可以定谳了,也就无须再议。因此,这里我们只讨论《李太白贬夜郎》。
⑤ 我对所有现存元明共有的16种元杂剧曲数有过比较,结果除了《陈抟高卧》、《气英布》、《遇上皇》三种外,十三种都是元刊本曲多:《疏者下船》46曲,《元曲选》45曲;《看钱奴》元刊本57曲,《元曲选》41曲;《赵氏孤儿》元刊本49曲,《元曲选》45曲;《任风子》元刊本46曲,《元曲选》与脉望馆本44曲;《老生儿》元刊本47曲,《元曲选》37曲;《汗衫记》元刊本44曲,脉望馆本37曲,《元曲选》33曲;《衣锦还乡》56曲,《元曲选》27曲;《范张鸡黍》71曲,《元曲选》58曲;《魔合罗》61曲,《元曲选》60曲;《竹叶舟》52曲,《元曲选》51曲;《铁拐李还魂》44曲,《元曲选》54曲;《博望烧屯》49曲,脉望馆本26曲;《单刀会》48曲,脉望馆本38曲;《陈抟高卧》52曲,脉望馆本同;《气英布》43曲,《元曲选》44曲;《遇上皇》元明本曲同。
⑥ 邓绍基也说:“元杂剧的连套形式,显然受了宋金时代流行的赚词和诸宫调的影响。”(《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⑦ 十九曲是:[粉蝶儿]、[醉春风]、[迎仙客]、[红绣鞋]、[普天乐]、[喜春天]、[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么]、[满庭芳]、[十二月]、[尧民歌]、[哨遍]、[耍孩儿]、[么]、[三煞]、[二煞]、[尾声]。
⑧ 大概曲家最不赞同衬字,周德清赞扬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说“此方是乐府,不重韵,无衬字。韵险、语俊。谚云‘百中无一,余曰‘万中无一”,“无衬字”是周德清论剧的一个重要指标。(周德清《中原音韵》《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册,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第253页)所以李开先抄曲删去许多衬字。
参考文献:
[1]李开先著,路工辑校.李开先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古本戏曲丛刊(四集)[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
[3]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M].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
[4]郑蹇校订.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M].北京:世界书局,1962.
[5]宁希元校点.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6]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7]朱权.太和正音谱[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8] 李开先.词谑[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9]严敦易.元剧斟疑[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0]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1]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M].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