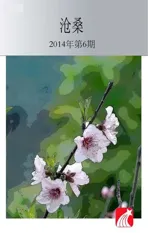常乃德“生物史观”析论
2014-04-10王斐
王斐
常乃德“生物史观”析论
王斐
作为五四运动后的新派历史学家,常乃德在生物史观的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本文主要讨论了常乃德和他的生物史观思想,以及生物史观作为国家主义派理论依据的相关内容。常乃德从史学科学化的立场出发,主张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根本上受到生物学法则的支配。生物史观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类比于生物的自然进化过程,以解释国家的兴衰存亡。这一观点为国家主义派的集体意识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又因其反对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说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常乃德 生物史观 国家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陷入民族国家的危机之中,西方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成为我国知识分子挽救民族危机的理论工具。严复翻译《天演论》将进化论思想第一次引入中国,首次系统地在中国介绍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思想。常乃德充分运用这一生物进化原理,将有机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提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受到生物法则支配,且将生物史观作为国家主义派的理论依据。
一、生物史观
“生物史观,即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1]从广义上说,凡以生物学原理来解释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现象的都可称为“生物史观”。但常乃德的生物史观并非完全无条件接受所有生物学原理而不加以选择。由于生物学本身有很多观点,因此用来说明人类历史现象的生物史观又可分出众多派别。常乃德所主张的生物史观正是许多支派中的一种,他以人类社会的有机组织为重点研究对象,认为社会有机组织的特性才是支配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常乃德指出:“一切生物的演化有一个根本的趋势,就是由无组织趋向有组织,由简单组织趋向复杂组织,这种趋势我们可以呼之为组织化的趋势。”[2]就相当于自然界中原始单细胞组织的生物演化成为复杂细胞组织的生物,组织简单的低等生物演化成为组织复杂的高等生物,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如同生物界,受这种有机组织的演变趋势的支配。在自然界中,较高等的动物如鸟类及哺乳类动物,他们一般有比较简单的社会生活组织,即由两性及亲子关系构成的家庭。而在人类社会中,这种趋势则更为明显,不仅在内容上得到了丰富,在组织上也发生了较大的进步,出现了各种社会组织,大体可分为自然社会和人文社会两类。
二、常氏史学思想
常乃德生物史观如同斯宾塞等其他达尔文主义者一样,多用类比法。他的生物史观主要建立在以下四个设定中:
首先,他指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实体,和其他任何生物个体一样。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具备生物有机体发展的所有特征。例如:(1)人类社会的发展像有机体一样有生长的现象;(2)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其结构和功能会出现分化作用;(3)人类社会各部分之间不是独立存在的单独个体,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既有分工亦有协作;(4)一个社会不是由一个单个的个体构成,而是由许多个个人构成,就像有机体也是由无数个细胞组成一样;(5)社会中的经济体系相当于生物的营养系统,政府组织相当于生物的管理系统,中央政府则相当于生物的神经中枢。其次,他将有机体的进化阶段归纳为:原始单细胞、复细胞个体和复个体社会三段。他认为,社会有机体乃是自然界生物在进化演变的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再次,他断言促成社会组织由简单组织趋向复杂组织进化的原动力,从根源上说不是其他而正是生物本性的要求。也就是说,人类的发展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其不断发展变化当然不会脱离自然而进行的。最后,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进必然受着生物学某种法则的支配。其中最具决定性的生物法则,则是达尔文所强调的“物竞”和“天择”,也就是生物竞争和自然淘汰。从进化的方向和方式来看,人类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组织的由简而繁,功能的由粗而精;另外则是自我意识由无到有,由模糊而明确甚至强烈。以上这四点为常乃德提出生物史观史学理论的大前提。一方面,他兼收并蓄,吸收与生物有机论相通的社会科学理论,如社会心理实在论;一方面,对和生物论相悖的其他历史学说进行批判。从而建立了常乃德独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史观。
常乃德深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认为生物界的进化都是“生存竞争”的结果,人类社会更是如此。他在著作中反复强调,不管是生物,还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其演化的根本趋势都是由无组织趋向有组织,由小趋向大,由简单组织趋向复杂组织。不管是生物还是人类社会,组织越严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也就越大。
人类与生物不同的则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衍生出各种文化,而生物则不具备。常乃德在对文化的变迁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社会的兴衰与国族的存亡,都被遗传、适应和追求平衡等生物学原理支配着。而这些文化“无论其为观念的,制度的,或物质的”,都是生存竞争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在演化过程中,为了使集体生存而发展出来的“工具”。
三、常氏史学与其他学派比较
有些学派认为,社会发展之所以有长短、丰俭之分,其决定性因素在自然环境,常乃德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支配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即其原动力,是社会自身所具备的条件。首先是“血统新鲜,社会分子有活泼进取的精力”;其次“信仰统一,社会意识一致”;其三,“组织巩固,社会有控制个人的威力”;还有“文化程度较高,物质及精神生活均较为优美”等等。而环境条件居次要地位。在环境条件中,自然环境又不及人为环境重要[3]。
1.政治方面。
从社会神经中枢的政治体制而言,深受国民性支配与影响。首先是组织,不同的国家即使有同一体制,但由于国民集体意识差异而导致社会组织仍有区别。例如英国与日本二者同为君主立宪体制,但由于两国长期以来的国民意识差异极大,导致了其君主立宪制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其次是国民性对变革手段的影响。例如英国人擅用和平改良之法,而法兰西人则以戏剧性的革命为主。又如一国政治领袖的领导风格及其治国的长远国策,也深受国民性的影响。例如,同属社会主义的运动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与基尔特主义,法国的工团主义,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正是由于各国的国民性的差异导致其呈现方式的差异。
2.经济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程度看,同样深受国民性支配。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以及各国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的确立都是建立在一国长期的集体性之上的,例如同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在结构和功能上常因国民性而不同,就好比同是工业革命,英、德、美、日虽都属资本主义国家,但其发展程度及发展方式各不相同。
3.思想文化方面。
以基督教为例,各国因民族不同而分成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流派。另外从政治经济思想方面来看,英国之所以出现重商主义,是由于其崇尚自由;德国之所以产生国家主义经济原理,是由于其崇尚秩序;法兰西爱好自由民权的激进思想;英国盛行和平改良之路等等,以上所列无不与各国的民族性、国民性有关。而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及教育制度等必然也为国民性所左右。
常乃德指出不论民族性还是国民的集体意识,二者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因为任何国家的国格的养成都是由其先天的国族气质与后天的历史文化环境相结合,以及在自然环境的磨合中逐渐养成,因此一国的国民性必然会受到遗传与环境影响。即使形成一种比较成熟且可以左右国家、民族的社会习惯时,也同样不能摆脱历史文化环境影响。然而,历史文化环境并非一成不变,历史文化环境的改变也必将会使国民性随之而变。因此,可以这样说,国民性与一国的历史文化环境本身有着共通性,实为一物,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即由历史文化环境造成某种模式的国民性,国民性同时又会改造历史文化环境,彼此之间不断的相互影响、变化。
另外,特别要提的是,常氏还接纳了雷海宗所提倡的多元文化周期论,这一点极有意义。在这种观点中,他以积极的文化再生说取代消极的延年益寿说,认为“人类社会经过文化蜕变之后,亦可获一新生命的新文化”[4]。这种蜕变通常有两条途径:“(1)自然途径,由原先不被重视的、潜在的文化支流或逆流转而取代昔年当道的文化主流。(2)人为途径,方案有四:1.生物的,即采行优生政策以改良人种,或与血缘相近之有种合并;2.地理的,即移民于新环境,俾取新养料新刺激,以改进社会成员的生理心理组织;3.文化的,针对生存需要从事内部革新,或吸取他文化之长;4.社会的,加速人才流动,以下层进去的新锐取代上层僵硬腐化的老朽。”[5]
四、国家主义理论中的生物史观
20世纪初我国陷入沉重的民族危机之中,知识分子为使国家摆脱民族危机积极探索新的出路掀起一场文化论战,这一时期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大动荡时期。
五四运动前后,国家主义思潮通过留学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成为当时重要思潮之一。最早受国家主义思潮影响的是五四时期的少年中国学会,其中的会员曾琦、李璜、陈启天、余家菊、左舜生、常乃德等人组建了中国青年党,作为国家主义派大本营。他们一方面大力宣扬国家主义,同时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成为他们宣传自己党派思想主张的具体阵营,因此国家主义派又被称为“醒狮派”。
国家主义派积极倡导建立一个“内求统一、外求独立”的国家的主张,他们认为任何个体的一切行动都要本着国家主义的精神。他们认为应该通过“全民革命”和教育的手段,从救国走向建国,他们把这当作是当时军阀混战下的中国摆脱危机的唯一道路。本着国家主义精神,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现代国家。
国家主义派将其理论支撑建立在生物进化学说之上,运用生物进化论对国家主义进行阐述。他们将“国民性”认定为历史上决定一切的最重要原因,否定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反对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产物这一基本事实。常乃德作为生物史观代表人之一,将社会有机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救亡理论,为国家主义的集体意识提供了理论依据。
生物史观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类比于自然生物界进化,并且从社会有机论视角出发,认为社会性质、功用及发展始末和发展趋势等方面都与所有的有机体有相似的地方,且受同样生物法则支配。常乃德在论述中强调生物进化最大的特点是“物竞天择”,要想在竞争中优胜劣汰,生物体必须具备强大的体力和智力,更重要的是适应环境的能力。但个体能力是有限的,必须通过团结协作而形成一个集体或群体,才能在竞争中取得更大的胜算。常乃德将这种生物进化论观点运用到人类社会,于是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分为家族社会、部族社会、民族社会和国族社会,这是一个不断联合且不断进化上升的过程。
国家主义强调国家至上,主张个人为国家要牺牲一切,反对任何阶级性。个人离不开社会,个人须在国家制裁之下,通过团结协作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物质与精神社会。事实上,这种观点违背了斯宾塞关于“不侵害个人自由的范围里,注重有机体与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平衡,并不是支配或统制个人的自由与权利”[6]的达尔文社会主义观点。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家主义派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建立在生物史观的理论之上,也就是用生物进化的原理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而解释国家的兴衰存亡。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从根本上反对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说的正确性,具有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倾向。因此,国家主义派在运用这一理论的同时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这就是这一派别为何没有成为历史主流的原因之一。
[1][2][3][4]黄欣周.沈云龙校.常燕生先生遗集.台北:常燕生先生七旬诞辰纪念委员会印,文海出版社, 1967.503,507,758—761,310.
[5]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346.
[6](韩)孙承希.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王 斐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责编 高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