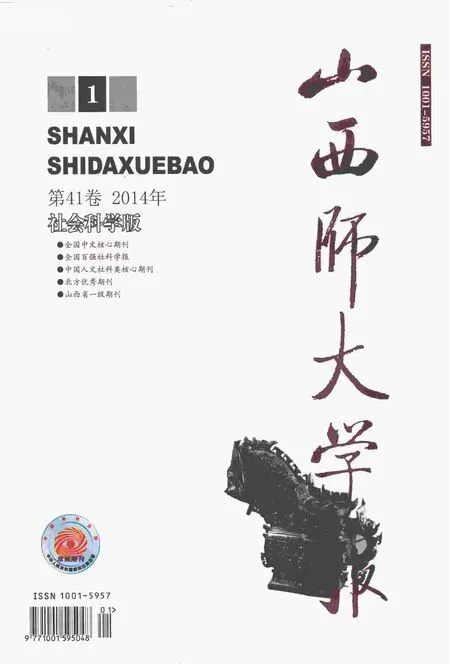浅论探索本雅明的“纯语言”观
——以《三国演义》英译本为例
2014-04-10张泽嬛
张泽嬛
一、本雅明生平
本雅明的一生短暂却又充满了漂泊的动荡,苏珊.桑塔格称他是“欧洲最后一名知识分子”和“现代文化中的土星英雄”。“本雅明的一生集众多身份于一身,在文艺批评、翻译、哲理思考、随笔写作等领域均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他在诸多看似对立的思想神风之间孤独而自由的行走。”本雅明1892年在德国柏林出生时家庭宽裕,父母都是犹太教的忠实信徒。他高中毕业、后又在弗莱堡大学专攻哲学专业;之后曾往慕尼黑、瑞日的伯尔尼等地求学、居住;最终在1919年本雅明以佼佼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学业可谓一帆风顺,然而本雅明的生活却一波三折:22岁时,年轻的他经历了好友诗人里兹.亨勒的自杀,这对他震动很大;30岁时他策划出版杂志《新天使》,未果;33岁时,意欲凭借《德国悲剧的起源》申请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未遂;38岁时,婚姻破裂,那时的他也完成了生前重要著作《单行道》;41岁时,正值希特勒上台屠杀犹太人,于是本雅明也彻底开始了他的逃命生涯;47岁时,本雅明被剥夺了德国国籍;48岁时,本欲越过比利牛斯山出逃,计划失败后,在西班牙边镇帕堡,他毫无眷恋的服药离世。“他的一生动荡漂泊在国际大都市间游荡,柏林、法兰克福、巴黎、马赛、佛罗伦萨、那不勒斯、莫斯科等地,足迹遍及欧洲,所以他的身份、职业、著述、主题、信仰,他的只言片语,都是难以分类的,但他的博学、才华和敏锐、深刻却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实现了真正的辩证融汇。正是这种融汇,留给20世界一个巨大的思考空间。”
二、本雅明的作品《译者的任务》
《译者的任务》是本雅明1923年所撰写,该文原本是他翻译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诗集《巴黎风貌》后为其所做的序言,但该文恰好与解构主义翻译思想有相近的见解之处,所以被解构主义翻译界推崇备至。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在《翻译诗学:历史,理论与实践》(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History,Theory,Practice,1993)一书中说“文章篇幅不长,却具有《圣经》的性质。因为文章深刻,有敏锐的洞察力,尽管意义晦涩而令人费解,但又极富有启发性。”在对理论的抵抗(The Resistance of Theory)里,德曼甚至声称:“如果没有对本雅明这篇文章有所阐发,你就是无名小辈。”由此可见,该文章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重要性。
在《译者的任务》中,本雅明先后解释了译文与原文的关系、探讨了文本的可译性、率先对传统翻译的忠实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翻译不是简单的在原作和译作之间进行内容的转换和传达,译作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扮演好原文本“后世”的角色。“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是保证语言的生存,并以此保证原文生命的延续,原文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封闭体。相对于未来的可能性而言,它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的状态中。译者的任务,就是赋予原文新的生命,使其生存下去,生存的更好,更充分”。而可译性又是指翻译的价值所在,也是“是某些作品固有的本质特征和其再生能力,只有当作品的语言在自身中蕴含的是精神存在,是真理,是启示,是那不可说的纯语言,它才有可译性”。“原作的语言品质愈低,它就愈接近信息,愈不利于译作的茁壮成长。反之,一部作品的水准愈高,它就愈有可译性。”本雅明对忠实的精辟论断为:“在译作中,对个别词句的忠实翻译几乎从来不能将该词句在原作中的本意复制出来。”他认为译文与原作无忠实可言,“二者的关系如同切线之与圆周:切线只与圆周在一点上轻轻接触,二者随即分道扬镳。”(刘宓庆)在文章里本雅明也指出,“以追求与原作相似为其终极本质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原作后来的生命里——如果不是经历一种生命的改变和更新,就不能称之为后来的生命——原作已经发生了变化”。
三、本雅明“纯语言”的提出
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本雅明提出了纯语言这一概念。他对纯语言的定义是:“所有超历史的语言间的亲属关系都存在于每一种语言各自的整体意指之中——然而,这种意指不是任何单一的语言可以通过其自身实现的,而只能通过各种语言一切互补的意指集合来实现,这个意指集合即是纯语言。”(译者的任务)本雅明认为纯语言是语言的最高级别,译者的任务就是开发纯语言。纯语言被他比喻做一个完整的花瓶,而各种不同的语言如同这个完整花瓶的各部分碎片。他认为:各部分碎片无需完全一样,但是当他们粘合起来后看上去必须浑然一体,无懈可击。如此一来,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在翻译的过程中,将潜藏于各种语言中的加以提炼,最终开发出无限接近于上帝的纯语言,实现让原文与译文的和谐统一,这也被本雅明看作是翻译最了不起的功能。为了达到纯语言这一最高境界,译者就要挣脱母语的束缚,实现对语言界限的跨越。
四、纯语言在罗慕士英译本《Three Kingdoms》中的体现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它是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全书以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为开端,截止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统一结束,时间跨度共97年。他生动的展示了以曹操、刘备、孙权为代表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该书极具艺术价值,为后来的文学界开辟了一种全方位描写复杂历史事件的体裁。
而1937年生于美国纽约的著名西方汉学家罗慕士长期活跃在美国高校和美国汉学舞台,现任纽约大学东亚研究学院教授。他有着扎实的汉学功底,多次以学者身份造访中国,长期醉心于中国文化,尤其对“三国文化”情有独钟。素有“中国通”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JOHN S.Service)在序言中指出,“罗慕士的翻译,首次让三国演义这不伟大而不朽的世界文学名著有了权威的、注释详尽的英文译本”。以下部分笔者意欲通过罗慕士的英文全译本来对本雅明的纯语言加以分析和印证。
例1.原文: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之者也。”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
译文:“What defines a hero is this:a determination to conquer,a mine of marvelous schemes,an ability to encompass the realm,and the will to make it his.” “Who merits such a description?” Xuande asked.Cao pointed first to Xuande,then to himself.“The heroes of the present day,”he said,“number but two ——you,my lord,and myself.” Xuande gulped in panic.
刘备丢失沛城后,失意的他投身于曹操部下。为了提防被曹操谋害,他去后园亲自灌溉种菜,以为韬晦的权宜之策。有日,曹操将玄德唤至相府,盘置青梅,煮酒畅饮。酒至半酣时,阴云滚滚,将至骤雨。此时曹操意欲试探玄德的本心,所以以龙做饵,实指当今英雄。译者在定义英雄时,用了排比的名词短语,其主干名词为决心、矿藏、能力、意愿(a determination,a mine,an ability,the will)。其中,译者更形象生动的将过人计谋比喻成一个丰富的矿藏资源,说明译者已经把人类的智慧视为大自然宝藏的一部分,这是从广义上揭示一个真理。二者的意指对象是相同的,但是意指的方式却不同,而笔者认为,译文中的意指方式颇为贴切生动,使得源语言和译文更加和谐、更加靠近于“纯语言”。当曹操又称玄德和自己并称世间枭雄时,玄德甚为吃惊。原文只是用了吃惊一词,译文中对突如其来的赞许和试探感到吃惊之余,还哽住了呼吸,内心既充满对隐藏杀机的惊慌,又从容的、小心翼翼的控制着自己的理智,“gulp”一词用的非常之巧妙,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如临其境的紧张感。如此一来,本来平淡的原语言在文学的长流中,确保了对语言和原文本生命的延续,我们可以认为此种文字处理方法更进一步的接近了“纯语言”。
例2.原文:生死无二志,丈夫何壮哉!不从金石论,空负栋梁才。
辅主真堪敬,辞亲实可哀。白门身死日,谁肯似公台!
译文:In life,in death,an undivided will——
A hero staunch and doughty!
But only to a lord of rarest worth,should a vassal pledge his fealty.
All homage for upholding his liege lord.
We sorrow as he bids his kin farewell.
At White Gate Tower he met his death unbowed:
The conduct of Chen Gong none can excel.
此诗是后人为同情陈宫之死而写的颂诗。陈宫辅佐吕布,但吕布未听从陈宫良言致使被曹所擒。曹操因感其救己之恩欲释放之,但陈宫大义凌然,只求速死,曹操忍痛下令斩首处决陈宫。陈宫死后,曹操以棺椁盛载其尸,葬于许昌。译者在翻译前俩句诗文时,很显然没有用直译的方法,而是采取了意译:生和死是不可兼得的事情,英雄具有坚定而勇敢的特质;仅为了实现上帝眼中的高贵价值,诸侯应该实现对主的忠诚。译者并没有像原作那样笼统地高歌称颂其“大丈夫”、“栋梁材”,而是从确认陈宫的坚定、勇敢、忠诚的人性高贵方面入手加以释义,这正与吕布性格的势力、多变形成鲜明对比,并帮助原作者在对外文化交流时,让读者感知到对此文学历史人物塑造的丰满,揭示了陈宫这一英雄因选错主公而必将导致其最终惨烈死亡。相比之下,译作对原作的补充,似乎向本雅明心目中的上帝“纯语言”又迈近了一步。
例3.孔明听罢,哑然而笑曰:“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
Kongming broke into laughter.“ The great roc ranges thousands of miles,can the common fowl appreciate its ambition?……”
诸葛亮只身随鲁肃过江、游说东吴群臣。时值刘备新败,退守夏口,曹操大军压境,东吴上下主降之风日盛。在此情势下,诸葛亮以其超人的胆识同东吴群儒展开舌战,并以其滔滔辩才使对手们皆成“口”下败将,并最终说服了孙权,使吴蜀联盟共抗曹操的局面得以形成,此句正是诸葛亮舌战张昭时的开场白。译者将原作中的“鹏”、“飞”、“群鸟”分别译为“the great roc”、“range”、“the common fowl”,我们可以发现译文中的“the great roc”和“the common fowl”形成了意指方式上的对比,而这点在原作中并无体现;原作中的“飞”,译作中为“range”,此词在词典中的解释为“be capable of projecting over a certain distance(有能力延伸至一定的距离)”,和“飞”相比,后者更突显大鹏展翅时广大的空间维度,使读者更能捕捉到大鹏横空的傲视群雄之感,更好的弥补了原作中仅此一“飞”的动作。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纯语言”在实践中视可行的。
自古以来,在译坛界中的探索层出不穷,历史上人们对本雅明所阐发的翻译思想也各持意见。笔者认为他的理论代表了翻译研究的一种思潮,尤其是对“纯语言”的提出,值得我们从多方面去思考和研究。真正的译作不会遮挡原作,更不会阻拦原作在古老历史中散发出的光芒。所以,译家应该借用原作和译作间的和谐互补、催生出无限接近于完美的“纯语言”,以求逐渐完成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后世传递。
[1]杨庆茹.本雅明思想身份的生平解读[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4).
[2]Willis Barnstone,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History,Theory,Prac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
[3]Paul de Man,Resistance to Theo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
[4]本雅明.本雅明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Moss Roberts,Three kingdoms.Foreign Languages Press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