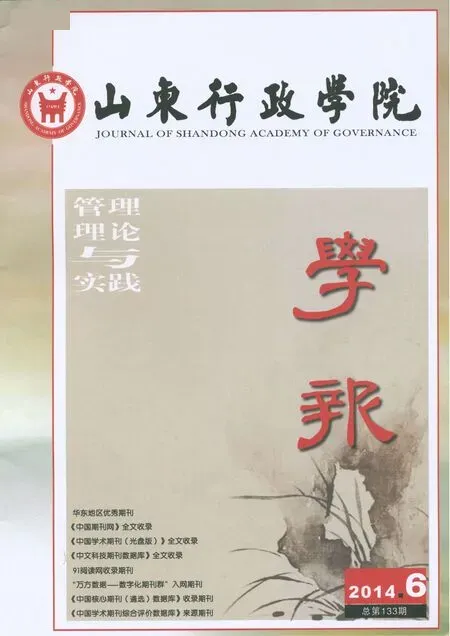试论媒体传播在培育积极社会情绪中的作用
2014-04-10唐颖,李龙
唐 颖,李 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100872)
媒体传播与社会情绪的关系极为密切,特别是随着网络新媒体以井喷式的发展渗透至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之后,两者的关系更趋紧密。厘清媒体传播对社会情绪培育的作用机制,形成媒体传播对社会情绪培育的良性格局,既要关注社会情绪的消极方面,更不可忽视社会情绪的积极方面。
一、社会情绪的概念及其现实
(一)社会情绪的概念
情绪既是主观的心理感受,也是客观的生理表达。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关系、政治体制、文化环境等方面的种种发展变化都会对情绪反应发生作用。基于公众个人情绪的相互感染,社会情绪是在特定的时间、一定的地域内持续弥散、普遍表现于公众之中的情绪体验,具有共同性和整体性的基本特征,是公众个人情绪反复渗透而成的有机体。它是现实生活中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既关系到社会稳定,也影响着社会活力。
情绪维度理论认为,效价(valence)这一基本维度上有着愉悦和非愉悦的正负两极,据此可对情绪做出积极与消极之分[1]。处在正效价一极的积极情绪可以给人带来愉悦的体验,而处在负效价一极的消极情绪则会为人平添非愉悦的感受。在积极情绪的众多定义中,事情进展顺利、需求得以满足、个人意义实现往往成为其主要诱因,这种主观体验常常被描述成“美好”、“快乐”、“轻松”的[2]。关于积极情绪功能的研究还揭示出积极情绪在实现心理健康、预防生理疾病、应对压力、促进认知以及提升社会公众幸福感等方面的作用。消极情绪则几乎与之相对,通常具体表现为不满、怨恨、愤怒、敌意等形式,其恶性功能已经被传统心理学所广泛验证。
社会情绪是在公众个人情绪相互感染的基础上形成,其所具有的共同性和整体性使之同样如公众个人情绪一般有着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社会情绪是公众个人积极情绪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而形成的社会情绪机制,而消极的社会情绪则是公众个人消极情绪普遍滋生和过度发育而产生的社会情绪机制。积极社会情绪无疑能够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团结,而消极的社会情绪则会弱化社会信任、扩大社会焦虑。
(二)社会情绪的现实
中国社会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环境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转型、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的国内环境之中。在食品安全、住房保障、反腐倡廉、环境保护等社会热点话题上,当前特定时期的“阵痛”无疑对社会公众产生着刺激性影响,时刻考验着社会情绪。虽然现在社会情绪的总体基调依旧是积极正向的,但是消极的社会情绪在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逐渐分化、社会共识和社会团结逐渐淡化、社会冷漠和社会焦虑逐渐泛化的进程中逐渐萌发和蔓延。
现在,社会情绪演进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突出倾向亟待加以关注。其一,面对一些社会事件,社会情绪反应较为反常,在传统价值观念中本该同情或本该谴责的现象,却有很多民众为之欣喜,为之赞美。例如,针对2012年3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生的患者家属刺死一名医生、刺伤三名医生的血案,人民网对六千余名网民的读后心情进行的调查发现,表示高兴的多达65.3%,而表示同情、难过、愤怒的却仅有25.2%[3],一场惨剧反倒成为网民的“精神狂欢”。其二,围绕一些社会问题,社会情绪表现出耐受性不足、引爆点降低、极端化凸显的特征,不少民众习惯于盲目声讨和跟风围观,正义和理性却未获得广泛恪守、普遍遵循。例如,2010年12月发生在浙江乐清的钱云会案一经报道便引发网民热议而谣言四起,随着信息的不断披露,本该愈益清晰的真相却因意见领袖的情绪化渲染和谣言的“正义化”包装,反而愈益扑朔迷离,网民对有理有据的官方通报不予理睬甚至愤怒声讨,而对捕风捉影的各类流言却颇加追捧。
积极情绪是社会发展的“正能量”,消极情绪则是社会发展的“负能量”。在社会情绪“正能量”和“负能量”的相互博弈过程中,消极的社会情绪如果不断滋生、发育和传染,势必要挤占积极社会情绪的发展空间和“阵地”,挑战积极社会情绪的主体地位。一旦社会事件加以煽动、意见领袖借以撺掇,消极的社会情绪就会成为群际冲突和社会摩擦的“培养基”。如此一来,社会公众幸福感受其影响而难有显著提升,实现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也会为之掣肘。
二、社会情绪建构中媒体传播的影响
(一)媒体传播与社会情绪建构的研究现状
众所周知,社会公众往往需要借助媒体传播对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加以了解和把握,这种依赖性也随着媒体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而不断强化。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传播逐渐成为社会公众主要甚至唯一的信息来源,其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刻画与呈现得客观与否,将会显著地塑造社会公众对现实的认知-行动。
国外相关研究发现,媒体传播中充斥的鼓噪消费主义观念的广告信息和展现富裕阶层生活的影视信息往往容易使得社会公众产生认知错觉,高估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4],并由此产生拜金主义观念[5]。而长此以往也就难免滋生不满、怨恨等消极的社会情绪,偏信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作用而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作用,社会信心不足,社会信念缺失,幸福感不高。也有研究进一步揭示出,当社会公众从媒体传播中普遍觉察并逐渐认可某个问题时,如果针对问题的相应补救措施显得合理且适用,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在公众中引发焦虑,对德国报纸关于石油危机报道的研究佐证了这一结论[6]。媒体传播对社会公众认知-行动和情绪体验的建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国内既有研究则重点强调,社会情绪受媒体传播影响显著,特别是媒体传播对消极的社会情绪的疏导、解烦、抚慰等功能应当给予更多关注[7]。
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也促使学界关注其对社会情绪的影响。网络新媒体传播将媒体选择转变为群体选择、将完整型传播转变为碎片化传播、将单向传播转变为多向传播。这些特征使得网络新媒体传播的效果更为复杂多元,反向社会情绪往往在其传播过程中得以放大[8]。除此之外,网络新媒体激化消极的社会情绪所呈现出的突发性与扩散性、逆反性与偏执性也引发了相关讨论,不少学者呼吁警惕网络新媒体传播的“负能量”。不过,尽管媒体传播对社会情绪的建构作用已经受到研究者的肯定,但其对积极社会情绪的培育作用却几乎没有任何研究。如何面向社会现实、适应公众需要,利用网络新媒体提振积极社会情绪、激发“正能量”也少有研究给出系统的回答。
(二)媒体传播对社会情绪培育的作用机制
俗语有言:“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较之于积极信息,消极信息的媒体传播往往能够通过对公众的好奇驱动、集群感召而更有其社会心理方面的“优势”,传播消极信息的媒体因此更有其社会心理“市场”,社会公众的情绪体验往往也就更易受其干扰和诱导。如此一来,积极信息的媒体传播本就有其天然的劣势,即便在其和消极信息传播两者间均衡用力,前者的收效也往往不及后者。而一旦媒体为了迎合社会公众猎奇、围观等心态偏重消极信息传播,其结果更是可想而知。
当前中国消极社会情绪的滋生、发育和传染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与媒体传播对社会情绪的引导密切相关。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网络技术进步的历程,转型中国暴露出的社会热点话题在媒体传播对社会情绪的迎合与社会情绪对媒体传播的裹挟中卖点炒作接踵而至、负面报道层出不穷。纯粹情绪宣泄的揭丑新闻、已成报道死结的循环新闻、缺少人文关怀的“无人”新闻等“问题”新闻随之不断涌现,新闻传播中的绝望倾向日益浓重,希望姿态逐渐低迷。特别是在钱云会遇难、击毙周克华、留美学生遭受枪击致死等一些公共事件上,媒体传播的介入、跟踪和报道总是为错误民意而动,不是关注何为事实真相,而是关注是否吸引眼球,“一边倒、一阵风”的问题相当明显。以上这些问题不仅无助于对社会公众传播理性声音、疏导消极情绪,反而有助于消极情绪的进一步发育和传染。另一方面,媒体传播对积极情绪的培育作用尚有诸多弊病。过度刻画、崇尚“造神”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套方式依旧被相对不足的媒体积极信息传播所沿用,这种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与民众期待难以契合的传播方式不仅无法得到认同与共鸣,反而容易引来反感与抵触,积极信息媒体传播的作用因此而适得其反。由此可见,当前积极信息的媒体传播既难有主动权,又缺乏感染力,并未发挥培育积极社会情绪的应有作用。
近年来,网络新媒体传播渠道兴起,传统媒体的传播主宰权受到巨大挑战,社会公众个人由此在媒体传播中分得一杯羹,媒体传播对社会情绪的影响也随之得以扩大。目前,中国网民数量已经约有6亿,手机网民规模也已经超过4.5亿,这无疑成为全球最庞大的媒体传播源和最复杂的舆论生态场。然而,网络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是社会情绪自然发酵的“沃土”,社会情绪的传染作用和共振效应表现得更为突出。缺少新闻专业主义的束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一些特定群体习惯于在其中表达内心不满、宣泄负面情绪,加之部分“意见领袖”的蓄意鼓动和大量“网络水军”的推波助澜,令人难辨真假的消极信息肆无忌惮地得以传播。几近个人主宰的网络新媒体中,易于引发集体情绪响应的消极信息往往经由群体选择而进入媒体传播渠道。网络新媒体俨然为消极的社会情绪发育、滋生提供了“温床”,更应受到关注。
三、推动积极媒体传播,培育积极社会情绪
培育积极社会情绪是媒体传播在引领社会道路、动员社会力量、振奋社会精神的过程中承担的重要责任。推动积极的媒体传播是培育积极的社会情绪的关键举措,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对无序自发的媒体传播加以监管和治理,使理性的声音盖过盲目的声潮,同时也要让励志乐观的媒体传播得以延伸和扩散,使积极的力量超越消极的力量。
一方面,消极的媒体传播应当加以监管和治理。媒体传播中的消极信息,相当比例都是谣言。它们对社会热点话题的真相蓄意扭曲、对社会焦点事件的危害刻意夸大,公众因好奇对其加以关注时往往受之蒙蔽而增添对社会前途的怀疑、削弱对国家未来的信心,消极的社会情绪就会随之弥漫于其间。媒体传播既有自己的职业操守,更有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的约束。特别是网络新媒体传播不能把自由表达的话语权异化为无端传播谣言的“发声器”和肆意宣泄情绪的“出气筒”,任凭某些“意见领袖”呼风唤雨和大量“网络水军”甚嚣尘上,从而助长消极的社会情绪。
针对消极信息,媒体传播管理者和运营方应守好土、把好关,强化监管力度不缺位,提升监管效率不掉队。应以谣言治理为重点,追根溯源地查明真相,公开透明地说清事实,明确妥当地追究责任,从而让谣言的制造者无处可藏、谣言的传播者无据可讲、谣言的接受者无当可上。媒体传播管理者和运营方同时应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有理有据的消极信息不能只给人绝望,不给人希望,不能只讲批判性,不讲建设性,应在在客观和理性中努力寻求和谐的新闻采写视角和话语表达方式,尽最大努力变消极的媒体传播为积极媒体传播,以最大限度降低消极的情绪影响。
另一方面,积极媒体传播应当得以延伸和扩散。媒体传播“正”的影响力和“暖”的感召力同样不可或缺。培育积极社会情绪既要努力置换消极媒体传播的空间,疏导消极社会情绪,创新积极信息媒体传播的内容、形式和渠道,提升媒体传播的社会效益。这是因为社会情绪中“正能量”和“负能量”消长的过程中,纯粹消减“负能量”而出现的空间并不会被“正能量”所自动占据,因此只能达到治标的效果、发挥一时的作用。唯有激发和汇聚“正能量”才能推动社会情绪的健康发展。
媒体传播管理者和运营方应当牢牢掌握媒体传播工作的主动权,在改革创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实现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相互融通,加强媒体从业者队伍建设,树立积极媒体传播的理念,使之通过全面的报道代替网络新媒体片断而散乱的信息,专业的评析改变网络新媒体扭曲甚至错误的导向,从而让冰冷的社会事实也能在字里行间充满正气、焕发暖意。同时应当调动网络新媒体中个人的积极性,依托实质性的鼓励、扶持和引导措施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筑牢积极媒体传播的“堤坝”,打造积极媒体传播的品牌,从而使网络新媒体以积极传播为主,为积极传播所用。
四、结语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社会情绪环境,推动积极媒体传播应当按照党中央的相关精神,因时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当前,既不能对消极的媒体传播听之任之,更不能对积极媒体传播不闻不问,而应摆正姿态,服务大局,充分发挥积极媒体传播的作用,为“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凝聚智慧和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锻造自信与自觉。
[1]Russell J.A.A Circumplex Model of Affec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0,39(6):1161-1178.
[2]Lazarus R.S.Emotion and adapt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3]王俊秀.关注社会情绪,促进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2012~2013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C]//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Sirgy M.J.et al.Does television viewership play a role in the perception of quality of life?[J].Journal of Advertising,1998,27(1):125-142.
[5]Shrum L.J.,Burroughs J.E.&Rindfleisch A.Television's Cultivation of Material Values[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5,32(3):473-490.
[6]李永健.传媒对公共情绪宣导抚慰功能的研究设计[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1):111 -116.
[7]詹绪武.公共情绪与大众传媒的宣导机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59-163.
[8]许莹.网络群体传播中反向社会情绪的放大效应及其疏导[J].中州学刊,2013(6):174-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