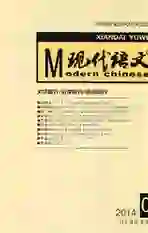粤语吴川话和湘语的关系
2014-04-09陈宇宇
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历史考据和词汇对比,论述粤语吴川话和湘语的关系。粤语广州话、吴川话和湘语有不少共有的的词语,它们有的直接来源于中原古汉语;部分粤语吴川话词汇直接来源于湘语;粤语吴川话和湘语都留有壮语的痕迹;粤语吴川话和湘语有不少共通的地方。
关键词:粤语吴川话 湘语 历史考据 词汇对比
一、前言
吴川县位于广东省西南部,南临南海,东与电白县接壤,北与化州市、茂名市交界,西与廉江市、西南与湛江市毗邻。吴川地处粤西的鱼米之乡——鉴江平原。周朝时期,吴川属百越之地,县境内居住着部分南越族的先民——古越人。秦统一后,许多中原的汉族“谪徙民”强制迁到岭南,“与越杂处”。此后,由于战乱、灾害等原因,中原汉族人民又多次南迁,发生民族融合,古越人逐渐同化于汉族。唐宋以后,许多福建人来吴川当官或经商,后定居下来[1]。
因此,粤语吴川话的成分很复杂,它受到了上古汉语、壮侗语、闽语、客家话的影响。粤语吴川话保留了大批上古汉语词汇,如卬(第一人称代词)、集(鸟停在树上)。也有古壮语词留下的痕迹,如翻书、书页(壮语:55;吴川话:p55)[2]。粤语吴川话也存有一些闽语词汇,如种公猪(雷州话:猪公22 213;吴川话:猪哥55 55)。[3]明清以来进入粤西的客家方言虽然对粤语影响不大,但也有少量词语进入了粤西粤语,进而影响到粤语吴川话,如吃早饭:食朝(客家话:5 45;吴川话:4 55)。[4]
以上四者,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是粤语吴川话和古楚语的关系,似乎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因此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予以证实。本文就历史考据和粤、湘方言的词汇比较两个方面,试图探讨二者的某些关系。
二、古代的粤、楚关系
据考据,战国初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相,实行变法,南攻扬越(扬越最初分布在湖北江汉之间的汉水一带),有部分扬越人不甘臣服于楚,通过“湘桂走廊”或东南沿海,南迁岭南以外,有的进入雷州半岛,跟当时散布在沿海极少数过着半流动生活的、以渔猎为生的“土著”(交人或称鲛人)杂处,最后“融合”了“交人”。故《史记·货殖列传》:“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扬越多焉。”而南迁儋耳,雷州半岛是必经之地。1977年12月,在雷州半岛东部附近的硇洲岛出土一批青铜器,经鉴定出自一座战国时期的墓葬。这些青铜器的形制跟湖南、湖北等地楚墓出土的青铜器形制相似。有关专家根据此墓出土的青铜剑考证,认为墓主有可能是当时楚国“抚征南海”时牺牲的“军人”。[5]明朝黄佐《广东通志》云:“楚子熊挥受命镇粤,至此(指雷州)开石城,建楼(即楚豁楼)以表其界。”也就是说,战国时期,雷州已成为“楚界”。[6]这可作为楚国势力南伸粤西的佐证。
另一方面,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记载,楚成王时,“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地为楚有,故筑庭(即地方行政机构)以朝楚”[7]。可见这时楚国已与岭南部分地方发生了政治关系。直到楚威王时,楚国才基本把整个岭南地区置于楚国统治之下。于是现在的广东地区全部归入楚国版图。[8]因此,吴川也自然落入楚国囊中。
由于年代久远,吴川又偏居粤西一隅,古代吴川与楚国的关系在典籍中没有体现。2001年版的《吴川县志》关于吴川的建制仅有如下记载,“吴川县地先秦时属百越之地。秦属象郡”[9]。
要把这段历史钩沉出来,有些地方只能靠推理了。
从地理环境看:吴川是粤西地区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江河纵横交错,鉴江是粤西最大的河流,以鉴江为主流,从北至南贯穿全县,其支流袂花江、梅江、三丫江分布于东北部,塘缀河、板桥河(板埠河)、乌坭河分布于西南部,形成了鉴东和鉴西两大水网。而且吴川是多雨地区,累年平均降水量为1579.8毫米。
从生产方式看:楚国以稻作为主。鉴江平原也是以稻作为主。雷州虽然为其边界,但毕竟靠海,淡水资源并不丰富,再加上雷州半岛的西南部属于少雨区,如此粤西最为肥沃宜农之地应为鉴江平原。况且吴川开发得比较早,5000多年前就有人居住了。而且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中原人来此定居,留下了一大批上古汉语词汇(例子请参看本文第一段)。吴川自然应该成为外地移民首选之地。
三、粤语与湘语词汇比较
从语音上看,粤语和湘方言的语音差别很大,泾渭分明,二者没有太大的联系。从语法上看,这两种方言的语法差别又太小,没有可比性。从词汇上看,湘方言和粤方言中有不少相同之处,我们只能根据这一线索来探讨二者间的关系了。
因为吴川话是粤方言的次方言,而粤方言区的中心方言又是广州话,湘方言区的中心方言是长沙话。将吴川话、广州话、长沙话三者进行比较,可以使我们高屋建瓴,更能看清粤语吴川话和湘语的关系。下面的两个词表,主要用广州话和吴川话的词语对照长沙话相应的词语制成,以说明广州话、吴川话和湘语之间的关系。第一个表现的是湘语、广州话和吴川话共有的词语;第二个表现的是粤语吴川话中独有的湘语成分。
(一)粤方言共有的湘语成分
粤方言共有的湘语成分
长沙 广州 吴川
菢u11:孵卵(动词) 菢pou22:孵卵(动词) 菢pou32:孵卵(动词)
哴ln11:晾晒(衣物)[动词] 哴l22:晾晒(衣物)[动词] 哴l32:晾晒(衣物)[动词]
挦11:拔取(动词)[湖南祁阳话] 挦im11:拔取(动词) 挦in21:拔取(动词)
嗍so33:啜,吸(动词) 嗍k33:吸饮;深吸气;深吸着气闻(动词) 嗍uk5:吸(动词)
辘liu33:推滚、滚动、转动(动词) 辘lok55:滚;滚压;摔(动词) 辘lok5:滚动(动词)
fa35:用力甩(动词)[湖南新余话] fek22:用力甩(动词) fek2:用力甩(动词)
绹tau13:绳索;用绳索捆(动词) 绹tou4:(用绳索)捆绑、拴紧(动词) 绹tou21:(用绳索)捆绑、拴紧(动词)endprint
簕lie35:植物的刺、荆棘(名词)[湖南衡山话] 簕lk22:植物的刺(名词) 簕lk2:植物、动物的刺(名词)
当tan24:地方(名词)[湖南衡阳话] 定t22:方位、地方(名词) 定t32:地方(名词)
杀sa24:割(动词) 杀at33:切(一般指把物体切开)[动词] 杀at5:切(瓜果)[动词]
丫a33:张开(动词) 丫a22:叉开肢体;占地方、占据(动词) 丫a32:叉开肢体(主要是脚);走开(祈使)[动词]
觇tan33:抬头(动词) 觇tam55:抬头(动词) 觇tan55:抬高肢体(动词)
讠厊讠厏a55 tsa55:性情乖戾,喜欢扯皮(形容词) 讠厊讠厏a22 ta22:体积过大;占地方;横行无忌(形容词) 讠厊讠厏an55tan55:霸道(形容词)
扌刍:tsu33:双手托物(动词) 扌刍:tu55:提(动词) 扌刍:tu55:用手搬、捧;提(动词)
禾o13:水稻(名词) 禾w11:水稻(名词) 禾w21:水稻(名词)
新妇si24 fu11:儿媳妇(名词) 新妇m55 pou13:妻子;儿媳(名词) 新妇n55 pou44:儿媳(名词)
崽tsai41:儿子;幼兽(名词) 仔i35:儿子,年轻男子;泛指儿女;年纪较小的人;动物幼子(名词) 仔ti35:儿子;泛指儿女;年纪较小的人(较少用)[名词]
女24:女儿(名词) 女ny35:女儿;用于年轻女性;女恋人(俗)[名词] 女n44:女儿;未婚女性(名词)
崽女tsai41 41:子女(名词) 仔女i35 ny35:子女(名词) 仔女ti35 n44:子女(名词)
龅pau55:牙齿不齐,向口外突出(形容词) 龅pau22:牙齿不齐,向口外突出(形容词) 龅pau21:牙齿不齐,向口外突出(形容词)
镬o45:锅(名词)[湖南新化话] 镬wk22:锅 镬wk2:锅
搇tsn11:用手按(动词) 搇k6:按、摁(动词) 搇kn32:按、压(动词)
核ua24:果核(名词)[湖南新化话] 核wt22:果核(名词) 核wt5:果核(名词)
屙o33:排泄(动词) 屙55:排泄(动词) 屙55:排泄(动词)
睺hu24:羡慕,想得到(动词) 睺hu55:希望得到;想要(常用于否定);(对某些情况或人等)注意、留意;侦伺;监视[动词] 睺hu55:虎视眈眈,想得到;侦伺;监视;要(动词)
炅mia55:很黑(形容词) 麻ma1:用作词缀(如夜麻麻、黑咪麻) 麻ma55:用作词缀(如暗麻漏夜)
估ku41:估计(动词) 估kwu35:猜想;以为;谜语(动词) 估ku35:预测、猜测;以为(动词)
走tsu41:跑(动词) 走tu35:跑(动词) 走tu35:跑(动词)
企ti11:站(动词) 企kei22:站立(动词) 企ki44:站立(动词)
凼to11:坑(水坑、粪坑)[名词] 凼tm13:水坑(名词) 凼tm35:水坑,水窝(名词)
细si55:小(形容词) 细i3:小(形容词) 细i44:小(形容词)
餐tsan33:顿(量词) 餐tan55:顿(用于饭);顿、场(用于做事情等做得时间长的):如打咗个仔一餐(打了儿子一顿)[量词] 餐t55:顿(用于饭);顿、场(用于做事情等做得时间长的):如得餐做(做得很辛苦)[量词]
癫tie13:疯病(形容词) 癫tin55:精神病(形容词) 癫tin55:疯病、精神病(形容词)
起屋ti41 u24:建房子(动词) 起屋hei35ok55:建房子 起屋hi35 uk5:建房子
熛piau33:(火花、油、泥浆、水等)飞溅[动词] 标piu55:喷,冒(出来);迅速往上长;长高[动词] 标piu55:喷,冒(出来);迅速往上长;长高[动词]
谷ku24:稻谷(名词) 谷kok55:稻谷(名词) 谷kuk5:稻谷(名词)
屋u24:整所房子(名词) 屋ok55:房子;楼房(名词) 屋uk5:房子;楼房(名词)
跳皮tiau55 pi13:顽皮、跳皮(形容词) 跳皮tiu33 pei11:顽皮、跳皮(形容词) 跳皮tiu44 pi21:顽皮、跳皮(形容词)
手板su2 pan2:手掌、手心(名词) 手板u35 pan35:手掌、手心(名词) 手板u35 pan35:手掌、手心(名词)
吊颈tiau55 tin41:上吊(动词) 吊颈tiu33 k35:上吊(动词) 吊颈tiu44 k35:上吊(动词)
部pu11:辆、台,用于机器、车辆(量词) 部pou22:辆、台,用于机器、车辆(量词) 部pu32:辆、台,用于机器、车辆(量词)
撩liau13:招惹、挑逗、挑衅(动词) 撩liu11:(用言语)戏弄、逗弄;招惹、挑衅[动词] 撩liu21:招惹;玩耍(动词)
怕丑pa55 tu41:害羞、害臊(形容词) 怕丑pa33 tu2:害羞、害臊(形容词) 怕丑pa44 tu35:害羞、害臊(形容词)
潲水sau55 yei41:泔水(名词) 潲水au33 y35:泔水(名词) 潲水au44 ui35:泔水(名词)
帮pan33:替,给(动词) 帮p55:替,给;同、和;帮助(动词) 帮p55:替,给;帮助(动词)
黏ia13:粘贴(动词) 黏nim11:粘贴(动词) 黏na55:粘贴;有粘性;紧紧地跟随,不肯离开(动词)endprint
人客13 k24:客人(名词) 人客jn11 hak22:客人(名词) 人客j21 hak4:客人(名词)
丢格tiu33 k24:丢脸(形容词) 丢假tiu55 ka35:丢脸(形容词) 丢假tiu55 ka35:丢脸(形容词)
(二)粤语吴川话中特有的湘语成分
粤语吴川话中特有的湘语成分
长沙 吴川
佻tiau11:下垂、摇摆(动词) 佻tu44:下垂(动词)
晚man41:排行最末的亲属称谓(形容词) 晚man24:祖辈、父辈中排行最末的(形容词)
焮in55:小火焖(饭);小火焙干;把冷了的食物重新热一下(动词) 焮t24:用蒸汽加热(动词)
啜to55:骗(动词) 啜55:唆使、哄骗(动词)
达ta24:没有相遇;错过;耽误;遗漏 达ta35:遗漏
爹tia33:祖父(名词) 爹t55:祖父;伯伯(名词)
惯肆kuan55 s:溺爱、娇惯、纵容 惯肆kwan44 i24:溺爱、娇惯、纵容;习惯
干kan33:口渴;干旱(形容词) 干k55:口渴;干旱;干燥(形容词)
墈ko55:高陡的堤岸(名词) 墈h24:陡坡(名词)
易得i11 t:容易(形容词) 易得ji32 tk5:容易(形容词)
自家ts11 ka:自己(代词) 自家ti44 ka55:自己(代词)
听讲tin33 kan41:乖、听话(形容词) 听讲t44 ka35:乖、听话(形容词)
插田t24 tie13:插秧 插田ta55 tin21:插秧
蔸tie33:棵(量词)[湖南衡山话] 蔸tu55:棵;条(量词)
发风fa24 xo33:刮风 发风fat4 fu55:刮风,打台风
点ti55:点播、种豆(动词) 点tin35:点播、种豆(动词)
走棋tsu41 ti13:下棋 走棋tu35 ki21:下棋
嫁二嫁ka55 11 ka55:改嫁、再嫁 嫁二嫁ka44 l24 ka44:改嫁、再嫁
心子sin33 t:包子、饺子的馅儿(名词) 心55:馅儿(名词)
郎lan13:女婿(名词) 郎l21:女婿(名词)
目古ku41:怒视、怒视(动词) 目古ku44:生气而不说话(动词)
打眼ta41an41:惹人注目,显眼,突出(形容词) 打眼ta35 an44:惹人注目,显眼,突出(形容词)
颈根tin41 kn33:脖子(名词) 颈根k35 k55:颈部(名词)
冲33:山谷(名词) 冲55:山间田(名词)
四、结论
由于粤语吴川话的湘语成分见于文献的很少,因此笔者不敢妄下结论,只是在此谈谈笔者得出的一些推论。
(一)三者都有直接来自上古汉语的词汇。如:
(1)熛:(火花、油、泥浆、水等)飞溅。战国《尸子·贵言》:“熛火始起,易熄也。”
(2)绹:用绳子绑;绳子。在《诗经》中就已出现。如《豳风·七月》:“宵尔索綯。”《尔雅·释言》:“绹,绞也。”刑昺疏:“绹,绳之绞也。”
(3)走:跑。《左传》:“循墙而走。”
(二)粤语吴川话许多词汇直接来源于湘语。如:
(1)易得:容易。长沙话[i11 t]:如咯件事易得,我包你办好(这件事容易)。吴川话[ji32 tk5]:呢件事好易得(这件事很容易办)。
(2)啜:长沙话[to55]:骗,如他被别个啜咖二十块钱(他被别人骗走了二十块钱)。吴川话[55]:唆使、哄骗,如你冇好听佢啜哦(你不要听他唆使,不要受他哄骗哦)。
(3)佻:长沙话[tiau11]:下垂、摇摆,如打佻(物体下垂)、佻脑袋(摇头)。吴川话[tu44]:下垂,如被佻下来嗲(被子垂下来了)。
岭南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远溯至商周时代。当时南北的交往,主要是经过楚地。尽管那时还没有灵渠,但珠江支流桂江和湘江的上游很近,因此从楚到广州并不艰难。[10]后来,正如裴渊《广州记》所载:“六国时,广州属楚。”当时广州是楚国的行政机构驻地,楚人与广州人之间的来往必定更加频繁。秦始皇扫灭六国后,为方便运送征讨岭南所需的军队和物资,于是命史禄开凿河渠以沟通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漓江。它自贯通后,二千多年来就一直是岭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与偏居粤西的吴川相比,广州人与楚人的来往更加密切。据《湛江市志》记载,汉末是广东陆路交通处于开创时期。[11]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战国时广东主要交通运输方式是水运,楚人应该是从水路来鉴江平原的。楚人经湘江,转桂江,再溯西江,驶向西江的南江口,再沿罗定江(即南江)而下,至信宜处,可沿鉴江信宜段直到吴川。[12]楚人至吴川也可以有另一条路线,我们根据《古代广东史地考论》可以推测,楚人可从西江上溯到广西梧州,再从浔江进入郁林(今玉林市)的北流市,后从九洲江的陆川段进入廉江,而吴川就正位于廉江的东南方。[13]从路线来看,楚人来广州是比较顺利的,这有利于保持古湘语的纯粹性。而楚人来吴川是比较困难的,要经过今湖南、广西、广东三个省,湘语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与古壮语、古粤语进行接触、借鉴,那么楚人来到吴川后,他们的古湘语就不太纯粹了。
如此说来,上古时期,广州和楚地的关系远比粤西和楚国的关系密切,而二者方言的相互影响程度也会比粤西深,但是为什么现代吴川话保留的湘语词汇反而会比广州话多呢?原因主要是历史演变。我国沿海都市中,拥有最辽阔腹地的港市,首推广州。珠江流域是它的基本腹地,而且越过南岭上的低平山口,就可以北达长江而至于黄淮流域。加之古代集散于广州的商品多为海外输入和热带地区的珍贵物品,如珠宝香药之类,为王室及各地贵官富豪所喜爱,这些物品便于长途运输,所以广州自昔有“犀、象、珠、玉,走于四方”的说法。[14]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商贸名城,国内外人士活跃其中,受多种语言的影响,因此方言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很多湘方言词汇因而被淘汰。而处于鉴江平原的吴川则不然,它偏于粤西一隅,被廉江、电白山区、南海等包围起来,地理环境较为封闭,语言间的交流、接触不像广州如此频繁,因此湘语来到吴川后就停留在此,以至吴川话中保留着较多的湘语词汇。endprint
(三)粤语吴川话和湘语都留有壮语的痕迹。如下[15]:
(1)馅儿:壮语:im24;湘语:sin33 t ;粤语吴川话:55
(2)点播、点种:壮语:tim35 ;湘语:ti55 ;粤语吴川话:tin35
(3)女婿:壮语:lu33 ki24;湘语:lan13;粤语吴川话:l21
粤语吴川话和湘语中都留有一些壮语的痕迹,而广州话中却很少有。自古以来,岭南地区都是百越族的聚居地。以百越族为主体发展而来的民族主要是壮侗语族各民族,他们的语言有壮语(广西、云南、广东)、侗语(湖南、贵州、广西)等等。[16]据地方志所载,直到宋代,吴川的汉族人口数才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相当[17]。可见吴川汉壮杂居的历史很长。而且秦朝时吴川属象郡(郡治在今广西崇左),吴川与广西较近,二者交往也较为密切。吴川话中自然就留下了壮语痕迹。再者,吴川的地理条件相对封闭,语言的更新换代较为缓慢。因此,虽然吴川结束了杂居的历史,但许多壮语成分依然留在吴川话当中。湖南在原始社会时是三苗、百濮与扬越之地,至今也是多民族杂居之所,存在壮语成分不足为奇,如湘方言的次方言邵阳南路话的形成,不单是汉语本身分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汉语和古越语及其后继者(即壮语)互相融合的结果。[18]可见粤语吴川话与湘语中留存的壮语痕迹较多。而广州古属“南越”之地,自秦始皇岭南设郡开始,大批中原人(士兵、流放的官吏、犯人)移居到此,渐渐地与越人通婚,两族逐渐融合了。[19]由于广州地理位置优越,大约秦汉时期就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陆续不断有汉人南下,中原汉人的语言渐渐地成为了主流,“打败”了该地区的古百越语,于是两个民族彻底融合了。又由于广州开发早、经济发展快,对内、对外交流频繁,语言的发展较快,而且很早地结束了汉壮杂居的历史,于是便更加容易冲刷掉残存的古百越语痕迹。
(四)粤语吴川话中的湘语词多有同义形式
举例如下:
(1)女婿:粤语吴川话:阿郎 55 l21、姑爷ku55j;湘语:郎 lan13
(2)陡坡:粤语吴川话:墈h24、坡po55;湘语:墈ko55
(3)插秧:粤语吴川话:插田ta55 tin21、插秧ta55 j55、登田t55t in21;湘语:t24 tie13
由于粤语吴川话词汇来源复杂,所以同义词多[20],而湘语词则为此提供材料。同义词的出现是出于不同语族间交际的需要,如果是同一种族的人,又何必使用同义词呢?同义词只会成为语言的累赘。这可能透露了一项珍贵的信息:部分楚人南征后就在吴川定居了。在两个甚至多个语族交流的过程中,人们有时需要使用对方语言中的词汇以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长期以往,同义词就产生了,有些同义词源于湘语,有些源于壮语,有些源于吴川话。
这也说明了一点:吴川话是具有“湘语”底层的。李敬忠先生认为“基本词汇”是“表示全人类活动共同的、最基本的概念与情境的词汇”,是语言词汇总库里最稳固的部分,因而也是变化最缓慢的部分。如果一种语言真的是另一种语言的“底层”的话,那么“底层”保留的则主要是“基本词汇”。[21]从表一、表二以及同义形式举例中可以发现,这些词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词汇,也即基本词汇。如果楚人当年只是南征时路过鉴江平原,他们根本不可能留下与生活关联如此密切的词汇,他们的词汇更不可能在两千多年后依然保留在吴川话中,这再一次证明了楚人曾经在吴川地区生活过。
五、结语
本文主要通过历史考据和词汇对比,论述粤语吴川话和湘语的关系。粤语广州话、吴川话和湘语有不少共有的的词语,它们有的直接来源于中原古汉语;部分粤语吴川话词汇直接来源于湘语;粤语吴川话和湘语都留有壮语的痕迹;粤语吴川话和湘语有不少共通的地方。粤语吴川话和湘语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只是提出一些管窥之见,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及本人能力有限,有些地方论述得不够透彻。期待更多的专家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注释:
[1][9]吴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川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2][3][4][20]参见李健:《吴化粤语的多种词汇成分及特征词研究》。
[5][6]王增权:《试论先秦时期雷州与楚国的关系》,岭南文史,1993年,第2期。
[7][8]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0][14]徐俊鸣,郭培忠:《古代广州的对内交通和贸易初探》,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0年,第4期。
[11]湛江市志办:《湛江市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12]欧锷:《林召棠上京》,湛江新闻网,http://www.gdzjdaily.com.cn/news/2007-04/22/content_368083.htm.
[13]颜广文:《古代广东史地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5]罗黎明:《壮汉英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16]王文光,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从越、僚到壮侗语族各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17]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化州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8]黎良军:《邵阳(南路)话中的“那”文化成分——湘语中的壮语底层现象研究系列论文之二》,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19]宋蜀话:《百越》,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1]李敬忠:《粤语中的百越语成分问题》,学术论坛,1991年,第5期。
(陈宇宇 广东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510006)endprint
(三)粤语吴川话和湘语都留有壮语的痕迹。如下[15]:
(1)馅儿:壮语:im24;湘语:sin33 t ;粤语吴川话:55
(2)点播、点种:壮语:tim35 ;湘语:ti55 ;粤语吴川话:tin35
(3)女婿:壮语:lu33 ki24;湘语:lan13;粤语吴川话:l21
粤语吴川话和湘语中都留有一些壮语的痕迹,而广州话中却很少有。自古以来,岭南地区都是百越族的聚居地。以百越族为主体发展而来的民族主要是壮侗语族各民族,他们的语言有壮语(广西、云南、广东)、侗语(湖南、贵州、广西)等等。[16]据地方志所载,直到宋代,吴川的汉族人口数才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相当[17]。可见吴川汉壮杂居的历史很长。而且秦朝时吴川属象郡(郡治在今广西崇左),吴川与广西较近,二者交往也较为密切。吴川话中自然就留下了壮语痕迹。再者,吴川的地理条件相对封闭,语言的更新换代较为缓慢。因此,虽然吴川结束了杂居的历史,但许多壮语成分依然留在吴川话当中。湖南在原始社会时是三苗、百濮与扬越之地,至今也是多民族杂居之所,存在壮语成分不足为奇,如湘方言的次方言邵阳南路话的形成,不单是汉语本身分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汉语和古越语及其后继者(即壮语)互相融合的结果。[18]可见粤语吴川话与湘语中留存的壮语痕迹较多。而广州古属“南越”之地,自秦始皇岭南设郡开始,大批中原人(士兵、流放的官吏、犯人)移居到此,渐渐地与越人通婚,两族逐渐融合了。[19]由于广州地理位置优越,大约秦汉时期就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陆续不断有汉人南下,中原汉人的语言渐渐地成为了主流,“打败”了该地区的古百越语,于是两个民族彻底融合了。又由于广州开发早、经济发展快,对内、对外交流频繁,语言的发展较快,而且很早地结束了汉壮杂居的历史,于是便更加容易冲刷掉残存的古百越语痕迹。
(四)粤语吴川话中的湘语词多有同义形式
举例如下:
(1)女婿:粤语吴川话:阿郎 55 l21、姑爷ku55j;湘语:郎 lan13
(2)陡坡:粤语吴川话:墈h24、坡po55;湘语:墈ko55
(3)插秧:粤语吴川话:插田ta55 tin21、插秧ta55 j55、登田t55t in21;湘语:t24 tie13
由于粤语吴川话词汇来源复杂,所以同义词多[20],而湘语词则为此提供材料。同义词的出现是出于不同语族间交际的需要,如果是同一种族的人,又何必使用同义词呢?同义词只会成为语言的累赘。这可能透露了一项珍贵的信息:部分楚人南征后就在吴川定居了。在两个甚至多个语族交流的过程中,人们有时需要使用对方语言中的词汇以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长期以往,同义词就产生了,有些同义词源于湘语,有些源于壮语,有些源于吴川话。
这也说明了一点:吴川话是具有“湘语”底层的。李敬忠先生认为“基本词汇”是“表示全人类活动共同的、最基本的概念与情境的词汇”,是语言词汇总库里最稳固的部分,因而也是变化最缓慢的部分。如果一种语言真的是另一种语言的“底层”的话,那么“底层”保留的则主要是“基本词汇”。[21]从表一、表二以及同义形式举例中可以发现,这些词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词汇,也即基本词汇。如果楚人当年只是南征时路过鉴江平原,他们根本不可能留下与生活关联如此密切的词汇,他们的词汇更不可能在两千多年后依然保留在吴川话中,这再一次证明了楚人曾经在吴川地区生活过。
五、结语
本文主要通过历史考据和词汇对比,论述粤语吴川话和湘语的关系。粤语广州话、吴川话和湘语有不少共有的的词语,它们有的直接来源于中原古汉语;部分粤语吴川话词汇直接来源于湘语;粤语吴川话和湘语都留有壮语的痕迹;粤语吴川话和湘语有不少共通的地方。粤语吴川话和湘语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只是提出一些管窥之见,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及本人能力有限,有些地方论述得不够透彻。期待更多的专家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注释:
[1][9]吴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川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2][3][4][20]参见李健:《吴化粤语的多种词汇成分及特征词研究》。
[5][6]王增权:《试论先秦时期雷州与楚国的关系》,岭南文史,1993年,第2期。
[7][8]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0][14]徐俊鸣,郭培忠:《古代广州的对内交通和贸易初探》,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0年,第4期。
[11]湛江市志办:《湛江市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12]欧锷:《林召棠上京》,湛江新闻网,http://www.gdzjdaily.com.cn/news/2007-04/22/content_368083.htm.
[13]颜广文:《古代广东史地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5]罗黎明:《壮汉英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16]王文光,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从越、僚到壮侗语族各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17]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化州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8]黎良军:《邵阳(南路)话中的“那”文化成分——湘语中的壮语底层现象研究系列论文之二》,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19]宋蜀话:《百越》,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1]李敬忠:《粤语中的百越语成分问题》,学术论坛,1991年,第5期。
(陈宇宇 广东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510006)endprint
(三)粤语吴川话和湘语都留有壮语的痕迹。如下[15]:
(1)馅儿:壮语:im24;湘语:sin33 t ;粤语吴川话:55
(2)点播、点种:壮语:tim35 ;湘语:ti55 ;粤语吴川话:tin35
(3)女婿:壮语:lu33 ki24;湘语:lan13;粤语吴川话:l21
粤语吴川话和湘语中都留有一些壮语的痕迹,而广州话中却很少有。自古以来,岭南地区都是百越族的聚居地。以百越族为主体发展而来的民族主要是壮侗语族各民族,他们的语言有壮语(广西、云南、广东)、侗语(湖南、贵州、广西)等等。[16]据地方志所载,直到宋代,吴川的汉族人口数才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相当[17]。可见吴川汉壮杂居的历史很长。而且秦朝时吴川属象郡(郡治在今广西崇左),吴川与广西较近,二者交往也较为密切。吴川话中自然就留下了壮语痕迹。再者,吴川的地理条件相对封闭,语言的更新换代较为缓慢。因此,虽然吴川结束了杂居的历史,但许多壮语成分依然留在吴川话当中。湖南在原始社会时是三苗、百濮与扬越之地,至今也是多民族杂居之所,存在壮语成分不足为奇,如湘方言的次方言邵阳南路话的形成,不单是汉语本身分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汉语和古越语及其后继者(即壮语)互相融合的结果。[18]可见粤语吴川话与湘语中留存的壮语痕迹较多。而广州古属“南越”之地,自秦始皇岭南设郡开始,大批中原人(士兵、流放的官吏、犯人)移居到此,渐渐地与越人通婚,两族逐渐融合了。[19]由于广州地理位置优越,大约秦汉时期就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陆续不断有汉人南下,中原汉人的语言渐渐地成为了主流,“打败”了该地区的古百越语,于是两个民族彻底融合了。又由于广州开发早、经济发展快,对内、对外交流频繁,语言的发展较快,而且很早地结束了汉壮杂居的历史,于是便更加容易冲刷掉残存的古百越语痕迹。
(四)粤语吴川话中的湘语词多有同义形式
举例如下:
(1)女婿:粤语吴川话:阿郎 55 l21、姑爷ku55j;湘语:郎 lan13
(2)陡坡:粤语吴川话:墈h24、坡po55;湘语:墈ko55
(3)插秧:粤语吴川话:插田ta55 tin21、插秧ta55 j55、登田t55t in21;湘语:t24 tie13
由于粤语吴川话词汇来源复杂,所以同义词多[20],而湘语词则为此提供材料。同义词的出现是出于不同语族间交际的需要,如果是同一种族的人,又何必使用同义词呢?同义词只会成为语言的累赘。这可能透露了一项珍贵的信息:部分楚人南征后就在吴川定居了。在两个甚至多个语族交流的过程中,人们有时需要使用对方语言中的词汇以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长期以往,同义词就产生了,有些同义词源于湘语,有些源于壮语,有些源于吴川话。
这也说明了一点:吴川话是具有“湘语”底层的。李敬忠先生认为“基本词汇”是“表示全人类活动共同的、最基本的概念与情境的词汇”,是语言词汇总库里最稳固的部分,因而也是变化最缓慢的部分。如果一种语言真的是另一种语言的“底层”的话,那么“底层”保留的则主要是“基本词汇”。[21]从表一、表二以及同义形式举例中可以发现,这些词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词汇,也即基本词汇。如果楚人当年只是南征时路过鉴江平原,他们根本不可能留下与生活关联如此密切的词汇,他们的词汇更不可能在两千多年后依然保留在吴川话中,这再一次证明了楚人曾经在吴川地区生活过。
五、结语
本文主要通过历史考据和词汇对比,论述粤语吴川话和湘语的关系。粤语广州话、吴川话和湘语有不少共有的的词语,它们有的直接来源于中原古汉语;部分粤语吴川话词汇直接来源于湘语;粤语吴川话和湘语都留有壮语的痕迹;粤语吴川话和湘语有不少共通的地方。粤语吴川话和湘语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只是提出一些管窥之见,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及本人能力有限,有些地方论述得不够透彻。期待更多的专家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注释:
[1][9]吴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川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2][3][4][20]参见李健:《吴化粤语的多种词汇成分及特征词研究》。
[5][6]王增权:《试论先秦时期雷州与楚国的关系》,岭南文史,1993年,第2期。
[7][8]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0][14]徐俊鸣,郭培忠:《古代广州的对内交通和贸易初探》,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0年,第4期。
[11]湛江市志办:《湛江市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12]欧锷:《林召棠上京》,湛江新闻网,http://www.gdzjdaily.com.cn/news/2007-04/22/content_368083.htm.
[13]颜广文:《古代广东史地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5]罗黎明:《壮汉英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16]王文光,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从越、僚到壮侗语族各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17]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化州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8]黎良军:《邵阳(南路)话中的“那”文化成分——湘语中的壮语底层现象研究系列论文之二》,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19]宋蜀话:《百越》,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1]李敬忠:《粤语中的百越语成分问题》,学术论坛,1991年,第5期。
(陈宇宇 广东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51000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