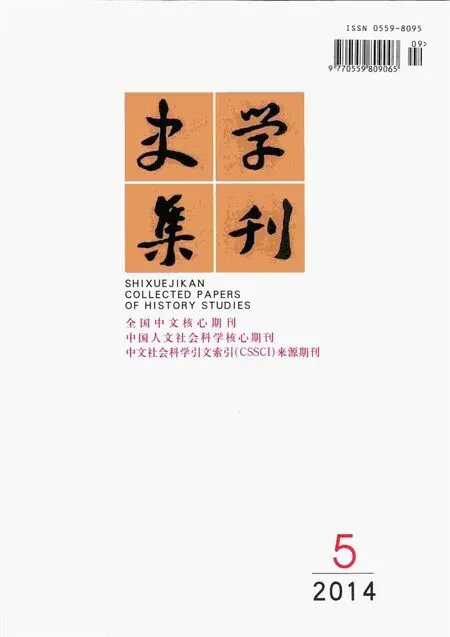西方国际体系扩张中非西方地位与作用的重新审视
2014-04-09王文奇王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王文奇王(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西方与非西方,尽管我们难以划定确切的地域与国家归属,但殖民时代以来,大体上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和以亚非拉国家为代表的非西方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一直在持续。国际关系史作为一门以“国家 (即主权)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演变为主要研究对象”①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的学科,必然要思考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在欧洲国际体系的扩展中形成了怎样的互动。实际上对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互动的关注程度与阐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史研究与编纂的角度和路径。
以国际体系变迁视角进行的国际关系史编纂,往往将叙事的起点放置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或者更早些的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和葡萄牙、西班牙缔结《托尔德西拉斯条约》。之后国际关系的演进历史成为欧洲大陆 (后来加上美国)强国之间的纵横捭阖,非西方国家遭受了极大的忽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研判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时,长久以来形成了强势的路径依赖——西方中心论,并衍生出了若干种对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二分法式判定,如文明—野蛮、冲击—回应、中心—边缘等。
造成西方中心论在国际关系史编纂中的长期固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西方中心论是客观历史事实的一种反映。不可否认,构成现代国际关系的诸多要素,譬如主权国家的形成,常驻使节的派驻、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等最初都产生于西方国家。伴随着欧美向全球范围的扩张,其他国家与地区或积极或消极地接受了西方国家设定的国际体系,正如亚当·沃森所说,“欧洲人使世界连结为一个整体,通过扩展欧洲体系为今天的全球体系奠定了基础并继续主导规则的制定”。②Adam Watso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London:Routledge,1992,p.265.另一方面,现有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众多学术概念、研究范式,都是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借鉴而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恰如汤林森所说“我们所关心的话语 (discourse),深深根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我们无从逃遁”。③[英]汤林森著,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因为这种话语体系,比如关注国家互动中的优势一方,强调国际规则的设定者,将权力博弈中的强者看成是国际关系演进的推动者等,也是造成我们忽视非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1500—1900年间的国际关系史,基本上成为西方国家内部的权力游戏,非西方国家只是变成西方国家扩展其国际体系的注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非西方国家在卷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时的转变、挣扎或固守。
然而,正如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站在当代的时间节点上进行国际关系史研究与编纂,就要求我们有对现实的关怀,通过追寻历史发现现实问题的历史症结,而不是简单地因循研究定式展开历史叙述。当代国际关系正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标志着国际体系处于转型期,当下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因素,不是来源于西方国家,而是非西方国家。
一方面,“权力转移”是目前学界讨论颇多的话题。伴随着美欧日经济比重的相对下降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比重的相对提升,“毫无疑惑地,在国际关系中,一些专家开始将权力转移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及其同侪身上”。④Steven Chan,“Is there a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The Different Faces of National Power,”Asian Survey,Vol.54,No.5(Sep./Oct.2005),p.688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像中国这样的未来国际格局塑造者,他们希望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曾经无法进入全球关注视野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走向的重大问题,如内战、难民、地区冲突等,而这些事件正集中爆发在非西方世界。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难题集中在非西方世界?而要回答上述问题,都要重新回归历史,去探寻在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长期互动中,非西方国家存在着哪些转变、挣扎或固守。因而,在国际关系史编纂中,有必要重新发现非西方,重新审视西方国际体系扩张中非西方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实力对比问题。如果我们均衡地看待1500—1900年间全球范围内国际关系的历史演进就会发现,非西方的一些国家与地区在与西方的互动中曾长期处于优势地位,那种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代表了国际体系”,①[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从而陷入“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叙事显然是存在偏颇的。在具体到个案分析时,由费正清奠定的冲击—回应模式,长期成为学者们分析西方与非西方互动关系时不断因循的研究路径。非西方无论是主动积极地融入西方国际体系,还是痛苦地反抗与挣扎,都可以在冲击—回应这一大的模式之下进行细分,差别只在于冲击的方式方法与回应的方式方法之间的排列组合。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模式。但是这一模式选取的时间节点多是放置在西方国家相对于非西方国家具有绝对优势之时。而将历史的视野放宽,看到非西方国家与地区在与西方互动中的优势地位后,就会发现,西方国家在1500年后的很长时期内是要融入非西方国家构筑的区域国际体系,这一点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中表现尤为明显。从实力对比来看,有学者指出,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直到18世纪中期中国的综合国力依然居于世界首位。“当时的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是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国 (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②[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在与中国的互动中,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地位。如在17世纪,诸多欧洲使团到访中国,但是“欧洲人从未挑战过他们所碰撞的中华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世界观、合法性以及主导性。他们接受、默认或者适应了中华世界秩序的规范、规则以及机制,用以指导欧洲与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③[英]张勇进著,颜震译:《中欧文明碰撞的另一页:1514-1793》,《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47页。
除了中华帝国的庞大影响力在与西方国家的互动中不可忽视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也正是在欧洲国家开启海外殖民扩张时,走向了帝国发展的辉煌时期。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中,奥斯曼帝国一度成为欧洲列强惧怕和争相拉拢的对象;在国家的影响力上,正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使非洲出现了一系列规模较大的城市,“伊斯兰日益强大的影响,包括不断拓展的商业联系及其他方面,为塑造以城市为中心的良性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种乃至几种模式”。④Bill Freund,The African City:A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37.
其次,非西方的衰落,是因为自身的问题还是在与非西方互动中受到致命冲击导致的结果?我们经常先验式地认为是西方国家的冲击导致了非西方国家的衰落和前现代国际体系的土崩瓦解,因而作为除旧部新的西方被置于国际关系的核心位置上。但很多情况下,非西方不是在互动中因为权力对比的失衡而失去了自身的优势地位,而是自身问题的不断发酵导致了衰落。如印度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内部的分崩离析给了殖民者可乘之机。进入18世纪后,大封建主们拉帮结派,形成了几股力量争夺对皇帝的控制权,不断废立皇帝。“从1707年到1837年,换了14个。1719年就四易帝位”。⑤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与中央的混乱局面并行的,是地方脱离中央管辖的独立王国越来越多。一些原本就与帝国只有松散联系的地区持续坐大,如马拉塔联盟、迈索尔等。到18世纪50年代,独立与半独立的王国已经成为瓦解帝国的核心力量。再如奥斯曼土耳其,在呈现出衰落迹象的时候,也曾出现励精图治的改革者,但是改革者自身的改革理念导致了国家难以重振雄风。“在17~18世纪的关键时期都出现过改革家和改革行动。但是,这一时期最明智和最有洞察力的奥斯曼改革家都坚持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奥斯曼制度远优越于异教徒所能建立起来的一切制度,这一态度只有在16世纪最初形成时才有充足的理由”。⑥[美]斯坦福·肖著,徐序雅,张忠祥译:《奥斯曼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再次,非西方与西方的互动,对于国际体系的演进有着怎样的意义?以国际体系视角编纂国际关系史,必然会重点关注体系的革新与转换,因此我们常常重点阐释那些能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意义的事件,如国际战争、战后大国的利益分割、大国竞争的激化直至下一次战争的爆发。无疑,无论从1500年算起还是从1648年算起,西方都是国际战争与战后利益分割的主导者,非西方相对之下处于劣势地位。但问题是,只有促成体系产生变革的事件才具有重要意义吗?不同的国际体系存在的时间长短同样值得关注。而要考虑到体系维系的时间问题,就不只是西方国家内部权力博弈的缓和或激化能够解释清楚的,非西方国家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于西方国家扩张的接纳、反抗或两者兼而有之等不同形态,对于既有国际体系的加速变革或延缓变革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换言之,在既往的国际关系史中,非西方国家尽管没有成为国际体系转变的塑造者,但是它们却对于体系变迁的时间维度产生了重要意义。而在今天,在经过几百年西方与非西方互动后,非西方国家保留下来的与西方国家格格不入的世界秩序理念、社会结构等,正成为当今国际体系转型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甚至不排除非西方国家塑造一种新的国际体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