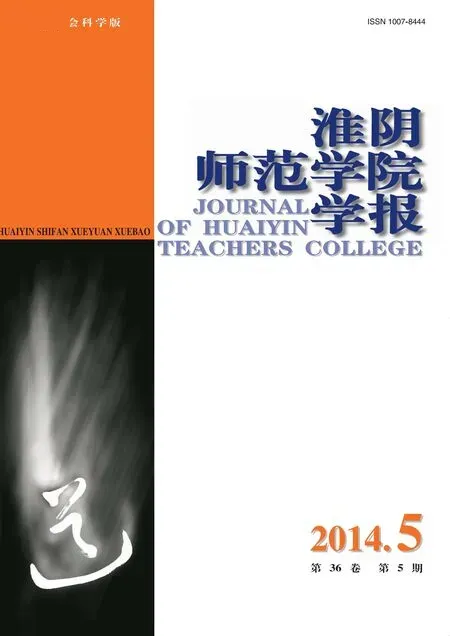史学史视野下的中外史学关系研究
2014-04-09王秋月
王秋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一、外国史学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是在社会变动和西方史学思想的冲击下完成的,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传入中国,其中进化论、地理环境论和社会学方法等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①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和德国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中的诸多论述影响了日本的浮田和民与坪井九马三等学者。20世纪20年代以前,西方史学理论主要通过日本传入国内,梁启超史学主张实是承袭了日本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等书。相关研究有胡逢祥《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等。在1901年和1902年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倡导“史界革命”,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学的崛起。中国历史学学科的建立是近代引入西方学术体系的结果,“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的基本范式、分析工具、研究方法乃至写作形式,无不受到了域外思想学术的支配性影响”[1]。同样,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也是在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和观念大量输入的过程中兴起的。1926年至1927年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首先公开提出了“史学史”这一名称,倡议对于中国史书“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并将中国史学史作为学术思想史的一部分,规划了史学史的具体做法:“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下列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2]185这对史学史学科建立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30—40年代撰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例如,194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魏应麟《中国史学史》和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无一不是在此论的启迪下完成的。
“我们近百年的史学受到外国不少的影响,不探本溯源,不易进行深入的分析。”[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从多角度对西方史学如何传入中国、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成果显著。例如,胡逢祥与张文建合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1995年版),张广智《20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20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于沛《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张越《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从多角度多方面梳理了西方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随着外国史著的不断被译介,国外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广泛传播,特别在某些西方史学家对中国史学采取藐视的态度,不认为欧洲以外存在博大精深的史学的环境下,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强烈反思,当今的中国史学处于何种地位,中西史学差别究竟在何处,中外史学平行比较研究兴起,成果丰硕。
白寿彝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强调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中外史学应有共同的规律,也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特点。不研究外国史学,就没有一个综合比较研究,也就不能认识各国史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我国史学的民族特点。”[3]刘家和认为在今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应加强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只要有了比较研究的同中见异,才能够完成对中外史学的一次完整的认识过程,这样的认识过程需要是不断深入进行的,而全部这样的认识过程都必须也必然是在比较的研究中实现的”[4]。
在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中,杜维运所著《清代史学与史家》(中华书局1988年版)、《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等,创立了系统的中西史学比较理论,可谓筚路蓝缕,为中西比较史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王晴佳《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社会科学》1984年第8期),胡逢祥《中西史学源起比较论》(《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试论中西古代史学演变的不同途径与特点》(《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乔治忠《古代中国官方修史视角下的中外史学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与中外史学比较》(《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等,众多学者从多方面继续探索,丰富了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
二、中国史学对外影响
“任何事物都是千差万别的,各国史学发展的差异性也必然存在;任何文化也是在交流中发展的,史学当居其中。于是就有一个影响、被影响,传播和接受的问题。这都使史学的比较研究成为必要。而比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史学发展的异同,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探讨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揭示当代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据此,朱政惠认为“比较史学”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三方面:“其一,不同国家和地区史学发展状况的平行比较研究;其二,一国、一地区史学对它国、它地区史学影响和交流之比较;其三,一国、一地区史学影响它国、它地区史学中介因素的探讨。”[5]中国古代传统史学,无论是修史制度还是史书的编纂方法都对周边国家产生过深远影响。例如,《十八史略》①参见乔治忠《〈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是一部在中国已经不大出名的史籍,却在日本影响深远。以上所述的研究成果,都是聚焦在西方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和中西史学异同的平行比较,但外国史学特别是东亚国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吸收同样不可忽视。朱云影的《中国史学对日韩越的影响》一书,最早就中国史学对日本、韩国和越南史学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索。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单从中国史方面看,似乎还有不足,如果从环绕中国的邻国史来看,可能显得更突出。”[6]1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亚洲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对流布于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中国古籍的研究,例如严绍璗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的中国典籍流播日本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从2005年始,由张伯伟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年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自2008年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②《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是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项目,写入《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之中。等。这些成果引起了国内学者对中日、中韩史学交流与影响研究的极大兴趣。
乔治忠提出了对中、日、韩等国史学“进行同源分流之东亚史学的比较”,主张在东亚文化的视野内考察中国史学史的新课题。“中国史学史的古代部分,应当讲述中国传统史学对朝鲜半岛、日本等亚洲邻国的影响。朝鲜、日本古代的史学,其实是现成地接受中国史学的观念和方法,然后发展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凡中国通史著述,皆包含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所以中国史学史著述亦当将对外影响作为自身学科体系之内的必备内容。”[7]孙卫国《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流》(《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4期),整体考察了中国史书在东亚的流布和古代日韩越对中国史馆制度及史书体裁的模仿情况。
盛邦和是近年来较早涉及中日史学交流领域的学者,《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化》和《日本的中国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5期)两文就中国对日本史学的影响做了初期探讨。乔治忠《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和《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及其近代转型的比较》(《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论述了古代日本接受中国史学传统后,如何经过演化,形成自己特色并发挥了重大的社会作用。姜胜利《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5期)考察了当代日本对中国明史的研究动态。
2000年以来,在中韩史学交流的研究领域中,孙卫国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明实录〉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文献》2002年第1期)、《〈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求是学刊》2005年第5期)、《〈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对朝鲜之影响》(《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史记〉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6期)等,探讨了中国官修和私修史书在朝鲜半岛的流传及影响。《朝鲜燕行士人与清朝儒生——以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陆飞交往为中心》、《清乾嘉时期中朝士人之学术交谊——以朝鲜〈韩客巾衍集〉之西传清朝及其关涉之士人交往为中心》[8]、《纪晓岚与洪良浩初晤略考》(《学术研究》2013年第4期)等,以中朝学人间的交谊为视角论述两国史学间的互动,将研讨的问题大为扩展和具体化。崔岩《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与中华传统史学》(《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展现了14、15世纪朝鲜史学与中华传统史学的关联。虽然以上专论中日、中朝史学交流与影响的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尚待开拓。
多年来,除了流布于东亚各国的中国古籍,朝鲜和日本还藏有大量记载中国的历史文献。这些史料是朝鲜和日本对于当时中国的记忆和评论。对这些史料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跳出中国,同时又反观中国,为中国史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葛兆光把以往中国史学的发展分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时代”“一面镜子的时代”“在多面镜中认识自我的时代”三个阶段,并进一步提出“从周边看中国”的构想,拓展了文史研究的新视野,为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新方法和新典范。他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对比,只能在大尺度上粗略地看到自我特征,而那些看似差异很小,甚至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的不同国度的比较,才能真正认识细部的差异,才能确认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9]。仅仅依靠中国的资料来研究中国的史学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当前的史学研究也必须通过“他者”来了解“自我”,看清自己的位置。针对目前选取“他者”进行比较研究的状况,葛兆光指出:“过去中国的自我认识,常常太倚重西方这个‘他者’,却不大习惯用似乎‘本是同根生’的朝鲜、日本、越南、蒙古以及印度这样一些周边文化来作为参照。也许很奇怪,当我们谈论‘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突显彼此‘异’,可是,当我们在谈论‘中国’和‘东方’的时候,却总是在强调我们文化的‘同’。”[10]
三、“海外中国学”的研究
国外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向来十分关注,特别是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对中国的史学研究动态就更重视。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前苏联(俄国)、日本,都从未将研究的视线从中国史学上移开。许多著名的外国学者,例如英国的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法国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美国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和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1916—1999)等,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和影响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为此,“我们还应该注意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3]。华东师范大学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提出了很多与此有关的国际学术前沿问题。朱政惠《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史林》2006年第4期)从宏观上考察了美、加、英、法、韩、日等一些国家对中国史学的研究状况,对当前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作了系统梳理。《近30年来中国学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收获和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又详细全面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国外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成为一门积累雄厚和学术性相当成熟的学科,而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通过对海外中国学的批评和研究,了解他们与中国本土研究者在方法和思路上的差异,可以明确中国文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自觉立场。”[9]海外中国学同样给我们的史学研究以启示:中国史学发展已无法避免海外史学的影响,必须融入世界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仅以中国的史料解释中国显然已不够,有必要借助“他者”来认清“自我”,避免研究领域和研究资料的偏狭。
四、研究中的问题
在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实践中,要做到既能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固执偏见,又能跳出“以西方来透视中国”的单一模式,也并非易事。史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改进,固然代表学术的进步。但如何运用新史料和新理论,又牵涉到如何理解和诠释中国史学的大问题。由此,在中外比较研究中,还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不仅要继续翻译和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还要将中国的优秀论著输出到国外,让世界听到中国史学界的声音,才能形成真正的交流。这就对当今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还要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由于各国语境的不同,有时会造成术语转译的误差,所以在面对中、外史学论著的翻译和术语引用上要力求准确。
但在目前的研究中,存在对某些外国理论术语随意比附和滥用的现象。比如,法国孔德(August 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与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历史客观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实证主义”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认为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定律,其思维方式对现代西方历史结构功能主义的模式归纳方法影响深远。而“历史客观主义”则认为客观上存在真实的历史,主张历史研究者要“排除自我”,“让史料说话”。实际上兰克是反对孔德的“实证主义”的。但是近来国内不少学者都将“实证主义”与“考据”“考证”的语意等同,甚至曲解为“实证主义”就是兰克的史学主张。这种现象亟待关注和予以纠正。
其次,中国的史学研究对外国的学者同样是一个挑战,要想全面把握中国古代、近现代的史料,真正领略中国史学的意蕴,除了文化背景和语言功底外还存在诸多困难,不是轻易能做到的。这就使他们容易在史料的理解和诠释上产生误解,甚至是牵强附会。所以,对国外学者的成果我们要谨慎地辨别。例如,格朗特·哈代(Grant Hardy)在《历史和理论》发表的《司马迁的多重叙述:中国古代史学能否对现代西方史学有所贡献》①Grant Hardy,“Can 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 Contribute to Modern Western Theory?The Multiple Narratives of Ssu-ma Ch'ien”,History and Theory,vol.33,no.1(1994):26-31.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1 辑,大象出版社2003 年版。,将司马迁的观点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等现代西方史学家的观点进行比较,认为司马迁对精确叙事强烈关注的历史方法论,恰恰是西方史学家为摆脱传统编纂模式所苦苦思索的问题。这一案例先不论恰当与否,但可以启发我们利用新观点重新认识和解读中国史学的传统价值,是可以学习吸收的。然而,美国史学家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C.Rogers)《苻坚载记:正史的一个案例》[11],运用后现代的分析方法,把“淝水之战”说成是初唐史家的杜撰,并非前秦的真实历史。孙卫国《淝水之战:初唐史家们的虚构?——对迈克尔·罗杰斯用后现代方法解构中国官修正史个案的解构》(《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对其进行了质疑和批评,指出其论史方法虽新颖,但结论却是荒诞不经的。面对国外史学的冲击,我们要有更高的洞察和辨别力,对外国的理论成果要在批判中加以吸收。而外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从选题上看,往往又与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动密切相关,比如当前的“新清史”“区域史”“同心圆理论”等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更应理性地分析其史学研究背后的真正意图。
最后,从史学传播、史学接受或史学影响的角度考察问题,对史学传播的媒介进行研究。朱政惠早在1986年就提出“从接受角度研究史学”②朱政惠《从接受角度研究史学》,《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6期。提出对史学的研究三个部分的问题:一是对史学主体的研究,即对史学著作、史学方法、史学理论、史学思想的研究;二是对史学的接受者或读者的研究,即对史学著作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研究,是对他人或后人接受此前史学著作的史学思想、历史观点、研究方法及其编撰思想后的史学诸种情况及其影响程度的研究;三是对史学中介的研究,探讨史学著作在传播过程中被介入的因素及其影响。的建议。他认为,如果只注意史家的著述过程,而忽视读者和社会的接受过程,仅是完成了一半的研究,这种不完满的研究“当然会影响史学发展全过程的发展特点及其规律的探讨,从而影响到对现实史学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12]。在新文化史思潮的影响下,书籍史是当前研究的热门,探讨的问题多与史学著作的刻写、印刷、审查、发行有关,是史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目前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大都重视史学著作输出影响的一面,很少涉及读者对史著的接受、传播及由此产生的进一步影响①目前国内学者除翻译外国学者的相关专著和介绍研究动态外,有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韩琦和[意]米盖拉主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王勇主编《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耿相新《中国简帛书籍史》(三联书店2011年版)、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2007年第5期)等。。因此,中国史学研究应在史学媒介的研究上多加关照,将其纳入研究视野,借助书籍史的研究成果来讨论史学的社会价值。作为史学传播媒介的“人”是最关键的因素,对于中外学者间的交谊、史学群体、史学机构等的考察也应引起重视。从学者交往的角度考察史学的传播,就要重视古今中外学者的文集、日记、书信、档案等资料的研究,特别是对国外保存的相关文献进行广泛搜集。
“要深入认识一个事物,必须与其他相关的事物进行比较,所以要想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就有必要进行中外历史的比较,这是史学界早已形成的共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只有将中国传统史学与外国史学发展的异同点予以比较,才能认清中国史学的特点,才能领会各国史学的共性,才能真正找到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13]17在对中外优秀史学遗产的比较研究中,扩大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建立新的研究思路和历史解释体系,开创新的研究领域,是当前史学发展的趋势所在。
中国史学史学科建立至今,在中外史学交流和比较研究中,经历了从学习西方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方法,到探索中国史学的对外影响,再到重视外国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和“从周边看中国”构想的提出,突破了以往“自我诠释”和借鉴“西方透视”的思维局限,开拓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涉外交流还是薄弱的,对中国史学的海外传播及其接收情况的研究是不够的,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主要观点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这都不利于我们对民族史学的全面认识和评估”[14]。所以,我们不仅要继续翻译和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还要将中国的优秀论著输出到国外;对国外学者的成果我们要谨慎辨别、理性分析,不能跟风盲从;对史学传播媒介的研究也应加以重视。新领域的开拓则更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史学发展动态,及时总结和反思当前的研究成果,完善史学评价体系,通过学术梳理发现问题所在。
[1] 李剑鸣.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J].南开学报,2003(2).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N].人民日报,1964-02-29.
[4] 张越,何佳岭.史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比较史学——访刘家和教授[J].山东社会科学,2007(5).
[5] 朱政惠.关于中韩史学比较研究的若干问题[J].韩国研究论丛,1995(1).
[6] 朱云影.自序[M]//中国史学对日韩越的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 乔治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J].史学月刊,2009(7).
[8] 孙卫国.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兼论两国学术交流与海外汉学[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9] 葛兆光.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J].复旦学报,2007(2).
[10] 葛兆光.揽镜自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J].复旦学报,2008(2).
[11] Michael C.Rogers.The Chronicle of Fu Chien:a Case of Exemplar History[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12] 朱政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思考[J].历史教学问题,2011(2).
[13] 乔治忠.中国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4] 朱政惠,刘莉.柳暗花明又一村——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的对话[J].史学月刊,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