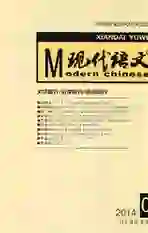《孟子》论辩艺术之微探
2014-04-09陈晶晶
摘 要:《孟子》高超的论辩艺术体现在:善于设譬引喻,运用类比推理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擅长设置“陷阱”,引君入瓮;字斟句酌,明确其含义,针对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当遇见对方提出两难问题时,先提出自己的观点,再转变对方的观点,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先提出问题使对方承认,然后揭示该问题所蕴涵的结论,使对方不能不接受;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法论辩。
关键词:《孟子》 论辩艺术 设譬引喻 设置“陷阱” 两难相诘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是著名思想家、散文家,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一位大师。他授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以继承孔子之业,宣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后世多将他与孔子并称“孔孟”。孟子早年曾游掌各国诸侯,其才学受到各国诸侯尊礼,但其学说终不见用,原因是在兼并战争激烈的战国时代,诸侯崇尚“攻伐”,而孟子从“性善论”出发,主张行“王道”,施“仁政”,与时代潮流相悖。于是“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 。
《孟子》一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孟子》基本上为对话体。它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孟轲游说各国诸侯王以及其他一些学人辩难各种问题的经过和言论。其次,《孟子》善于论辩。他为了维护儒家的思想主张和伦理道德,对杨朱、墨翟的学说和其它违反儒家思想观念的学说进行了论辩。而孟子对“好辩”则从来自认不讳,《孟子》一书虽然并非全由孟子自著,但长于辩论,富于辞采,全书皆然,像是经过统一整理的。[2]在《孟子·滕文公篇》中,孟子的学生公都子问他:“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一语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在那诸子争鸣、纵横捭阖的战国时代,人民生活惨苦,“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现象触目皆是。各派学术思想兴起,相互批评,相互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孟子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宣传他的“仁政”思想,为天下百姓而辩,为消除质疑而辩,为博取正确的观念而辩。首先,孟子的文章文才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胜。其次是“知言”。孟子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这里所说的是一种知人之言而知人之情的体会,这种修养,用之于批评固然重要,用之于创作也同样重要。孟子所讲的养气和知言,属于内在的修养。他的文章,总是给我们一种波澜壮阔、辞锋犀利的美感。[3]如《梁惠王》的言仁义,《滕文公》的辟杨墨、辟许行,《告子》的辩性善,《离娄》的法先王,都是气势纵横、文才华赡的文章。郭沫若在他的《十批判书》中写道:“孟子是以好辩而受非难的人。他不断地和人辩,和宋坑辩,和墨者辩,和自己的门徒辩,辩得都很巧妙,足见他对辩术很有研究。”[4]郭沫若在这里所说的辩术,就是指孟子的论辩艺术。孟子熟练地运用各种论辩手段,成功地达到了他的论辩目的。其论辩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孟子在论辩过程中,善于设譬引喻
首先,孟子擅长设譬引喻。战国时期的人们长于形象思维,在说明复杂事理时,常用譬喻使抽象的概念形象化,让读者心领神会。汉代第一个《孟子》研究家赵歧在《孟子题词》里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5]《孟子》全书二百六十一章中,就有九十三章总共使用了一百五十九种譬喻。[6]这不但使精简的文章更富有形象性,而且起到了加强论辩气势和说理力量的作用。譬如在《寡人之于国也章》中,孟子为了宣扬“仁政”来见梁惠王,而梁惠王却是一个崇尚武力、不谙“仁政”之辈。故一见面,梁惠王就向孟子提出了自己施行“移民”“移粟”等措施,而结果却“民不加多”,这种疑问实际上是对“仁政”提出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孟子没有直接指出梁惠王所采取的“移粟”“移民”措施不是民众归往的根本方法,而是用了“以五十步笑百步”作比喻,并要梁惠王表态。这个比喻非常浅近,朱熹曾在《孟子集注》中注解说:“言此以譬邻国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养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7]所以,梁惠王爽快地回答:“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这正好落进了孟子所设置的陷阱,故孟子说:“王知如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是因为“移粟”“移民”等临时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和邻国的不“移”也强不了多少,正如五十步之于一百步,其本质都是一样的,故就不要指望人民归附了。这个比喻虽然浅近但含义却很深刻。所以,梁惠王对孟子“仁政”之说只得洗耳恭听。其它如“挟泰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缘木求鱼”等设譬引喻手法在孟子散文中随处可见。
二、在论辩过程中,孟子善于设置“陷阱”,“引君入瓮”
孟子在论辩中,善于抓住对方的心理活动和思想矛盾,从反面、侧面顺着对方的意思引申,让对方不自觉地进入预先设置的圈套,在水到渠成的情况下,才把自己的主张和盘托出。比如《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章》最能体现孟子的这种论辩艺术。这是孟子和齐宣王关于“王道”的一次重要谈话。谈话伊始,齐宣王向孟子请教“齐桓晋文之事”,孟子以一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臣未之闻也”,撇开齐宣王所问的齐桓晋文图霸之事,而是紧紧抓住齐宣王希冀“称王”的心理,提出了实行“王道”的话题。但齐宣王向往的“霸道”正好和孟子的“王道”相悖,要解决这一矛盾,使齐宣王接受自己“保民而王”的主张,孟子故意把谈话放纵开去,他先迎合对方的心理指出“大王可以保民而王”,并把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事例作为证据,指出“以羊易牛”这种“仁术”是“保民而王”的基础,经孟子一说,宣王高兴地说:“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孟子又紧紧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深入阐发,连续用了“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足舆薪”和“挟泰山以超北海”以及“为长者折枝”等一连串比喻,说明“王之不王”是“不为”而非“不能”,指出了齐宣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百姓”的弊端。接下去,孟子又对“兴甲兵”之弊与“保民而王”之利作对比,使宣王原有的效法“齐桓晋文之事”的想法进一步动摇。此时,他又紧紧抓住了齐宣王的所谓“大欲”对实行王道是“缘木求鱼”,又用邹人和楚人战的结果设喻,说明了“以力求霸”的“大欲”必定失败。论辩至此,齐宣王终于无路可走,无路可退,说“吾惛,不能进於是,愿夫子明以教我”,表明要接受孟子的“王道”主张。至此,孟子才水到渠成地从正面阐述了实行王道的种种措施和办法,达到了向对方推销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全文就是在这曲折多变的论辩过程中,阐述了孟子的基本思想——“保民而王”。
三、通过给关键概念以准确的定义,明确其内涵,从根本上驳倒敌论
孟子的基本思想虽属儒家,他也自命是孔子学派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观点却要比孔子激烈得多,性格也刚烈得多。孟子对于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肆意攻伐,对于“民之憔悴于虐政”的现实极为愤慨,对于诸侯的残暴统治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激烈的抨击。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孟子则语含锋芒,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而对于那些暴虐之君,他甚至认为可以杀掉。比如《梁惠王章句下》中,按照儒家“君臣有义”的理论,武王杀纣实属大逆不道,但孟子对此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者谓之一夫,闻诛杀一夫纣矣,未闻杀君也。”他首先确定“贼”和“残”的含义,然后确定“残贼之人”的含义,最后才得出武王诛杀独夫殷纣、未闻以臣弑君的结论。要断定殷纣是不是独夫,就要断定他是不是残贼之人;要断定他是不是残贼之人,就要断定他是不是“贼仁”“贼义”之人。殷纣是“贼仁”“贼义”之人,所以他是残贼之人,而残贼之人就是一夫或者是独夫。他认为像纣这样残害人民、破坏仁义的暴君是可以诛杀的,他不承认这样的人是君,而称之为“独夫”“民贼”;诛杀独夫民贼,是合理的正义的行动。只是杀了独夫民贼,算不上杀什么国君,是正义之举,无罪可言。其言辞之激烈,见解之新异,不唯在诸子中少见,而孟子对齐宣王这番答话,不仅言简意赅、逻辑严密,而且表达了他“民贵君轻”的思想,这也是孟子思想体系中的精华。
四、面对两难问题时,先提出自己的观点,再转变对方的观点,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孟子的各种行为经常受到质疑,他也经常替自己辩护。与孟子论辩的对手,有不少是当时的名士,如告子、淳于髡等,及其弟子陈臻、万章等,他们常提一些尖锐的二难问题。对于这些提问,孟子从不简单、抽象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对辩题做具体分析,寻找突破口,破斥敌论。比如在《滕文公下》中,彭更曾经指责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彭更更是认为:“士无事而食,不可也。”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说:读书人没有工作也不耕田,就不应该有饭吃;木匠、车工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应该有饭吃。孟子追问彭更:“子食志乎?食功乎?”彭更回答说:“食志”。孟子举例说:“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彭更说:“否。”孟子则立刻反驳道:“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自此,孟子转变了彭更的观点,使自己处于正方。这段辩论同时也说明,孟子是非常看重读书人的,他认为读书人对国家和社会是有着长远贡献的。在此例中,孟子的理由不仅充足,论辩有力,而且还巧妙地消除了对方的疑虑,并且为自己赢得了高尚的人格与尊严。
五、在辩论中先设置前提使对方承认,然后揭示该问题所蕴涵的结论,并使对方不能不接受
例如在《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中,农家学者许行在滕文公那里受到了礼遇,使本为儒家学者的陈相十分羡慕,也从宋国来到滕国,弃儒从农,并在孟子面前宣扬农家“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主张,也就是要求人人劳动,反对社会分工。孟子听了后,并不急于反驳,而是拐弯抹角,慢慢套问,从许行吃饭、穿衣、戴冠等问题问起,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已在朝着自己的逻辑接近:他已套出了许行所穿的衣服、所戴的帽子、做饭所用的炊具、耕地所用的铁制农具等都不是自己亲自制造出来,而是用粮食交换来的。于是便突然发起凌厉的攻势,咄咄逼问道:“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这样强有力的反问,使陈相穷于应付,不得不承认:“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抓住这句话又反问:“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至此,孟子已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以铁的事实论证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然后乘胜追击,进一步扩大战果,正面阐述其“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的社会分工观点;又以尧、舜、后稷等先贤治天下为例,论证其“不得耕”“不暇耕”“不用于耕”,而其作用却远远大于亲自耕作的道理,实质上也借机提出了社会活动的功利性。[8]由于要害抓得准,又以生活中大量铁的事实作为论据,因此反击十分有力,而且处处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锐气,体现了孟子高超的论辩艺术。
六、当对方故意隐瞒其观点,作出两可之辞时,答辩者可使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应对
例如在《公孙丑下》中,沈同曾问孟子曰:“燕可伐与?”孟子答曰:“可”。后来齐国果然伐燕,这时有人质问孟子:“劝齐伐燕,有诸?”质问者显然是话中有话,含有孟子不该“劝齐伐燕”之意。为此,孟子答辩道:“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孟子答辩的逻辑思维是很严密的,燕无道,当然有道者皆可以伐之,断非无道者可伐无道。朱熹在《孟子集注》中也注解道:“言齐无道,与燕无异,如以燕伐燕也。”[9]沈同不辩“有道”与“无道”的区别,却问“可伐乎”,乃属两可之辞。在这里,沈同“以其私”问孟子显然另有目的,故不确定问意,只是含糊其词地问“可伐与”。面对沈同的两可之辞,孟子能否知其“私”姑且不说,单就其问而曰“可”,就问而答,理所当然,如知其“私”则因其问地含糊,当然也可以含糊地应答。这正好说明了孟子的聪明之处。因此,当沈同企图以两可之辞让孟子承担齐伐燕的责任时,孟子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使沈同的目的没有得逞。
纵观《孟子》一书,其气势磅礴宏大,语言生动明快,形象个性鲜明,不愧是儒家最经典的著作之一。从文本来看,孟子的论辩技巧是高明的,方法也是多样的,以上只是略举几例加以说明。这种特色对后世说理文章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孟子》一书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孟荀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43页。
[2]郭预衡:《中国散文简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4]赵歧:《孟子章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5]罗星明:《<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
[6]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7][9]朱熹:《孟子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13页,30页。
[8]夏传才:《孟子讲座》,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陈晶晶 甘肃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