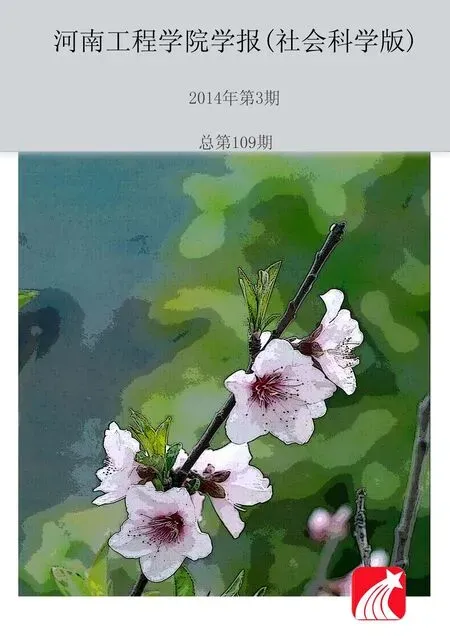河南文学“中”字的文化意蕴
2014-04-08李中华
李中华
(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1191)
一、河南文学的独特现象——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大量存在着“中”字
“中”是河南人最常用、最有代表性的口头语。河南以外的人知道“中”表示中间、中心、适合等意思,但一般不拿它做口头语。河南话中的这个口头语有两个基本意思:一是表示某件事情恰当,切实可行;二是表示满意、赞赏。在河南作家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中”字。一是河南作家的叙述语言大量使用“中”字,如周同宾《皇天后土·尿儿》的叙述语言:“老了有人管就中。” 周大新《湖光山色》也这样叙述:“中,中。开田笑着。”二是人物对话更大量地实录“中”字,例如:
通信员又跑来了,牢骚、委屈地说:“人家说,亲爷也不中!”[1]
上去拍拍马三的肩膀,“哥儿们,中。”[2]
“中”字作为回答问题的肯定用语,不只流行于河南,在河南周边地区(例如徐州)也是存在的。但是,在文学创作中,我们很少发现其他地域的作家用“中”表示肯定。《水浒传》《红楼梦》的人物对话,没有用“中”表示肯定回答之例。河北作家孙犁的作品中,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回答语。山西作家赵树理的作品中,人们回答问题用“可以”而不用“中”字。如:
小顺道:“可以!你要想听这,管保听到天黑也听不完!”[3]
小福很高兴地说了个“可以”,扔下镰就跑了。[3]47
在浙江作家鲁迅、周作人的人物对话描写中,找不到“中”字。陕西作家贾平凹的作品中,人物对话也不用“中”字。由此看来,在作品中用“中”字作为回答问题时表示肯定的用语,是河南作家所独有的。即使发现反例,也非常少。至少可以说,如此高频率地使用“中”字表示肯定,任何地域都不及河南。河南周边地区,人们对话有时也用“中”字表示肯定,但在文学上很少用。
二、“中”的文化意蕴分析
河南人爱用“中”字,与以下因素有关:
1.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
华夏民族是一个有着天下抱负的民族,中国人思考问题,往往是从天下的范围去着眼。当然,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所谓天下,仅仅是指现在中国的腹心地区,其范围远不能包括现在的世界,甚至不能包括中国现在的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中国人所谓的天下中,居于中心的是河南地区,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华夏”“诸夏”,其余四方皆为蛮夷、夷狄、戎狄。中国的“中”字,其基本意义即是中心、中央之意。在全国五岳中,河南的嵩山正处于中心,位于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的环抱之中。虽然现在从中国地图上看河南远不是中部,而是位于东部,但现在人们仍然把河南划为“中部六省”。这是因为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地虽地域广大,却人口稀少,经济落后。
据考证,“中国”一词最早就是指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把这个地区命名为“中国”,除了这个地区的先民自认为自己处于天下之中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字表示好、优秀、可行、可靠之意。此后,“中”被推广到整个汉字文化圈,但是它的好、优秀、可行、可靠这些基本意思却很少被别的地方的人们所运用,使用这些意思频率最高的仍是河南地区。
2.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
河南不但在地理位置上居于全国之中心,而且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它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在河南建都起,先后有夏、商、西周(成周洛邑)、东周、西汉(初期)、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五代、北宋和金等二十多个朝代在河南定都。中国八大古都中,河南一省就占了四个,分别为郑州(夏朝和商朝的都城)、安阳(商朝都城)、洛阳(十三朝古都)和开封(七朝古都)。
3.中道思维和中庸思想
“中”字又是儒家哲学中庸的“中”,也是道家哲学守中的“中”。它包含着异常丰富的哲学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凝聚着河南人高度的生存智慧。
有人对河南人的处世哲学作过如下概括:
他们深知天时、地利都不如人和,于是人与人之间和和气气,既不阿谀卑屈,也不轻视傲慢,保持一种友善与诚挚;处事之道,既不粗鲁、浪费,也不怯懦、吝啬,强调勇敢与慷慨。他们把自己始终放置在群体之中,既不张放也不驰紧,而以深厚的节制、健全的心理修养应对周围的一切。他们在“过”与“不及”之间坚守中道,“执两用中”,在“狂”与“狷”之间,兼具之长又无其弊,把做人的智慧尽情随欲地发挥出来了。道德的力量和意志的力量,在其间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3]48
河南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和嵇文甫,前者是南阳唐河人,后者是豫北汲县人,所以二人被河南学术界称为“南冯北嵇”。他们的思想都具有明显的“中庸”特点。
冯友兰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接受过西方哲学的系统教育,但是他以“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4]作为自己的终身使命和宗旨,在哲学精神上和二程理学有相通之处。冯友兰认为,中西之分的本质就是古今之异。西洋文化之所以优越,原因在于它是现代的,中国文化之所以落后,原因在于它是中古的。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赶上甚至超过西洋文化,同时又保持自己的同一性。这种思想当然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它与中国长期盛行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有着明显的背离与游移,得不到青年们的认同和欢迎。
在哲学上成就略次于冯友兰的是嵇文甫。嵇文甫既反对胡适的“全盘西化”论[5]与钱玄同的“扬粪主义”[6],又反对“国粹主义”[7]和“中国本位文化论”[8],主张融合中西,他受河南最后一位有影响力的理学家李敏修的影响,长期致力于王阳明哲学的研究。嵇文甫的思想也带有稳健、中庸的河南特色。
河南作家也多具有中庸思想。周大新总结拿破仑失败的原因,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生上的教训:不懂得适可而止”[9]。张宇带着崇敬心情塑造了《活鬼》中的侯七形象,其重要特点也是适可而止,不做“露头椽子”,在港商杨忠信为报恩答应资助一百万时辞而不受。侯七是张宇的理想人物,颇能代表作家的思想。
4.混世心态
中庸思想虽然使河南人稳健老成,做事有分寸、合情合理,但更多的则是负面的影响:凡事糊涂、折中调和。
“中”本来是一个哲学名词,充满着辩证法的意味。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偏不倚,把握好分寸,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河南地处中原,在历代战乱中饱受蹂躏,成为苦难最为深重的省份之一。河南人恶劣的生存条件(包括物质生活条件和人文环境)使他们常常受到不公正对待,心中自然会产生怨气甚至戾气。受到命运反复嘲弄的河南人,也被迫想出应对办法,河南民间就不乏游戏人生的智慧。在许多河南百姓的理解中,“中”滑落成为一种生存智慧,成了一种滑头哲学,成了折中调和、糊里糊涂的同义词。河南人就这样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从来不主动追求人生的极致,而甘于贫困,甘于愚昧无知,无所作为地悠闲一生。
这种心态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是乔典运的《村魂》。乡里干部老王负责管理筹集石料修沥青路,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干部熟知老百姓的心理,在动员大会上要求“一律要指头一般大的”石头,村人按照惯例,交出的石头都大得多,只有张老七认真,严格按照上级的要求办事,结果他费了比别人大得多的气力,石子还验不上。乍看起来,这似乎不合情理,实际上却反映了河南民间根深蒂固的难得糊涂、得过且过的心理。检视河南作家的作品,“混”字出现的频率特别高,笔者翻阅李准、姚雪垠、周大新、张宇、刘震云、田中禾、刘庆邦、阎连科、乔典运、周同宾、孙方友等人的作品,都出现大量的“混”字。河南话的“混”字还可以用来表达“认认真真做事”的意思。张宇的《二月河漫记》这样评价二月河:“这年头,就这么老实混,还混出来一个奇迹,真是不容易啊。”[10]这里的“混”字,明显是认真做事之意。
张宇《活鬼》的主人公侯七,一生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看透世事,而他看透世事之后的境界不过是能“混”而已。侯七经过“肃反”“三反”“五反”的锻炼,个人历史上又有些污点,变得精明圆滑起来。在后来的运动中,不管运动的主持者说得如何合情合理、生动形象,他再也不相信这一套。开会发言,写大字报鸣放必须人人过关,主人公就记住一条,“老说共产党好,共产党怎么好,共产党就是好,就是好”[10]。
乔典运的《从早到晚》则写了基层干部们醉生梦死、消磨时光、把一切都当玩笑的心理状况。正因为这种凡事没有认真态度的混世心理,才使得河南人没有独立的主见,没有自己的原则性。从好的方面来说,河南人“尊上易使”,民风柔顺;从坏的方面说,河南人没有主心骨,处处吃亏。乔典运的《驴的喜剧》是揭示中原农民混世心理的形象画面。本来要开群众大会,批判德成走资本主义道路,驴却不懂得革命规矩,对天长嚎,主持社员大会的国舅爷要把驴的嘴掐往,驴却挣扎着叫得更欢。“有人笑得直流眼泪,有人笑得前仰后翻,有人笑得弯下腰直叫肚子疼,笑声震天动地。”[11]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德成是不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严肃的问题,却没有人认真思考。一场批判会变成了群众的狂欢,最后德成表示投降才告结束。李准的《瓜棚风月》中农民的对话非常鲜明地揭示了河南农民凡事随大流的心理。李准在小说中也对此种心理作了准确的概括:“他们的本分习惯,告诉他们一个处世哲学就是‘出头椽子先朽’,为人不要多出风头,一切事情还是随大流好。”[12]
对于这种混的心态,河南的有识之士早就作过批评。冯友兰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说:“社会上一般之人,或混事,或混饭,教席混钟点,学生混资格,一混而无不混,此河南各界之写真也。”[13]可惜,这种混世态度似乎至今也并没有完全消失。
[1]张一弓.张一弓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11.
[2]刘庆邦.走窑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28.
[3]赵树理.赵树理文集(一)[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47.
[4]丁离.河南人谁也没惹——为河南人说句公道话[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149-150.
[5]冯友兰.冯友兰自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179.
[6]胡文生.向西方学习——走近胡适[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19.
[7]于文善.抗战时期的“学术中国化” [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16.
[8]周大新.历览多少人与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109.
[9]张宇.与自己和平共处[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344.
[10]张宇.活鬼[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39.
[11]乔典运.乔典运小说自选集[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202.
[12]李准.李准全集(三)[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304.
[13]冯友兰.《心声》发刊词[M]//河南新文学大系·史料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