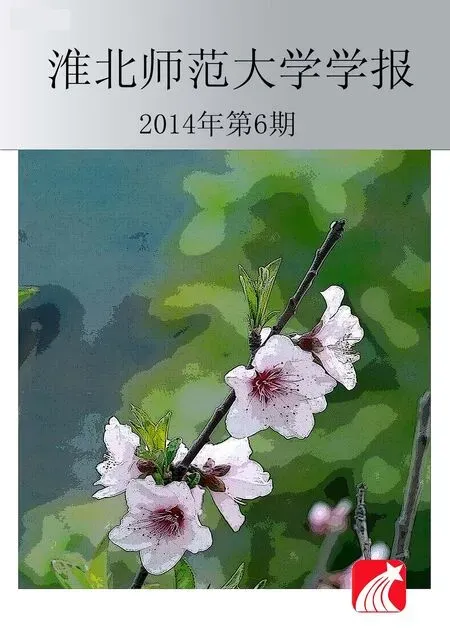教师:对话者抑或传道者?
——从苏格拉底及其“产婆术”看教师的本质
2014-04-08宋学红
宋学红,张 鸽
(淮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年—前399年)是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一直被学界奉为对话者的教师典范而备受赞誉和倡扬,其“产婆术”更是作为对话教学的样板蜚声于世。然而,远在唐朝,韩愈就在其教育名篇《师说》中一语中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1]287。教师之所以是教师,因其“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天然的走在学生的前面对他们加以引领。也就是说,教师只有作为传道者,方能“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2]137。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教师传道者的本性永恒不变。
一、教育史上的苏格拉底及其“产婆术”
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士。“产婆术”作为苏格拉底首创的一种教学方法,深受他母亲职业的影响。苏格拉底将知识之获得比为婴儿之降生,在二者相互对应的情境里,产妇就是学生,助产士就是教师,产房就是教室,而婴孩就是观念。这种方法的产生还建立在他的“先天观念”说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一出生,就禀有观念,这些观念是天生的并非后天才拥有。教师的教学,类似产婆将胎儿“引出”而已,产婆绝对无法“由外往内”地赐予产妇婴儿,却只能“由内往外”将婴儿接生下来。所以,苏格拉底认为教师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自己”重新“发现”早已存在的观念,或者“回忆”遗忘但未曾消失的记忆。[3]30
因此,在教学中,苏格拉底首先摆出一副很无知的样子,去向学生请教某一个问题,然后顺着学生的思路一步一步的发问,当学生有了矛盾和迷惑时,他并不急于告诉学生答案,而是举出一些生活中的实例,引导和启发学生思考,并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受这种思想和态度的影响并经过长期的实践,苏格拉底形成了由讥讽、助产术、归纳和定义四个步骤组成的“产婆术”。“讥讽是就对方的发言不断地追问,迫使对方自陷矛盾,回答不上来,然后终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助产术即举出一些实例,帮助对方自己得出正确的答案。归纳即从各种具体事物中找到事物的普遍原则和规律,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比较寻求一般。定义是把个别事物归入一般概念,得到关于事物的普遍概念”[4]57。
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学生独立地思考问题,有利于青年人正确地树立人生观、道德观。从具体学科来看,“产婆术”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学科,仅适用于道德教育。[5]42他和学生尤苏戴莫斯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历来被视为“产婆术”的经典案例:[6]146-148
“苏格拉底:虚伪是人们中间常有的事,是不是?
尤苏戴莫斯:当然是。
苏:那么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正义还是非正义?
尤:显然应该放在非正义的一边。
苏:人们彼此之间也有欺骗,是不是?
尤:肯定有。
苏:这应该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尤:当然是非正义的一边。
苏:是不是也有做坏事的?
尤:也有。
苏:那么,奴役人怎么样呢?
尤:也有。
苏:尤苏戴莫斯,这些事都不能放在正义的一边了?
尤:如果把它们放在正义的一边那可就是怪事了。
苏:如果一个被推选当将领的人奴役一个非正义的敌国人民,我们是不是也能说他是非正义呢?
尤:当然不能。
苏:那么我们得说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了?
尤:当然。
苏:如果他在作战期间欺骗敌人,怎么样呢?
尤:这也是正义的。
苏:如果他偷窃,抢劫他们的财物,他所做的不也是正义的吗?
尤:当然是,不过,一起头我还以为你所问的都是关于我们的朋友哩。
苏:那么,所有我们放在非正义一边的事,也都可以放在正义的一边了?
尤:好像是这样。
苏:既然我们已经这样放了,我们就应该再给它划个界线:这一类的事做在敌人身上是正义的,但做在朋友身上,却是非正义的,对待朋友必须绝对忠诚坦白,你同意吗?
尤:完全同意。
苏:如果一个将领看到他的军队士气消沉,就欺骗他们说,援军快要来了,因此,就制止了士气的消沉,我们应该把这种欺骗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尤:我看应该放在正义的一边。
苏:又如儿子需要服药,却不肯服,父亲就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而由于用了欺骗的方法竟使儿子恢复了健康,这种欺骗的行为又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尤:我看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
苏:又如,一个人因为朋友意志沮丧,怕他自杀,把他的剑或其他这一类的东西偷去或拿去,这种行为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尤:当然,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
苏:你是说,就连对于朋友也不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坦率行事的?
尤:的确不是,如果你准许的话,我宁愿收回我已经说过的话。”
显然,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是通过“诘问式”进行的,以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从而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其实质乃是一种启发式教学。这种教学,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思考道德、人生问题的智慧。但是,苏格拉底不管以何种方式教或者教什么样的内容,其根本都是在“教”亦即传道,而绝非对话。然而,在倡导教师是对话者、教学的本质是师生对话的学者们那里,苏格拉底却从传道者嬗变成对话者,“产婆术”则从师生之间的教与学演绎为师生对话。
二、对苏格拉底及其“产婆术”的误读
(一)苏格拉底:对话者而非传道者
苏格拉底在与学生讨论的过程中,没有以权威者自居,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学生承认自己的无知。学者们认为,这一过程并没有教师的教和知识的授受,只有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而共识的达成。因此,苏格拉底是对话者而不是传道者。
1.“传道”的曲解
主张教师是对话者的学者通常将“传道”等同于“授受式教育”,并且认为“授受式教育”就是传递知识;进而抨击“授受式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1)“传道”被窄化、贬抑为僵硬地传递知识
“传道”几乎与“独白”是同义语,而“独白”则是“授受式教育”的典型特征。所谓“授受式教育”是以知识为终极性的价值载体,学生在教师的传递过程中获取知识,并由此实现他的人生价值。[7]26-30“授受式教育”中,知识的获得成为教育教学的目的,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必然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客体,教学过程就是作为主体的教师对学生这个客体进行加工、塑造的过程。因此,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只是把固定的教学内容传输给学生,而学生只是“知识的容器”,被动、机械地等待教师的注入。
(2)“授受式教育”的师生关系必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授受式教育”中的教师是知识的讲授者,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壶与杯”的浇注关系,是“上施下效”的关系。[8]37-38更重要的是,“授受式教育”以知识本位为价值取向,教师掌握着课堂的绝对主动权,拥有话语霸权,剥夺了学生的话语权力,“使学生沦为被压制、被操纵、被管理、被奴役”的地位,[9]26-30师生关系必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2.“对话”对“传道”的颠覆
“传道”遭千夫所指,似乎只有“对话”才能力挽狂澜。而“对话”通过摧毁“授受式教育”,把师生之间的教与学的关系颠覆为对话关系,藉此终结统治与被统治的传统师生关系。
(1)对话取代“授受式教育”
“授受式教育”遵从“教师权威”和“知识本位”的价值取向,它“剥夺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和权利”[10]33-39。而对话教学是以“以师生心理世界的开放为特征,以互动为方式,语言交融,心灵交流,师生双方均从对话中获得道德和理性的升华”[11]22-25;“对话不仅形成了师生交互性的关系,而且也使知识转变成学生个人的认识,使学生的精神受到对话的启迪和引导”[12]135。因此,教学的本质在于对话,即教育教学是教师与学生沟通、合作、对话的过程,其知识的传递功能被以各种信息为媒介的沟通功能,以及通过师生双方的思考、见解和知识交换为指标的价值评判功能取而代之。[10]33-39
(2)对话是传统师生关系的终结者
对话是对“教师是知识的权威”从而也是对“授受式教育”的反动,“教师不应以知识的权威者自居”,“教师和学生只是知识的先知者与后知者的关系,并不存在尊卑关系”,“学生与教师一样,在人格上是独立的,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都需要教师的理解和尊重”[13]12-17。师生双方只有作为平等的对话主体,在共同的情境下调动各自的背景知识,针对课程内容和学生的发展展开对话与交流,通过辩论、商谈,最后达成理解与共识,逐步在师生之间形成民主、平等、共生的人际交往关系。[14]90-94
一言以蔽之,师生关系的本质是对话,而对话的实质就是教师的人格精神与学生的人格精神在教育中的相遇,“双方在思想、精神和情感上发生真实的沟通与交流”;对话教学的最终追求“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理解、信任和爱”[15]19-24,它将彻底颠覆统治与被统治的传统师生关系。
3.苏格拉底是对话者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将教育划分为三大类型:经院式教育、师徒式教育和苏格拉底式教育。[16]7-8经院式教育是以书本知识或教学内容为中心来进行的,教师作为“教书匠”,照本宣科地“传授知识”,学生只能学习固定的知识,学会一些现成的结论和答案。师徒式教育完全以教师为中心,充斥着教师的绝对权威,学生丧失了自己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而苏格拉底式的教育迥异于前两类教育,它以“真理”为中心,教师和学生处于一个平等地位,师生之间只存在善意的论战关系,而没有屈从依赖关系。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基于对话哲学,将教师的角色定位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助产士”,而不再是传统的教案组织者和知识的传授者。[17]130-147教育应该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师不断的为学习者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他们能够愉快、创造性的学习。
苏格拉底在与学生讨论的过程中,以学习者和真理为中心,师生双方经过平等协商而后达成某种共识。教育过程中既没有知识的灌输,也没有屈从依赖。因此,苏格拉底是对话者而不是传道者。
(二)“产婆术”:对话而非教学
产婆术“是一种反复运用的独特的对话方式,其特点是教师为探求某种理念的真谛,主动向对话的另一方,不断地追问,使对方不断地从自以为知到知道自己无知”[18]3-6。甚至,苏格拉底在同学生“对话”前,并没有掌握真理,而是以自己的无知来构建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19]65-70如关于“正义”的“对话”,苏格拉底与尤苏戴莫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没有向其传递任何知识和真理,所做的只是对尤苏戴莫斯头脑中错误的观念进行剖析和澄清,让其自己在头脑中构建“正义”。因此,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是对话而非教学。
三、为苏格拉底及其“产婆术”正名
(一)苏格拉底:传道者而非对话者
1.“传道”正解
对韩愈所言称的“传道”中的“道”,我们应作全面、准确的把握,“理解为教师所担负的教学任务”则较为妥帖[8]37-38,而把“传道”仅仅作“传授知识”的解读是偏狭的。系统知识的传授是教师基础而根本的传道任务,一方面,教师应当不止于知识的传授,还应追求智慧的启迪和实现精神的传递;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传授知识与启迪智慧、传递精神经常交织、融合在一起,且前者是实现后者传道任务的渠道和桥梁。
不同层面的传道任务,则要求具有分别与之相适应的志趣迥异的教学方式。所谓系统知识,指的是悠久的历史文明积淀下的、业已被证实的结论性的知识,诸如概念、公式、原理等等。这一层面的传道,教师以教材为例子进行系统、生动地传授或者讲授被证明较为高效、简捷;第二个层面则为师生双方思想、智慧的碰撞,要求教师以自身的灵性去启迪学生的悟性;第三个层面表现为情意的交融、精神的传递。教师若要传递、培育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其教育教学的方法、手段就必须是道德的,试图以不道德的教学去促进学生道德人格的成长和壮大,无异于缘木求鱼。恰如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倘若要使学生真正明晓何为“正义”,教师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式就必须充满正义,这正是苏格拉底“产婆术”的魅力和真义所在。因此,传道既不等同僵硬的“授受式教育”,也不止于狭隘的传授知识,更不必然导致统治与被统治的师生关系。
2.“对话”正解
对话在辞典中主要具有两种意思,一是“相互间的交谈”,如:以对话消磨时间;二是“指对立或无联系的国家、集团等之间所进行的接触或谈判,也指政府机构负责人士等与群众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的谈话”,如:两国就贸易问题进行对话。就哲学的意义而言,与对话相反的是独语,对话既是目的又是方式,它强调对话参与者的投入,没有使对话参与者产生变化的交谈不能称之为对话。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个人或一类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才能参与到一定的对话情境中”,对话者双方的的身份、地位等制约着对话的开展,“处于社会或专业领域不同等级的人,由于权利和能力素质上的不平等,很难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对话双方“必须具有共同的利益和追求”,而“处于不同文化背景或不同专业领域的人,由于信念的不一致,也很难进行实质性的对话”[11]22-25。
综上所述,对话指的是一种商谈、协商、谈判的方式或机制,它有两个基本点,其一,对话的前提是双方主体地位必须平等;其二,对话的目标是求同存异,促成共识的达成。
3.苏格拉底是传道者
根据《教育大辞典》的解释,“教育是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教育既不是因师生双方协商、谈判的需求而诞生,教学内容也不是师生协商、谈判的成果,教学目标更不是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师生双方在人格上的平等,并不能简单地推论出他们在教育关系上,其地位也应当是对等的。教师只有当下走在学生的前面,具备丰富的学养才情和较高的职业素养,才能为学生构筑起坚实的知识、思想与道德的平台,以引领他们看得更高、走得更远,也才能寄希望未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苏格拉底认为没有人可以掌握绝对的真理,但是他并不否认相对真理的存在,这种相对真理的占有也是进行教育教学的前提。如关于“正义”的讨论,苏格拉底相对于尤苏戴莫斯而言,他占有了真理。他在谈话之前,已然对“正义”有相对准确的认识和理解。否则,他何以对尤苏戴莫斯头脑中错误的观念进行剖析和澄清?何以让尤苏戴莫斯自己去建构正确的“正义”观念?但是,苏格拉底却没有直接告诉尤苏戴莫斯答案,而是从尤苏戴莫斯的谬误或矛盾着手,把其思想引到他要阐述的问题方面来,让尤苏戴莫斯陷于思维和逻辑的自相矛盾中,从而产生领悟和顿悟。显然,苏格拉底的传道更注重智慧的启迪和精神的传递,而不是既定结论的宣讲。因此,苏格拉底不仅是传道者,而且还是十分高明的传道者。欲终结统治与被统治的师生关系,就必须从提升教师传道的境界、层次和水平上作文章。而一切通过反动、颠覆教师的本质,以期构建所谓新型师生关系的努力,最终都只能化为镜中花、水中月。
(二)产婆术:教学而非对话
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一种人类特有的人才培养活动,它既是科学,更是艺术,其方式、方法与手段应当因人、因地、因时和依据教学任务的不同而灵活多样。正如孟子所指出的:“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2]203。意即拥有高超教学艺术的教师,其教育学生的方法大致有五种:有像及时雨一样启迪人的;有成就德性的;有培养才干的;有解答疑惑的;有感化他人使其模仿的。苏格拉底与人讨论,并不作长篇大论,而是提出问题,往返之间,令对手渐渐自缚于矛盾,而从困境中产生领悟和顿悟,获得新见地,其教学艺术可谓出神入化。但教学方式方法的艺术化绝不意味着教学本质的改变,教学过程依然是师生之间的教与学的关系,而没有嬗变为对话关系。“对话”充其量只能构成教学的方法和手段,却不会转化为教学的目的与本质。
现代教学论的发展业已将学与教划分为知识、技能、态度(情感)三大领域。前文已述,苏格拉底通过“产婆术”向学生进行的是道德教育(如关于“正义”的讨论),即属于态度(情感)领域的学与教。而“态度(情感)学习”既不同于以听讲、记诵、复述为主的“知识学习”,也异于以模仿、练习、实践为主的“技能学习”,它要诉诸于学生的体验和认同。因此,通过“口授式教”和“训练式教”这种“直接的教(direct teaching)”,能够传授知识和技能,但却很难教道德。道德的教需要使人在态度或情感上形成认同感,因而只能进行“间接的教(indirect teaching)”。间接的德育是一种广泛而有效的道德影响,它渗透在知识技能教学、师生人际交往乃至学校集体生活的各个层面。
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即属于“间接的教”,他没有直接呈现正确的结论,而是在与学生谈话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诘问对方,迫使其因自陷矛盾而觉悟,教学目的就在不知不觉之间而达成。在这种间接的德育中,师生关系的本质仍旧是教与学的关系,亦即教师的教指导学生的学,不是直接教知识,而是教思考道德、人生问题的方法,以唤醒学生的内在自动力量。
四、教师是传道者而非对话者
在知识经济时代和网络普及的今日世界,学校的教育教学正在经受着愈来愈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教”的内涵、方式与手段不断丰富和拓展,但教师传道者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师生之间教与学的关系远没有嬗变为对话的关系。
(一)教师的本质:传道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教师的职责现在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与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
可见,今天对教师传道的境界、层次与水平的要求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高。我们需要对教师的“教”进行全面、深刻的解读和把握:其一,教最基本的内涵是“教授,教师传递正确的思想,传授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并解答学生在学习中或生活中的疑惑和问题”;其二,“教”蕴含“教导”之意,即“引发、启迪、点化”,要义在于对学生智慧的启迪、学习兴趣的激发与主动性的唤起,而非知识的灌输;其三,“教”也指“建构学习环境”,为学生卓有成效的学习——知识的积累,心智的发展和个性的形成营造宽松愉悦的心理氛围;最后,教即“教化,这包含着校园文化的建设,良好的校风、班风,教师人格的示范等,即潜移默化。”[8]37-38
因此,在现时代,教师其传道者的本质不仅没有改变,相反教师只有切实扮演好传道者的角色,完整地履行传道者的职责,才能有学生的知识建构、心智成长、情感陶冶与个性发展。
(二)师生关系的性质:教与学
“民主平等”已经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但是“民主”“平等”本是政治学上的概念,它强调的是公民的权利和公民相处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制社会的基本法律原则,它赋予所有公民在法律地位和人格精神上的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和学生是民主平等的关系。但是师生关系却是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因知识的授受而相遇,它直接受教育目的和教学任务的制约。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把泛泛的、一般社会意义上的人际平等,直接移植到学校里特定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中,言称教师是对话者、师生关系是对话关系,是把抽象的人格精神的平等简单等同于具体的社会工作关系上的平等。
《教育大辞典》中将学校定义为:“学校是人类进行自觉的教育活动,传递社会知识文化,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为一定社会培养所需人才的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他要“教书育人”,“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因此,教师是教育者,承担着国家和社会所赋予的委托,对学生——受教育者进行传道、授业、解惑。教师作为传道者,首先自己必须先有“道”,“闻道在先”才有资格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教师理应具有较高的教育思想、教育智慧、专业精神和专业人格。这决定了教师与学生在教育关系、地位上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平等和对等的。因此,师生关系的性质是教与学,而非协商对话。诚然,教师和学生作为普通的社会公民,他们之间也必然存在超越教育目的与教学任务之外的正常的人际交往和平等对话。但是,此时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已经不属于教学关系或师生关系,俨然超出了本论题的讨论范畴。
结 语
教师的工作对象是学生——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学生不仅把自己的社会生活经验和个人的需要、兴趣、情感与希望带入教育过程,而且在教育活动中他们有自己的判断、选择、建构与评价;他们已有的发展水平、倾向和当下的心态,是他们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是教育活动的起点。因而,教师的传道就必须关注教育对象的生命特征,尊重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教师虽然不是对话者,但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却应有主动与学生进行对话的意识、姿态和精神。于此,教师多层面的、充满诗情画意的传道过程才不会蜕化为单向度的知识信息的流淌,而是更充满着师生双方之间思想智慧的撞击、情意的交融和精神的传递。
[1][清]苏渊雷.经世文鉴[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1.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3]林玉体.西方教育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4]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缩编本)[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5]刘新科.国外教育发展史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古希腊]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周兴国.对话教学:有待进一步澄清的几个问题—对当前对话教学理论研究的审视与反思[J].课程·教材·教法,2010(7).
[8]孙喜亭.也谈教学中的师生关系[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10).
[9]王永祥.强势话语的弱势化与弱势话语的强势化——如何实现课堂场域教师话语的对话性[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2(2).
[10]钟启泉.对话与文本:教学规范的转型[J].教育研究,2001(3).
[11]刘庆昌.对话教学初论[J].教育研究,2001(9).
[12]金生鈜.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13]徐洁.民主、平等、对话:21世纪师生关系的理性构想[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12).
[14]王向华.对话教育论[J].教育研究,2010(9)
[15]杨小微.在对话中达于理解—关于中学对话教育的理论反思与实践重建[J].课程·教材·教法,2007(10).
[16][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17][美]卡尔·罗杰斯.与人交往[M]∥人的潜能和价值.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8]陈桂生.“对话教学”三题[J]. 江苏教育研究,2009(8).
[19]梁君.“苏格拉底的无知”引发的“师生关系”[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