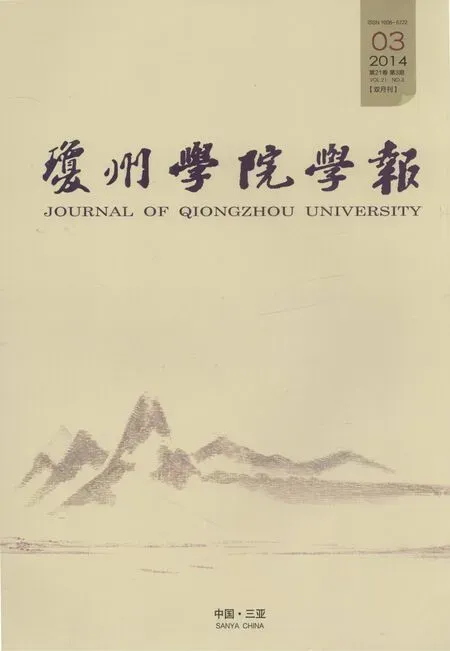超越自恋,积极与现实世界对话——再谈女性自恋写作
2014-04-07刘栋
刘 栋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安徽淮北235000)
一、现象与背景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一度形成热潮的女性自恋式写作,在当代中国是一个独特而耐人寻味的文学和社会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热闹围观可能是一时性的,但对它的观察和思考应该是冷静长远的。拉开些时间的距离,或许我们能审视得更加全面客观。女性自恋式写作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女性”“身体”等敏感概念上,它对今天和今后的文学创作和女性思想发展都影响深远。在陈染的《私人生活》《无处告别》、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瓶中之水》、海男的《我的情人们》《疯狂的石榴树》、徐小斌的《羽蛇》《双鱼星座》、春树的《北京娃娃》、棉棉的《糖》等典型文本中,“镜像之恋”与“同性之恋”是女性自恋情结主要表现情节与载体,女性由“被窥”转为“自窥”,由“被爱”转为“自恋”,她们采取背对男性和人群,也背对历史和社会的姿态,把自我封存在狭小独立的个人空间里,自我凝视,自诉心语,精神的满足和爱欲的获得完全不需要男性的参与。女性书写者们认为这种自恋式书写是女性自我认知、自我肯定的一种方式,也是女性保持精神独立的一种姿态。
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多重的政治、文化、经济背景。
20世纪以来,女性解放的使命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艰难而又执着地行进着。中国女性解放的话题常说常新,但问题层出不穷。中国女性解放的艰难,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男权观念没有得到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清除;另一方面,由于女性一直处于缺乏主体地位的“被解放”的地位,自我意识先天不足。新时期的女性写作正是立足于“男女不一样”两性有别的基点上来培育先天不足的女性意识,探寻女性自我身份的确认。同时她们也认识到,“男女平权”这一由法律自上而下先验设定的外在的社会组织层面的大而化之的口号与两性内在意识层面上的“不平等”所带来的矛盾,给女性的自我认同造成了新的心理冲突和困惑。表面看起来令人羡慕的“平等解放”仍遭受着意识深处传统性别观念以及种种社会现实缺憾的围困和束缚。怎样“自觉地揭开这层貌似公允浑然天成的纱幕,暴露其人文性质与强权色彩”[1]成为今天女性的历史使命。并且,这种围困与束缚不仅来自社会、男性(有时这二者是重合的),也来自女性自身。因为在按照传统的男性规约来塑造女性的历史进程中,女性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男性对她们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自我锁定在“被看”的位置上。男权观念已成为难以漂洗的血缘因子浸淫到了女性的血脉流动中,造成女性文化身份的分裂状态。正如“认识你自己”的千古箴言凝结着人类痛苦的追索与思考一样,认识女性自我同样是灵魂的冶炼。女性书写者们认识到,要真正改变女性的非主体性的身份,必须从深层的意识领域着手,从自我意识着手,由内而外地探索、挖掘女性的身份与价值。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表明,女性作家在“我是谁”的现实追问中始终在有意识地探寻、建构着具有独立性别内涵的女性身份,甚至以激进反叛的形式实践着自我的性别思考。
当然,这一思考空间的获得也与时代的际遇是分不开的。上世纪80年代始,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传入中国,给在蒙昧中摸索的中国女性打开了一扇敞亮的理论之窗。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妙》、凯蒂·米勒特的《性政治》等早期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的到来拉开了中国女性文学者用这一新的理论体系思考、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序幕。90年代,更多的理论译著进入中国,如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托里·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等,这些译著有力提升了国人对女性主义文论的全面认识,为其写作提供了崭新的话语坐标。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程度和女性主义理论、女性写作在现实及文化中的份量。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的生活与思维方式等都逐渐发生了重大转变,多元文化格局渐趋形成,这些也给女性个性化的书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空间,成为女性自恋式写作现象出现的时代契机。
二、困境的出现
在上述背景下,女性自恋式写作的出现确实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与现实意义。它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产物和表现,也是女作家探索女性自我精神确认、挑战与抗衡传统男权观念的一种方式,其创作实践还补充、开拓了原有的文学创作与阅读经验,丰富了文学表现方法,促进了文学风貌的多样化。这无疑对女性写作,乃至对整个文学创作活动都是有益的开拓。但硬币的另一面很快被反转过来。纳克索斯因迷恋自己倒映在湖面上的动人身影而坠湖身亡,这个古希腊传说本身就是个深刻的寓言——自恋发展到极端就会导致自我毁灭。艰涩夹生的外来理论与逼仄狭小的创作视野使得创作困境紧随热潮而至:自叙传写作与身体写作演变为商业式展露与卖点、情节与形象简单复制、意绪化随处弥漫、理论追求陷入悖谬迷茫……局面尴尬混乱,这是许多女性书写者始料未及的。自恋式写作已然成为“失去笼子的囚徒”。
诚然,短暂的母系时代结束后,人类历史就是女性被压抑的历史。“女性因为沉默太久,缄口的时间竟可以用百年千年来计算,所以,若不在沉默中爆发,便是在沉默中死亡”[2],而爆发的愤懑激情使女性作家过激地排斥着男性而陷入自恋的漩涡不能自拔。在继80年代《方舟》式的丑化男性、抗拒男性后,90年代《一个人的战争》式则是完全回避男性、无视男性。女性在两性关系上的矫枉过正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心态,但矫枉过正如果走得太远,不仅不利于营造两性的和谐,还会削弱女性自身内在的力量。崇高和滑稽只是一步之遥,真理再往前多走一步往往就是谬误。因此,在充分肯定,尊重自我的个体性的基础上,又必须超越(不是简单的否定与抛弃)自恋,对创作中的自恋问题进行及时的自审自省。可以说,没有对自恋的有效超越,就不会有真正自由的生命和生命的自由,“人只有彻底摆脱自恋才能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人”[3]。背对男性与社会幽闭地自恋虽然可以保持和享有心灵的宁静与思考的自由,但也将自己生存与发展之门闭锁了。孤芳自赏的心灵愉悦是虚幻而短暂的,当女性只拥有自己时,也孤立了自己,成为没有经纬与重力的飘渺的悬浮物。自恋不是女性重建自我的目标,最多只能是阶段性的方式手段;疯狂更不是与生活和解的方式,只能是向无奈妥协的结局;纯粹感官和欲望的书写并不能构成生活的真实和全部,却极易滑落为媚俗的展示。女性隐秘心理和经验若不能上升到精神、灵魂的高度,必将败落枯竭。当女性把自己关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只关注“私人生活”,不关注民国家、世界时,国家、世界更不会关注女性,女性将丧失对他人、对世界的理解力,将丧失文化言说的能力与权利,作者的身份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在反动以往以“人性”完全遮蔽“女性”的片面时,如以女“性”去遮蔽“人性”,无疑是舍本逐末,以一个更大的错误去挑战另一个错误。挑战男权中心文化的立足点应是以女性的视角去思考整个人类,而不仅仅是女人自身,甚至仅仅是女人的身体。邓晓芒曾指出:“一个女性作家的作品,如果不能让男性读者也从中读到自己的灵魂,而只是满足着男性的某种窥视欲和好奇心,这种作品就无法达到人道主义的层次。”[4]张光芒更是立足于整个当前文学,指出了自恋情结给文学发展造成的障碍和伤害:“自恋的膨胀还使文学丧失了真诚,虚伪和矫饰横行,带来了病态的叙述、语言和浮躁喧哗的文风,并进而造成了文学生态的混乱。”[5]在男权话语的遮蔽与压制下,女性没有看到过广阔的蓝天;在自筑的封闭堡垒里,压迫机制依然存在,女性的天地仍是黑暗狭小的。镜中看到的自我也未必是全面真实的自我,那所封闭的堡垒不是女性驶向新生的方舟。如果纳克索斯有勇气离开湖边,如神所预言,他将获得长寿与快乐。女性书写者也必须穿越镜像,走出自恋的窠臼,树立新的航标,奋力振动或许还不够丰满的羽翼,翱翔于广阔天地。
三、出路——从自恋到自在,积极与现实世界对话
新的航标在哪里?和世界抗辩,与现实交流。“女性文学应真正走向一种有性别又不唯性别的‘人’的文学。这是一种从‘众声合唱’和权力话语的双重遮蔽中抽身而出的在多元化文学格局中属于个人化的文学。”[6]穿越自我,走出自恋的幽闭状态,在自我之外发展自己,与现实积极对话,与男性平等交流,在日以相守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的社会生活中与男性共同寻找有关正义、幸福和美的价值,分担寒潮,共享虹霓,并从中不断完善自身和追求真理仍然应是女性写作的最高境界和目的。
那么,还要做好那些方面的调整和准备,才能行走到这一光明境界呢?大体说来,既需要作家的主观努力,也需要客观环境的有效配合。
首先,从主观上说,作家要自觉调整自恋的自闭心态,向现实世界敞开,并在思想与艺术层面都努力提升自我。
可能是出于对自己创作才情的自负,或是对惯性创作的懒惰依赖,或是急功近利心态作祟等,仍有相当的女性作者没能从自恋创作的泥淖中抽身而出。在一片土地上过度的开掘,已明显导致其创作力日趋匮乏,创作的“瓶颈”往往是正是由于精神的“窄门”,而一个真正艺术家的魅力则在于她能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探索与创新。这一点,我们在林白新世纪以来的创作中看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林白曾说:“我的写作是从一个女性个体生命的感官、心灵出发,写个人对世界的感受,寻找与世界的对话。”[7]尽管曾一度拒绝现实,只关注内心经验,沉醉在女性个体生命的感官感觉中,沉醉在自恋情结中,但可贵的道德操守和自省精神使林白还是保持着清醒的创作头脑,并没有忘记她创作的最终也是最高目标——寻找与世界的对话,寻找人类的整体关怀。她在超越与创新的道路上在不断努力探索着。
2000年,林白发表的《玻璃虫》尽管还继续着自传体的叙述风格,但其间的些许变化,细心的读者还是不难看出。她像只柔软的小虫子一样,向外在的现实世界探出她的触角,慢慢蠕动着爬出了那个自闭的“私人”窠臼,努力与现实对话,与生活和解,努力上升到关注普遍人性的更高层面。女主人公林蛛蛛不再是那个缀在B镇岁月枝头上的犹如一只青涩坚硬的番石榴的林多米,她微笑着面对生活,融入社会,并希望获得现实的认同。到了《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林白的变化就更加明显了。《万物花开》中,作者将心灵的翅膀插在了一个农村少年大头的瘤子上并创造了一个野生的自我,这个野生的自我跟牛和南瓜厮混在一起,自由自在,用一双穿透一切的眼睛观察周围,重塑一切。在《妇女闲聊录》中,林白面对大千世界不仅要放任想象,而且要放任言说。她采用“闲聊“的方式把话语权交给了一个操着北方方言的农村妇女,让那些最普通,甚至最蛮荒的农民成为最大权利的话语者,他们忠实地传达出底层农民的声音。到《致一九七五》,林白完成了从崇尚个人的女性主义向关注社会与历史的转变,作品风格也进一步由凄美凌厉转向朴素的民间叙述。林白倾听关注现实,向现实世界彻底敞开的姿态也进一步得以彰显。对此,林白这样感叹说“多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我和世界之间的通道就这样被我关闭了”,“而现在,人世的一切,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8]
除了要对自恋心态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之外,在思想、道德及艺术层面都努力提升自我,自觉抵制名利市场的干扰与诱惑,高标文化深度和文学崇高感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样一个“整个世界都得通过文化工业的过滤器”[9]的时代,文学的纯粹性、崇高地位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强烈的名利吸引刺激着一些作家的物欲创作,使其在与市场的联姻中迷失自我。其中,对“身体写作“的改写与利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缺少灵魂的相契,许多所谓的“身体写作”实质上已沦为肉体的商业展示与卖点。女性写作要健康发展,对人性的剖析、对灵魂的探索就是必不可少的。其次,从客观上说,整个社会要作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的多元协调,以营造出健康清新和谐的文学生态环境,引导、促进女性文学创作向良性发展。
文学创作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在表现人,表现社会的同时,社会环境,尤其是文学创作环境必然会对文学创作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它本身就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整个社会也要担负起关注并有效引导女性写作向良性发展的职责。这就需要整个社会作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的多元协调,以营造出健康清新和谐的文学生态环境。女性文学虽然发展较快,但它在中国正真成为一种文学的“类”毕竟只有短短近二十年的历程,并且带着观念先行、理论夹生的深刻印记。对于仅有一点五四“新女性”文化和文学传统的遥远背景,话语资源几近空白的当代女性写作而言,其自身的理论积累、实践积累非常不足,还是一个幼稚的存在,其数量和速度的发展并不一定能与质量的提高同行。这时候,一个健康清新和谐的良性文学生态环境的营造就对其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1]杨莉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9.
[2]徐坤.因为沉默太久[N].中华读书报,1996-12-10(2).
[3][美]弗洛姆.人心[M].孙月才,张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78.
[4]邓晓芒.当代女性文学的误置——《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评析[J].开放时代,1999(3):64-71.
[5]张光芒.自恋情结与当前的中国文学[J].学术月刊,2007(9):89-97.
[6]刘思谦.女性文学这个概念[J].南开大学学报,2005(2):1-6.
[7]林白,荒林,徐小斌,等.九十年代女性小说四人谈[J].南方文坛,1997(2):33-35.
[8]林白.低于大地——关于《妇女闲聊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5(1):48 -49.
[9]陶东风.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