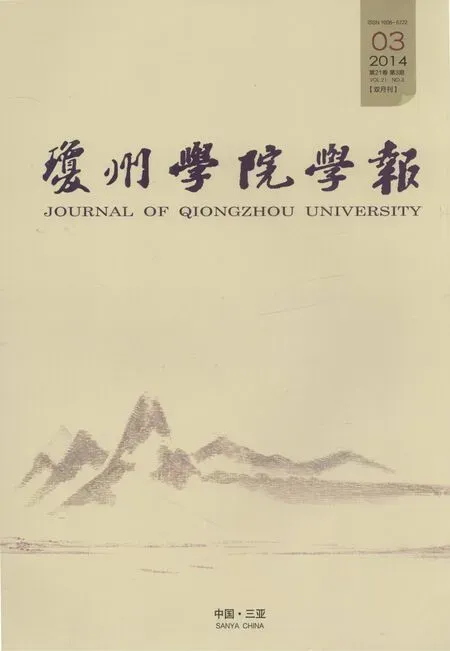论《古诗十九首》中的异文与模件化套语
2014-04-07刘美惠
胡 旭,刘美惠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 厦门361005)
由于《古诗十九首》“不可句摘”“不可字求”,而能“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1],并且被定位至较早的创作时代(通行观点为早于建安或建安初期①有关《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与作者的讨论众说纷纭,有“两汉说”(见《文心雕龙·明诗第六》)、“西汉枚乘说”(见《玉台新咏》)以及“建安曹王说”(近世支持“建安说“的论著如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等等。自梁启超对此做出详细考证认为此为东汉末年作品后,学界目前通行“东汉末年无名诗人说”。),它获得众多诗人的攀仿与无数诗论家的崇高评价②拟作《古诗十九首》的全部或部分成为后世诗人常见的行为。较著名的有陆机的拟作。诗论家的评价可见于钟嵘《诗品》、王世贞《艺苑卮言》、谢榛《四溟诗话》、胡应麟《诗薮》、陆时雍《古诗镜》与王士祯《带经堂诗话》等。是理所应当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无法得知有关作者的任何信息,这组诗依然引起了批评家将其安放回线性文学史的极大热情③自《昭明文选》将十九首古诗编纂为一组后,历代论者若对其予以评价,均会或多或少涉及其作者与创作年代的考证与推测。这可被视为企图将本不知时代与何人所作的作品安放到既有体系(以时代与作者系年)中去的努力。。人代④“代”字疑为“世”,唐人避讳所改。类似《诗品序》中有“古诗渺邈,人世难详”之语,可资佐证。冥灭的现状决定我们几乎不可能重新发现作者身份或创作时代(除非出现考古奇迹),然而仍有众多研究者汲汲于对二者不断进行考证与挖掘。因此,尽管它看似超脱于传统文学史叙述框架外,事实上只是以对立的形式被纳入其中。在这个框架下,《古诗十九首》展现了双重的不适,这种不适既体现在对文本不可撼动经典性的反叛中(以流变的字句和不可靠的传抄为表现),也体现在对诗歌反映个人志趣的前提的破坏中(以程式化的文字组合为标志)。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即使是在这样的不适中,《十九首》仍有其独特的美感与价值,并且不因异文的存在和模件化的套语组合而受损害。
一、“一字千金”[2]——手抄本文化下的“经典”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文本自身的神圣性。所谓“一字不易”与“不刊之论”,强调的都是经典文本的不可变更和自足完满。被推为“千古五言之祖”[3]的《古诗十九首》自然也具有一定的经典性。然而,在手抄本传播书籍的时代,文本几乎从不曾凝滞过,意义所赖以保存的文字被轻易地更改,“作者”、抄写者与阅读者享有几乎同等的权力,在非经学类的书籍中,衍文、错置、删改甚至大段的修订都有可能出现①田晓菲《尘几录》中对这种手抄本文化做了详尽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古诗十九首》等诗歌的流传则由于口头传承因素的加入更为复杂②值得注意的是,自《古诗十九首》的诞生之日到它们被写定的梁朝之间,有着一段可疑的空白。这段时期古诗以何种样貌与状态流传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即使当时已有手写本,口头传承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关曹植的一段描写提醒着我们这种可能性。“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南朝裴松之注所引《魏略》)。“诵俳优小说”显然与诵读古诗有着相似之处,并就文本长度而言更为复杂和难于记忆。如果我们承认口头流传的存在,那么口头文学的某些理论(如帕里—洛德的“口头套语”理论)将同样可能适用于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如果更进一步地想象,我们甚至可以揣测所谓的异文就是口头演绎的数种并行版本,而非某个原本的变体。
大多数异文并不太影响对文本的理解,或者可以明显看出两种版本的不同为传抄过程中的失误。然而有一些异文则将导致迥异的判断,对于这些并不像“失误”的异文,则需谨慎对待。所能见到的“定本”为什么选择了这种异文而非那种异文?这种选择又反映了辑定者怎样的心态?正好比站在一个延伸出数条道路的交叉口,当一个权威告知我们只可以遵循某条“正路”时,或许看一看标有“此路不通”的小道将引向怎样的风景会更为有趣。当然,对异文的选择下武断的结论并非明智,笔者只愿开辟出另外的可能性,以窥知被选择的版本何以当得“一字千金”的美誉。
除了“以”“已”互换通用之类常见的异文外,有一类异文也很有可能为传承过程中的失误,这样的异文通常字形或字音相似,均可以在该语境下成立,时有细微差别。而另一类异文则更像是另外的版本,提醒读者可能存在的不同来源。下即分别举例论之。
《行行重行行》中的“会面安可知”一句,“知”字一作“期”[4]329。与之类似,《迢迢牵牛星》中的“相去复几许”中“复”字一作“讵”,一作“知”[4]331。这些异文意义大体相同而略有出入。在第一个例子中,通行本使用“知”字有一种再见面之日难以预知的迷茫和无力感,而“期”则隐含了不可盼望的意思。并非不知何日相见,而是连日期都不要约定的劝告,使得“生别离”显得愈发绝望。第二例中的“复”较“讵”“知”二字略为难解。“讵”字后加“几时”或“几许”在当时及后世是较常见的用法,如潘岳《悼亡诗》中的“尔祭讵几时,朔望忽复尽”,鲍照《代悲哉行》中的“我行讵几时”,至唐时的“百年讵几时”③[ 唐]韩愈《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二首》中一联“百年讵几时,君子不可闲。”“欢娱讵几许”④[唐]独孤及《送相里郎中赴江西》中一联“欢娱讵几许,复向天一方。”等。尤为有趣的是王维的《偶然作六首·其三》中的“相去讵几许”几乎是该句的原样翻作,这似乎证明了“讵”字在此种语义环境下的使用传统。而“知”字显然更加浅白平易,属于较低修辞层次的用字。在三者之间,《文选》中选择较少用且意义不甚明的“复”字,似乎与传统并不完全吻合。
有两联在定本中对仗工整的语句恰恰在异文中呈现出了并不工整的迹象。《行行重行行》中被广为称赞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4]329中的“胡”有“代”字之异文,而“依”则另作“思”或“嘶”字。此联的出处或许与《韩诗外传》中的“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有关,这一联对仗显然并非十分工整。“胡”与“越”较“代”和“越”更具有对比和两极化的趋势,故而也更适合在对偶中使用。而“思”字以拟人手法将马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提到了和人一样的高度,“嘶”则以纯动物性的词汇将其限制在低等的兽类中。“依”恰好处于二者之间,既有类人的动作姿势,又没有将其动作提升至与人等高的程度。
《青青河畔草》中的“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4]329的另一个版本作“自云倡家女,嫁为荡子妇”。相较前者的今昔对照,后者并非对仗的联句。然而后者却包含了更为有趣的一点细节——“自云”。本来“空床难独守”的内心独白已经饱受道德指责,而“自云”则使接下来的陈述显得更为可信也更加无法曲解掩饰①朱自清先生在《古诗十九首释》中提及了这一异文的存在并认为“自云”“太野了些”,“引文没有被采用,这些恐怕也都有关系的。”(见《朱自清马茂元说古诗十九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其中论述《青青河畔草》一节的末尾。)在后世儒学乃至理学传统的影响下,这一不太符合传统女子规范的行为的确很容易被“屏蔽”或被有意识地修改。但对朱自清先生有关异文的这一联与上下文衔接并不顺畅的论述,笔者持保留意见。。并且,言语这种向外发散的动作不仅从听觉的角度丰富了画面内容,更在“出素手”的动作“越轨”的层级上更进一步升级,使得诗中女子的形象愈发直率放浪。同时,“自云”暗示了一个距离女子较近的听者的存在(这个听者包括每个阅读这首诗歌的人),无论这个听者是否真实存在,显然,他与女子已经处在超出礼法所允许的距离内。
有些异文则可能将诗歌导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东城高且长》中一句看似不起眼的“驰情整巾带”[4]332有“中带”的异文。由于《东城高且长》中两段并不融洽的内容,对这一首诗究竟本为一首还是两首偶然凑成则成为历代论者讨论的焦点,对后半段主人公的判定也难有定论。但“巾带”和“中带”有着相当不同的性别指向。与“巾”相关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男性,而“中带”则无比明确地指向女子的内衣带②见《仪礼·既夕礼》:“设明衣,妇人则设中带。”郑注:“中带若今之裈衫。”。在“燕赵多佳人”的后半部分中,对女性的描写贯穿始终,前半部分直抒胸臆的男主人公并未直接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中带”更为恰当。但视角的游移转化在《古诗十九首》中并非特例③如《涉江采芙蓉》中游子与思妇的视角转换。,也许在此处拼合型的模式再次出现,因而穿插了一段稍显突兀的自述。
《庭中有奇树》中在对奇树之花进行细致描写后,有“此物何足贵”[4]331的感慨,而另一版本作“此物何足贡”。学者木斋据后者推测此诗与曹甄之恋有关④参见木斋在《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中的相关论述,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能否以“贡”字的“进献”义将其断为下级对上级用语尚且存疑。如果仅将其作为“贡诚”之意,那么“贡”与“贵”的分歧显然有着微妙的态度差异。“贡”字表明:这花配不上你,它不值得被送给你;而“贵”字则隐含了“本来奇花是很宝贵,只不过没有你那样珍贵。”的递进义。当然,由于二字的字形十分相似,也不排除二者中其一为抄写错误的可能。
看上去并不太像是“失误”的一个异文出现在《西北有高楼》中的“愿为双鸿鹄”[4]330。“鸿鹄”又被替为“鸣鹤”与“鸣鸟”。“鸿鹄”与“鸣鹤”或许在字形的层面上有可能被误认,但由于“鸣鹤”一词在古诗中的出现绝非特例⑤有关诗句如鲍照《拟阮公夜中不能寐》“鸣鹤时一闻,千里绝无俦。”,武断的仅仅将其定位为抄写错误显然有失考量。这或许是流传的两个不同诗歌版本,而非一个“正本”与一个“误本”。“鸿鹄”在汉魏诗歌中的出现频率显然高于“鸣鹤”,并且几乎成为了一个结尾套语,那么,少见的“鸣鹤”与“鸣鸟”(“鸣鸟”似乎转自“鸣鹤”)是代表了另一个已经湮灭的传统,还是在大传统下偶然出现的小波折?这些已无法得知,但至少,它指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让我们得以重新思索对套语的认知。
还有一些极为有趣的异文,如《生年不满百》中的“仙人(小人)王子乔”[4]333等,这里不一一细解。这些异文摇摆浮动于所谓的、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原本”上,迷惑了我们企图追寻诗歌初始样貌的目光。而后世诗论者多将其作为自诞生之日就恒定不变的“经典”整体而加以分析,自然会将“一字千金”之类的激赏慷慨赠予。倘若我们所看到的定本只是流传过程中无数大同小异(有时也许有“大异”)版本中的一个,那么这一文本的权威与经典地位势必将遭到质疑,建立在其权威性基础的赞誉则也将随之瓦解——幸好,《古诗十九首》本身的美感已足以相称对其大多数的褒奖,而这或许也是众多异文存在但人们仍将其奉为经典的部分原因。
这些异文同样提醒我们,论者常用来作为坚实基础的文本其实并不可靠。在推敲诸如“为什么定本选择此字而非彼字”之类的问题时,我们已经落入了圈套。将某个字句的妙用推崇至极高的地位则有类似的危险⑥例如陶渊明诗中著名的一联:“采菊东篱下,悠然望(见)南山。”《诗人玉屑》与《能改斋漫录》中载苏轼以为“无识者以见为望,不啻碔砆之与美玉。”然而目前对陶渊明的诗歌原本应为“见”还是“望”尚有争议,仅以“见”优于“望”的论述来阐述陶渊明诗歌的风格显然是不完全可靠的。。通过“错误”的文本来前溯作者的“本意”显然是缘木求鱼,而面对散佚已久,在距离创作时代近三世纪后才得到重新编定择选的汉魏诗歌时,我们又有多大的把握声称自己面对的文本就是“正确”的?齐梁时代择选者的品味与传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错误暂且不论,即使在它们被创作出来的最初阶段,这种可能有着大量口头创作成分在内的作品本来就无所谓“正误”之分,每一个被创作出的版本都有着自身所适合的环境与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纠结于细节的考证显得徒劳而可笑。
这便提醒读者,有些时候文本细读的方法并不适合《古诗十九首》之类的中国早期诗歌。“不可字求”的告诫不再仅是阅读指导,而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对于这些诗作,我们唯一能够确认不变的,只有其中饱含着的浓烈情感,这种情感由生死无常和人生苦短的感慨触发,并通过离别与衰老两大主题表现出来。异文的存在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情感的抒发和表达,这也是即使文本流变而人们依旧相信它们代表了经典的“原貌”的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这些被我们相信反映了创作者内心的情感都不再可靠①此处的“可靠”指情感的独特性、私密性与被表述的原创性。,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作品呢?
二、“天衣无缝”——并非自由拼合的模件
雷德侯在《万物》一书中这样定义他在书中用来形容中国艺术规模化生产的术语“模件”——“零件可以大量预制,并且能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迅速装配在一起,从而用有限的常备构件创造出变化无穷的单元。”[5]4《古诗十九首》以及众多被认为产生在汉魏时期的古诗及乐府中(这二者之间通常会出现分类与界定的混乱)有着与这个定义相近的语言组织模式。并且,这些频繁出现的套语的组合模式也十分固定,一个意象或主题会像指路牌一样导向另一个主题②宇文所安在《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一书中对这一现象做出了细致的分析。。这一组织模式显然与人们所惯常认为的那样不同,即认为诗歌是一种完全表现诗人内心感受的自由形式,它并不应有固定的语言叙述套路,倘若庸俗的作者不幸堕入了套路中,那么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诗人③这与人们对“原创性”的追求有关。在文学史中,对“源头”的追溯,同样反映了人们更倾向于对位于较早时期的个体赋予更高价值。尤其在诗歌中,人们“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的行为显然是对“套路”竭力避免的结果。。正如钟嵘所认为的那样,只有毫无拼接痕迹的“天衣”才配的上《古诗十九首》的浑然天成④见钟嵘《诗品·古诗》:“天衣无缝,一字千金。”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亦有“《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处”语。。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单独看《古诗十九首》,那么这些套语以及其相互组合关系已经有了重复出现的迹象。最常出现的一个话题即对人生短暂的感慨,这一情感的表达有着标准化的模式,即“人生XXX”⑤汉魏诗中有关“人生”的诗句的搜集和整理可见于[美]宇文所安著、胡秋蕾等译《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Stephen Owen《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6月第1版,第379-381页。。人生也可以由“生年”“年命”等近义词语替代。而其后所加的三字语不是以比喻或否定形式如“非”“不满”等来表达寿命之短,就是描述性的“一世”“天地”(后一句再以比喻、反问或直接陈述等极写时间急促)。产生这一感慨的场景也是标志性的——不是极凄冷的旷野墓地就是极欢愉的游乐宴会。这一句话在诗中出现的位置则较为随意,既可以放在开头而引发及时行乐的行为,也可以放在对枯寂景象的描写后,仿佛触景生情般得出了结论。不管怎样,这个话题后必然紧跟着另一个话题:及时行乐或追求功名。(这二者在本质上都是悟得生命长度之短暂后努力求得生命密度的增加)。
将目光放宽至汉魏诗歌,则描写人生苦短的类似诗句不胜枚举,出现的场合也与之相仿。一个略略熟悉相关背景的读者在看到这句诗时很容易产生心理预期,能猜测到之后的诗歌走向。很明显,这样的模式使创作变得有迹可循,也使作者被限制在狭小的框架内,所有能够表达的事物以及表达的方式均已被传统规定,他所能调整的只是具体使用过程中的细节,如究竟用什么比喻来形容人生之短。正好比已经基本定型的模件,其所应被安放的位置已经排定,工匠能做和应做的就是将它细微地打磨至更适合的状态。这样的比喻很容易颠覆人们对诗歌创作的基本印象,尤其是将“艺”层面的诗人与“技”层面的工匠相提并论或许会冒犯到那些坚信诗歌艺术纯粹与自由性的人们。但这样的比喻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将《古诗十九首》放回古诗与乐府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无数的相似乃至重复。
《明月何皎皎》中的“忧愁不能寐”[4]334就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曹丕《杂诗》中的“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曹叡乐府诗中的“忧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长”;《长歌行》中的“静夜不能寐,耳听众禽鸣”;徐干《室思》(四)的“展转不能寐,长夜何绵绵”;王粲《七哀诗》(二)中的“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以及著名的阮籍的《咏怀》中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等均表达了这个主题。其中可以发现无数模件式的组成部分:(经常是秋日的)明月、揽衣、床帏、抚琴、鸣鸟(虫)、观星、泪下等。这些模件并不一定要全部出现在每一首诗中,而是由诗人的个人喜好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进行拼合。但有些核心是无论怎样都不能被省略的,如关键句常为“XX不能寐”。组合的顺序也不能轻易更改,通常诗中的主人公在夜晚难以成眠,于是披衣走出室外,见到明月或星空,听到鸟啼或虫鸣,因此忧愁难止,叹息或流泪。有时作为附带,还会有主人公走回房内的结尾。
“夜不能寐”并非是单独出现的主题,“不能寐”的原因如果在诗中被提及,要么是客行在外的思乡之情和彷徨不见出路的“穷途”之感,要么就是思妇怀游子的相思之情。因与思乡有关,诗中也往往有淹留外乡而志不得成的悲慨。于是这个主题便成为引向行旅主题的一个楔子。的确,这些情感很有可能是当时可以创作诗歌的群体所共同具有的,但是令人怀疑的是,这些作者是否真正有着如此相似的夜中徘徊的经历?词汇以及词汇间组合高度近似的诗歌并不太可能产生自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中,唯一的解释即这些作品也许产生自诗人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受到传统的高度影响①即诗人的创作并非完全是“触景生情”,而很可能是“缘情造境”,即为了表达某种情感而沿用现有的模式化情景,使读者一接触到这一文本,就能在典型化的场景中迅速理解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这些标志性的情景可以在汉魏诗歌中被频繁发现。。
这种影响并不仅是简单的相互模仿与拟作,而是一个口头诗歌形成与传承传统下作者们下意识的趋同倾向②相关口头诗歌的论述可见[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中华书局,2004年5月第1版。。他们在一个可能存在的(尽管是非主观形成的)庞大诗歌语料库与组合规则的影响下,将一些词汇娴熟地加以小幅修改并重新组合,而这种拼合的程式化以及模件化在汉魏诗歌中并不稀见。
《古诗十九首》中涉及音乐的三首《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和《东城高且长》,后两首与音乐密切相承接的结尾均为化作双飞鸟,而《今日良宴会》虽无这样的套语,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在音乐的描写与结尾中间插了一段较长的叙述,从而干扰了这一模式的形成。由音乐引出化为飞鸟的愿望屡见不鲜。曹丕的《清河作》与《善哉行》中均有在对音乐的详细描述后“愿为晨风鸟”和“比翼翔云汉”的描写。为什么音乐能引起比翼高飞的联想已不可知,或许与悲乐之慷慨激昂有关,又或许与描写音乐的“奋”“发”等字引起的想象有关,也有可能只是习惯性的套语,在结尾处以示终结,并无实际意义。无论怎样,这显示了模件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固定的模式下填充同属一大类的事物,具体选择则因人而异。在化为鸟的例子中,鸿鹄、鸣鹤、晨风、飞燕、黄鹄等鸟类均可以被放入“愿为XXX”的框架内,表达的意思则几无差异——读者心知肚明此处只是需要一种飞鸟而已。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古诗十九首》的第一首《行行重行行》几乎是聚合众多模件的范例。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套语。“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令人老”“努力”等。这首诗是《古诗十九首》中拼合最多而模件最为丰富的一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很适合“发凡起例”。虽然这些模件频繁出现在其他乐府诗歌中,却并不影响它们被放在此处的语意表达。相反,它们融合得“天衣无缝”。尽管如此,拼合仍令人起疑,这些模件能否表达出作者真实的想法?拼合是否有损于诗歌的艺术性和自由性?
这些问题难以得到确切的回答。但读者至少要放弃一部分对诗歌的过分想象和苛求。诗人个人的创作灵感和天才喷涌当然值得激赏,然而被“组成”的诗歌如果自然流畅,那么也应得到赞扬。只是这并不太符合我们对“诗歌”的期待。或许用雷德侯形容中国文人画的话语来解释这个问题更为合适——“富于个性的艺术手法,正是文人画家的作品区别于工匠的特质所在:在不断变化的细节描绘中发挥无穷无尽的创造热情。”[5]280
结语——诗能否“观”①“诗可以观”出自《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对“观”字的解释,郑玄认为所观为“风俗之盛衰”,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熹,即认为《诗》可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诗经》的文本在产生之时固然承载了向统治者表现风俗盛衰以及政治得失的历史使命,然而,在文本基本固定后,也就是在孔子说出这句话的春秋时代末期,士大夫对《诗》的使用已经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完成了文本和初始创作目的的分离,这可被视为对文本的二度“创作”。对《诗》的熟练运用成为考察引用者是否为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政治家的标准之一。相关的例证可以在《国语》《左传》中大量发现,不复赘述。因此,此处对“观”的解释,应为“观察使用者是否能够正确运用《诗》进行顺畅的交流”以及“观察使用者(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作者)运用《诗》所要表达的志意并推测其前途命运”。本文正是着眼于“观”的这一含义,讨论“中国早期古典诗歌(此处特指《古诗十九首》)究竟能否表达作者的个人志趣”这一问题。
对《古诗十九首》异文与套语的分析使钟嵘“一字千金”“天衣无缝”的评语显得无比尴尬。一方面,异文的存在使一切针对个别字句的夸赞都显得可疑;另一方面,套语的拼合使“无缝”的评语简直像反讽——虽然钟嵘并无此意。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两句评语又的确成立。“一字千金”,因为文辞精妙、每一字都有着深重的情感;“天衣无缝”,因为模件组装的太完美,以至于令人看不出拼合的痕迹。
在传统“知人论世”的批评理论框架下,《古诗十九首》是一个具有特性的个例。因其无法获知除文本自身外的几乎任何信息,任何企图从外围来接近或阐释《古诗十九首》的尝试都不可能达成。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后世之人只得反其道而行之,用另一个与“知人论世”相反相成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组文本,即“赋诗观志”。评论家正因为相信文本与作者间有着几乎对等的关系,对作者的一切描述实际都适用于文本,才以“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②见[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的方式从文本来反推背景。这一尝试要求双重保障:一重来自文本的可靠性;另一重则是文本与作者间连接的紧密性。不幸的是,《古诗十九首》在这两方面都未能经得起质疑。
而作为远离《古诗十九首》创作环境近两千年的当代读者,唯一可以作为赏鉴依据的便是现存的诗歌文本。论者便更加习惯性地将这一支点当作坚牢的出发点而对想象中的作者生平、创作心理乃至时代环境加以考证,并得出看似无懈可击的结论。只是中国早期诗歌的文本远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稳定可靠。首先,在文本的产生阶段,就已充满了口头诗歌的即兴与多变,更兼高度的相似与拼合;而在文本的传承阶段,则充满了偶然的增删与修改。最终呈现在齐梁人眼前与当代读者眼前的《古诗十九首》,正仿佛一场文字游戏中的极少数幸存者,难以呈现出“原始”状态的完整面貌。
笔者强调这一点,并非过于注重偶然性而忽视必然性。当面目全非的、并且有可能在创作伊始就是因袭的而非独创的文本成为一切论述的基石,这些论述的可靠性也不得不遭受质疑。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古诗十九首》所获得的如此高的赞誉,绝非因其文本中异文与套语的存在便能抹杀的。事实上,正因为其部分离开了“知人论世”的框架,论者才更能将注意力移向文本本身,而不像其他有着确切固定位置的文本,被完全安放回特定的时间线索。并且,这些诗歌中的情感便不再只是一人一事一时一地的感怀,而升华为对人生境遇的普遍关切。作为一面可以折射出“人人心中有而不能发”的情感的镜子,《古诗十九首》无疑是当得上“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称誉的。当我们回溯千年的时光,在遥远的诗歌中找到心灵共鸣时,那种难以表达的心事被一语道破时的惊异与震动,足以推动这组诗歌作为经典一代代流传下来。
“悲莫悲兮生别离”,生离与死别,人生中不可避免又最难面对的两种情形,正是《古诗十九首》的两大主题。在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威胁与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下,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索与实现是其作者们想要完成而不能完成的。《古诗十九首》的一大震撼与魅力所在,就是在明知无价值中努力寻找价值的徒劳而决绝的举动。对人生存在意义之疑问是人类共有之疑问,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人类永恒求索的目标。而《古诗十九首》又以平实自然的语言出之,避免了华丽的辞藻可能带来的对意义的伤害和注意力的转移。这也是它得到后世读者喜爱、推崇的原因之一。
《庄子·外物》有言:“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一表述大体适用于对《古诗十九首》的阐释与探寻。在文字并不完全可信的情况下,仅仅依赖文本而探求出的结果自然也摇摇欲坠,但这并不意味这诗不可以“观”。只是,诗中究竟可以“观”出什么?哪些诗中的“观得”可以被相信并被还原至作者与时代?谨慎地避免将诗歌完全当作个人心志的抒发,小心地考量作者与作品间复杂的联系,或许是最为恰当的做法。
[1]胡应麟.诗薮:内编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6.
[2]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75.
[3][明]王世贞.艺苑卮言[M].罗仲鼎,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73.
[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雷德侯.万物[M].北京:三联书店,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