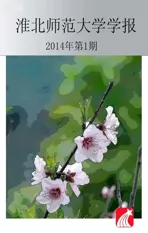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2014-04-07唐明亮
唐明亮
(南通大学 范氏诗文研究所,江苏 南通 226019)
诏令奏议是最直接反应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意志的材料。《汉书》自《武帝纪》至《平帝纪》的七个本纪,以及《王莽传》的内容,主要以诏令奏议为主。这七纪一传中的诏令奏议中,引用、转述、摘抄了大量儒家经典中的内容,并以西汉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解释——经学——来处理各种政治事务,反应了经学在西汉不同时期的地位。比较西汉时期诏令奏议的前后变化,可以看出经学与西汉政治之间的关系,为梳理汉代经学的产生、发展、蜕化的过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汉武帝时期诏令的前后变化
如果以经学地位的变化为依据来给西汉时期分段,那汉武帝时期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其前期诏令与后期诏令,在内容和文风上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为了揭示这一变化过程,首先需要对文景时期的诏令的特点稍作总结。
文景时期的诏令,有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文风朴素,用语平实易懂;其次,所宣诏令既不引用儒家经典,也不以儒家经典中的故事为制定国策的依据,而是以古之成法为制定国策的依据。其起句往往是“古者”“古之治天下也”寻找古制之类的语句,所引用的语句多为民间谚语;再次,诏令的具体内容,都是处理国家事务,如重农、轻徭薄赋、减省刑法、安抚藩王等等,并不涉及到灾异、祥瑞等内容,总体来说是非常务实的。试举一例为证: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1]115
《汉书》文帝纪中共记十五条诏令,景帝纪中共记十条诏令,都显著地凸现了这三个特点,无一例外。武帝即位以后,这种诏令风格渐生变化。
汉武帝即位之初,太皇太后窦氏掌权。窦太后好黄老之术,故儒学不昌。御史大夫赵绾、王臧欲兴儒术而下狱至死。在窦太后生前,仅见武帝一条诏令:
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则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1]156
这条诏令的内容和风格,与文、景二帝时期的诏令几乎完全一致。太皇太后窦氏死后,汉武帝提倡儒术,董仲舒的经学思想得以大行其道,这是西汉经学史,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经学史的开端。董仲舒对于儒学的阐释,不仅关注治国治民,而且还关注天人之间的沟通,这种沟通在人间的反应就是各种祥瑞和灾异现象。其所著《春秋繁露》一书不断申述国家政治与阴阳异象之间的联系,如:“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2]101董仲舒所提出的这种观点,是将阴阳家的理论融入到了儒学中来,其理论依据是“同类相动”,“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2]358如此对统治术的解释,大受汉代统治者的欢迎,但也为儒学走向神秘化埋下了伏笔。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汉武帝时期诏令之文风大异于前。元光元年(窦太后崩第二年),汉武帝所下诏令行文已见明显变化,其文曰: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呼,何施而臻于此!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1]160
可以看出,这条诏令富有极其浓重的儒学色彩,重在讲修德治国,并引儒家经典中唐虞故事。尤其是它体现了董仲舒公羊家所宣扬的“天人感应”思想,所谓德及鸟兽、麟凤、河图洛书等等,明显是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与文景时期的诏令相比,其变化有三:一、常引三王、五帝、殷周故事作为定国是之依据,诏令中的首句往往以“昔在唐虞”“五帝”“三代”等词为引;二、除宣扬“仁”“义”“爱人”等儒家教化外,诏令中常直接引用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以为制定国策之依据;三、开始关注灾异、祥瑞,借以宣扬儒家的治国理念。可见,这些诏令特别注重宣扬儒家思想。但此时的诏令绝不是仅仅注重宣扬儒家的教化,也继承了文景时期务实的特点,对民生问题也表现出很大关注,试举一例:
朕闻咎繇封禹,曰在知人,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盖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已赦天下,涤除与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悯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1]174
《汉书·武帝纪》共收录元光元年后诏令二十六条,称引三王五帝故事的有五条,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五条,记祥瑞的两条,关于外交和军事的各两条,轻徭薄赋和减省刑法的九条,共引儒家经典三部六句。可见,虽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从一出现便开始影响汉代统治者的决策,但这一时期的诏令内容虽然大力宣扬儒家思想,但主要关注的仍然是现实中的政治问题。
二、昭帝纪至平帝纪中所见之诏令
昭帝以后,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加强,不仅在中央设五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连皇帝本人也亲自研读,并不断注意在各郡国选举研习儒家经典的学者,授以官职。汉昭帝时的诏令曰:
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1]223
而汉宣帝也是“师受《诗》、《论语》、《孝经》”,其德行“操行节俭,慈仁爱人”,颇合儒家所宣扬的人君之风,故霍光奏请太皇太后迎其继承昭帝之帝位。此后元、成、哀三帝,习儒之风愈来愈浓。史称元帝“柔仁好儒”[1]277,成帝“壮好经书,宽博谨慎”[1]301,哀帝通习《诗经》。故儒学对统治策略越来越起到决定性作用。从昭帝至平帝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两个变化,其一是诏令中完全体现儒家的治国修身思想。在形式上表现为引用儒家经典语句增多,不仅引用《诗经》《尚书》《左传》中的内容,而且将其中语句转述为诏令内容,故其文风颇似儒家经典中之古文。如:
夫《洪范》八政,以食为首,斯诚家给刑错之本也。先帝劭农,薄其租税,宠其强力,令与孝弟同科。间者,民弥惰怠,乡本者少,趋末者众,将何以矫之?方东作时,其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致劳来之。《书》不云乎?“服田力啬,乃亦有秋。”其勖之哉![1]314
这是一则劝农桑之诏令,短短一百余字,竟引用《尚书》两处。文末“其勖之哉”,与《尚书·泰誓》中之“勖哉夫子”,《牧誓》中的“夫子勖哉”文法类似。可见,无论从文体上还是从内容上,这一时期的诏令都完全“儒化”了。除此以外,在减省刑罚、轻徭薄赋、选举人才的诏令中,动辄引用儒家经典作为依据。自《宣帝纪》至《平帝纪》,共记录诏令88条,直接转述或引用儒家经典语句30条。另外,如“温故知新”“战战栗栗”“辜在朕躬”“惇任仁人”等词也均出自儒家经典中,所见不甚枚举。故这一时期诏令的文风大异于汉初诏令,也可见经学在汉代统治思想中得到不断地加强。
其二是更加关注灾异、祥瑞、阴阳等问题。《汉书》宣帝至平帝时期的各个本纪中,记载灾异的内容比其他各种历史事件的总和还要多。这表明最高统治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逐渐发生了转变,而关于这类问题的诏令也大量出现。自汉初至武帝时期,有关灾异祥瑞的诏令仅有两条,而宣帝至平帝时期这方面的诏令共有32条,并且篇幅较长。宣帝即位后的第一条关于灾异的诏令,是在四十九郡国大地震之后发布,其文曰:
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琊,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2]245
该诏令之目的在于罪己、求贤治国,所求之士为通儒家经典的贤士,但诏令中尚未将灾异与儒家思想联系起来,并未从儒家经典中找出解释。在此后几年所出现的地震和祥瑞等事件中,汉宣帝的诏令大抵与此相同。五年以后,即元康元年,汉宣帝再下诏令追忆地节二年凤凰集于鲁郡之事,在内容上便起了很大变化。其文曰:
乃者凤凰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极。《书》不云乎?“凤凰来仪,庶尹允谐。”其赦天下徒,赐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1]254
该诏令除了“朕未能章先帝休烈”一句与之前“未能和群生”等句式相同外,其他内容完全迥异。不仅将凤凰、甘露的嘉瑞与儒家经典联系起来,而且在文风上也完全采用儒家经典中的语言,如“调序四时”“夙夜兢兢”等等。在此后的诏令中,都表现出对四时阴阳、灾异祥瑞极大的关注,进一步宣扬天人感应说,并力图从儒家经典中找出答案,以解释这类现象与现实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是以阴阳风雨未时。”[1]255“三月辛丑,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观。朕之不敏,惧不能任,娄蒙嘉瑞,获兹祉福。《书》不云乎?‘虽休勿休,祗事不怠。’”[1]266这些都是以儒家经典来解释祥瑞灾异,并据此来规劝百官,大赦天下。
由此可以看出,儒学在指导汉代国家决策中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统治者由原来直接引用儒家经典发布诏令,转而依靠儒家经典来解释灾异祥瑞,借以宣扬天人感应以治国,给儒学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宣帝时对灾异祥瑞的解释,虽然依据儒家经典,但并未完全脱离实际,统治者们依然以对现实问题处理的好与坏来推测灾异祥瑞产生的原因。随着灾异祥瑞被越来越多地关注,使得儒学渐趋神秘化,脱离了实际政治。在西汉成帝以后的诏令奏议中,儒学这种神秘化倾向愈来愈明显,至王莽统治时期则发展到极致,如同宗教。这一变化,在《王莽传》中可以明确地看出。
三、《王莽传》中所见之诏令、奏议
《王莽传》分上中下三卷,分别记其即位前后之事迹,故笔者将其传记中的诏令、奏议也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王莽即位之前的史事中可见,自汉成帝统治后期,儒家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褒贬人物的唯一标准。王氏家族虽位居显赫,但王莽初期仍是孤贫。最终得以征召,正是因为他“折节为恭俭”,侍奉世父大将军王凤“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颇有儒家经典中所见古贤者之风,因此赢得朝野一片赞誉之声而登用。
从这一时期的诏令奏议中,可以发现西汉经学在国家政治中的指导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首先是古文经学地位的提高。从王莽辅政之初开始,其行事动辄以儒家经典中所记之古事古言为依据,在制度方面也更加注重发掘儒家经义,尤重古文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1]4069
因王莽言行颇合儒家经义,故其同党常在他的授意下据此为其请赏,哀、平二帝在位期间,册封赏赐王莽的诏令接连颁布。在册封赏赐王莽的诏令中,对古文经的引用开始增多,不仅引用《诗经》《尚书》,而且引用《论语》《左传》。而为王莽请赏的官员奏议中,也大量引用古文经,在张竦和陈崇称颂王莽功德的奏议中,共引《论语》《尚书》各四次,《诗经》五次,《易》一次。在这些奏议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大量引用《左传》中的故事以解释《春秋》之义,这表明古文经学的地位愈来愈显得重要。而奏议中所引《春秋》,都是指《左传》,如“春秋晋悼公用魏绛之策,诸夏服从……魏绛于是有金石之乐,《春秋》善之。”[1]4063“《春秋》列功德之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贤然后能之。”[1]4066此外,如“九族亲睦,百姓既章,万国和协,黎民时雍”取自《尧典》,“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出自《左传》,封赏敕文中的“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胄一具,秬鬯二卣……虎贲三百人”出自《周官》,又见于《左传》,以上典籍皆属古文经,而此时大量引用古文经的诏令不胜枚举。在后来的奏议中,又见引《谷梁传》“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可见,此时《公羊传》在经学上的地位,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其次是经学宗教化的倾向愈来愈明显。在各类事件的处理上完全取法儒家经典,甚至仿照儒家经典中之先贤圣王作策作诰。平帝生病,“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1]4078这是仿照《尚书·金滕》中周公代武王赎身之事。各地起兵反对王莽擅权时,王莽亦仿《尚书·大诰》所记周公故事,作《大诰》,“谕以摄位当反政孺子之意。”[1]4078对其他各类政治事件的处理,也完全依照经典而行,经学的宗教化倾向愈来愈明显。
经学宗教化倾向的另一个表现即是更加注重以儒家学说来解释天人感应。在诏令奏议中,沿袭了前代以“仁”“礼”等伦理观念解释“禾长丈余,一粟三米,不种自生,醴泉自地出,凤凰来仪”[1]4079等祥瑞以外,又开始将它们作为解释谶纬的依据。谶纬“是有文献体系的政治神话。其中有完整的三皇五帝系统,感生受命的传说,精心阐释的符瑞,有哲学、神学、历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种文化因素,这些都被纳入阴阳五行的天命周转之中,作为解释政治、推测天意的工具”[3]。它开始出现在西汉哀、平时期,其所宣扬的三皇五帝天命周转的规律常常依托儒家经典中的记载,但早期并不与儒家的伦理观念相联系。元始五年,为助王莽篡汉,有人作谶语于白石上,书曰:“告安汉公莽为新皇帝”。太后斥之为诬罔,而王舜则以《尚书》中“天工,人其代之”为解,为王莽索取更大的权力。这是以儒家经典解释谶纬,助王莽接受符命的开始。其后刻有谶语的石块、石牛,乃至梦中谶语不断出现。其中有“摄皇帝当为真”一句谶言,王莽上奏议解释这句谶语大量引用古文经中的文字:
《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此二经周公、孔子所定,盖为后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称假皇帝。其号令天下,天下奏言事,勿言“摄”。[1]4094
这是王莽利用儒家经典解释谶言,为进一步篡权寻找依据。因王莽以谶纬篡位,故其即位后完全确立了经学和谶纬的准宗教地位,在其即位后的诏令中这一特点表现得更加显著。
王莽即位后所发布的诏令中,儒学的宗教化被发挥到极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1.文体上几乎全仿古文经。其册封孺子婴的诰命最为典型,其文曰:
咨尔婴,昔黄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于予躬。《诗》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尔为安定公,永为新室宾。於戏!敬天之休,往践乃位,毋废予命。[1]4100
此诏令前半部分仿《论语》,《论语·尧曰》记尧策命舜:“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4]756而后半段则仿《尚书》,“永为……宾”仿《微子之命》,“敬天之休”出自《洛诰》,“毋废朕命”仿《盘庚》等篇。在诏令的撰写上,由原先的转述、引用转而变成完全摘抄。
2.关于改制的诏令,力求恢复儒家经典中的古制,而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王莽依照儒家经典所作的改制颇多,所作新制度都仿照《周官》《尚书》等古文经中所记故事,毫无实际意义。其中最与现实相背离的就是恢复井田制度,限制奴婢买卖。其诏令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又曰:“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於臣民,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书》曰:‘予则奴戮女’,惟不用命者,然后被此辜矣。”[1]4110其改制本意,是为了解决西汉末年土地高度集中以及人口买卖问题。其中“天地之性人为贵”一句出自《孝经》。[5]36然其脱离实际,一味信古泥古,迷信儒经,将儒家经典教条化,甚至在惩罚措施也取法于《尚书》,对违法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此改制严重脱离实际,故犯法者甚重,“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1]4112于是,反对新莽政权的人越来越多。
3.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问题时,也是教条地依照儒家经典行事。其诏令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谬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1]4105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出自《礼记》的《曾子问》《坊记》等篇,王莽据此将诸侯王以及西汉时期所封的周边少数民族首领的王号一律废除,收回汉王朝颁发的印玺,而改称他们为“侯”,于是招致四方少数民族的反对。自始建国二年至四年,匈奴、句町、夫余、秽貉、高句丽、西域以及南蛮纷纷起兵反抗,三边战事纷扰。然王莽一意孤行,四处出兵,州郡苦于军粮供应,使百姓疲敝,遍地流民。各种矛盾迅速激化。
此外,因王莽篡权利用了谶纬符命,所以笃信符命,于是当时人为求富贵,“争为符命封侯”[1]4122,而其大臣也借符命恢复古制,破坏了原本征召、察举、辟除的选拔程序,也威胁到王莽的统治。其所制定的六筦制度、官吏俸禄制度、礼乐制度等等,也皆依《周礼》所记之古制,施行不便,又禁令繁多,所以官吏得不到俸禄,百姓为生计所迫,相聚为盗贼。对于如何安抚民众,王莽不着眼于现实,却又从儒家经典寻找依据,通过不断改官名、国名、赐姓来顺应符命,为其统治的困境解围。下诏曰:
《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帝,
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
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
未明,乃今谕矣。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
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
盛德,生生之谓易。”予其饗哉![1]4154
王莽作此诏令,“欲以诳燿百姓,销解盗贼。众皆笑之。”[1]4154在王莽统治后期,直视儒家经典为沟通天人的圣经,虔诚地信奉儒学如同宗教。因此,这类遭世人嘲笑的荒诞诏令频繁颁布,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反而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最终导致其政权的崩溃。
四、结语
从《汉书》七纪一传的诏令中可以看出,自儒学在西汉统治阶层中确立了指导地位以后,汉代经学在政治上的作用愈来愈重要。经学作用于政治,使政治更加依赖经学,于是统治者便不断拔高经学地位,二者之间的依赖性愈来愈强,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结果就是儒家学说由指导国家的纲领逐渐上升为一种宗教经典的地位。这种变化在诏令奏议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1.儒家经典中的内容,由国家政策的指导思想逐渐转变为具体政策条文;2.古文经学在国家政治中地位隆升,复古的倾向明显;3.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在政治上的作用被不断夸大,诏令内容由原来着重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演变成完全利用儒家经典解释灾异、祥瑞、谶纬等神秘现象,以证明统治是否合法。总的来说,西汉的经学在政治与学术的互动之中愈来愈走向神秘化、宗教化,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致的一种表现,也是其蜕化的一个征兆。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徐兴无.谶纬与经学[J].中国社会科学,1992(2).
[4]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邢昺.孝经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