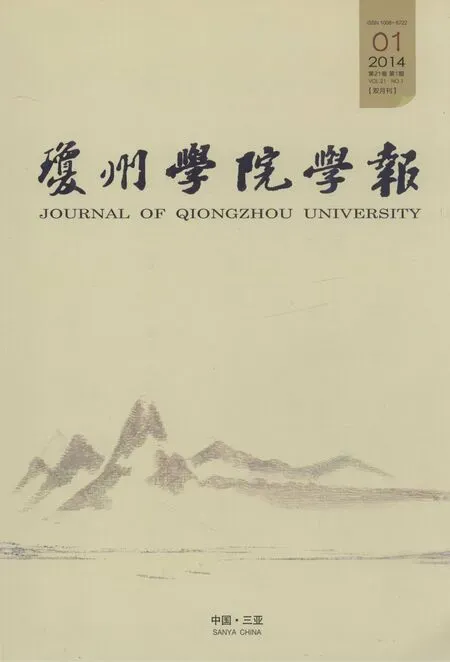学术史的抉择
2014-04-07木斋
木 斋
《琼州学院学报》开设的《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专栏,包括本期已经四期,对以《古诗十九首》为中心所连带六朝文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成果斐然,值得祝贺。主编邀请我来主持此一期专栏,惶恐惶恐!专栏此前的几期以我的汉魏古诗研究作为讨论中心,原本我是不应该参与的,学者理应专心研究,而不承担传播和接受的学术史责任。《琼州学院学报》开办的此专栏,截止本期,所发表的十余篇论文,确实很有特色。就其作者而言,多为青年才俊;就其作品而言,视角新颖,才华横溢。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广阔的学术视野,从而将汉魏古诗的研究,引向更为深入的问题讨论之中。未来之学术史,必定会能认识到这些研究的学术价值。
以本期所发表的两篇论文为例,就其研究的深度、广度而言,都无疑是一种飞跃,且具有相当敏锐的学术史走向的针对性。譬如当下有相当多的学者,对《古诗十九首》的产生时间,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东汉末年”的说法。这一说法,较之传统主流的“东汉中后期无名氏所作”之说,显然前进了一小步。说《十九首》产生于东汉秦嘉的桓灵之际,或说是公元160年前后,这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十九首》这样的“意悲而远,文温以丽”,令人能产生“惊心动魄”“几乎是一字千金”的伟大诗歌作品,必定是有伟大之诗人所写,必定是经历过“意悲而远”、“惊心动魄”之人生经历方能写出。而公元160年左右及其前后,不用说伟大之诗人,即便是一般水准之五言诗人,如班固、秦嘉、张衡等东汉零星的几首五言诗作,其真实性也都被以如美国宇文所安先生、日本铃木修次先生所否定,即便不否定,在这些可能会偶然写作五言诗的诗人之中,也毫无伟大诗人之踪影,并无可供学术史遴选的作者候选人。就时代的历史文化特征,政治背景、文人风气等,也还都与《十九首》等古诗的气质风马牛不相及。《十九首》“东汉说”论者,将其说为“东汉末年之作”,可以说是一种且战且退。对于一种错误的学说,且战且退,就是对历史真相的渐次接近。本期专栏所刊登于国华先生之鸿文,正是极有针对性的研究了东汉灵帝时期是否具备《十九首》产生条件的问题。灵帝的鸿都门学,显然是对传统儒家一统的反动,是一种以文学对抗儒学的表现,它对后来的曹魏建安时期的文化风俗,包括五言诗写作的腾涌,新兴清商乐乐府诗的兴盛,都有某种开启意义。但也非常明显,这一短暂的开启,还仅仅是由东汉腐朽的经学统治向建安曹魏文学时代、文艺时代的解放转型的一个短暂的瞬间而已,它还并不具备产生《十九首》不朽诗作的历史文化条件、诗人群体的作者条件和思想通脱解放带来的写作内容、题材条件,以及五言诗体形式的艺术准备等诸多条件。《古诗十九首》,就其写作时间而言,既然灵帝时代尚未具备,则理应在稍后一些的建安曹魏时代搜寻,建安曹魏就传统说法,仍在东汉之版图。当然,《十九首》之作,更多的为魏文帝黄初年间之作。
“无名氏”之说,更为无稽而荒唐。无名氏若解作“失去姓名的伟大诗人”尚可一说,则学术史的裁决,仍可在汉魏时期的伟大诗人之中找寻,而汉魏时期的伟大诗人,则必定在三曹七子之中。三曹七子之中,唯有曹植具备前述的个人生平遭际;“无名氏”若作“不是诗人的无名者”来解,则更为无稽之谈。这就会将诗歌美学的许多根本原理推翻。根本不知道名姓者,就是所谓民间的贩夫走卒,歌姬妓女。我们不能用一个抽象的民间伟大,来假定为一个具体的民间人物——其人根本就不会写诗,但写出了不朽的《十九首》。
其余两文,台湾学者张衡《同声歌》的研究,比起以前相关的研究,显然更为深入,也更为大胆,假定这些所谓汉魏古诗,如同宇文先生所说,是“同一首诗”,它们同本同源,那么,《同声歌》假定为甄后之作,未尝不是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文学侍从》一文,以文学侍从的独特视角,宏观与微观结合,更能看出曹魏建安时代作为一个“历史的夹缝”的特点——《十九首》的特殊性,也只能从这种历史的夹缝中才有可能产生出来。
关于汉魏古诗的研究,自2010年《社会科学研究》首发专栏以来,已经约略有数十篇论文先后在将近十家的刊物上发表,其中多数篇什,是延续着我的研究视线,不,应该说是延续着现代学者徐中舒、罗根泽包括梁启超先生的新方法论走下来的,以内证外证结合,以作家作品的演变历程为根据的新兴方法论,显示了学术史在往前走(我本人的研究,不过是现代学术新兴方法论演变的延续和必然结果,是这一方法论学术史长河之微不足道的水滴);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一些所谓商榷论文的陆续出现,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说:我就像是匆匆夜行肩负使命的使者,顾不上道路两边抛下的砖石瓦块,更顾不上暗夜中射来的暗箭,我要匆匆赶路,去传递火把和光明。坦率说,这些商榷,不能说是商榷,他们并未读懂我的研究,或说是故意没有读懂,顽固地将已经定型于他们思维之中的陈腐旧说作为论据,全然不顾这些所谓的历史记载,在历代学者的论证和揭示下,早已经被证明是历史的谎言,裸露出它们原本的历史真相。
自今年秋季,从台湾中山大学客座任上返回以来,我就结束了汉魏古诗研究工作,而转向了先秦文学的研究。汉魏古诗的研究,对我而言,已经基本完成,而与汉魏古诗以及中国诗歌史密切牵涉的先秦文学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摆在面前。中国诗歌的最早源头是什么?中国的诗歌是怎样由无到有渐次产生的,诗歌和散文的关系如何?《诗三百》的作者阶层属性是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是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基本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我的初步判断是:中国文学的最早体裁是散文而非诗歌,文早于诗,诗源于文和乐,中国诗歌的最早形态是周公时代制礼作乐的产物。而要证明这一点,需要对甲骨文、金文进行研究。以我来看,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之前仅有简单的刻写符号,这里所说的文字,是指以字成文,方能称之为文字。也就是需要通过字来表达完整的意思或是含义。甲骨文中并无诗歌,也无“诗”字。周公时代,不仅仅是奠基礼乐制度的重要时代,同时,也是由甲骨文字、青铜器金文向竹简文字转型的重要时期,因此才有《尚书》的出现。甲骨文字、金文文字、竹简文字在反复的散文文字,主要是应用文体裁的反复书写中,渐次出现了具有诗歌因素的句式,周公摄政时期,制礼作乐,于是,先以散文形态出现《清庙》等篇什,这些祭祀祖先的文字,原本并不押韵,是由于这个时代还没有诗歌,制礼作乐的政治制度,需要将这些文字配乐,于是,音乐的韵律节奏直接启发、促进了诗歌的产生。诗的押韵,来源于歌的韵律。以上所说,都有很多的文献材料所支撑,由于这里并非论文,因此,一概述而不论,只说观点,不加论证,具体的论证,敬请参考此后笔者即将发表的相关论文。
在相关先秦时代文学的研究中,我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很多重要的研究,这里指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实际上都已经接近了历史的真相,或说是接近了历史的完成,但在这些研究之后,却未能得到学术史的接受,相关的文学史写作仍以旧有之说为说。学术史为何不能采用新的研究成果以替代旧说?这种情况即便是学术大家或是大师也往往不能幸免。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决定了学术史的抉择?这可能是一个永远的斯芬克斯之谜。
这种情况,举不胜举。先以王国维关于先秦文学、文化的研究为例,王氏《殷商制度论》开篇即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①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12 页。此可视为王国维有关殷周制度变革之总纲,可谓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周公摄政期间开创的礼乐制度变革,可谓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诸多重大变革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事件之一,亦可谓中国礼乐文化之发轫,同此,亦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之开端,可惜,此论并未得到学者的广泛认同,也未能成为中国历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的主流诠释。②详论参见此后笔者将陆续发表的相关研究。其次,关于《商颂》的写作时间。《说商颂下》则重在辨析商颂非商人之作:“然则商颂果为商人之诗舆?曰否。”①王国维《说商颂下》,见《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5 页。其主要理由有三:
1.《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景山在河南,王国维左氏传、水经注等,景山为景亳,商自盘庚至于帝乙居殷墟,纣王居朝歌,皆在河北,造高宗寝庙,不得远伐河南景山之木。唯宋居商丘,居景山仅百数十里,又周围数百里别无山名,则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庙,于事为宜。此商颂当为宋诗之一证;2.自其文辞观之,则殷墟卜辞中所纪祭礼与制度,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名地名成语,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此尤不可不察也”;3.卜辞称国度曰商不曰殷,而颂则殷商错出;卜辞称大乙不曰汤,而颂则曰汤曰烈祖曰武王等。②参见王国维《说商颂下》,见《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5 页。王国维对于《商颂》非商人所作,辨析甚为有力,基本可以定谳。③详论参见此后笔者将陆续发表的相关研究。但对于非正考父之作的辨析,却不一定准确,也受到很多学者的非议。因此,学术史理应择其合理之内核而弃其不够准确部分,将《商颂》暂且安排于非商人之作而是宋人之作,以俟后来者给予更进一步的探索和解决。
其三,关于《诗三百》的来源问题,流行了很久的民间说、民谣说,从班固到何休,构成了一个以想象来虚构历史的一个链条,后来学者不查,或者是明知其为虚言诳语,由于政治的需要,学术的需要,而听从偏信,并引证以为根据。“采诗说”对后来之学术,影响深远,譬如一直到当下流行的各种文学史版本。其实,对于采诗民间说,自古至今,也足可以构成一个批判史。如清代学者崔述《读风偶识》批判甚为有力,随后有日人青木正儿的批判,青木正儿著《自诗教发展之径路见疑于采诗之官》一文,以为采诗之官不过为儒家传统之一种理想,殊无事实可以依据。其论分《诗》教之完成为三个时期,谓:在西周仅有乐教而无诗教,及春秋赋《诗》之风盛行而《诗》教渐行萌芽,至战国时代而诗教已完成。复以音乐进化之观念考察殷商时代,分谓乐主诗时期,及诗教定础期,因而推定孔子以前实无诗教,而孔子实亦未尝删诗。其结论遂主张:周王室有采乐之事而无采诗之事,诗之内容亦仅供音乐之实用,而非供政教之资料。孔子未尝删诗,诗之亡逸为自然淘汰之结果,献诗、采诗、陈诗诸说,不过为《诗》教发展之后,自《诗》教之见地而构成之一种理想论而已。④参见柳存仁等著《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32 -33
对《诗经》特别是《国风》出自民间采诗而来的质疑,最为有力者,当属朱东润先生的《诗三百篇探故》,其首篇就是《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此文最早发表于1946年的《国文月刊》,他的研究方法其实非常简单明了,即一切从作品本身出发,他首先提出通行之说有难安者三:一、《诗三百》五篇以前及同时之著作,凡见于钟鼎简策者,皆王侯士大夫之作品。何以民间之作,止见于此而不见于彼?二、即以被指为“民歌”代表作的《关雎》、《葛覃》诸篇,关雎之君子、淑女、非民间之通称,“琴瑟”、“钟鼓”非民间之乐器,《葛覃》之“师氏”非民间所能有;三、后代之文化高于前代,何以三千年之前之民间能为此百六十篇之《国风》,后世之民歌远不及矣。随后,朱先生又从两个角度论证了《国风》的作者问题:1.据《毛诗序》,作者可考而得主名者六十九篇,据“三家诗”说,得四篇,作者皆为统治阶级,2. 就诗篇本文考察,作诗者或自言,或言其关系之人,或言其所歌咏之人,涉及地位、境遇、服御、仆从诸端,可以确定为统治阶级之诗者凡八十余篇,即《国风》一百六十篇总数之半。相反,欲以同样方法论证某诗确实出于被统治阶级所作,不能得一篇。⑤骆玉明《诗三百篇探故重刊弁言》,见朱东润著《诗三百篇探故》,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 页。有朱东润先生的这样翔实的论证,《诗三百》民间说,《国风》民间说,可以休矣,文学史理当可以改写,但我们所见到的文学史、诗歌史,照样还都是按照传统的说法,不为所动。
近十年以来,“诗经学”的研究,越来越肯定了《诗经》是两周礼仪制度的产物,《诗经》作品从创作、编辑到传播,都是两周时代王室贵族、上层社会的产物,其中刘毓庆、郭万金著《从文学到经学》、王昆吾著《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马银琴著《两周诗史》、陈致著《从礼仪化到世俗化》,刘冬颖著《出土文献与先秦儒家诗学研究》,李山著《诗经的文化精神》等,更是其中之翘楚。有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诗三百》民间说,《国风》民间说,可以休矣,文学史理当可以改写,但我们所见到的文学史,诗歌史,照样还都是按照传统的说法,不为所动。
在《诗三百》问题的研究上,学术史固守着民间说,民谣说,摒弃一切非民间之说,王国维《商颂》非商人之说,以及“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之说,自然就不能受到重视,因为这些说法,在中国文化、文学、起源于民间创造的说法之外,清晰地指明了另外的演变路线;而在屈原“楚辞”的研究方面,有学者提出对屈原是否真实存在提出质疑,或认为《离骚》为淮南王刘安之作。但在这一点上,学术史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当下流行的主流文学史,仍然坚守着对于屈原真实存在的认同。
随后的重大问题,就是关于《古诗十九首》代表的古诗问题的研究了。一直有误解,以为我的这一研究是前无古人的,为此,我写作了相关的论文,阐发了我的这一研究对古今学者的继承。(参见《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6 期拙文)实际上,在梁启超作出东汉说的判断之前后,古诗问题已经接近了历史的解决,如徐中舒先生、胡怀琛先生,特别是后来罗根泽先生的阐发,已经解决了汉魏古诗非汉诗的问题,当下宇文所安先生等外国学者的研究,更进一步确认了这一方向。但决定学术史走向的,握在一只无形的手中,我们需要耐心等待最后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