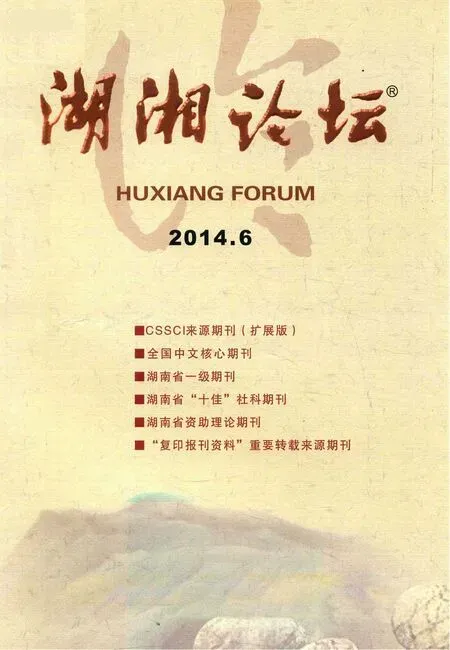近代湘学对“夷夏之防”和“中体西用”的突破*
2014-04-07陈代湘周接兵
陈代湘,周接兵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015)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以及清政府腐败的双重影响,原本已经存在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终于于19世纪中叶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不满既有的侵略成果,为了继续扩大侵略,趁中国内乱之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较之《南京条约》更加丧权辱国《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北狩”。于是,严重的内忧外患摆在了清政府和封建士大夫面前,也摆在了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为代表的湘学人物面前。湘学人物为了应对这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他们对内领导湘军坚决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对外,则主导进行了一场旨在“求强”、“求富”以抵御外来侵略的洋务运动。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先后发生过同文馆之议和海防之议两次大的论战。顽固派坚守纲常名教,訾议洋务派的造船造炮行为为“奇技淫巧”,虚骄自大,盲目排外,其指导思想就是所谓的“夷夏之防”;洋务派虽然强调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但依然固守封建纲常名教,强调在不触动封建专制体制和封建文化的前提下进行器物改革,其指导思想就是所谓的“中体西用”。
一、湘学对“夷夏之防”的突破
“夷夏之防”观念源于先秦,是中国古代民族矛盾的产物,后经孔子发展为“内诸夏而外夷狄”,成为“春秋大义”之一,它强调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随着儒家独尊政治地位的确立,“严夷夏之防”成为封建社会的一条根本大纲。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有利于保持华夏文化(主要是汉族文化)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果说古代汉族文化较之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确具有优越性,严夷夏之防尚情有可原,那么到了近代,在中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依然顽固地保守这一观念,无疑不利于中国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这种不利影响反映在洋务运动上主要有两点,一是办洋务只变“器”,不变“道”,即只学习西方船坚炮利,而拒斥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对之持否定、鄙夷态度,洋务派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态度。二是外交上始终不肯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虚骄自大、固步自封、满目排外,对西方始终缺乏正确的、深入的认识。顽固派基本上都是这个态度。
那么,有没有人突破夷夏之防,主张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进一步学习西方呢?有!海防之议后,随着西学的广泛传播,人们对西学的认识逐步深化,于是在批判、总结近二十年洋务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洋务派内部逐步分化,形成了早期维新派(又称改良派),代表人物有薛福成、冯桂芳、郑观应、马建忠、王韬等,这些人的思想各有特色,但大体上不外如下几个方面:经济上反对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主张发展民族工业、发展实业、发展对外贸易、商战等;政治上主张效法西方议会制度、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文化上主张变革科举,学习西方教育体制,创办新式学校等。早期维新派的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对夷夏之防的重大突破。
湘学人物中突破夷夏之防的主要郭嵩焘和曾纪泽两人。二人都曾作为外交使臣分别于1876年、1878年出使欧洲,他们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认识较之其他洋务派人物更为深刻,对夷夏之防的突破比早期维新派也相对早一些,现在我们择取他们出使欧洲过程中与顽固派有冲突主要经历和见闻来考察一下他们是如何突破夷夏之防的。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率人到云南“探险”,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被杀,这就是所谓的“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寻衅滋事,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烟台条约》,进一步攫取了在中国的更多特权。随后,英国政府强烈要求清政府派大臣亲自到英伦“道歉”。清政府被迫无奈,任命郭嵩焘为中国驻英国公使。此消息一出,舆论大哗,郭嵩焘立即成为顽固派的众矢之的,讥笑、谩骂铺天盖地而来。同僚目之为“汉奸”,认为他出使英国“有损国体”、“辱国”;同乡耻与为伍,湖南士绅质问他有何面目回湖南,有何脸面对天下人,湖南士子甚至动议捣毁他的住宅;京中清议派有人联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等等,极尽讽刺之能事。面对顽固派的攻击,郭嵩焘毫不畏缩,慨然允命。他豪迈地说:“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 ”
同年十一月,郭嵩焘上折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要求将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交部严处,并表达了自己的外交理念,他援引《周礼》认为,古代“以礼亲邦国”,三代之所以享国长久,皆“源于此”,春秋时期,列国“以礼相接,文辞斐然”,这些礼节今日办洋务者“实多可取法”。他还抨击了那些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顽固派士大夫。说他们“不考古今之宜,不察理势之变,习为高论,过相诋毁,以致屡生事端,激成其怒(指马嘉理事件激怒英国——引者注)”,此等士大夫“太无学识”,以致“办理洋务不得其平”,长此以往,“求无误国误民不可得也”[1]P786-788郭嵩焘此议自然又遭到顽固派的毁谤,“汉奸”、“贰臣”之类的指责咒骂,汹汹而至。
在这种横遭非议的情况下,郭嵩焘于1876年底踏上出使征程,航经香港、新加坡、锡兰等地,游览参观,考察各地风土人情、政教习俗,并将其感受、见闻逐日记载,写成《使西纪程》一书。该书称赞英国人彬彬有礼,并非蛮夷;称赞英国教育“规条整齐严肃”,深得中国古代“陶养人才之遗意”;盛赞西方民主制度,认为西洋立国“政教休明,具有本末”,“以信义为先,尤重邦交之谊,质有其文”;提出中国要学习研究西方治国之道,“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2]P128-129;还提出要在理、势、情的基础上研究应对西方挑衅的“应对之方”。抵达伦敦后,他将《使西纪程》寄总理衙门刊刻,“以期有益于国”。不料此书刊出后,又引起轩然大波。顽固派指责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刊刻此书“诚不知是何肺腑”云云。在顽固派的攻击之下,清廷下令将该书毁版,禁止流行。该书毁版后,他的副使,顽固派人物刘锡鸿也趁机发难,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一、不当批洋人衣;二、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致敬?三、听音乐,屡取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又“密劾”郭嵩焘藐视朝廷、擅议旗色、违悖程朱、迎合洋人等“十条罪状”。
可以看出,顽固派的这些指责千条万条,归结到一点就是“夷夏之防”。对此,郭嵩焘他在《办理洋务橫被构陷沥情上陈疏》中作出回应,主要有两点:
一是阐明洋务形势和对洋务的看法。他认为自道光以来办理洋务,因办洋务者“不能尽知洋务底蕴”,导致“变故迭生”,所以“急应于此推考事理,以求应付之方”。对内,应“兴利劝学,驯至富强”,则可以“固国本”;对外则应讲求“应接之术”,即“唯礼可以御敌”、“诸事皆可以理折之”否则“战、守、和三者俱无足言”[1]P831-833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认为与洋人交接,应根据“洋情、国势、事理”来“推知洋务情形”,现在的“洋情”是: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其至中国,惟务通商而已。[3]P116窃查西洋通商已历一千四百余年,与历代匈奴、鲜卑、突厥、契丹为害中国,情形绝异,始终不越通商之局。[1]P833言下之意,现在的西洋不再是像古代辽、金那样的夷狄了,既然“洋情”变了,那么“应付处理之方”也应变通。而顽固派一味主张排外,“无故悬一和字以为劫持朝廷之资,侈口张目以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者”,他认为持这种言论的人是一种“气矜”的“妄人”,他们只知道“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君父于不顾;必使覆国亡家,以自快其议论而为名高”,这种人“不足与言国是”。[2]P116-117
二是针对顽固派的攻击,郭嵩焘忧愤交加,他一面上折弹劾刘锡鸿,指陈他的种种劣迹,并在日记中斥之为“妄人”、“妖孽”[2]P273;一面上奏请求辞职并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两年以来,……污蔑讪讥不遗余力,臣亦无从置辩。……臣区区老病之身,奔走万里,负辱就瞑,何辞以解于人世。……自问耿耿此心,无一念不求裨益大局。遭值时艰,于国家得失利病,臣亦不得不引为咎责,参劾诟辱,所敢不避。……万口交谪……乃使一生名节,毁灭无余。私心痛悼。……[1]P833显然,他对自己的耿耿忠心不为士大夫所容感到非常痛苦,又万般无奈,这种痛苦和无奈伴随了他整个晚年,最后郁郁而终。但是,正如他临终前所说:“流芳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他的洋务思想、他对西方的认识、他提出的外交原则,特别是他的思想对“夷夏之防”的突破,早已被历史所证明和肯定,他的英名和业绩将永垂史册。
接替郭嵩焘担任使臣的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曾纪泽(1839-1890)自幼接受庭训,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又广泛涉猎西学并自学英语,加上他出使欧洲的经历,使得他对中西文化均有较深的理解。他出使欧洲后,政事之余,广泛参观考察西方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对西方各国“政教之绪”,“富强有本”,“艳羡之极”[3]P161;称赞西方教会的各项便民措施“术仁而法良,可敬”[3]P317;称赞西方的机器工业“鬼斧神工”;对西方的教育也很欣赏,认为它“争奇而并重”,可以“集思广益”[3]P331等等。
基于此种认识,他认为当前中西的局势乃“亘古未有之奇局”,“诚与岛夷、社番、苗瑶獠猓,情势判然”,中国士民不能通晓此种奇局,对西方“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如禽兽,皆非也”。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中国很强大,视之为夷狄则可;若果中国不强大,则可以像春秋战国的晋、楚、齐、秦那样“鼎足而相角”[3]P184。何况,“今日泰西各国之君,非犹是战国时之君;各国之政,非犹是战国时之政”[3]P20了,所以,“平心而论”,不可“因其礼仪教化之不同,而遽援尊周攘夷之陈言以鄙夷之”。[3]P184而当时顽固派的“严夷夏之防”的各种论调,使他对西方政教,既“艳羡之极”,又“愤懑随之”,为什么愤懑?因为顽固派“清流士大夫”言必称三代,动辄引古训,“高论唐、虞、商、周糟粕之遗”,不明事势,盲目排外,“助成者鲜,而促毁者多”,对国家不仅了无一益,而且“实足贻误事机”。[3]P161所以,面对这“千古未有之奇局”,“中国不能闭而不纳,束手而不问”。[3]P311既不能畏之如神明,也不能鄙之如禽兽,而应该内审国势,外度敌情,“以至诚待邻封”[3]P46,以礼待西人,平等交往,“务将与西方一切交接,基于国谊而立之国约,非基于败衄而立之和约”[3]P374。同时,应该学习西方、整顿海防、修建铁路、筹度国是、肃整纪纲、保护华侨等等。[3]P374
曾纪泽对西方的认识是深刻的,所以他能够客观地、理性地面对西方国家,能在与俄国就伊犁问题的外交谈判中以及中法战争中外交谈判中折冲樽俎,据理力争,为捍卫我国领土主权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曾纪泽虽然突破了“夷夏之防”,但是相对于郭嵩焘而言,他还是有点保守。因为他虽然强调学习西方,但仍然认为西方政教“多与《周礼》相合”;其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逐渐而来”;“西人一切局面,吾中国于古皆曾有之”;“西洋人近日考求者(指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器物等——引者注),中国圣人已曾道破”[3]P331、344等等,显然,这是典型的“西学中源”论。
二、湘学对“中体西用”的突破
如果说“夷夏之防”是洋务派和顽固派所不同程度共同持有的对待洋人和西学的态度问题,那么“中体西用”则是洋务派所独持的如何学习西方的指导思想问题。其基本内涵是:以“中学”即儒家的纲常名教为“体”、为“本”、为“主”,以“西学”即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商业、教育、贸易、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为“用”、为“末”、为“辅”,强调在维护满清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以挽救西方列强入侵所带来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其最早提出者是冯桂芬,他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中体西用的最初表达;薛福成在《筹说刍议》中提出“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是“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他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中体西用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治世事”、“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制也,非器物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夫所谓‘道’、‘本’者也,三纲四维是也。”张之洞此论,在当时有着“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语)的巨大影响力。
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贯穿于洋务运动的整个过程,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把鸦片战争初期的“开眼看世界”落实为具体的“动手学世界”,在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发挥过积极作用。从文化上看,它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在封闭保守的传统文化一统天下的中国打开了一个缺口,使得西学从这个缺口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冲击着旧的思想,旧的传统,在中与西、新与旧的激烈冲突中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体西用已经完美无缺。事实上,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洋务派把学习西方的内容限制在船坚炮利上,后来虽然扩充到天文、地理、算学、物理化学、语言文字等方面,希图以此等“器物”来“自强”、“求富”,抵御外侮。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体”(腐朽的封建专制体制和封建文化)上嫁接外来的“西用”即“器物”的时候,封建专制体制和封建文化这片土壤究竟能不能给这些“器物”提供健康成长所必需的养料?我们看到的是,当“器物”需要引进西学营养来滋润的时候,“同文馆之议”义正词严地来抵制西货了;当“器物”需要精心管理呵护的时候,“官督商办”大腹便便地出来瞎指挥了,当“器物”试图使自己枝繁叶茂的时候,“海防之议”拿着剪刀煞有介事地来修理枝叶了。可见,这片“土壤”非但不能提供“器物”健康成长所需要的优良坏境,反而不断地摧残它、扼杀它,使它变得畸形,萎缩,最终惨败于晚它几年生长于东瀛“蕞尔小国”那片土壤里的“器物”之手。中国“器物”的畸形和萎缩,反映了中国传统力量的强大和根深蒂固,同时也反映了把“中体”与“西用”这两个格格不入的东西放在一起就像“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严复语)一样是多么的不协调。
要想使“器物”健康成长,就必须打破这个“不协调”,谁来打破?曰:早期维新派;曰:湘学人物郭嵩焘。郭嵩焘作为我国近代第一位外交使臣,对西方的认识相对而言比早期维新派要早,所以我们称之为打破“中体西用”观念的“第一人”丝毫不为过。
郭嵩焘对中体西用的突破首先体现在对夷夏之防的突破上,前文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考察一下他的三重本末观对中体西用的突破。
郭嵩焘认为西方国家“政教修明”,“立国自有本末”,所以我们办洋务,不能舍弃其本不学,而只学其“器物”之末。所以他在“理、势、情”的基础上,结合出使西方的经历和见闻,提出了“朝廷政教”、“通商”、“人心风俗”三个本末观。
就朝廷政教而言,他在日记中多次描述英国议会开会两党议员辩论的情景,称赞其议会制度“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2]P449。美在哪里?他详细指出:
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巴力门(Parliament,议会——引者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待,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而终以不弊,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2]P357
其君民上下相与考求如此,是以所用必当其才,而无敢以私议援引,此西洋各国所以日趋强盛也。[2]P484
这里,他把议会制度提到“立国之本”、强盛之原的高度,可谓推崇之至。那么,中国的政教呢?他认为,“中国以一虚骄之气当之,通官民上下相与为愦愦,虽有圣者,亦无可如何也已矣”[2]P464为什么会这样?他在与英国公使威妥玛的谈话时谈到了这一问题,威妥玛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内修”不够,中国只知道买几尊大炮,修几处炮台,而“无一实政及民”,“请问有何益处?”这种做法在西方称之为“乱国”,土耳其就是例子。郭嵩焘赞同这种说法,“其言语可云耸切”,并认为,中国与土耳其相比,有胜过它的地方,但在“仿行西洋兵制,设立议政院”方面,不如土耳其,中国只是“议论繁多,不求实际”[2]P322。
教育方面,他曾对西方的教育体制、教育章程、课程设置等进行过考察,认为“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皆学问考核之功也”[2]P341认为其学问是“务实之学”[2]P399,凡是“虚饰”、“伪饰”者“必黜之”,“此西洋人才之所以盛也”[2]P450。此外,他还对欧洲的女学、民办学校、教会学校、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等称赞有加。
他还特别欣赏“万国公法”,认为它“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每议一事,“必展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大时哉?”所以对中国而言“惟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舍是无能自立者”。[2]P128
那么中国应当如何改善政教呢?以俄国与日本为例,他认为俄国强大始于彼得大帝,彼得曾隐姓埋名游历欧洲,“往观其政教风俗”,结交了大量智能之士并将他们带回俄国,彼得归国之后,开始改革内政,“广开制造局”、“讲求练兵经国之计”、“募西洋各国富商”、“大变风俗,广通商贾,兼立富强之基”[2]P362,最终成为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强大国家。日本则“考求西法,志坚气锐”,所以他预言,日本“二三十年后,其制造之精必可以方驾欧洲诸国”。反观中国,只知道船坚炮利,“恃此……用以称强乎?抑何所见之不广也。”[2]P351因此,效法俄国和日本学习西方的政教才是当务之急。
就通商而言,他认为“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肃,条例秩然”[2]P113怎么个“整齐严肃,条例秩然”法呢?在商业管理体制上,西方国家官吏并不直接参与商业活动,而是由商民自主经营,“自知其中利益而争赴之”,相关官吏只是在经济秩序上“为之经理而已”[2]P313。所谓的“经理”即“推考百货盈虚,达知本国,权衡物价之轻重以为制国本之用。”[2]P323-324郭嵩焘盛赞此举,认为这样可以“使商情与其国家息息相通,君民上下,同心以求利,此中国所不及也。”[2]P324对中国而言,这种做法与洋务派“官督商办”管理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他强调必须“急通官商之情”,与其官督商办而造成“烦费日甚,库款之支发日穷”,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理顺也”[1]P779,相关官吏只需要“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即可,这才是真正的富强之本,“利国之方”[1]P778。在财政管理上,他盛赞西方的财政预算制度,认为其财政收支状况均交议会讨论决议,是“君民上下,并力一心,以求制治保邦之义,所以立国数千年而日臻强盛者此也”[2]P446。他还认为这是“量出以为入”,与中国“量入为出”形成鲜明对比。
就人心风俗而言,郭嵩焘认为西方风俗厚重。就政治风气而言,他认为西方议会制度自创立以来逐步“习为风俗”,“其人民周旋,一从其实,不为谦退辞让之虚文……一有诈伪,皆以法治之,虽贵不贷……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深矣”。[1]P377就宾客交际而言,他认为西方“以游历交接为义,已成风俗”,其接待宾客“致情尽礼”,而中国“不许人民私行出入,无至外国游历者”,相比之下,中国“气局”[2]P255未免太小。社会方面,他称赞西方田地防灾具体而微,“不殚烦劳”;居家卫生干净利落[2]P286;监狱制度“规制严整”,“一主于劝善”,“使人油然生其仁爱之心”[2]P257,等等。总之,西方人心风俗各个方面都比中国优越。
上述朝廷政教、通商、人心风俗三个方面,西方均比中国优越,因为“西洋制法,亦自有本末”,而“中国大本全失”[2]P425,他批判了洋务派的做法,认为其只不过是“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1]P784所以,从上面三个方面进行改革才是真正的“务本”之道。
如何改革呢?他认为“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加强宣传,对西方良法“当明著其所以然,刊行天下,使人人皆知其为利益,则得失利病较然于心,自然知所信从矣”。[2]P453二是要“除忌讳”、“便人情”、“专趋向”。[2]P453这明显是针对顽固派而发。三是实事求是,“以西法佐中法”[3]P696,包括政府“开诚布公以泯行迹”即效法西方议会制度“通上下之情”、选择西方政教书籍以备采择、禁烟等。四是要“通民气”,“一切新政,皆鼓舞百姓为之,其源尤在学校,学校章程必应变通”。[2]P609五是政府要厉行改革,“一意推行其长处”,无虚骄自大之气,“无争强之心”,“一切可以取益,而不必存猜疑”[2]P609。
综上,可以看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已远远超出了“中体西用”范围,不仅涉及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涉及到政治制度改革的相关内容。如果说洋务运动是在封闭保守的封建专制体制和封建文化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引进了西方“技艺之末”,那么郭嵩焘则是在洋务派内部打开了一个缺口,引进了西方的“政教之本”。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看,郭嵩焘的这一引进无疑具有开创之功,尽管它只是记载在日记中,没有被付诸实践,但其远见卓识却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早期维新派在内的后来者,可谓开维新变法之先声。
[1]郭嵩焘.郭嵩焘全集(四)[M].长沙:岳麓书社,2012.
[2]郭嵩焘.郭嵩焘全集(十)[M].长沙:岳麓书社,2012.
[3]曾纪泽.曾纪泽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