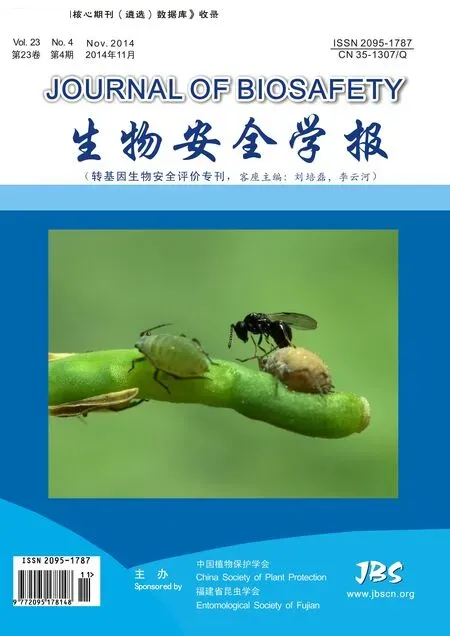国际上主要国家和地区农业转基因产品的标识制度
2014-04-07徐琳杰刘培磊武玉花杨雄年
徐琳杰, 刘培磊, 熊 鹂, 武玉花, 吴 刚, 杨雄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北京 100122; 2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62
自1994年首例转基因番茄上市以来,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发展迅猛。截至2013年,全球共批准27种转基因作物用于环境释放、种植、饲料或食用,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达到1.75亿hm2,并保持连续增长势头,转基因产品正以多种形式融入人们的生活(James,2014)。转基因产品是否应该特别标注以及如何进行标注,成为政府和公众共同关注的议题,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政策与方式也有所差异。本文总结分析了当前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转基因标识管理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管理政策的特点与利弊进行了研究,为完善我国的农业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1 转基因产品标识的形成及内涵
1.1 标识的含义
标识是指用于识别产品及其质量、数量、特征、特性和使用方法所做的各种表示的统称,可以用文字、符号、数字、图案以及其他说明物等表示,是传递产品信息的基本载体。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得产品呈现出功能特性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普通消费者难以凭借自身能力判断产品属性。通过标识,生产者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信息、做出质量承诺,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得以保证(孙汉强,2001)。目前,标识已成为购买产品的重要依据。
1.2 转基因标识的形成和发展
转基因标识是表明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或由转基因生物生产、加工而成的一种标识。由于进入市场的转基因农产品都通过了充分的环境安全评价和食用安全评价,因此其与清真食品、无糖饮料、全脂牛奶等标识一样,都是为了帮助消费者了解产品的属性,与其安全性并无对应关系。转基因标识旨在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并不属于安全指示。
转基因标识的形成与发展和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应用基本同步。早在1990年转基因产品商业化应用前,欧盟便在转基因生物管理法规(220/90号指令)中确立了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框架。1996年转基因作物开始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后,欧盟于1997年颁布实施《新食品管理条例(258/97)》,对所有转基因产品进行强制性标识管理,并设立了最低含量阈值(金芜军等,2004)。20世纪90年代末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迅猛发展,转基因产品涉及国际农产品和食品贸易的多个方面。另一方面,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一系列报告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出于国际政治、经济和公众接受等多重考虑,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转基因产品实施标识管理,1999年美国政府提出自愿标识管理系统,2001年日本实施《转基因食品标识法》,2002年我国发布施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目前,已有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韩国、泰国以及欧盟各国等在内的近70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制度(Hudson,2013)。
2 国际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制度分析
当前不同国家(地区)的转基因标识制度差异很大。按特性大体上分为如下类型:成分关注与过程关注、自愿标识与强制性标识、定性标识与定量标识、全面标识与目录标识等。
2.1 成分关注与过程关注
根据标识对象的不同,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分为成分关注型和过程关注型。成分关注是以最终产品中转基因成分(外源DNA或蛋白质)的含量为标识依据;过程关注则以产品在加工、生产过程中是否采用转基因原料为依据,不论最终产品中是否存在转基因成分。目前,绝大多数实施转基因标识的国家(地区)采用成分关注型标识制度,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地区)实施过程关注型标识制度,主要为欧盟、巴西、中国(Gruère & Rao,2007)。
过程关注型标识对转基因产品实行追溯管理,需要对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等所有环节进行全过程追踪,各级生产加工和经营销售者必须建立信息传递系统和程序,这将明显增加产品成本,因此实施难度大、管理链条长、监管的可操作性不强。成分关注型标识重在对最终产品进行转基因成分分析,管理环节集中、管理手段多样,同时利于执法监管。
2.2 自愿标识与强制性标识
自愿标识是按照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意愿,对产品中的转基因成分进行标注。强制标识又称义务标识,必须按照法规规定对相应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未标识和不按规定标识的不得进口或销售。采用自愿标识的国家(地区)主要有美国、加拿大、菲律宾、阿根廷、南非以及中国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于与原有品种在组成成分、营养价值等方面等同的转基因产品不做强制性标识要求。但当转基因生物的组成成分、营养价值、用途、过敏性等与传统对应产品发生显著变化时,则需要进行相关说明。其他国家和地区均采用强制性标识,如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日本、韩国、泰国等(Gruère & Rao,2007)。
在各国构建转基因标识制度的同时,国际组织也开始建立转基因标识的协调机制。《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TheCartagenaProtocolonBiosafety,BSP)于2000年1月通过,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专门对转基因标识进行阐述。议定书规定含有活性转基因生物的产品必须进行标识,各国有权禁止进口其认为可能对人类及环境构成威胁的转基因产品(乔雄兵和连俊雅,2014)。世界贸易组织(WTO)要求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制度符合《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精神,并将标识作为技术贸易措施纳入谈判和规则制定的讨论范围。总之,转基因产品标识已成为较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共识。
2.3 定性标识与定量标识
根据标识阈值的差异,转基因标识制度分为定性标识和定量标识。定性标识是指应用规定的检测方法,只要产品中检测出转基因成分,就进行标识,即标识阈值为零。定量标识则设立一定的阈值,只有产品中转基因成分含量超过阈值时,才需要标识。
中国是目前唯一采用定性标识的国家,其他国家则施行定量标识,即阈值管理。从世界范围看,各个国家的标识阈值差异较大,欧盟1997年规定当食品中某一成分的转基因含量达到该成分的1%时必须进行标识,2003年颁布的法规EC No1829/2003和No 1830/2003将这一阈值降至0.9%(王荣谈等,2013)。日本规定当产品中主要原料的转基因生物含量超过5%时需要进行标注,主要原料指原材料中含量位于前3位且占原材料重量比在5%以上(日本《转基因食品标志法》,2001)。韩国规定当产品中含量最高的前5种成分,转基因生物含量超过3%时需要进行标注(韩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基准》,2001)。巴西则规定转基因成分超过1%的产品必须标注(Cevallos,2006)。
阈值的确定与技术检测水平直接相关,同时也是该国对转基因产品接受程度、贸易需求、政治因素等的综合反映。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转基因标识阈值在3%~5%之间,一些国家阈值为1%。由于偶然因素或技术上不可避免因素,产品中转基因成分含量很难控制为零,因此实施阈值管理更利于标识制度的实施,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2.4 全面标识与目录标识
标识目录是各国根据转基因产品的应用情况,转基因成分的含量以及检测技术等因素,列出的详细产品名录,其主要目的在于方便转基因标识制度的实施,增加制度的可操作性。
根据标识范围,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分为全面标识和目录标识。全面标识包括所有的转基因产品,实施国家和地区主要为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西等。目录标识则针对特定的转基因产品,日本、韩国、泰国、以色列、印度尼西亚、中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制定了标识目录。日本标识目录最开始包括5种作物:大豆、玉米、马铃薯、油菜籽和棉花,以及上述作物经过加工后重组DNA或蛋白质仍然存在的24种产品,如豆腐、玉米小食品、纳豆等。此后,日本农林水产省对目录进行修改,增加了马铃薯及其加工品、三叶草及其加工品、糖用甜菜及其加工品等(付仲文,2009)。2001年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制订颁布《转基因食品标识基准》的标识目录为大豆、玉米及其制成品,包括豆粉、豆糕、大酱、豆瓣酱等27种食品和食品添加剂,此后也增加了马铃薯和其加工品等产品。一般认为精炼油中不含有外源DNA和蛋白质,因此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未将油脂类产品列入标识目录(金芜军等,2004)。
2.5 标识豁免
标识豁免是对标识范围和标识对象的附加说明,一些国家规定可以对某些特殊产品实施标识豁免。如澳大利亚规定,餐厅和服务业出售的膳食可不进行转基因标识,日本、俄罗斯规定动物饲料不需要转基因标识。此外,除欧盟外的多数国家都将食品添加剂和调味品、散装食品等列为豁免对象(Carter & Gruère,2003; Gruère & Rao,2007)。
2.6 阴性标识
阴性标识是指在产品上标注“非转基因”或“无转基因”,以告知消费者该产品不含有转基因成分。国际上对阴性标识的管理主要分为3类:(1)明确禁止阴性标识,如泰国禁止使用“非转基因食品”等表述方式,认为类似表述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2)允许阴性标识,但设立严格的条件和管理程序,如日本等国家规定进行阴性标识的产品必须经过IP(非转基因食品身份保持)认证,欧盟、韩国等国家规定阴性标识的产品必须确保产品中100%不含转基因成分;(3)允许阴性标识,但不能误导消费者,如美国和加拿大允许阴性标识,但要求标识内容必须真实、易懂,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易产生歧义或暗示阴性标识食品优于其他食品的标注不得使用,对于市场上根本不存在转基因生物的食品,不允许非转基因标注(付仲文,2009; 金芜军等,2004)。总之,国际上对阴性标识统一要求是不能误导消费者认为非转基因产品优于转基因产品。
3 对我国农业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的启示
目前我国采用的是2002年制定的按目录定性强制标识制度。近年来随着转基因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的飞速发展,我国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现行的转基因生物标识制度面临着一定挑战,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零阈值的定性标识制度无法规避转基因成分无意混杂现象,易导致产品过度标识;(2)市场上转基因产品类型与2002年相比出现较多变化,公众对豆腐等部分转基因产品纳入标识目录的呼声较高;(3)近几年来部分商家利用消费者购物心理,以“非转基因”为噱头进行广告宣传,市场上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转基因阴性标识,对消费者产生明显误导,扰乱了产品的正常市场秩序,影响了转基因产业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国际上转基因标识管理的制度和经验,将会对我国迎接上述挑战,制定适合现状的标识阈值、标识目录,规范阴性标识管理等提供借鉴与参考,有助于我国进一步完善农业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制度。
付仲文. 2009. 一些国家和地区转基因生物标识制度概况. 世界农业, (11): 37-42.
金芜军, 贾士荣, 彭于发. 2004. 不同国家和地区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政策的比较. 农业生物技术学报, 12(1): 1-7.
乔雄兵, 连俊雅. 2014. 论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国际法规制—以《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为视角. 河北法学, 32(1): 134-143.
孙汉强. 2001. 浅论产品标识. 上海标准化, (4): 38-47.
王荣谈, 姜羽, 韦娇君, 张大兵, 杨立桃. 2013. 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标识与检测. 植物生理学报, 49(7): 645-654.
Carter, C A and Gruère, G P. 2003.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 to the labeling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Choices, 18: 1-4.
Cevallos, D. 2006.Wanted:LabelsforGeneticallyEngineeredProducts. Inter press service news agency (IPS).
James C. 2014. 2013年ISAAA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 34(1) : 1-8..
Gruère G P and Rao S R. 2007.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abeling policie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to evaluate India's proposed rule.AgBioForum, 10: 51-64.
Hudson B K. 2013. 64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label GE food.SoundConsumer, 479: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