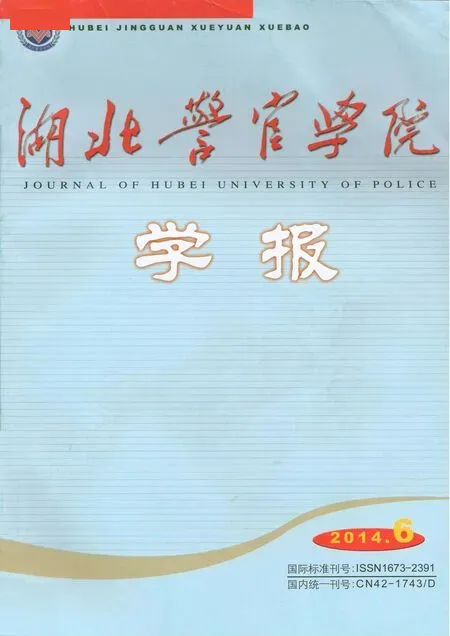关于侦查程序中律师在场权的理性分析
2014-04-06王超
王超
(贵州大学 法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关于侦查程序中律师在场权的理性分析
王超
(贵州大学 法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由于受“打击犯罪、维护稳定”司法价值观的影响,我国侦查程序中长期存在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问题。当前,在侦查程序中确立律师的在场权,对于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维护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侦查程序;律师在场权;犯罪嫌疑人
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阶段,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尤为激烈。犯罪嫌疑人较之侦查机关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弱势的个人权利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对抗中,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往往受到粗暴的侵犯。我国的侦查实践受到传统的“口供中心主义”的影响较深,刑讯逼供现象时有发生,冤假错案频出。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一定程度的沉默权,是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美国学者华尔兹认为,刑事被告人的沉默权与律师的在场权,是保证实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宪法性权利,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在新《刑事诉讼法》中,作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重要组成部分的律师在场权却未得到确立,着实令人堪忧。基于这种考虑,认真研究侦查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问题,并提出较为合理的设计方案就显得极为必要。
一、侦查程序中律师在场权的涵义
律师在场权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受到侦查机关讯问时,可以要求辩护律师在场的权利。除非犯罪嫌疑人自愿放弃,否则如果律师没有在场,侦查机关所进行的讯问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律师在场权是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权利,是其诉讼主体地位的体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对律师在场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体现着对公权力强有力的制衡。
二、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在场权缺失的原因
在新《刑事诉讼法》施行之前,律师在侦查程序中未被赋予辩护人的法律地位,处境十分尴尬。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推进,我国的辩护制度有了新的突破。新《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使得我国的律师终于摆脱了在侦查程序中的尴尬角色,被赋予了辩护人的地位。但随着律师在侦查程序中辩护人地位的确定,作为辩护权重要组成部分的律师在场权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却仍未得到确立。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无权要求律师在场,如此会阻碍律师进行有效的辩护。我国律师在场权缺失的主要原因有: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不利影响
我国侦查机关长期比较注重打击犯罪,而忽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而且公众普遍希望犯罪分子受到最大限度的法律制裁,这往往形成了将律师的辩护活动看作是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的错误观念。因此,律师在场权的确立,必然会对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活动造成诸多限制。在“宁枉勿纵”的法律文化下,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律师在场,犯罪分子都如此猖狂,而若有律师给其撑腰,其将更加有恃无恐,打击犯罪的目的将难以实现。
(二)律师的地位和素质不高
在我国,长期存在着“公、检、法”是一家的国家主义观念,他们与律师之间隔着明显的界限。律师作为孤军奋战的社会法律工作者,所代表的是公民个人。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往往联合起来限制律师的权利。律师被“公、检、法”视为“异己”,其地位较低。此外,我国的律师队伍良莠不齐,本身存在着很大问题。律师帮助犯罪分子做伪证、串供等妨碍侦查的现象频现,使得律师队伍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三)侦查能力较为低下
毋庸讳言,我国现在的侦查能力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准。就侦查技术而言,不仅DNA技术等新型科学技术的水平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各种常规的司法鉴定技术也相对落后。因此,在我国侦查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往往成为侦破案件的捷径。即使讯问中无法获得其直接的供述,也会争取获得更多侦查线索。而这些口供的取得往往存在程序违法的嫌疑。因此,如果允许律师在场,必然会影响讯问效果,进而影响到对案件的侦破。
三、我国侦查程序中确立律师在场权的利弊分析
(一)确立律师在场权的有利方面
1.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在刑事诉讼领域,我们不仅要打击犯罪,更要保障人权,尤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合法权利。总体来说,侦查程序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因此不可避免存在滥用侦查权的问题。而且,因犯罪嫌疑人处在较为封闭的侦查程序中,其请求救济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均受到严重的限制,极易受到侦查机关的违法侵犯。而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当辩护律师在场时,侦查机关一般不会明目张胆地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因此,确立律师在场权,有利于实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有效保护。
2.有利于促进侦查结构的合理化
公正是现代司法的生命,权力制衡则是保障公正最有效的手段。因此控诉、辩护、审理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呈现出三角形的基本结构,也就是所谓的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现代诉讼格局。由于侦查程序具有封闭性,而控诉方与辩护方之间存在着较为激烈的对抗,辩护方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为了防止权力被滥用,有必要在侦查程序中确立律师的在场权,通过“权利制约权力”,以加强对侦查程序的监督。这实际上是我国吸收了英美法系的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使得侦查结构更加合理。
3.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在审判阶段常常进行无谓的翻供、上诉或申诉,其较为普遍的理由就是在侦查阶段受到了刑讯逼供。这导致审判程序一再地重复,严重影响了诉讼效率。而如果律师在场则能够平衡被告人的心理,保证口供的质量,减少翻供。同时也能证明侦查机关讯问程序的合法性,增强口供的效力,从而保障审判程序的运转流畅,进而提高诉讼效率。
(二)确立律师在场权的弊端
1.不利于侦查活动的迅速进行
众所周知,侦查人员在讯问中不可避免地会运用一些讯问技巧。由于立场不同,律师往往会对这些讯问技巧当场提出质疑,从而打乱侦查人员的讯问计划,使讯问达不到预期效果。同时,律师在场也可能在客观上起到为犯罪分子撑腰壮胆的作用,增强其抵抗心理,致使侦查人员的讯问活动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及时打击。
2.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目前我国律师人才仍十分缺乏,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而确立律师在场权,则要求在一个案件中往往需要两到三名律师,来适应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不定期讯问时在场的需要,这无疑给现有的紧缺律师资源造成更大浪费。由于律师在场不可避免地会对侦查人员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因此造成侦查人员过多地纠结于一个案件,势必会影响对其他案件的侦查,这样也是对侦查资源的浪费。
四、我国侦查程序中确立律师在场权的设想
辩护律师处于控方的相对面,与控方形成对立关系,处处遏制着侦查机关的权力,对于快速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目的造成一定的影响。刑事诉讼法不仅要打击犯罪分子,更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处罚。因此,遵循现代法治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借鉴域外先进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亟需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在场权。
(一)合理确定适用律师在场权的案件范围
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对于在侦查程序中适用律师在场权要进行详细的分类,不能搞“一刀切”;而且必须要由法律明确规定,以免造成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否则不仅是对我国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还可能会影响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目的的实现。在侦查程序中,除了以下情形,均应要求律师在场。第一,严重犯罪案件不强制要求律师在场。例如,涉及恐怖活动的犯罪案件、共同犯罪人在逃或突发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等。这类案件往往具有突发性、紧急性、较大社会危害性,为了能够及时排除危险,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可以对这类案件不强制要求律师到场。第二,普通的轻微犯罪案件。这类案件事实清楚,犯罪证据容易搜集,在现实情况中侦查机关对犯罪分子的侵害情形极其少见。再加上此类案件社会危害性较小,刑罚较轻。考虑到目前我国的律师储备数量,因此对这类案件可以不强制要求律师到场。
(二)律师在场权的行使方式
目前,国际通行的律师在场权的行使方式是“可视不可闻”模式和“可视又可闻”模式。所谓“可视不可闻”就是把律师与犯罪嫌疑人在讯问场所中隔离开来,律师仅仅能够看到讯问过程而无法亲身参与。而“可视又可闻”则是指律师与犯罪嫌疑人处于同一讯问场所,律师亲身参与讯问过程。
“可视不可闻”模式割裂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联系,无法对侦查机关的各种非法讯问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我国的律师在场权应当采用“可视又可闻”模式,使律师能够及时地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并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予以制止。同时,为了保障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律师的权利也应受到部分的限制,即如果律师对侦查人员的合法讯问行为无理由地进行各种阻挠,侦查人员可以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隔离,但对于这种情况需要严格限制。
(三)规定在场律师的权利和义务
1.在场律师的权利
主要包括:(1)异议权。当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出现诱供等非法讯问情况时,律师可以当场对侦查人员的行为提出异议。(2)时间保障权。当律师确有正当理由在讯问时确实不能到场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要求侦查机关变更讯问时间,侦查机关应当允许。(3)签字确认权。在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结束后,律师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笔录有最后签字确认的权利。如果没有律师签字,其证据能力应该受到质疑。
2.在场律师的义务
主要有:(1)保守秘密的义务。在场律师对于讯问犯罪嫌疑人过程中所获知的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情况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对外宣传。如果在场律师违反此项义务,可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2)不得妨碍侦查讯问的义务。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在场律师应当严守讯问纪律,不得通过肢体语言等方式向犯罪嫌疑人传递信息。同时,在场律师也不能故意曲解法律,阻碍侦查人员的正常讯问。如果其违反此项义务,侦查人员有权要求律师离场。
(四)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一项制度的设置往往引发相关制度的变革。律师在场制度的构建,还需要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套完善。第一,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对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援助应从审判阶段扩展至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侦查阶段。第二,完善证据制度。律师在场权制度一旦确立,证据规则必须做出相应的修改。比如,将没有律师在场而获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归于非法证据,从法律上确认其无效;又如,辩护方对有律师签字的供述笔录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存在异议的,其举证责任将由控诉方移转到辩护方。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弱者,即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有时候社会种种复杂的因素容不下我们那种简单的想法——“身正不怕影子斜”、“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佘祥林案是如此,赵作海案也是如此。因此,犯罪嫌疑人在面对强大的国家侦查机关时,需要有效地保障其合法权利,同时限制侦查机关过分扩张的权力。而侦查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恰恰能对侦查机关形成较有力的制约,以平衡控辩双方的地位。虽然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了对讯问过程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但相对于冰冷、简单的机器,我们应该更相信具有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的律师。
[1]田荔枝.论我国侦查讯问阶段律师在场制度的构建[J].法学论坛, 2009(3).
[2]熊秋红.刑事辩护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赵海峰.欧洲法通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袁荣林.关于确立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构想[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5(2).
[5]葛泉宝,常永达.看得见听得到的正义[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D915.3
A
1673―2391(2014)06―0126―03
2014-04-03 责任编校:袁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