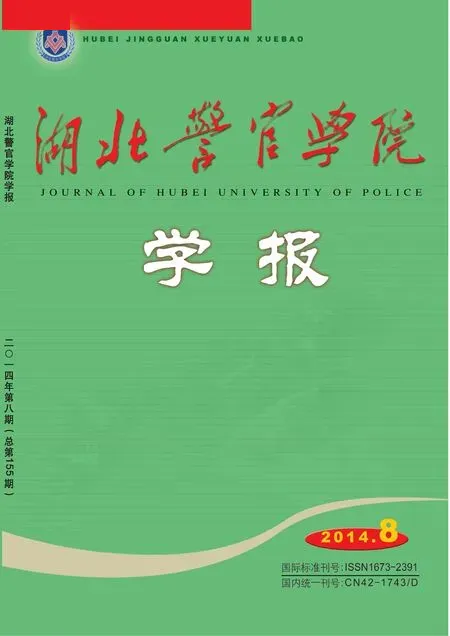临床试验受试者知情同意权的民法意象
2014-04-06刘学民
刘学民
(河北医科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17)
临床试验受试者知情同意权的民法意象
刘学民
(河北医科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17)
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是临床试验民事法律关系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在民法视阈中,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是一项持续性的精神性具体人格权,是一项被《侵权责任法》确认了的法定权利。它的法律意义和法律效力在于其直接影响着临床试验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消灭,这与常规医疗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存在明显区别。受试者知情同意权被侵害后,发生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在请求权选择问题上,主张侵权责任请求权对保护受试者更为有利。
临床试验民事法律关系;受试者知情同意权;法定人格权;缔约过失责任;侵权责任
临床试验是医学发展的必经环节。正如《赫尔辛基宣言》所指明的那样,“医学的进步是以研究为基础的,这些研究最终必然包含了以人作为受试者的研究”。①此处为《赫尔辛基宣言》(The World MedicalAssociation Declaration ofHelsinki:EthicalPrinciplesfor Medical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2013年修订版的表述("Medical progress is based on research that ultimately must include studies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需要注意的是,此处表述与我国《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等规范性文件所援引的2000年版本略有不同。参见http://www.wma.net/ en/30publications/10policies/b3,2014年5月19日访问。实际上,几乎所有新药、大部分医疗器械和医疗卫生技术都必须经过临床试验,才能进入临床应用。②参见《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31条、《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17条和《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第3条。临床试验的目的是获取医学知识,但参与试验的人类受试者却承受着医学试验的固有风险。有时,受试者甚至需要承受技术因素之外的不正当的人为风险,从而使其处于权利被忽视、被侵害的状态,成为科研利益和商业利益的牺牲品。2012年,引起媒体和公众广泛关注的“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事件即为一例。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的调查结果,美国和中国科研工作者在湖南省某小学联合开展“黄金大米”(转基因水稻)试验。美方人员将烹调好的“黄金大米”米饭非法携带入境,分发给该小学儿童受试者食用。但课题组没有向受试者家长和监护人说明试验将使用转基因的“黄金大米”,也未发放完整的知情同意书,仅发放了知情同意书的最后一页。该页上没有提及“黄金大米”,更未告知食用的是“转基因水稻”。③参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省医学科学院、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黄金大米中的-胡萝卜素与油胶囊中的-胡萝卜素对儿童补充维生素A同样有效〉论文的调查情况通报》,http://www.chinacdc.cn/zxdt/201212/t20121206_72794.htm,2014年5月19日访问。鉴于受试者知情同意权的重要意义,学术界对于受试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集中于医学伦理学、医事法学领域内的伦理规范、试验管理、具体措施等问题,较少涉及民法视阈下知情同意权的法律性质等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些探讨。
一、临床试验民事法律关系与受试者知情同意权
一般来说,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Clinical Experimentation)是指对药物、医疗器械等医疗卫生产品或者医疗卫生技术的安全性、有效性等情况按照规定进行研究、试用或验证的行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临床试验有时可以代指“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Bio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即所有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生物医学研究活动,具体来说就是指以人体为试验对象,通过干预人体获取医学研究所需物质、资料、信息或以其他方式从人体获取供医学研究的物质、资料、信息的行为。[1]临床试验活动中存在多方当事人,但主要的参与者仍是申办者、研究者和受试者。申办者(Sponsor)负责发起、申请、组织、监查和稽查一项临床试验,并提供试验经费。在实践中,申办者一般是各医药公司、生物科技公司等。研究者(Investigator)是经过资格审查,具有临床试验的专业特长、资格和能力的人。研究者负责实施临床试验,并对临床试验的质量及受试者安全和权益负责。①参见《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第68条。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国关于临床试验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条款均以研究者为主语,但真正的当事人是研究者所属的研究机构。在实践中,临床试验研究机构主要包括符合特定条件的医院、研究院、研究所等。②具体的临床试验机构名单可以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上查询。受试者(Human Subjects)是指参与临床试验,作为研究对象或试验对象的人类个体,媒体有时称之为“试药人”。在不同的试验中,受试者可能是健康人,也可能是患有目标适应症的病人(例如药物的II期、III期临床试验)。对于后者,临床试验在追求医学新知的同时,可能也具有治疗性效果。
由于各方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人格和法律地位,在临床试验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将形成多种民事法律关系。从狭义上讲,临床试验民事法律关系仅指受试者与研究机构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从广义上讲,还应包括申办者与研究机构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等。本文仅探讨狭义的临床试验民事法律关系。其主体是受试者与研究机构,客体是临床试验行为。在内容方面,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利。
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直接与临床试验的固有风险联系在一起。受试者有权知晓自己准备参与的试验的各种信息,是因为临床试验具有高风险性,用于试验的医疗产品和技术是不成熟的产品和技术,尚未进入临床应用,副作用、不良反应,甚至给药剂量等均未得到确认。例如,药物临床试验的环节之一为确定人体对药物的最大难受剂量。[2]受试者参与临床试验,或者出于奉献精神,有意助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学科研的顺利进行,或者出于经济考量,期望通过参加试验获得经济补偿和报酬。③有时研究者会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有的研究机构工作人员也接受试验。这些人员主要是基于奉献精神参与实验,属于志愿者。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的受试者被媒体称为“职业试药人”,他们往往是无业人群、贫困大学生等。“职业受试者”群体有时通过网站或论坛彼此交流临床试验信息。但不论出于何种动机,受试者的权利均需受到保护,而其首要权利便是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Right to Informed Consent)是指有行为能力的受试者在被充分告知与研究有关的信息并充分理解这些信息后,在没有任何外力胁迫或诱导下自愿作出参与、不参与或者退出临床试验的权利。[3]在临床试验中,研究者应当严格遵守“知情同意原则”或者“告知后同意原则”(Doctrine of Informed Consent),以保护受试者的自由和尊严,使受试者得以根据研究者说明义务的履行,充分了解临床试验的研究目的、方法、可能的利益冲突、预期的受益、潜在的风险、可能出现的不便与不适等各种信息,以便自主作出是否参与试验的决定。
二、受试者知情同意权的法律性质
(一)受试者知情同意权的人格权属性
首先,从知情同意权的性质上说,知情同意权是一项精神性具体人格权。知情同意权以受试者的一般人格权为基础,目的在于保障受试者的人格自由、人格独立和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化,属于具体人格权。同时,知情同意权以自然人的人格利益为内容,属于精神性人格权。
其次,知情同意权是一项法定权利。《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何为“特殊检查”、“特殊治疗”,《侵权责任法》并未作出解释。笔者认为,所谓的“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是包括临床试验在内的。《侵权责任法》的这一概念应是来源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该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88条,“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包括“临床试验性检查和治疗”,即临床试验。可见,《侵权责任法》实际上确认了临床试验中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以及相对应的研究者的说明义务)。此外,《执业医师法》第26条第2款明确规定:“医师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属同意。”当然,我国目前关于知情同意权最全面的规定是《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定》。前者第14条规定:“研究者或其指定的代表必须向受试者说明有关临床试验的详细情况:(一)受试者参加试验应是自愿的,而且有权在试验的任何阶段随时退出试验而不会遭到歧视或报复,其医疗待遇与权益不会受到影响;(二)必须使受试者了解,参加试验及在试验中的个人资料均属保密。必要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伦理委员会或申办者,按规定可以查阅参加试验的受试者资料;(三)试验目的、试验的过程与期限、检查操作、受试者预期可能的受益和风险,告知受试者可能被分配到试验的不同组别;(四)必须给受试者充分的时间以便考虑是否愿意参加试验,对无能力表达同意的受试者,应向其法定代理人提供上述介绍与说明。知情同意过程应采用受试者或法定代理人能理解的语言和文字,试验期间,受试者可随时了解与其有关的信息资料;(五)如发生与试验相关的损害时,受试者可以获得治疗和相应的补偿。”后者第8条作了稍有不同但大体类似的规定。可见,在我国,知情同意权已经被界定为一项法定权利。
再次,从知情同意权的内容上说,知情同意权包括知情权和同意权。知情同意权的要素包括信息的揭示、信息的理解、自愿的同意和同意的能力,[4]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理解”。理解是告知的目的,也是同意的前提。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认为,“告知后同意”原则的精神,与其说重点是在“同意”,不如说重点是在“告知”和“了解”,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希望民众于充分的理解与认知之下,在评估所有可能影响其是否参与该研究的因素之后,自由决定是否愿意参与研究。[5]
最后,从知情同意权的特点上说,知情同意权是一种持续性权利。知情同意权的行使是受试者与研究者双向交流的过程。研究者单方面提供信息或者受试者被动接受信息,都不构成有效的知情同意。[6]知情同意过程是一个解释、说明和交流的过程,[7]是一个包括研究者的告知、受试者的理解与询问、研究者的再告知等一系列阶段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知情同意书的签署这样一个单一过程。其中,知情权的持续性表现为研究者必须将临床试验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可能影响受试者决定的信息及时告知受试者,使之有机会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同意权的持续性表现为受试者在同意参加试验后,享有随时改变自己同意的结果、随时选择退出的权利,而且不能因为退出试验而受到歧视或报复。这一点在受试者是病人时显得尤为重要。病人退出试验后,其原本享有的常规医疗不能因此而受到影响。[1]
(二)受试者知情同意权的法律意义——兼论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区别
受试者知情同意权在临床试验民事法律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与该法律关系存在紧密联系:受试者的同意决定直接影响着临床试验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和消灭。对于临床试验合同来说,研究者招募受试者的行为构成要约,受试者在充分理解试验相关情况后签署知情同意书的行为构成承诺。因此,受试者知情同意权的行使是临床试验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和消灭的必然环节。这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是不同的。患者在常规医疗中也享有知情同意权,但它对于常规医疗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影响不大。按照通说,常规医疗民事法律关系在患者挂号后成立。[8]对于医疗合同来说,病人要求挂号的行为构成要约,医疗机构收取挂号费并发出挂号凭证的行为构成承诺。[9]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行使很多时候只影响具体治疗方法的选择,只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变更的效果。
由此可见,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与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是不同的。二者尽管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而且在当医院本身即为临床试验研究机构、医生本身兼为研究者的情况下,二者存在的时空环境也几乎一致。但是,这两项权利不能相互混淆。上述内容是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即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不同。
受试者知情同意权和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另一个区别是二者对应的义务不同。在性质上,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对应的是医生的说明义务,该项义务属于合同义务;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对应的是研究者的说明义务,该项义务属于先合同义务。在程度上,研究者的说明义务具有某种绝对性,要比常规医疗中医师的说明义务更为严格。[10]在医疗行为中,医患双方的利益在很多时候是一致的,即双方均追求患者疾病的成功治疗。但是,在临床试验行为中,研究者与受试者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临床试验行为的本质是科研行为,研究者追求的是试验方案得到严格操作,并获取准确的研究结果。受试者的人身利益需要外部力量,即法律或伦理规范来强调并加以保护。因此,研究者要尽到比医生更加严格的说明义务。即便是在说明义务可以免除的场合,临床试验的相关规定也远远要比常规医疗更为严格。按照《侵权责任法》第56条的规定,在常规医疗中,免除医生的说明义务需要满足下列条件:(1)属于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2)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3)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按照《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第15条第4项,在临床试验中,免除研究者的说明义务需要满足下列条件:(1)属于紧急情况;(2)无法取得本人及其合法代表人的知情同意书;(3)缺乏已被证实有效的治疗方法;(4)试验药物有望挽救生命,恢复健康,或减轻病痛;(5)在试验方案和有关文件中清楚说明接受受试者的方法;(6)事先取得伦理委员会同意;(7)该项免除研究者说明义务的规定只适用于受试者为患有目标适应症的患者的临床试验,不能适用于所有临床试验(这一点条文没有明示,但不难推断)。由此可见,研究者的说明义务免除条件远比医生苛刻。
三、侵害受试者知情同意权的民事责任
(一)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如前所述,研究者的说明义务属于临床试验合同的先合同义务。研究者未履行此义务,即构成合同责任中的缔约过失责任。根据民法基本原理,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形式是损害赔偿。因此,研究机构应当赔偿受试者由此而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这主要包括直接损失,即受试者为订立合同所付出的费用,如往返差旅费、通讯费等。
至于是否应当赔偿受试者的间接损失,即因丧失其他机会所造成的损失,则需要慎重对待。这涉及伦理与法律两种社会关系调整手段的冲突问题。临床试验属于伦理性很强的领域,伦理规范在受试者保护等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临床试验相关立法也带有十分明显的伦理性和国际性。例如《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等,通过援引和列为附件的方式,直接把国际伦理规范《赫尔辛基宣言》转化为国内法律规范。国际伦理规范的精神是不主张给予受试者过多的经济补偿的,甚至在招募受试者时不允许对受试者允诺过多的经济利益:报酬不应太多,[11]否则将构成“不当诱导”(undueinfluence)。①参见《贝尔蒙特报告》(TheBelmontReport:EthicalPrinciplesandGuidelinesfortheProtectionofHumanSubjectsofResearch):"Undue influence,by contrast,occurs through an offer of an excessive,unwarranted,inappropriate or improper reward or other overture in order to obtain compliance.Also,inducements that would ordinarily be acceptable may become undue influences if the subject is especially vulnerable."http:// www.hhs.gov/ohrp/humansubjects/guidance/belmont.html,2014年5月19日访问。尤其是在受试者处于经济等方面的不利地位和困境时,其可能会因为丰厚的经济回报而忽视试验风险,盲目进入试验。由此可见,伦理规范是不鼓励受试者出于经济目的参与实验的,临床试验伦理世界的理想图景是“志愿受试者”完全出于推进科学发展和卫生技术进步的目的而甘愿自我牺牲,自愿参与实验。但事实是,现实中存在大量的所谓“职业试药人”。他们频繁参与各类试验,目的恰恰是获取经济回报。“职业试药人”的存在是违反伦理规范的基本理念的。不难推断,按照伦理规范,是不能赔偿受试者因丧失其他机会所造成的间接损失的。然而,法律,包括民法,与伦理规范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律调整的是人的外部行为。法律难以对受试者提出过多的道德要求,也不会过多考量受试者甚至“职业试药人”的主观意图。因此,按照民法理论,受试者在知情同意权受到侵害后,是有权主张其因丧失其他机会所造成的间接损失的请求权的。
研究者没有完全、适当、充分、及时履行说明义务,在符合其他要件的情况下,也构成侵权责任。根据研究者侵权的具体情况,受试者可以要求研究者承担损害赔偿、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礼道歉等责任。损害赔偿即要求研究者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范围除了包括往返差旅费、通讯费等直接损失以及因丧失其他机会所造成的间接损失之外,也不排除精神损害的可能。停止侵害即要求研究者及时、充分履行说明义务,将临床试验的相关情况告知受试者。排除妨碍即要求研究者对知情同意书中的专业术语以通俗的语言、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适当的方式进行解释,并给予受试者充分思考的时间,使受试者得以准确理解并作出决定。赔礼道歉即要求研究者对置受试者人格权于不顾,使之承受被商品化、物化的人格尊严损害的行为进行道歉。
可见,研究者如果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完全、适当、充分、及时履行对受试者的说明义务,在很多时候将同时符合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出现民事责任竞合的现象。
(二)受试者的请求权选择
在请求权选择问题上,从受试者的角度出发,相较而言,主张侵权责任请求权更为有利。侵权责任比缔约过失责任在很多方面更能有力地保护受试者。
一方面,主张侵权责任可以避免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追究研究机构与申办者的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要求申办者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在缔约过失责任的情况下,由于申办者与受试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合同磋商关系,很难要求申办者承担民事责任,尽管申办者对受试者的损害后果可能也存在过错,例如申报者可能故意隐瞒部分试验信息。但是,在侵权责任的情况下,如果申办者与研究机构构成了共同侵权,就可以追究二者的连带责任,此外,在二者的行为构成“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情况下,也不排除追究二者按份责任的可能性。总之,主张侵权责任可以更好地确保受试者的损害得到填补。
另一方面,主张侵权责任可以使受试者得到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更多索赔款项。目前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一般不承认合同责任,包括缔约过失责任中的精神损害的索赔要求。若主张侵权责任,则存在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甚至有学者认为,如果研究者故意侵害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则应当准许受试者主张惩罚性赔偿。[12]另外,学者还主张,未能获得有效的知情同意而进行人体试验是对受试者自我决定权的侵犯,即使没有造成损害,受试者也可以提起侵害知情同意权之诉而要求赔偿。[12]此种见解完全“消解”了损害赔偿责任的“损害”要件。无独有偶,有些学者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消解”“损害”要件,认为《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2款提到的未尽告知义务(即说明义务)而造成的“损害”包括未尽告知义务侵害知情同意权并造成人身损害和未尽告知义务侵害知情同意权两种情形,应当分别依照《侵权责任法》第16条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和第22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要求侵权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13]这一观点应当来源于英美法上的“名义上的损害”(nominaldamages),即可能没有遭受实际上的损害,但对权利的侵犯已经造成了对被害人平等身份和自由利益的妨碍。[14]当然,适用惩罚性赔偿、“消解”“损害”要件是否合适,应当放在社会公众(医药卫生事业)、研究机构与受试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侵权责任法与民法的理论发展和理论自洽问题中进一步考量。但是,不得不承认,处于变动与发展中的、更为活跃的侵权责任法理论与实践给受试者提供了更多的利益保护可能性。
受试者是临床试验中的弱势群体。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和信息的严重不对等,受试者极有可能忽略或者不能正确理解这些风险,研究者也有可能以欺骗、胁迫、不正当诱导等方式使受试者难以作出理性选择。据媒体报道,在现实中甚至发生过受试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参与临床试验,最终死亡的严重案件。①参见孙展、刘溜:《地坛医院的“试药”风波》,载《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21期;沈颖:《上海东方医院治心术调查》,载《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第B10版。如何进一步有效保护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以及其他权利,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1]罗蓉.医学研究中试验人体的保护[A].[美]斯科特·伯里斯,申卫星.中国卫生法前沿问题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245,255.
[2]金丕焕,邓伟.临床试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4.
[3]张洪松,兰礼吉.医学人体实验中的知情同意研究[J].东方法学, 2013(2):128.
[4]朱万孚,陈冠英.生物医学安全与法规[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7:242-244.
[5]刘宏恩.试评日本基因资料库之相关伦理规范与制度设计——以其组织运作及告知后同意问题之处理为讨论核心[J].月旦法学杂志,2007(141):37.
[6]姜萍,殷正坤.人体研究中的知情同意问题研究综述[J].哲学动态,2002(12):30.
[7]王德彦.知情同意与人体试验[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1):15.
[8]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62.
[9]王金凤.无名合同[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148.
[10]和绿华.“知情后同意”原则适用于人体试验之研究——以受试者自主权为核心[D].中坜:中原大学,2005:34.
[11]卜擎燕,熊宁宁,吴静.涉及人类受试者研究的伦理指南[J].中国新药杂志,2004(6):570.
[12]徐喜荣.论人体试验中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从“黄金大米”事件切入[J].河北法学,2013(11):119.
[13]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研究”课题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草案建议稿[J].河北法学,2010(11):17.
[14]宁金成,田土城.民法上之损害研究[J].中国法学,2001(2):107.
D923.3
A
1673―2391(2014)08―0104―05
2014-05-06责任编校:王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