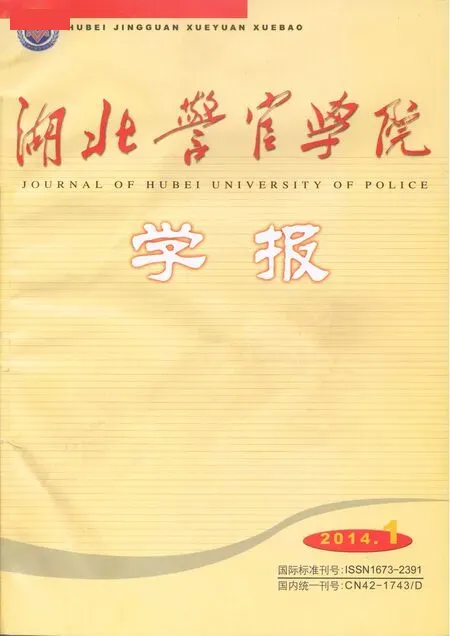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2014-04-06但小红
但小红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510521)
应该说,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具备了,但是论及胎儿,鉴于其仍与母体相连,学界公认胎儿无权利能力,更不可能成为民事主体。但不容忽视的是,我们每个人都经过了从母体受孕到生活在世上的历程(即便是试管婴儿,也须经母体孕育后生产)。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胎儿将来的权利利益需得到切实的保障,而在此之前或者现在的权利利益也要得到维护。因此,按照始于古罗马的传统立法例,现代国家的立法条文中几乎都有关于胎儿利益保障的专门款项。
从传统的罗马法律文书来看,其完全可以将未出生之胎儿与已经出生的新生儿视为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此外,罗马法规定了一些与已有惯例相反的原则,如否认还没有降临到人世的胎儿的完全人格特质。简言之,从罗马法规定的角度出发,如果涉及胎儿相关权利与利益的保障,胎儿此时可以被视为从母体受孕时即具有相应的人格特质和权利能力。
一、各国家及地区立法模式概述
近代以来关于胎儿相关权益的立法保护模式可以概括总结为三类:
(一)广延的总括主义(总括的保护主义)
广延的总括保护主义是对于胎儿的一切权利和利益没有任何的条件例外,统括地实行统一的标准,不遗余力地进行保障。可以说,这样的规定对胎儿的利益保障是系统的、详尽的、全面的。此种规定采取无间隙、全面、系统涵盖的方式,目的是将胎儿视为一个完整和健全的人,实现其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有此规定的国家和地区代表为瑞士和我国的台湾地区。
(二)有区别和例外情形的个别保护主义
有区别和例外情形的个别保护主义将未出生之胎儿视为没有相关权利能力,但是有一定的例外情形。这些例外多数体现于未出生之胎儿受遗赠和其法定代理人突然过世的继承的情形。这种法律语境视个别与特殊情况对胎儿的合法利益进行保障。具有类似规定的代表性大陆法系国家有法国、德国以及日本。《日本民法典》第721条规定了损害赔偿请求的情形,第886条和第965条是遗产相续的相关规定,第1065条规定受遗赠能力,第783条规定父亲对胎儿的认领等。
(三)绝对不保护主义
现在看来,绝对不保护主义是比较狭隘的立法原理。其主张不论在何种情形与条件语境下,对未出生之胎儿的全部权利和利益均实行统一的无视和不保障原则。近现代有此种规定的情形如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
二、我国《民法通则》之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总括规定了民众日常民事生活的行为准则和概况原理。在胎儿相关权益保障层面,总体的原则性规定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对未出生的胎儿参与相应遗产分配和赠与的问题,我国继承法律的态度是比较乐观和肯定的,即应保留胎儿应该继承的份额。出于这样的法理结构,我们可知,当胎儿的法定代理人死亡时,胎儿的法定继承份额要保留,这意味着胎儿并不是即时取得其继承的财产,即我国民法中的特别留存的份额实属“留而不给”,因为一个胎儿处于母体之中是没有遗产继承权利的。所以说,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并未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既没有实行概况的保护主义原则,也没有实行个别例外的保护主义原则。
国内学界对于我国民法之于胎儿合法权益保障问题观点不一。其中有部分学者担心:如果赋予胎儿一定的权利能力,就会相应出现很多关联研究问题,如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是否可为胎儿,又如为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而堕胎等伦理取向问题。鉴于此,有学者提出,胎儿将来的权利与利益仅需相关法律界定即可,目前并没有达到给予其相应权利能力的程度。而且,在后期实践总结中,很多学者认为绝对不保护主义是三类立法模式中最不可取的。由于理论上对赋予胎儿权利能力持否定态度,在司法实际操作过程中,胎儿的种种权益遭受损害后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补救的事实屡屡发生。所以,本文建议我国立法采取概况保护主义模式,以强化对胎儿民事权益的保障,顺从伦理道德以及民法革新的趋势。
对于前文提及的三类立法模式,笔者认为绝对的否定和不保护是最不能接受和采纳的。胎儿的民法利益保护纯粹是立法技术上的问题,不涉及基本的民法伦理立场和原则概况。而关于堕胎的合法性问题,则因各国的实际国情和民族特质、生活风俗而有不同的判断。有这样一种认知,即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的话,那么堕胎就是非法的,“流产就意味着杀人”。另外,当提及对自然人的生产以及相关胎儿权利的立法保障时,刑法与民法的法理基础和原则相差甚远。例如,在德国刑法中,若有人杀害出生之时的胎儿,那么就以杀人罪予以处罚。但德国民法规定,自然人从脱离母体时获得权利能力,实行个别的保护主义原则。鉴于以上实例,那种认为承认胎儿具有一定的权利能力会对中国的广大女性和社会的稳健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的言论和观点,是有点夸张和与事实不符了。
个别区分的保护主义原则和立场在具体的适用范畴方面存在优势。但归根结底,就胎儿的相关利益保障问题,立法并非是十分完美和健全的。伴随社会的发展与人们整体素质的提升,涉及胎儿相关利益保障之事务会更加系统复杂,立法者并不能全部预见。所以,总括的保护主义模式应为最合适的选择。
三、胎儿相关民法权益保护之案例
在日本,有关侵权赔偿的判例是这样的:甲在与乙一夜情后怀孕并生下了丙,但乙一直不知情。后来,乙被电车撞死,甲代理丙与相关责任公司达成死亡赔偿协议。丙知晓真相后要求法院判决协议无效。最后,法院支持了丙的诉讼请求,并对相关赔偿权益和经济利益进行了新的确认。此判例在日本法律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些学者认为,法定的停止条件说对保障胎儿的利益和权利更为有利。承认母亲对小孩有法定代理权,即母亲有权利处分胎儿权益,会造成对胎儿的不利益。也有人认为,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会对胎儿的总体利益保障更为有利。他们主张胎儿权利能力的有限性,而且认为,只有在对胎儿有益时,相关人(母亲)才可以进行代理,且不能处分该利益。
有鉴于此,我国应采取概括的保护主义原则,对胎儿的相关权利能力和经济继承利益进行全面的、无间隙覆盖的保障。这对胎儿的生产及成长是十分必要的。
四、胎儿应受保护的民事利益范畴
关于胎儿应受保护的民事利益的范畴问题,学者们可谓见仁见智。公认的原则和理论是,针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不应仅停留在财产利益层面,还应落实到具体的人身利益上,如胎儿的生命权、健康权等。笔者认为,胎儿应受保护的民法利益应当包括但并不局限于以下几类:
(一)生命权和健康权
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胎儿不具有生命权,但笔者却持有异议。生命权是每一个人应享有的最基本权利。基于自然法和生命法益论,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权不是法定权利,而是自然权利。虽然胎儿在出生之前与母体合一,但从自然伦理和人类发展角度而言,脱离母体成为独立的个体是其最终目的。因此,胎儿应享有充分、必要的生命权利,可以依据遭受的损害请求相应的补救和赔偿。
同时,胎儿的健康出生和身体保障权利不容剥夺。胎儿在母体内健康生存是其能够顺利生产的必要前提条件,关系到其能否成为一个完整健全的“人”。胎儿在母体中的健康权利遭受损害,不论对胎儿成人后的自己、父母还是社会均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将健康权纳入胎儿的民事权益范畴是十分必要的。
(二)受抚养权和继承权利
胎儿时期是形成一个健全“人”的必经阶段。基于胎儿的脆弱性和成长阶段的特殊性,承认其具有受抚养的权利,对于胎儿出生前及出生后的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不论因义务抚养人自身原因还是外人的侵权行为导致胎儿受损害,胎儿都可以基于此项权利,请求获得一定的保障。
至于法律上之于胎儿继承权的相关规定,基本上各国都是一致的,即胎儿享有继承权。我国民法也十分赞同这一做法。
(三)享有纯获利益的权利
我国民法中存在遗赠方面的规定。就胎儿而言,由于其出生时,法律规定的两个月的表示期间已经届满,这样将损害胎儿受遗赠的权利。基于此,笔者认为立法应当规定胎儿的法定代表人可作相关意思表示,以保护胎儿纯粹获益的权利,且不得实施相关损害胎儿合法利益的行为。
[1][日]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则[M].唐晖,钱孟姗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47.
[2][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30-31.
[3]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