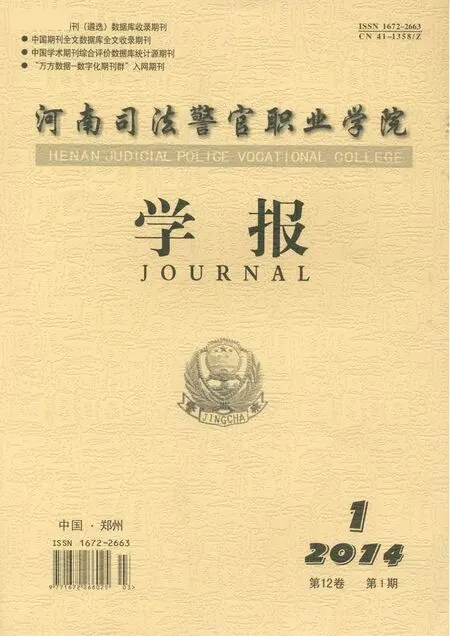必要共犯争议问题探析
2014-04-05李岚林
李岚林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在刑法共犯理论中,中外学者往往将共犯进行分类研究,以便区别对待各共同犯罪人,分清责任,从而科学定罪量刑。按不同的标准,理论上对共犯有不同的分类,其中以共同犯罪是否依照法律的规定必须由复数主体形成为标准,将其分为任意共犯和必要共犯。必要共犯在立法上出现的时间比任意共犯更早,但相对于任意共犯这个“宠儿”来说,必要共犯理论的研究仍属于刑法中的冷门领域,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必要共犯并无太多裨益〔1〕,或者没有多少理论意义〔2〕,是刑法释义学上的继儿。〔3〕而在必要共犯理论内部也是争议颇大,各家众说纷纭。
一、必要共犯概念界定
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德国学者Stübel为必要共犯概念的创始人。他于1805年在其著作《论犯罪的构成要件》中首次提出类似必要共犯的一种犯罪类型,并举互殴罪与肉体上的侵犯为例加以说明,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必要共犯这一概念,但理论上仍认为其见解是必要共犯概念的滥觞。直至1869年德国学者Schuetze在其论文中明确提出“必要共犯”这一概念并予以研究。①学界普遍认同必要共犯的概念最早是由Schuetze在1869年提出。参见:〔德〕佛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中译本),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57页。后来德国学者Kries指出必要共犯是在概念上以数人的加担为必要犯罪,这才使得必要共犯的概念得到真正确立,这种观点也成为通说。必要共犯由德国学者提出至今已有200余年历史,可以说是相当古老。虽然不如共犯其他领域命题的研究受人瞩目,但在理论上仍能稳定而持续地有学者不断提出新看法,提供新的研究重点。
在必要共犯的概念界定上,中外学者也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不同诠释。在必要共犯的发源地德国,有不少具代表性的见解。如李斯特认为:“根据其构成要件,从概念上看需要多人共同协作的犯罪,为必要共犯”〔4〕;耶塞克认为,“如果一犯罪构成要件要这样来理解,即实现该构成要件在概念上必须有数人参与,就成立必要的共犯”〔5〕;维塞尔斯认为,“构成必要的参与是指,如果行为的构成要件是被这样规定,使得从它的概念上讲就要求对构成要件的实现要有数人参加为前提条件,如亲属间的通奸”〔6〕可见,德国学者对必要共犯的界定,主要界定在“多人参与”这一必要性上,即要求有复数行为人。
在日本,对必要共犯也有不同的定义。如野村稔认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实现是取决于复数的人去实施犯罪行为,叫作必要的共犯。”〔7〕西田典之认为:“刑法分则中,有的犯罪类型本身规定了多数人的参与形态,将以此类型化的,称为必要共犯。例如内乱罪、骚乱罪、受贿、行贿罪等就属于必要共犯。”〔8〕山口厚认为:“在犯罪之中,还存在这样的场合:作为犯罪类型所规定的是多数人的共动、加功本身。比如说,内乱罪、骚乱罪、重婚罪、赌博罪、受贿罪与行贿罪、准备凶器集合罪等都属于此类,这样的场合称为必要的共犯。”〔9〕大谷实认为:“必要共犯就是指在构成要件的性质上,最初就是预定由数个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10〕大塚仁认为:“必要性共犯,是指在刑法分则的规定或者其他刑罚法规上预定为二人以上者的共同犯行而规定的犯罪。”〔11〕松宫孝明认为:“有些犯罪从一开始就无法被单独实施。例如,内乱罪和骚乱罪,如若没有众多人一同实施暴动或者暴行、胁迫就不成立。受贿罪,如果没有行贿人就不会成立。这种情形称为必要的共犯,以区别于犯罪可以单独实行之任意的共犯。”〔12〕可见,日本学者在定义必要共犯时,同样趋同于强调复数行为人的参与,只是大多数学者更强调指出此多数人犯罪的类型化规定由法律预先设定。
在台湾,学者对必要共犯也做出了不同的表述。如林山田认为:“……惟刑法分则编规定的各罪中,却有极少数的故意犯,其不法构成要件的实现,系以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参与为必要,这种不法构成要件的犯罪,即属学说上所称的必要的参与犯。”〔13〕林钰雄认为:“刑法分则有某些犯罪,立法者预先设了复数行为主体始能违犯,这主要包含复数参与者概念上皆为正犯者,但也包含复数参与者概念上有正犯亦有共犯者。以上可合称为必要之参与犯。”〔14〕黄荣坚认为:“相对于任意共犯,学说上还有所谓的必要共犯的概念,意指刑法分则所规定之某一特定犯罪类型,其犯罪构成的本身即以数人共同参与其不法行为为要件,因此如果不是数人参与,根本不具备不法构成要件该当性。”〔15〕陈子平认为:“所谓的必要的共同犯罪,即必要的参与犯,系指于犯罪构成要件上,以二人以上之行为人共同行为为必要之犯罪类型,即原本就以多数人之参与为必要之犯罪类型而言。”〔16〕可见,台湾学者虽表述不同,但多认同必要共犯的必要性体现在构成要件上须有多人共同行为的犯罪类型,只是在阐述的方式上各有不同。
我国大陆也有愈来愈多的学者研究必要共犯,虽延续德日的相关理论,但依然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陈兴良认为:“必要的共同犯罪是指刑法规定只能由二人以上构成的犯罪。因此,这种犯罪不可能由一人单独构成,而是以二人以上共同实行为必要条件的犯罪。”〔17〕马克昌认为:“刑法分则大多数条文都是以一个人犯罪为标准而加以规定的;但也有一些条文规定了由二人以上的共同行为才能构成的犯罪。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可做必要的共同犯罪。”〔18〕张明楷认为:“必要的共犯,是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必须由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的犯罪。”〔19〕大陆学者对必要共犯的定义基本大同小异,其多数将视角放在刑法分则规定,且以两人以上的共同行为为要件上。
综上,中外学者对必要共犯的概念表述各异,但仔细比较可发现,对于必要共犯的必要性基本达成共识,即以复数行为人共同实行为必要条件。研读大多数文献资料,提到必要共犯,为使读者能初步理解,皆提出任意共犯的概念来辅助,将必要共犯与任意共犯作为相对立的两种概念来理解。必要共犯在刑法规范体制中,仅在分则各构成要件中出现,总则中未有统一的规定。故此,对必要共犯实质内涵的探究,由分则法条各内容难以得出完整结论,必须从各犯罪类型的本质着手考察,才能得出必要共犯概念。笔者认为,探讨必要共犯的概念,可分为“必要”和“共犯”两个概念来观察。“共犯”当然与刑法总则中规定的共犯意义相同。“必要”的含义究竟何在,是侧重于复数行为人还是侧重于复数的行为组成?笔者认为可分情况讨论。通说认为,必要共犯概念下区分为聚众犯和对向犯两种类型。聚众犯即侧重于行为主体的复数,对向犯则不仅要求有复数行为人,且更要求要有确定的互相对向的共同加功行为。故此,必要共犯可以表述为“由刑法分则规定的必须由复数行为人实施的符合构成要件的共同犯罪”。
二、必要共犯是否有存在的意义
多数学者赞同共同犯罪可分为任意共犯和必要共犯来研究,但也有学者认为“必要共犯”概念并无存在的意义。如台湾学者黄荣坚教授认为:“所谓必要共犯,既然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犯罪类型之中以数人共同犯罪为构成要件,那么关于行为人是否构成此一犯罪,以及其刑事责任范围如何,完全属于刑法分则个别条文解释问题。……与刑法总则规定的共犯概念无关。因此,不论是必要共犯概念下所谓的聚合犯或对向犯,其犯罪构成之论证都没有适用刑法共同正犯规定及概念之余地。”〔20〕笔者认为,考察必要共犯是否有“存在的意义”,或者其是否仅为一种犯罪的现象形态而不具有法解释学上的价值,则需观察必要共犯是否有自己独自的问题结构,是否能够发挥规范的判断作用。必要共犯是刑法中已经预先设定的,该犯罪构成要件的实现取决于复数的人去实施犯罪行为,从而区别于偶尔复数的人涉及的能够单独实行的犯罪的“任意共犯”,这种类型化的现象的一种称谓,这也正是其概念存在的意义,更当然具有法解释学上的价值。〔21〕
大陆学者中也有质疑必要共犯概念的,如刘明祥教授认为,必要共犯是以“行为共同说”为理论依据的,而我国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共同说”,主张我国刑法中存在“必要共犯”观点,不仅与刑法的规定不符,而且对司法实践极为有害。因为,既然肯定有些聚众性、集团性、对向性犯罪必须由二人以上共同犯罪才能构成,那么一人以实施该种犯罪为目的而组织他人犯罪或聚众犯罪未逞、或者一方蒙骗另一方共同实施犯罪,在他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要么就都不能作犯罪处理,要么就都得当犯罪处罚。如果说都不当犯罪处理,势必会放纵犯罪,如果都作为必要共犯人来定罪量刑,则又会罪及无辜。〔22〕笔者认为,从我国《刑法》第25条第1款对共同犯罪的定义来看,故意共犯是客观上共同行为与主观上共同故意的统一,实际上,我国共同犯罪究竟是以行为共同说还是犯罪共同说,目前学界亦有不少学者从以前坚持的犯罪共同说转而支持行为共同说。但不论是犯罪共同说还是行为共同说,在面对各种共同犯罪现象时,难以贯彻始终如一的立场。学界在研究共同犯罪现象时,面临着只是单纯依据一种学说难以合理解决共犯所有问题的尴尬。例如,要承认间接正犯,就得借鉴行为共同说的理论,因为以主观主义为基础的行为共同说,认为正犯的成立并不限于亲自完成;要承认事后共犯,就要同意犯罪共同说的理论;要赞同共谋共同正犯的理论具有合理性,就得承认行为共同说是它的基础理论;而要赞同继承的共同正犯,则也需要同意犯罪共同说或行为共同说中所具有的合理性部分……如此等等。①此观点根据武汉大学刑法学教授林亚刚的研究生课堂授课讲义内容整理。从此视角来讲,引入必要共犯也并非与我国刑法规定不符,并且必要共犯理论本身也有其体系性和规范性,不会出现“罪及无辜”或“放纵犯罪”的情况。
三、必要共犯是否适用总则共犯的规定
学说上关于必要共犯的研究,争议的焦点主要在是否适用刑法总则共犯的规定上,对此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
台湾学者洪福增教授认为,必要共犯在各个参与者彼此内部之间,即使有行为适合教唆或帮助的情形,也应排除刑法总则关于共犯规定的适用;但行为主体以外的人自外部的参与,及自外部对于正犯加功的情形,则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23〕可见,洪福增教授认为必要共犯在适用关系上,可以进一步区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内部关系指必要共犯各个参与者彼此之间参与加功的行为,成立必要共犯的已经是共同正犯,当然不能既成立正犯又成立共犯,所以采取了否定的见解。在外部关系上,即必要共犯各参与者之外的人参与此犯罪关系时,当然有成立共犯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情况又回归到了单纯共犯构成的问题。
台湾甘添贵教授认为,应分不同情况讨论。在必要共犯下的聚众犯,可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来分别讨论,此部分与洪福增教授相似。在对向犯中,对向的双方或单方的参与人为数人时,方有成立共同正犯的可能。至于是否成立狭义共犯的问题,他认为不论法律是规定处罚单方或是双方情形下,均不可能成立狭义共犯,处罚双方时,刑法既然已经以正犯予以处罚,即使再有教唆或帮助行为,也无法适用总则共犯的规定;在处罚单方时,既然刑法都不认为成立正犯,当然不能依总则的狭义共犯来处罚。〔24〕可见,甘添贵教授将必要共犯之下的对向犯和聚众犯分别来研究,在对向犯的场合否定了适用总则共犯的可能,在聚众犯场合则认为在外部参与关系上适用狭义共犯的规定。①在日本也有多数学者持此观点,如大塚仁教授、大谷实教授、野村稔教授等。分别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270—271页;〔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33页;〔日〕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其、何力译,邓又天审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80—381页。
大陆学者张小虎教授认为,必要共犯系属刑法分则所设置的一种须由多人参与实行的具体犯罪,作为分则的具体犯罪并不排除其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构成总则共犯;尤其是,在总则共犯基于犯罪人作用的不同而实行主从有别的处罚原则的场合,对必要共犯的多个实行犯区别其主从而予相应处罚,显得尤为必要。然而,必要共犯又是分则设置的一种特殊类型,在某些场合其构成与法定刑已考虑二人以上因素,应当禁止已有评价在成立总则共犯中的重复评价。〔25〕张小虎教授的观点则重点关注两方面:一是要符合我国刑法总则共犯的构成条件;二是要贯彻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笔者认为,必要的共同犯罪参与者,当然各自作为共同正犯受到处罚,因为共同正犯的“正犯性”在于各正犯所实施的都是基本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这与教唆犯、帮助犯等狭义共犯实施的都是总则规定的修正构成要件的行为不同。〔26〕必要共犯也并非完全属于刑法分则个别条文解释问题,一般而言,必要共犯并不适用刑法总则有关共犯的规定,比如必要共犯下的聚众犯,其内部参与者是各自依参与形态而受处罚,因此并无适用总则共犯的余地,以聚众斗殴罪为例,即使在聚众斗殴集团的内部,实施符合教唆、帮助的行为,也是作为符合构成要件的有关行为进行处理,不另外再做处罚。〔27〕但这并不影响必要共犯定罪量刑时内部同样应贯彻“自己责任”原则,例如早稻田大学野村稔教授认为,日本刑法第106条骚乱罪,其各款的行为理解为分别的实行行为,由于这些实行行为而发生了聚众暴行以及聚众胁迫那样的结果,共犯是成立的,因此应肯定该条各款共犯的成立。同样持此观点的还有日本西原春夫、曾根威彦、大谷实等。〔28〕必要共犯中行为人应该也仅就自己所实行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责任,即使行为人符合该分则必要共犯的罪名,在量刑上也应根据总则共犯理论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而有所区别。立法者在规定必要共犯时,自然考虑了此种犯罪的特性而试图将处罚的对象限定于一定样态和一定限度的参与者,未加规定的样态的参与行为当然置于处罚范围之外,从而当然否定共犯规定的适用。〔29〕而对其内部参与者之外的其他行为人的参与行为是否有适用的余地,如上所述,学说上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否定说认为,聚众犯是意图在一定形态和限度上对参与集团行动的人进行处罚,因此对于上述形态之外的参与行为应当置于处罚之外。但在集团犯罪之外,比如聚众斗殴罪中,在聚众斗殴的参与人之外,教唆他人参加聚众斗殴的场合,对该教唆行为,认为不当处罚;同时认为必要共犯的处罚效果波及集团外的人,理论上难以找到根据。〔30〕肯定说则认为,必要共犯关系以外的人对必要共犯施加影响的场合,原则上也应适用总则共犯的规定处理,例如聚众犯中,对教唆聚众斗殴、提供凶器棍棒等帮助参与聚众斗殴的行为,仍应适用共犯的规定。对向犯中,积极地并且执拗地进行活动使贩卖者产生了贩卖意思的行为,已经不能说已被刑法预先设定的定型的犯罪构成要件所包含,所以认定其为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教唆犯是可以的。在日本,平野龙一、西原春夫、大谷实、曾根威彦都持此观点。笔者也较为赞同肯定说。
四、必要共犯在我国共犯体系的适用
如前文所述,刘明祥教授早期在研究必要共犯时,就明确提出我国共犯体系中并不存在必要共犯。随着德日刑法理论的引入,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必要共犯,从不同的视角展开了研究。但不难发现,我国学者通说认为,必要共犯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必须由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的犯罪。而德日刑法理论中,认为由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参与即可构成必要共犯,并未强调二人以上必须共同构成犯罪。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正是由于我国大陆共犯体系与德日刑法的共犯体系的不同。
大陆法系国家,其“共犯”分为三个层次,最广义的共犯、广义的共犯和狭义的共犯。最广义的共犯分为任意共犯和必要共犯。任意共犯是指在刑法总则中规定的共犯,由数人共同实行原可由一人单独实施的犯罪,如故意杀人罪。而必要共犯,可以理解为学说创设出来的概念,指在构成要件性质上必须由数人参与行为才能完成的犯罪类型。前者是刑法总则中规定的共犯,属于形式上的表述;后者指构成要件本质上必须由复数主体才能构成,属于实质上的表述。广义的共犯即指任意共犯中的共同正犯、教唆犯和从犯。一般情况下谈到共犯都指的是任意共犯。狭义的共犯仅指教唆犯和从犯。〔31〕
与德日刑法不同,我国犯罪定义是实质意义上的定义,犯罪成立条件也是一种平面的耦合结构,即行为符合犯罪四大构成要件才能成立犯罪。从《刑法》第25条第1款对共同犯罪的定义来看,我国故意共犯是客观上共同行为与主观上共同故意的统一。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分类,是在上述共同犯罪的框架之内做出的。必要共犯是在最广义的共犯下相对于任意共犯而言的一种共同犯罪形式,但在我国刑法的运用中就会产生矛盾。比如,按照德日刑法理论,重婚罪属于典型的对向犯,是必要共犯的一种。在我国刑法中,相婚者如果不知对方已婚时,按照我国共犯理论,没有共同的故意,当然不是共同犯罪。再比如,我国刑法在有的聚众性犯罪中,规定仅处罚首要分子或积极参加者,如《刑法》第291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和第292条聚众斗殴罪、第317条暴动越狱罪等,当首要分子可能只有一人的情况下,就不是共犯了,更不是必要共犯了。这样,必要共犯概念与我国刑法共犯概念之间就出现了不协调,产生这个矛盾的原因则是我国共犯理论与德日刑法的必要共犯不是同一层次上的概念。
我国学者在引进必要共犯时,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矛盾,对于如何协调这个矛盾,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设想。如有的认为,可以考虑两种方法:第一种思路是保持共犯体系的一元化,对必要共犯予以改造。这种设想的思路是将我国的共犯按行为自然属性分为单独犯和复数犯,单独犯是指单独一个人即能实施的犯罪行为,如杀人罪等;复数犯则是指从行为的自然性质上来考虑,必须有两个以上行为人才能构成的犯罪行为,如受贿罪、重婚罪等。这样一来,在复数犯的场合下,若复数犯中自然行为本身所内含的各行为人之间能满足我国现行共犯的条件,则此时在复数犯中成立的共犯称之为必要共犯。在这种解决框架内,必要共犯成为我国共犯的一个子集合,两者之间具有了种属关系。这样,改造后的必要共犯能够完全为我国的共犯概念所涵盖。〔32〕第二种思路是干脆承认存在不同层次上的共犯,承认必要共犯中的“共犯”和我国刑法学界以及司法实务界所理解的共犯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概念,它们不能混同,承认共犯的多元化。由此需引入大陆法系国家的最广义的共犯概念,即两个以上的人去实施符合刑法分则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是最广义的共犯,而无论他们是否成立犯罪。这样,必要共犯就成为一种“功能性的概念”或“技术上的概念”。〔33〕还有学者认为,德日刑法中必要共犯理论与我国共犯体系适用上的不协调,主要是由于在共同犯罪规定上、犯罪论的体系上、共犯分层观念上的差异导致的。所以,在研究必要共犯时,只要结合具体理论的差异性,并从研究的出发点对该理论加以消化吸收,能够达到研究的目的即可。〔34〕
笔者较赞同将必要共犯视为一种“功能性的概念”或“技术上的概念”的思路,亦即必要共犯并非刑法学上的本体性概念,即其“必要性”基础在于主体复数性,并不要求多个主体必须构成犯罪。这是一种前犯罪的自然意义上的判断,而非犯罪成立之后主体的事实性判断。之所以研究必要共犯,是因为刑法上有这样一类共犯的现象,其具备研究上的或曰法解释学上的价值,故必要共犯的概念的提出只要具备功能上的或者技术上的意义即可。在我国刑法体系里研究必要共犯,需要不困囿于我国狭义的共犯体系,引入德日刑法中最广义的共犯概念,从而达到研究的目的。而功能性必要共犯概念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可以通过它将刑法分则对主体数量有特别要求的这样一类犯罪进行集中研究,为进一步分析一些具体理论问题扫清障碍,这也正是必要共犯概念存在的法解释学上的价值。
〔1〕〔4〕〔德〕佛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57,357.
〔2〕〔日〕泷川幸辰.犯罪论序说〔M〕.王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55.
〔3〕林书楷.论犯罪之典型共同加工——必要共犯理论之研究〔D〕.台湾辅仁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转引自张忠国.试论德日刑法中的必要共犯理论〔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2):132.〔德〕佛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57.
〔5〕〔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847.
〔6〕〔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M〕.李昌珂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33.
〔7〕〔21〕〔28〕〔日〕野村稔.刑法总论〔M〕.全理其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79,379,381.
〔8〕〔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M〕.刘明祥,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09.
〔9〕〔29〕〔日〕山口厚.刑法总论〔M〕.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39.
〔10〕〔27〕〔30〕〔31〕〔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59,360,360,359.
〔11〕〔日〕大塚仁.刑法概说〔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70.
〔12〕〔日〕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补正版)〔M〕.钱叶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88.
〔13〕林山田.刑法通论(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2.
〔14〕林钰雄.新刑法总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67.
〔15〕〔20〕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88,489.
〔16〕陈子平.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22.
〔17〕陈兴良.共同犯罪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31.
〔18〕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502.
〔19〕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50.
〔22〕刘明祥.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必要共犯〔J〕.法学杂志.1990(3).
〔23〕洪福增.论必要共犯〔J〕.台北:刑事法杂志,1985(2):36.
〔24〕甘添贵.刑法案例解评〔M〕.台北:台湾瑞兴图书公司出版社,1996.171.
〔25〕张小虎.论必要共犯适用总则共犯处罚原则的规则〔J〕.当代法学,2012(5).
〔26〕陈家林.共同正犯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38.
〔32〕〔33〕李涛.必要共犯概念之探讨〔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6).
〔34〕张忠国.试论德日刑法中的必要共犯理论〔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