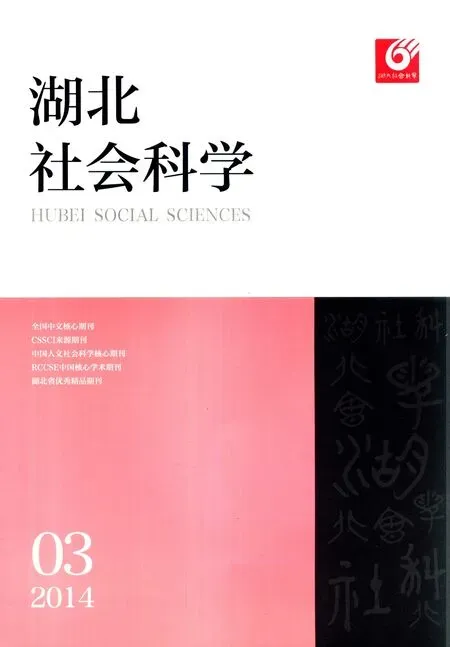法律权利的社会空间阐释
——作为社会空间的法律权利
2014-04-05朱垭梁
朱垭梁
(1.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2.江苏开放大学文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法律园地
法律权利的社会空间阐释
——作为社会空间的法律权利
朱垭梁1,2
(1.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2.江苏开放大学文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空间和社会空间是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重要范畴。社会空间是基于主体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主体意志与作为外在物的客体的统一体,它是一种人类实践,是人类行动的过程。社会空间这一重要范畴是对传统主客体二元论哲学的一种消解,也是对权利要素论的消解。法律权利无论在逻辑层面还是在历史层面,在本质上都可以被理解为是社会空间,法律权利的逻辑与历史的背后隐藏着空间的逻辑与历史。此外,社会空间理论可以为法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论。
权利;社会空间;二元论;方法论
在法理学中,“什么是法律权利?”的确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它就像一个谜,引得无数人去猜想,却无人能解,也无人能窥得其谜底。康德曾有言:“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什么是真理?’同样使他感到为难。”[1](p39)费因伯格则干脆说,对权利下一个“正规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应该把权利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不可定义、不可分析的原初概念。”[2](p3)本文重提这样一个棘手但却不得不去触碰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是完全可以换个角度去看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理论“空间转向”中的“社会空间”这一范畴似乎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角度。现有的权利学说往往是从权利的各项要素出发去分析和阐释权利的。夏勇先生就说,“要全面、正确地理解权利概念,较为关键的是把握权利的要素,而不是权利的定义。”[2](p4)国内外学者在这一点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法律权利解释为某些要素或者要素的组合——如,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等等。[3](p19)可以说,以往法律权利学说的争论焦点一直在于:哪种权利要素或哪些权利要素才是法律权利的本质要素?在中外法学论著中产生过的那些具有长期影响的林林总总的权利学说,如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利益说、法力说、可能说、规范说、选择说等,[4](p141)事实上都是这种争论的产物。对此,北岳先生的评价似为公允:“诸解说各自成立之处在于,它们各自都说明了权利概念中的某一要素或两个要素;它们未能尽如人意,是因为它们都未能全面、总体的阐释权利概念。”[5](p44)要跳出要素论的怪圈,我们需要引进社会空间理论中的“社会空间”范畴——因为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观察权利的全新视角。当然,这不是纯粹的偶然,更不是理论上的牵强附会和强拉硬扯。“社会空间”作为一个实践范畴,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必然与关涉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律现象有着莫大的关联。列斐伏尔说,“(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6](p86)社会关系的真正存在方式是空间。[6](p96)
一、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就是说,它是在与其他空间形态的并存中获得它的外部规定性的。这里所谓的其他空间形态,主要是指客观空间和主观空间。
(一)客观空间与主观空间。
客观空间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物质存在形式,是与人以及人的感觉、知觉、理性等主观因素无关的纯粹物理存在。这种物理存在在哲学上既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纯粹的空虚。客观空间是人的认知对象,由自然规律和技术规范加以调整。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客观空间还应该被区分为本体界的客观空间和现象界的客观空间。前者作为“物自体”,即自在自为的存在,是人的理性所不能认知的;后者即经我们的主观加工后所呈现出来的现象,才是我们的认知对象。可见,现象界的客观空间明显不是纯粹的客观空间。
与此相反,主观空间被认为是一种主观想象,是与自然物的特性、形状、结构或者外在的事件等客观因素无关的纯粹心理联想或反思。它与人类所追求的美和善有关,存在于美学和道德领域。在美学领域内,其主要表现为由某一自然物或某一作品所引发的观赏者、阅读者的心理共鸣或心灵触动。——可以称之为情感空间。如果是共鸣,那么形成的就是群体情感空间;如果是触动,那么形成的仅仅是个体情感空间。当然,若是观赏者、阅读者的主观想象与作者的创作感受相同,那么也可以视为是双方所构建的一种群体情感空间。在道德领域内,主观空间主要表现为由某一事件、行为所引发的道德分享或自我反省。——可以称之为道德空间。道德分享所形成的是群体道德空间,自我反省所形成的是个体道德空间。虽然,两者同为主观空间,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道德空间是建立在人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是以人的内在良心、品性等为内容的主观空间。它与人应当如何行为有关,具有社会性。情感空间则是建立在人将自己的心理感受、情趣赋予外在物(包括自然物和人造物)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情感空间与人的外在行为无关,只与内在的心理感受有关。
(二)社会空间。
与上述两类空间不同,社会科学中的社会空间既不是纯粹的客观空间,也不是纯粹的主观空间,而是人的主观意志通过其行为加诸外在物(即客观空间)的结果。它是一种社会建构,[7](p11)是人与人交往的产物。当一个人通过其意志行为将某一外在物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并且这一控制行为及其状态被他人所承认时,他就建立起了一个以该物为对象的社会空间。他可以称其为“领地”、“地盘”,也可以称为之“权利”。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社会空间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所谓主观性是指,社会空间是由主体意志建构起来的,其生成和维系必须以主体意志的介入和存在为前提,没有主体意志,社会空间就无从谈起。也即,没有人就没有社会空间。这一点与客观空间不同,后者是自在自为的纯粹客观,即使没有人及其主体意志,它依然存在。此外,社会空间的主观性与主观空间的主观性也有所不同。无论是在情感空间中还是在道德空间中,主体意志都是纯粹内在的心理活动,其不表现为任何外在的行为。而在社会空间中,主体意志均以外在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所谓客观性是指,社会空间的建构有赖于客观空间,没有客观空间,人的意志就没有了对象,空间建构也就成了无米之炊。当然,这里的客观空间必须是能为人所控制和利用的那部分客观空间——可以称之为外在物。这一点与主观空间截然相反,后者是由纯粹主观的情感、内省、反思等构成的,不以任何外在物为内容。
其次,社会空间具有个体性和独占性。社会空间是由原子论意义上的个体通过社会行为将外在对象纳入自己的意志范围内所建构起来的,因而,具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个体是社会空间唯一可能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空间就是个体社会空间。这种个体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法律拟制的人,后者如公司、基金会等等。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其建构社会空间时都是以单一意志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其所建构的社会空间必然都是个体性的。社会空间的个体性意味着社会空间必然是个体独占的,而不是共享的。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在同一个社会空间内,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主体意志。如果允许两个自由意志并存,则无异于剥夺或限制其中之一——这是与自由意志相矛盾的。主体意志都是自由并且独立的,因而任何一个主体意志都会将他者的意志视为异己的对象。相应的,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主体意志会将他人视为手段而非目的。
个体道德空间是单个的主体意志所建构和独享的,具有个体性和独占性。群体道德空间与之不同,没有成员会将自己视为完全独立、自由的意志主体,相反,其对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自我限制,以便容纳他者。在彼此接纳、相互容忍的过程中,各方主体意志会将彼此视为同类,继而视为自身。所以说,群体道德空间不具有个体性和独占性,相反,它们都是共享的,各方意志也不再将他人视为手段,而是当作目的本身。情感空间的情况与此相同。
最后,社会空间具有社会性和应然性。人的社会性赋予了社会空间以社会性的内在规定性,因此,所有以个体空间形式存在的社会空间都具有社会性。也即,个体社会空间永远都是社会性的个体社会空间。详言之,建构空间的个体不是形单影只、孑然一身的个体,而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个体。他在划定自己地盘的同时,也在为他人提供建构个体空间的可能性。社会空间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其同时具有应然性。个体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应当受到其他独立意志的承认和社会规范的正当性评价。比如,当某人将一座被废弃的房屋进行改造并占为己有时,他无疑是在以行为的方式宣告:这是我的空间。但这一空间还只是实然意义上的,主体的一厢情愿和自行其是还不足以让这一存在成为合法的、真正的社会空间。只有当其他意志事实上承认他的这种占有,或者普遍理性认为其合法时,这一以房屋为对象的社会存在才是应然意义上的、合法的社会空间。对社会空间进行正当性评价的依据往往是共识性的规范,如团体规则、习惯、风俗、道德、宗教、法律等等。当某一社会空间被国家法所承认时,其就是合法性社会空间,反之,其就是违法性社会空间。
综上所述,社会空间是主体通过其自由意志行为将外在物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所建立起来的,并经由社会规范进行正当性评价的,包含了主体及其意志、外在物和社会承认等要素在内的空间形式。它既不是纯粹的客观,也不是纯粹的主观,而是主观改造过的客观或者客观化了的主观。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空间是一个融合了主体意志、外在物和社会承认在内的有机整体。其中,主体意志、外在物以及社会的承认只是为社会空间的建构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它们本身并不是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是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从空间角度看待人及其生存状态的一个重要维度,它对于阐明同样以人为出发点的权利以及法律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实然意义上的社会空间就是权利,而应然意义上的社会空间就是法律权利。如果说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实存的话,那么权利就是我们给与这一社会实存的符号。换句话说,权利是社会空间的表象,社会空间是权利的本体。对此,我们可以从社会空间的演化和社会空间的结构两个层面加以证明。
二、法律权利的结构与社会空间——逻辑阐释
系统论认为,结构是系统要素的联结方式的总和。[8](29)其包含了系统的要素和各要素的联结方式两个方面。如果我们将社会空间视作一个系统或者整体,那么所谓社会空间的结构,就是指社会空间的各要素及其联结方式。社会空间是由主体及其意志、外在物和社会承认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其结构取决于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法律权利作为经由国家法进行正当性评价的合法性社会空间,其与事实领域的社会空间必然具有内在的同构性。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发展。[9](p305)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处于事实领域,另一个处于法律领域。由于要素是形成结构的材料和前提,因此,结构分析仍应从要素着手。
(一)法律权利的主体与社会空间的主体。
社会空间是作为主体的人将外在物内化(或者说将意志外化)的结果。诚如黑格尔所言,“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因而使该物成为我的东西;人具有这种权利作为他的实体性的目的,因为物在其自身中不具有这种目的,而是从我意志中获得它的规定和灵魂的。这就是人对一切物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利。”[10](p52)因此,任何社会空间都是由主体及其自由意志建构起来的。社会空间的主体既可以是有血有肉的自然人,也可以是企业等法律拟制的人。相应的,法律权利的主体包括了自然人和法人。由于自然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因此那些意志不成熟的自然人在构建社会空间时就需要他人的协助。法律基于此点,对权利主体进行了能力划分,并为能力欠缺者设置了代理制度。各种类型的公司在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和显赫地位,使得原有民法中的法人制度日显落伍和寒酸。作为回应,法人的内涵得到了极大地扩展,其不但包括传统的公司,而且还包括了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特殊的公司类型。
社会空间的建构需要主体,更需要主体意志的外化。因为只有主体将其意志加诸于外在物,社会空间才能被建构起来。反之,纯粹的内在意志只能建构起主观空间。黑格尔在谈到所有权时说,“为了取得所有权即达到人格的定在,单是某物应属于我的这种我的内部表象或意志是不够的,此外还须取得对物的占有。通过占有,上述意志才获得定在,这一定在包含他人的承认在内。”[10](p59)意志的外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主观意志必须表现为一定的外在行为即意志行为,二是该行为必须加诸于外在物,并实现对外在物的控制。外在行为既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但以积极的作为为常态。前者表现为行为和言说,如拾荒者从垃圾桶中捡拾丢弃物;后者表现为不作为和沉默,如对他人的赠与不置可否。主体对外在物的各种控制方式,就是社会空间归属的公示方式。它们可以是事实上的,也可以是观念上的。事实上的控制通常表现为某种形式的物理占有,如房屋的居住、土地的耕种等等。观念上的控制则表现为一些社会常识,如,手握车钥匙意味着控制了车辆,手持仓单意味着控制了货物等等。
主体意志行为的规范形式就是所谓的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因意思而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法律事实。”“意思表示为法律行为的核心。”[11](p250)法律行为与实然的主体意志行为都以主体的意思表示为要素,两者的不同仅仅在于,法律行为要求该意思为“发生法律上效果的意思”。也即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意志行为都是法律行为,只有那些以发生法律上效果为目的的意思表示才是法律行为。比如,邀请他人参加宴会,应允他人搭便车等所谓的好意施惠行为就不属于法律行为。社会空间公示方式的应然形式就是法律权利的公示公信制度。当社会空间的外在物是动产时,占有无疑是最为常见的公示方法,所以在法律上将其公示方式规定为占有(包括事实占有和观念占有)。当社会空间的外在物是不动产时,由于利益关系重大,因此法律上将其公示方式设定为登记。
(二)外在物与权利客体。
“物,是指那些不可能承担责任主体的东西。它是意志自由活动的对象,它本身没有自由,因而被称之为物。”[1](p30)外在物就是这样一些意志以外的物。它包括一般物、作为特殊物的人的身体和精神外化所形成的物。所谓精神客观化所形成的物是指人的智力活动的外在表达形式,如著作、发明、才艺等等。一般物是指除了人的身体和精神客观化所形成的物以外的物。以三种外在物为内容的社会空间分别形成了私法上的物权、人身权和知识产权。
获得一般外在物的方式既可能是不依赖于其他主体意志的原始的取得,也可能是与他人意志有关的继受取得。在原始取得的情况下,外在物不属于任何人的社会空间,主体可以将其意志直接加诸于外在物;在继受取得的情况下,由于外在物原本属于他人的空间内容,因此主体意志只能基于他人的让渡才能将其意志加诸于外在物。继受取得一般是通过契约来完成的。在契约中,双方自愿对自己施加于外在物上的自由意志进行限制,从而使彼此都获得了可以要求对方做出一定行为的允诺。法律上将以外在物为内容的社会空间称作物权;将以获取他人的外在物为目的,要求对方做出一定行为为内容的社会空间称作债权。债权与物权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1)它是以获取物权为目的的社会空间,是一种作为构建社会空间的手段的社会空间,因而具有临时性。所以相应的,物权中的所有权具有永久性,而债权具有时间性;物权一旦实现,作为手段的社会空间即债权也就消灭。(2)它是以对方意志的自我限制,即交付外在物的允诺为对象的社会空间,因此,债权的客体是债务人的行为。又由于自由意志是不能被支配的,因而债权在性质上属于请求权。当债务人的允诺不能兑现时,债权人只能要求债务人交付其空间中的物(即债权的标的物),而不能直接支配该物。因为在交付之前,该物仍然是债务人的社会空间的内容。
当社会空间的外在物是作为物理存在的人的身体时,该社会空间在法律上被称为身体权。人的身体是指行为主体的身体,在逻辑上,人的身体包括他人的身体和自己的身体两类。他人的身体与他人的意志一样,不是外在物。因为意志是以人的身体为依归的,身体是人普遍的、不可分割的、外部的定在,[10](p55)支配他人的身体就意味着支配他人的意志。其结果必然是一个意志被另一个意志对象化,也就等同于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当作奴隶。与此不同,主体意志占有的身体,即自己的身体,是主体意志的外在物。身体是人的意志的外部定在,作为人,我们可以像拥有其他东西一样拥有我们的生命和身体。[10](p55-56)但是,身体作为物质性外在物,还是有其特殊性的。它作为精神的栖居之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外在物,也是与意志共生、不可分离的物质空间。这与作为纯粹外部存在的、可以与意志分离的客观空间是不同的。因而,在法律上,人的尸体和死者的遗物被视为具有精神内容的特别的物。
以精神客观化所形成的物为内容的社会空间在法律上被称为知识产权。它们“固然是自由精神所特有的,是精神的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东西,但是精神同样可以通过表达而给它们以外部的定在,……这样就可把它们归在物的范畴之内了。”[10](p52)精神客观化所形成的物及其形成的空间包含着人的精神和情感。虽然客观化已经使其具有了物的外在形式,但它毕竟脱胎于精神,所以难免带有某些精神遗传。因此,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双重属性。比如,作品上的署名不得更改,他人不得修改作品等等。
(三)合法性与社会空间的正当性。
主体所建构的社会空间应当被社会所承认,即具有正当性。当这种正当性评价来自于道德观念时,该社会空间就是道德权利;来自于约定俗成的生活规则时就是习惯权利;而当其来自于国家法时,该社会空间就是法律权利,即合法性的社会空间。因此,“法律权利只是权利的一种存在形式,除此之外,还有道德权利和习惯权利。道德权利表示一种观念的存在,由哲学、宗教里的道德原则来支持。习惯权利则表示一种事实的存在,由约定俗称的实际生活规则来支持。”[12](p14)法律权利与其他权利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对社会空间的正当性评价标准不同,其本体都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空间。当社会空间的正当性评价标准发生变化时,权利的形态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化。例如,当某一习惯被上升为法律规范时,习惯权利也会相应地转化为法律权利,反之亦然。对此,马克思说道:“习惯成为合理的是因为权利已变成法律,习惯已成为国家的习惯。”“因此,习惯权利作为和法定权利同时存在的一个特殊领域,只有在它和法律同时并存,而习惯是法定权利的前身的场合才是合理的。”[13](p144)
三、法律权利的历史与社会空间——历史阐释
从哲学的角度看,人的自由意志需要扬弃自身的纯粹主观性,因而有一种将一切外在物内化的必然倾向,这就注定了社会空间是与人的自由意志共同成长的。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不论人们是否将它纳入认知范围,社会空间作为人的自由意志的伴生物始终自在自为地存在着。当然,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也必然是社会空间的内涵不停流变的过程。与此同时,权利也开始被用来指称社会空间,并经历了一次从自然权利到法律权利的历史蜕变。
(一)混沌的社会空间与法律权利。
在原初社会,由于个体淹没于氏族和部落之中,不存在个体意义上的人,因此不存在个体空间建构的可能性。在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和部落内部,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个体空间的分隔,相反,他们将氏族和部落视为自己唯一真实的归宿。这个扩大了的“家”是他们共有的情感空间,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不带有任何物质内容的,纯粹的情感交往。即便是在食物分配等涉及物质内容的场合,也不存在绝对的“你的”和“我的”之分,相反,其通常被转化成为情感问题加以处理。因此,在原初社会,氏族成员的物质空间和情感空间是混沌一体、不可分割的,也不存在作为个体的人的社会空间。相应的,从权利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氏族成员不可能拥有权利。一则,氏族成员没有主体资格,主体无从谈起;二则,财产是公有的,客体无法确定。这样看来,在原初社会,物质与情感仍然混沌一体,个体与群体始终你我不分,所以既不可能有社会空间,也不可能有权利。
(二)家庭土地型社会空间与法律权利。
步入古代社会,家庭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体;家庭财产也渐渐从公有财产中剥离出来,成为家庭支配的私有财产。这两个变化是促使社会空间脱离混沌状态,并得以成功分娩的关键。其中,家庭的出现创造了社会空间建构的主体条件和社会条件;私有财产的出现创造了社会空间建构的外在物条件。我们可以想见,当氏族和部落分化为众多的家庭,氏族和部落的公有财产被分割为无数的家庭财产时,原本庞大的共同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空间。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空间主要以家庭为主体,以土地为外在物,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家庭土地型社会空间”。其中,家庭是社会空间建构的主要主体,家长对内行使对家庭成员的绝对权力,对外代表家庭从事社会行为,如拥有财产、缔结契约等等。处于家长权力之下的家庭成员虽然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但和氏族成员一样,他们没有主体资格,无法创造和拥有自己的社会空间。奴隶虽然是自然人,但他们被视为意志的外在物,在一般情况下属于家庭的财产,也就是社会空间的内容,而非主体。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生产方式主要是农业,因而土地是最主要的外在物。虽然土地的出产物、生产工具等等也是重要的外在物,但是相对于土地而言,它们都是无关紧要的。正如康德所言,“对于土地上一切能够移动的每一件物来说,土地被看作是本体;那些可以移动的物的存在模式被看作是土地的一种固有属性。”[1](p75)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社会空间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判断往往源自于人们对具体事件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还不具有规范性特征,它往往是具体的和特殊的。每当一个社会空间受到他人质疑或社会空间之间发生冲突时,作出决定的依据都是个案性的。也就是说,此时实然和应然还没有分化,实然的社会空间就是应然的社会空间。
这种实然与应然不分,事实与规范不分的社会空间就是事实上的权利。家庭——土地型的社会空间就是以家庭为主体、以土地为客体的事实上权利,两者并无二致。易言之,社会空间的主体就是权利的主体,社会空间的外在物就是权利的客体,社会空间的社会承认就是权利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为权利的产生创造了可能性,权利是从原初社会的解体中诞生的。
(三)个人货币型社会空间与法律权利。
对于社会空间的演变而言,国家法的出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使得原本实然与应然不分的社会空间正式分裂为两种形式,一是得到国家法承认并由国家暴力加以保障的社会空间,即规范性社会空间;二是被国家法否定或者国家法不置可否并继续留在自然状态的社会空间,即事实性社会空间。前者为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权利——客观权利;后者为事实领域的权利——主观权利。
相比于家庭——土地型社会空间,这一时期的社会空间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家庭成员从家长的权威下、从家庭的整体意志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自由意志的真正主体,家庭在社会空间建构中的主体地位逐步被个人所取代。这样,家庭在一般情况下只是作为情感空间而存在。其次,货币的出现和普遍使用使得土地等一切外在物都可以转化成为可随身携带的一般等价物,从此,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变成了货币的获取和积累,社会空间被压缩成了货币,被等同于了货币。“货币是至关重要的,它是经济社会的润滑剂,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使得经济运行得更加顺畅。”[14](p50)同时,“货币发挥着价值储藏的功能,它是一种超越时间的购买力的贮藏。”[14](p51)最后,社会空间的合法性判断不再是个案的和非规范性的了,习惯法、国家法等建立在普遍性的社会共识基础上的规范成为了主要的标准。伴随着法律的出现,应然的和实然的、规范性的和事实性的社会空间也开始分化。需要注意的是,与家庭土地型的社会空间不同,此时的社会空间具有典型的商品化特征,即社会空间的建构不再是为了自给自足的消费,而是为了交换。所以,严格来说,社会空间的建构应该被称为社会空间的生产。个人和规模大致相当的企业是这一时期社会空间生产和消费的主要主体。他们通过生产和签订契约不断地生产和消费着各种社会空间。
随着社会空间分化为规范性的社会空间和事实性的社会空间,权利也相应地出现了客观权利和主观权利的分野。此后,法律权利一般被用来指称规范性的社会空间;而“社会空间”一般是指事实性社会空间,偶尔也被称为事实权利。法律权利作为法律规范调整社会空间的产物,其必然是对当时的社会空间的写照,其所具有的诸多特征也必然与事实领域的社会空间相契合:首先,法律权利的主体主要是平等的自然人和法人。这是对作为社会空间主体现实情况的应然表达;其次,法律权利的客体是包括不动产和动产在内的一切外在物。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成为了法律权利中最主要的客体。这是对社会空间的外在物的规范性表述;最后,法律权利的正当性依据是国家法。这是社会空间中的社会承认在法律上的翻版。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空间具有商品化的特征,因此法律权利也不再是单纯静态的物权,而是更多地包含了由契约而生的债权。
四、余论
“社会空间”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伴生物,人的存在必然伴随着空间的产生,人与空间是不可分割的,两者是共生共存的关系。这种人与空间的关系在存在主义哲学那里得到了更为深刻和准确的阐明。海德格尔在说“此在就是它的展开状态”时,[15](p155)他是在说人与空间是共同“展开”的。“说此在是在世的存在,就是说此在已经在世界上了。在传统哲学那里,人不是被规定为主体就是意识,世界是外在于人的。而在此则始终是在世界中,在世此在是它存在的基本条件。”[16](p231)也就是说,人与空间是互为条件和因果的。简而言之,空间是一种人类实践,是意志因素和外在因素的统一体,是人类行动的过程。——空间至此成为消解二元论哲学的重要范畴。“空间转向”中的空间概念就是建立在这种空间哲学基础之上的。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不能站住脚。”他的“空间三元辩证法”蕴含的答案是两者都是。“所以,社会空间应该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但不仅仅是两者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螺旋上升的超越。”[17](p25)这种试图超越二元论的社会空间理论为我们重新认识权利以及其他法律现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传统的权利学说是建立在主客、物我二元分离的哲学基础之上的,权利要么被认为是主体及其意志,要么被认为是作为客体的外在物,所以,我们对权利的理解也始终停留在权利的某个要素之上——权利的自由说、意志说等等无不如此。社会空间对于权利理论乃至整个法律理论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包含了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权利”在本质上其实就是社会空间。法律权利的逻辑与历史的背后隐藏着空间的逻辑与历史,这是权利与空间所具有的结构性的内在牵连。无论是以法律规范形式存在的客观权利,还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主观权利,甚至是在主客观权利未分化之前存在的那种权利,其本质都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社会空间”,也就是说,权利的本体是“社会空间”。法律权利是国家法所确认和保护的“社会空间”,道德权利是为道德规范所承认并为强力之外的社会压力所保证的“社会空间”,习惯权利是为一定范围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所一体遵循的习惯所承认的“社会空间”。由于“权利是基本的法学范畴,是构建法学体系的逻辑起点。”[18](p1)因此,权利的空间阐释必然有助于我们理解权利之外的其他法律现象——这应该就是社会空间的方法论意义。
[1]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沈叔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1.
[2]夏勇.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J].法学研究,2004,(3).
[3]范进学.权利概念论[J].中国法学,2003,(2).
[4]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北岳.法律权利的定义[J].法学研究,1995,(3).
[6]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7]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8]苗东升.系统科学大学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1]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2]夏勇.人权概念起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4][美]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刘毅,蒋理,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16]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7]赵海月,赫曦滢.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辨识与建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 (2).
[18]舒国滢.权利的法哲学思考[J].政法论坛, 1995,(3).
责任编辑 王京
D90
A
1003-8477(2014)03-0149-07
朱垭梁(1978—),男,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开放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