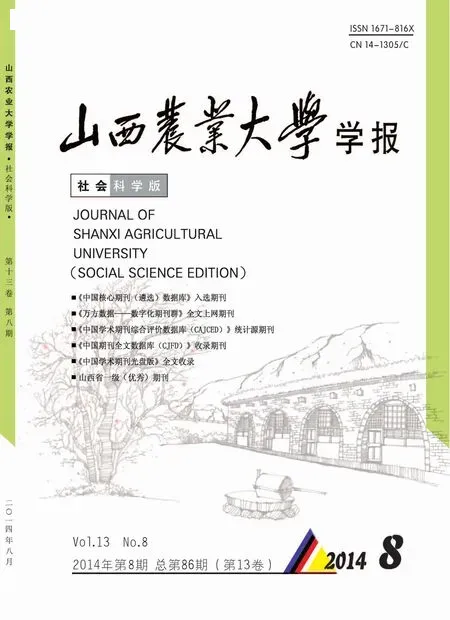桐城派文论与《文心雕龙》的暗合
——徐复观《文心雕龙》研究扩展
2014-04-03任雪山
任雪山
(合肥学院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601)
桐城派文论与《文心雕龙》的暗合
——徐复观《文心雕龙》研究扩展
任雪山
(合肥学院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601)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章学巨擘,桐城派是近代文章学大宗,作为一位心系中国文学命脉的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与两者都颇有渊源,并对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之关系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它们有许多暗合之处。特别是在文体论和文气论两个方面,桐城派文论对《文心雕龙》都有继承和超越。通过对桐城派和《文心雕龙》关系的细致考察和疏通条贯,徐复观希望展现古今文学发展的轨迹,沟通中西文学理论,为建立中国现代文体论作奠基尝试。
文心雕龙;桐城派;徐复观;文体论;文气论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章学巨擘,桐城派是近代文章学大宗,可是很少有人把两者联系到一起。作为一位长期心系中国文学命脉的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不仅受过桐城派的滋养,[1]而且与《文心雕龙》研究也颇有渊源。中国近代《文心雕龙》研究滥觞于刘师培、黄侃在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特别是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更是影响深远,两岸三地的一大批龙学研究者出自其门下,而徐复观也和黄侃有师生之缘。徐在武昌十年攻读期间,曾亲自聆听黄侃讲授《文心雕龙》。[2]20世纪50年代转入学术后,他在治思想史的同时在台湾东海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程,前后写了大量深度研究文章。张少康在综述20世纪《文心雕龙》研究时给予高度评价,“台湾五六十年代在理论上很有深度、并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文心雕龙》研究文章,当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艺术史很有成就的东海大学的徐复观教授”。[3]在徐的系列龙文中,张先生认为,徐的两篇长文《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和《中国文学中的气的问题——〈文心雕龙·风骨〉篇疏补》均是很重要的成果。事实确乎如此,两篇文章刊发后,引起海内外龙学界和文论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持续讨论。而两篇文章都大量援引桐城派文论的观点,最后结语也都归到桐城派,这自然引发人们对桐城派和《文心雕龙》之间关系的思考。概而言之,徐复观主张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之间“有许多暗合之处。”[1]我们尝试以两篇长文为主,分别从文体论和文气论两个方面来理解徐先生的观点。
一、无体之体,桐城派对刘勰文体论的继承超越
文学的特性是什么?这是文学理论的根本问题,也是徐文探讨《文心雕龙》文体的逻辑起点。他认为,文学的特性须通过文体的观念才能表达出来,所以文体论是《文心雕龙》的中心课题,甚至《文心雕龙》全书都可以成为我国古典的文体论。[1]张少康认为徐的文体论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不太一样,[4]徐复观理解的《文心雕龙》的文体,即文学的形体、形相,也就是西方的Style,它包括三个层面,即三个要素:体裁、体要和体貌。体裁主要是语言文字的排列与形相,体要主要以内容的事义为主,强调文学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法则方面,源头来自五经系统。体貌以情感为主,强调文学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声色文采方面,源头来自楚辞。三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统一,由低到高共同构成文章的文体。从徐文的论述可以看到,刘勰的文体论,不像我们今天说的文学体裁那么单一,而有更为广阔的蕴含,它既是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又是文学艺术性和实用性的统一,同时又突出强调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即文学的艺术性体貌。
徐文提出,刘勰的“体要”实际等于桐城派“义法”之“义”,[1]古文家强调的义法实际上就是继承体要传统,而之所以提出体要,“正是为了矫正当时过于重视体貌所产生的流弊。”[1]这是非常深刻的洞见。《文心雕龙》虽然是用骈文写成,总结过去文学的成就,但更欲挽救当时由于过分藻饰而带来的文体浮华之穷,所以徐复观说《文心雕龙》“在许多重要地方实开唐代古文运动的先河。”[1]唐代古文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挽救六朝骈文浮华之风,而桐城派方苞提出义法理论目标之一也正是对晚明以来士林空疏不学之风的反叛。方苞“义法”之“义”即“言有物”,强调的实际是古文的学识修养,只有学养深厚,才能言之有物。正如他在《书祭裴太常文后》中所说:“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由是观之,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向,然后所学有以为基,匪是,则勤而无所。”[5]而他所说的学养主要来自五经系统和秦汉古文的主张,正是继承了韩愈以来“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古文传统。这与徐复观看法也不谋而合,徐认为作为体要的事义,主要来自于学。[1]方苞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学,而且身体力行,他曾删减《宋元经解》,精通三礼之学,专研《春秋》《周官》,著有《周官集注》十二卷、《周官析疑》四十卷、《仪礼析疑》十七卷、《礼记析疑》四十卷、《春秋通论》四卷、《春秋直解》十二卷、《春秋比事目录》四卷等,可谓学养丰厚。重视学养是古文兴起的重要原因。
唐代的古文运动,为了挽救前代骈文浮华之风而提倡学养是有意义的,但也带来了相应的弊端,用徐复观的话就是,因为提倡道德实用性,而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艺术性要求。也就是说,体要之体的意识压倒体貌之体的意识,由此造成古文系统中观念上对艺术性体貌的隐没,后来唐宋元明的古文家几乎都是如此,一直到方苞几乎在理论层面都没有很大改观。而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却又呈现另一种状况,因为任何一篇好文章,其体要都会升华为体貌,艺术性是根本追求。韩柳的很多文章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徐复观认为这种观念上不重体貌而事实重视体貌的状况,到姚鼐开始转变。[1]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6]
徐文以为,姚鼐突破了方苞的义法(体要),进而谈到形貌。他所举的为文者八,即构成文章形貌的八种因素。神、理、气、味,乃构成形貌之精;格、律、声、色,乃构成形貌之粗。学习古人,要由形貌之粗,以通于形貌之精,最后遗粗遇精。这和刘勰的说法没有什么出入。徐文曾把《文心雕龙》下篇重新归纳组合,分为几项:核心(体性、事义)、根源(神思、养气)、实际(风骨、隐秀)、纲领(通变、定势)、语言(情采)、结构(熔裁、章句、练字、指瑕、附会)、声律(声律、丽辞)、外缘(物色、比兴、夸饰)、总结(总述)。虽然标准不同,但从整体来看,“不难发现与姚鼐所论相通的迹象。”[7]然而由于时代所限,刘勰所把握的体貌,主要是指文章的声色方面,而姚鼐更进一步,除了声色之外,还提出了神、理、气、味,所以徐复观评价其“直凑单微,达到了‘无体之体’的极谊。”[1]也就是说,姚鼐不但接上了刘勰的文体论,而且某种程度上完善了刘勰的文体论。众所周知,桐城派文章一直是雅洁有余,文采不足。姚鼐深知文章之道,在《古文辞类篆》中提出八条目,并特设辞赋类,包括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统一的观点,把“道与艺合,天与人一”作为文章的至境,都是吸收骈文重视文章艺术性的优点,使古文声色更加生动丰富起来。极力突出文学的艺术性,突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体特征,是姚鼐对文体论的重要贡献。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所说,“桐城派自姚鼐起,越来越明确地形成了古文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的共识”。[8]徐复观看到了姚鼐的用心,并把他与《文心雕龙》的体貌观结合起来,给予高度评价。当然,姚鼐不知道他所谓的形貌,就是六朝人的文体,所以徐复观说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的理论是暗合。
徐复观通过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细致搜检考察,以及桐城派对《文心雕龙》文体观念的潜在继承与发展,表面看起来是疏导条贯《文心雕龙》以降的文体论发展历程以及古文运动在中国的历史演化,实际有更深层次的意旨。徐文的逻辑起点是文学特性,归结点还是文学特性,他针对当时文学理论界对文体观念的研究状态,希望借此可以把文学从语言和考据的深渊中解救出来,特别是乾嘉 学派以来那些只顾语言而不顾义理的表面考据中解救出来,恢复《文心雕龙》的大文体观,重视文学的艺术性,对文学做更为正常的研究。同时,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梳理,能够帮助读者“进而窥古今文学发展之迹,通中西文学理论之邮,为建立中国之文体论作一奠基尝试。”[1]
二、生气灌注,桐城派对刘勰文气论的大明
气的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文论的基本理论范畴,大致有“物理、生理、心理、伦理、哲理等几个层次的含义。”[9]中国文学特别重视气的问题,先秦就有文学与气关系的表述,但真正探讨两者关系的还是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徐复观称赞曹丕的贡献在于“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两句,[1]表明了气与文学个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关系,但曹丕的认识还比较朴素,发展到比较完全阶段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1]
刘勰非常重视气,《文心雕龙》很多篇章都涉及气的探讨,还专设《养气》篇。徐文认为其专论气的是《风骨》篇,风骨就是“气在文章中的两种不同作用,以及由这两种不同作用所形成的文章中两种不同的艺术形相,亦即是所谓的‘文体’。”[1]风骨在文学中的作用,就是气在文学中的作用。创作时的气,承载情感与理性,向主题和文字塑造,同时流露出生命的节律。气一方面把情性乘载向文字,同时把文字乘载向情性。于是情性由气而向外传达,文字由气而获得活的生命,文字的美也就发挥出来了。后来李建中把徐复观的文体论概括为“主观情性”论是很有道理的,[10]重视情性在文体中的作用是徐复观文体论的鲜明特色。对刘勰文气思想最直接继承的是韩愈,他在《答李翊书》提出了“气盛言宜”的理论,但徐复观认为,把气与声的关系说得最精切的是刘大櫆的《论文偶记》。“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11]文学个性、艺术性由气而见,气由声显,所以学习、鉴赏古文必须因声以求气。因为刘大櫆的精到论述,后来桐城派的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和王葆心等都受其影响。
徐复观说气是生理的生命力,但仅有生理的生命力并不能成就文学艺术,气必须与才和志结合起来,才能成就自己的表现力。[1]而志与才又必须借助学,才能够充实扩展,所以气必须与学结合以完成在文学艺术中的作用。关于学与气的关系,刘勰有一段话:“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12]徐复观把刘勰的观点总结为两条:一是学可以增加气的表现力,一是学可以通过充实志,来加强气。因为气与学的密不可分,所以古文家重视气也无不非常重视学。像韩愈《答李翊书》里面的“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桐城派后学吴汝纶在《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中说:“夫文章以气为主,才由气见者也。而要必由其学之浅深,以觇其才之厚薄。”[13]徐文认为吴汝纶的观点可以和刘勰互相发明。[1]徐复观没有提到最强调学的方苞是个缺憾,可能因为方苞没有把学与气结合起来,使古文单纯强调经史之学而稍显古板。
重视气自然重视养气,刘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养气思想,特别是王充的养气理论,他把精神与血气紧密关联起来,养气即养神。徐复观把刘勰养气的理由归纳为两条:一是作文时用力不能太过,超过自己能力就会伤生。二是作文应由养气酝酿文机的成熟。否则劳力气短,文机壅塞。[12]古文家也很重视养气,从韩愈、苏辙到宋濂等都有论述,刘大櫆颇多精到之言,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11]徐文认为刘大櫆的“神”和刘勰《神思》篇的“神”是一致的,都是指文学的心灵活动。而文学的心灵活动是志、情、理相互融合的一种心理状态,其间实有赖于气的鼓荡之力,所以神与气密不可分。刘大櫆主张以气为主,神又主气,神气并举,立说周延。由是推之,养气必养神,“究其实,养神、养气只是一事。”[1]桐城派古文到姚鼐始大,姚鼐的养气观主要以《古文辞类纂序目》和《答翁学士书》为主。尤其是《答翁学士书》中有一段:“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态,彩色之华。故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14]徐复观认为,姚鼐强调意气相御对文章声色之美的影响,是和刘勰观念相会通的。[1]刘大櫆突出养神,姚鼐突出养意,徐复观把养神、养意和养气结合起来,认为他们从不同层面丰富发展了刘勰的养气思想。
实际上,徐文主要在三个方面,比较了桐城派和《文心雕龙》关于文气的思想,一是气与声的关系,一是气与学的关系,一是气与养的关系。气以声显,学以养气,意气相御,神气一体。气与声的关系,主要是刘大櫆、曾国藩等对文心雕龙的发展;气与学的关系,主要吴汝纶对文心雕龙的发展;气与养的关系,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对文心雕龙的发展。可以说,桐城派几代人对文心雕龙的文气论都有一定程度的暗合与发展,中国传统文气论从《文心雕龙》到桐城派走向成熟,所以徐复观说:“文气之说,得古文家而大明。”[1]通过徐复观细致入微的梳理分析,不仅中国传统的文气思想有了一个清晰的生长脉络,而且把桐城派文论与《文心雕龙》勾连到一起。这样一来,不只桐城派文论向上有迹可循,《文心雕龙》也在后世有所承继新延。
有同就有异,徐文看到了桐城派和《文心雕龙》的前后联系,也看见了两者对于文气的不同理解。徐复观认为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古文家言文气,是以气势为主。[1]林纾在《春觉斋论文·气势》中曰:“文之雄健,全在气势。”[15]所谓“气势”,就是气在文章中的灌注之力。刘大櫆在《论文偶记》里说:“古人行文至不可阻处,便是他气盛。”[11]这里的“气盛”是就气的灌注而言。曾国藩说:“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气。”[16]古文家口中的“行气”,也是说气的灌注之力。而刘勰言气,注重气形成之力对文章艺术性体貌的影响。比较而言,体貌是静的形相,气势是动的形相。古文家因为更重视文章的气势,而相对忽视了文章的色泽,于是在体貌的艺术性上多少会有些缺憾。徐复观通过古文家和《文心雕龙》的文气关系之比较,解释了为什么后来桐城派屡屡在艺术性上受诟病的理论原因,同时也说明了《文心雕龙》恒久的理论价值。
当然,这一切毕竟是通过徐复观深入细致的分析我们才得以明晓,虽然他认为,有清一代真正了解文学的只有桐城派及其旁支,包括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和其师王季芗的《古文辞通义》,但非常可惜他们并没有真正留心到《文心雕龙》,没有接上《文心雕龙》已经提出的许多明确概念和系统,只是与《文心雕龙》的某些地方暗合。[1]至于暗合的原因,徐复观分析可能由于骈散和汉宋之争。[1]乾嘉学派喜欢六朝骈文,站在骈文立场,自然喜欢《文心雕龙》,所以《文心雕龙》实际是由这一派人提出。但他们又反对宋明理学,反对桐城派古文,所以桐城派就不太喜欢《文心雕龙》,他们之间就相互隔膜起来了。这个见解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桐城派尊奉古文为文章正宗,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从归、方直接唐宋古文而上溯秦汉的文统,六朝骈文被排斥在这个统绪之外。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明确表达了这个意向:“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6]黎庶昌曾将姚鼐文论的要义归纳为:“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17]也同样说明了摒弃六朝是桐城家法的重要内容,后来其他学者的研究也佐证了徐复观的主张。[18]
综上所述,我们分别从文体论和文气论两个方面来评述了徐复观关于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之间有许多暗合的观点。徐复观作为一个与桐城派和《文心雕龙》研究都有渊源的现代新儒家,在这种双重文化背景和知识谱系下,沟通两者的关系实属情理之中。纵观整个疏通条贯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徐复观运用他一贯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以其宏阔的学术视野和中西学养,披荆斩棘,寻幽探微,探寻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之间理论上的暗合与会通,并试图借此把古代和近代学术勾连起来,形成一个绵延不断的学术之链。同时希冀沟通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学术思潮,为传统文论现代化寻求突破,为中国现代文论建设开辟大道。牟宗三先生在徐复观逝世十周年纪念研讨会上,评价徐复观:“徐先生这个人对维护中国文化,维护这个命脉,功劳甚大。这是我亲自切身的感受:疏通致远,功劳甚大。”[19]“疏通致远”既是对徐复观儒学思想成就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徐复观对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之间“返本开新”式研究之中。在徐复观那里,新与旧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脉相承延续发展,所以开新必须返本,离本无法开新,这是现代新儒家对待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徐复观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文论的态度。他由桐城派文论回溯魏晋《文心雕龙》,不只是简单的学术史的疏通,而是借由疏通发现中国文论的精义,以开出符合现代思想的中国文论。建立中国现代文论,必须疏通古代与现代的纠结,而桐城派文论恰恰是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之间的一个过渡。这是桐城派文论的一个突出意义,也是徐复观桐城派研究的一个重要启发。
[1]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 223, 145-147, 225, 168, 112, 229, 208, 209, 209,107,108,112,131,133,140,141,143,143,223.
[2]徐复观著.陈克艰编.中国知识分子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6.
[3]张少康.文心雕龙研究·导言[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2.
[4]张少康,汪春泓.文心雕龙研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33.
[5]方苞.书祭裴太常文后,方望溪全集[C].北京:中国书店,1991:5.
[6]吴孟复,蒋立甫.古文辞类纂评注[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8,18.
[7]王守雪.心的文学[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88.
[8]关爱和.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J].文学评论,2000(4):77.
[9]李存山.气概念几个层次意义的分殊[J].哲学研究,2006(9):34.
[10]李建中.龙学的困境[J].文艺研究.2012(4):52.
[11]刘大櫆.论文偶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4,6,4.
[1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14,647.
[13]吴汝纶著.施培毅,徐寿凯校.吴汝纶全集(第1卷)[C].合肥:黄山书社,2002:359.
[14]姚鼐.惜抱轩全集[C].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64.
[15]林纾.春觉斋论文[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76.
[1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C].长沙:岳麓书社,1994:950.
[17]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M].上海: 世界书局,1936.
[18]曹虹.清嘉道以来不拘骈散论的文学史意义[J].文学评论.1997(3):112.
[19]牟宗三.徐复观先生的学术思想.徐复观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台中:东海大学,1992:43.
TheCoincidenceofLiteraryTheoryofTongchengSchoolandTheLiteraryMindandtheCarvingofDragons
REN Xue-shan
(DepartmentofChineseandLiterature,HefeiUniversity,HefeiAnhui230601,China)
TheLiteraryMindandtheCarvingofDragonsis a gian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Tongcheng school is a huge sectarian of modern Chinese article theory. As a modern representative of Confucianism committed to Chinese literature, Xu Fuguan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both of them. He made a profound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ry theory of Tongcheng School andTheLiteraryMindandtheCarvingofDragons, and concluded they have many in common, especially in stylistics and Wenqi theory. Tongcheng School has an obviou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TheLiteraryMindandtheCarvingofDragons. Through careful inspe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ngcheng school and theTheLiteraryMindandtheCarvingofDragons, Xu Fuguan wanted to track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with the aim to make a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theories.
TheLiteraryMindandtheCarvingofDragons;Tongcheng school;Xu Fuguan;Stylistics;Wenqi theory
2014-03-10
任雪山(1976-),男(汉),安徽泗县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桐城派方面的研究。
I206
A
1671-816X(2014)08-0799-05
(编辑:佘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