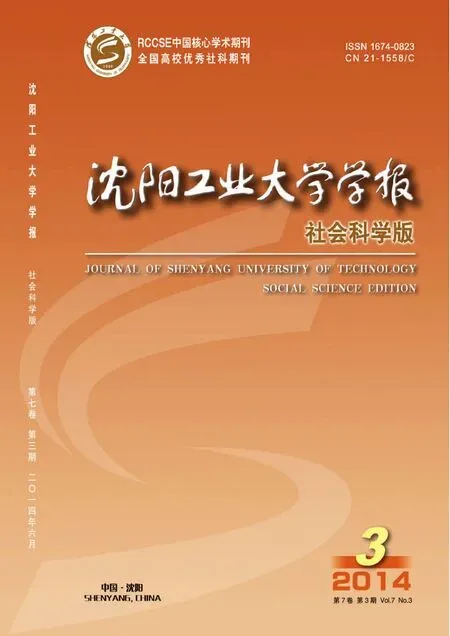法律发现的原则剖析*
2014-04-03张志文
张志文
(山东交通学院 交通法学研究中心, 济南 250357)
法律发现的原则剖析*
张志文
(山东交通学院 交通法学研究中心, 济南 250357)
在法官看来,法律渊源不能停留在仅是各种法律集合体的静止状态,其方法论意义只有与法律发现相结合才能被彰显。于是,司法立场的法律渊源成为法官寻找裁判纠纷规则的“仓库”。法官在法律渊源中发现法律时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正式法律渊源优于非正式法律渊源;规则优于原则;下位法优于上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法律发现; 法律渊源; 法律方法; 自由裁量权
随着法学研究的重心由“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论证”,更多学者站在司法立场去看待与研究法律问题。这在法律渊源的研究中表现得也尤为明显。现有的法理学教科书总是将法律渊源与法律形式混同在一起,这种观点导致读者认为法律渊源就等同于法律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立足于立法立场的表达,而法律渊源只有和法律发现结合在一起,才能凸显它的方法论意义。于是,法律形式不再仅是静态意义上立法者用来区分不同性质法律文件的标准,而成为法官更容易辨识、发现法律的“指南”。与此相伴,法律渊源也摆脱了只是各种法律集合体代称的这一“赋闲”状态,变成了法官经常“光顾”并用来发现裁判纠纷规则的“闹市”。总之,司法立场法律渊源的核心是指“法官寻找发现法律的思维方法”。不过,在法律渊源中,由于各种法律放置在一起,法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原则去发现法律,成为案件能否得到合法判决的关键。一般来说,法官发现法律时,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正式法律渊源优于非正式法律渊源
一般而言,法官裁判时首先应当从正式的法律渊源中发现法律。只有在正式的法律渊源中找不到解决案件的法律,才可以从非正式法律渊源去寻找。至于为何应首先从正式法律渊源中发现法律,除了对法治的恪守、对制定法权威的尊崇等原因外,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其一,从社会大众的认知层面来讲,制定法更易为其所知晓,从而增加自己行为的可控性和判决结果的可预测性。法律要被人们遵守的条件之一就是其能够被认知和了解。应该说,制定法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社会公布后,可以成为所有社会成员指引自己行为的标尺。与此相对应,由于其自身的局限,非正式法律渊源中的习惯、法理学说、理性与事物本质等显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一以贯之。这也正应验了那句话:“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有些习惯在某处实行得游刃有余,而在他处可能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窘状。如此一来,怎能以此处的规范衡量彼处的案件?而作为正式法律渊源中的主体,制定法以其普遍性、易为公众知晓和可预期等特点,让司法判决过程充满公平、正义,从而有助于法治目标的实现。
其二,从法官思维的角度来看,优先从正式法律渊源中发现法律能够培养法官正确的思维。“法官从哪里发现法律,是法律思维方法的首要内容。”[1]引导法官从制定法或正式法律渊源中发现法律是法治思维的必然结果,也是法治的最基本要求,否则法官会陷入任意司法的泥淖中。现实主义法学所倡导的正是法官造法或无法司法。如果法官也沿着现实主义法学设定的司法路径前进,极有可能导致法官个人意志代替社会公众意志,使司法失去社会的普遍认可,这将是对法治理想的背叛[1]。
当然,优先从正式法律渊源中发现法律并不是对非正式法律渊源的否定,也并未蕴含在正式法律渊源之余法官判决显得乏力或无奈时,法官可以任意司法的意思。正如奥斯丁所主张的:“一个法官可以从其主观信念中去寻求解决正式法律未作规定的案件的答案,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尽管这种主观信念可能是以社会功利之考虑或‘任何其他’考虑为基础的。这是因为除了正式法律之外,法官还可以获得一些其他方面的指导;而且尽管这些指导不如实在法的许多规则那么具体、那么直接,但它们却比法官依赖其无法控制的自由裁量权要可取的多。”[2]444-445对于非正式法律渊源的作用,除去前面已经提到的可以克服成文法的僵化性、弥补成文法的空缺之外,另外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它可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行为。习惯、理性与事物性质等,皆是促成约束法官裁量权的关键所在。
二、规则优于原则
在通常情况下,法官审判案件应该秉承着首先从规则中发现法律、坚持规则先于原则的原则。毕竟,与原则相比,“规则不仅为人们的行为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法官等提供了裁判标准,它对限制自由裁量权、保证实体规则的贯彻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法治的实施提供了操作技术。”正因如此,首先从规则中发现法律,为法治理想得以实现提供了支撑,能够保证法律价值的实现。不过,坚持规则优于原则只是从发现法律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并不意味着规则的效力高于原则。其实,“无论规则还是原则,它们说的都是‘什么应该是这样’;它们都能够使用诸如命令、禁止和允许等这样的基本道义论语句表达;原则与规则一样都是关于什么应该发生的具体判决的理由,只不过它们是不同性质的判决理由。总之,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都属于法律规范。这样,规则与原则的区分是两种不同类型规范的区分。”[3]
首先,规则的明确性决定了其适用的优先性。与原则相比,规则是明确的,这一点应该始自法典化运动。相信通过系统而广泛的立法活动,可以一劳永逸地制定出调整和概括所有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法律存在漏洞、法律需要解释等在后人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那时人们狂热的头脑中基本不存在。法官仅仅负责找出正确的法律条款,并将条款与事实相结合,在此结合的过程中会自动产生解决案件的办法。姑且不论这种观点在后来遭到了质疑和批判,仅从规则本身来讲,它的确明晰地规定了实施某种行为的条件。如果案件事实满足了规则的这些条件,就必须接受规则提供的解决办法。反之,就是对规则的践踏,对法治的蹂躏。规则的这种适用方式与它的两个性质有关:“第一,虽然任何规则都有例外,但精确的规则会把例外考虑在内。一个规则列举的例外越多,规则的表述就越完备。从理论上说,一个规则的例外是可以全部列举出来的。第二,规则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冲突。”[4]
另外,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更易操作。规则在表述上所采用的语言外延狭小,这些限制性词汇的使用更提高了规则的确定性。如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法律原则则是以概括性、抽象性文字加以表述的,其用词将法律用语与日常用语、文学用语相混合,其内涵模糊、分散,以致于法律原则的内容无法或者难以确定。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平等原则就是法律原则的典型代表。因此,文字表述上的清晰、明确是规则易于操作的首要条件。从内容上看,法律规则更为具体,其“本质上是立法者为行为主体所设计的具体行为规则,是预先确定的行为模式或事实状态赋予确定的法律后果的各种行为指示。”[4]原则上,每条法律规则只调整一种类型的行为,而法律原则虽说是立法者意图在法律条文中的体现,同时也体现了立法者所致力追求的理想,但是其并没有预先设定明确的假定条件,也没有对公民应如何行为进行告知,更没有对遵守或违反法律原则的后果进行明确界定。法律原则只是为裁判设定了一些概括性的条款,并没有规定如何才能实现或满足这些条款的要求。换言之,它仅为裁判或行为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或方向,至于如何把握,就看法官或公民个人的悟性了。如此一来,在对行为或裁判的指引上,涵盖面比较宽泛的法律原则显然不是精细化法律规则的对手。
其次,规则的优先性还体现在其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这样一来提高了规则的适用效率,二来也为法官发现法律提供了具体操作技术。法律规则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对此学界有“两要素说”和“三要素说”之分,其中后者占据着学界的主流。法律规则主要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组成:“假定是法律规则中指出适用这一规则的前提、条件或情况的部分;处理是法律规则中具体要求人们做什么或禁止人们做什么的那一部分;制裁是法律规则中指出行为要承担的法律后果的部分。”[5]92如此看来,在适用的过程中规则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应用于具体案件的。也就是说,如果案件事实符合规则中假定条件的内容,那么这条规则对于该案件来讲就是有效的,法官应该按照这一规则的处理后果进行裁判。反之,规则对某特定案件的裁判没有效力。而法律原则没有如同规则那般清晰的逻辑结构,它是以或多或少的方式适用于具体个案的,而这种分量的差异对于法官来讲不是那么容易驾驭的。因此,在两个原则可以同时适用于某特定案件而出现冲突时,法官就不如适用规则时那么轻松了。裁判者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有关的背景材料在冲突的原则之间进行衡量,往往分量较重的法律原则占据着案件裁判的上峰,但未被适用的法律原则也并没有因此被完全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总之,与原则相比,逻辑结构明晰的法律规则更易为法官采用。
逻辑结构清晰的法律规则也为法官发现法律提供了操作技巧。因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规则时消弭了各种价值之间的争论,法律的适用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没有必要为公平、正义等形而上的价值而争得不可开交。所以说:“在体系化法律的适用中,不管是法官还是普通民众,即使他不了解规则中蕴涵的基本价值的内容,但只要稍具有逻辑演绎的知识,即可按照规范体系的层级结构,通过法律推理的过程对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法律化分析,从而按图索骥地找到法律结论。”[6]218法官依法裁判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案件事实涵摄在具体法律规则之下的过程。“法律规则提供了逻辑推理技术,从而将法官的裁判限制在规则的构成要件对案件事实的涵摄之中,易于达致法治的最低限度,降低进入法治国家的门槛[4]。”
最后,规则优先根源于人类社会对规则理性的需求[6]227。人类社会只有依靠规则所划定的交往边界才能避免陷入人与人相互争斗的深渊,这也使得人们之间的互惠交往成为可能。人类社会对规则理性的需求主要有三:首先,在生理上。正如霍布斯所言,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互为战争状态,肉体的毁灭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是和非以及公正与不公正的观念在这儿(指的是自然状态,笔者注)都不能存在。”“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切的希望。于是理智便提示出可以使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条件。”[7]96-97其次,在政治上。人类本身就有追求正义规则的理性以及谋求秩序社会生活的本能。对此,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的话颇有代表性:“政治就是考察公民交往的规则。”最后,在心理上。合理清晰的规则“能够使个体心理获得一种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安全感,从而极大地减少为应付突如其来的精神紧张所带来的生理不良反应,帮助人类的神经系统节约更多的能量。”作为追求目的的动物,人类在经历了反复的法律生活实践之后,逐渐形成了对规则的依赖。
三、下位法优于上位法
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是依据法律规范的位阶关系对法律规范进行的划分。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效力层次是不一致的,这就是法律规范的位阶所反映的。处于高层次的法律规范被称为上位法,反之被称为下位法。其实,法官发现法律时到底如何在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进行取舍,也有陷入两难状态的可能。对此,可以从我国学术理论的几个观点中进行透析。
首先,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正如前述,上位法的法律位阶高于下位法,那么当两者在法律秩序中出现价值评判的矛盾时,上位阶的法优于下位阶的法显得理所当然。这也可以从我国的法律条文中找到明证。我国《立法法》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较大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是,在法官发现法律时,如果一味地坚持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也是不合适的。试想,法官均从宪法中发现法律去裁判案件,这可能吗?抛开宪法尚未司法化这一论题,单从宪法条文本身来看,它是否含有能够裁判具体事实的条文呢?举例来说,一起故意杀人的案件,如果采用刑法第232条规定就可以使这起案件得到圆满解决,此时是否还需要径直引用宪法来判案?因此,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适法原则值得商榷。在有低位阶的法律可以适用的情况下,法律发现不从低位阶的法律开始,反而从高位阶的法律中发现法律,那么立法机关费力耗时所制定的法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此一来,只有一部宪法一切就可万事大吉了,而这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说不通的。
其次,上位法和下位法同等适用。法官发现法律没有什么位阶之分,他会在整个法律体系内部对与案件事实相对应的裁判规范进行筛选、取舍。法官发现法律的起点到底是宏观性较强的宪法规范还是易操作的法规、规章,在这里皆可。也就是说,这种观点没有提出实质性的可供参考的发现法律的意见,其指导意义不大。
最后,附条件的下位法适用观。这种观点认为,效力高的法律规范往往只是一般性规定,反而效力较低的规范比较具体,在这两者不相抵触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效力较低的法律规范。可见,这种法律适用的观点是有条件的。详言之,这种观点要求法律适用主体必须对法律规范进行审查,只能是与上位阶法律规范不相抵触的下位阶规范才能适用。言外之意,一般来说下位阶法律规范是没有被适用的资格的。“只是在上位法缺乏具体性规定时,下位法方可‘乘虚而入’。”但是,这种上位法与下位法的适用模式,同前述第二种模式有异曲同工之意,也是对下位法的适用空间进行了压缩,只是这种模式与司法实践中发现法律的顺序有些颠倒了。
应该说,法官发现法律的顺序取决于两个因素:法律效力和法律位阶。法律效力是法所具有的约束力,这种效力的存在不以涉法行为的发生为条件。法律效力的存在意味着人们对义务的遵守和服从,而授予的权利或权力应当受到尊重,并在遭受侵害时得到司法机关的恢复或保护。法律效力是法律规范等级划分和存在的依据。从法律效力来说,有的法律规范等级较高,如宪法、法律;有的法律规范等级较低,如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但是前面所讲的三种下位法与上位法适用模式显然受法律效力的影响较深。而法律位阶制度与法律效力不同,“法律位阶是从法律体系的角度去说明法律规范等级地位的,它表现的是在一个法律体系内部一个法律规范同其他法律规范之间的联系。”在寻找个案的裁判规范时,法律位阶决定着发现法律的顺序。也就是说,法律效力决定着法律的位阶,而法律位阶实为法官发现法律顺序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单纯以法律效力作为发现法律的顺序依据,显然法官会倾向于从效力高的法律中发现法律;若以法律位阶作为发现法律的顺序,情形则正好相反。这也就是孔祥俊所说的效力优先与适用优先之间的关系。效力优先是指“上位法在位阶或者法律效力上高于或优于实施性规定,在实施性规定与其发生抵触时,适用上位法的规定,体现的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者(适用优先,笔者注)是指在实施性规定与上位法不抵触时,下位法可以优先适用和援引。适用优先显然是以效力优先为前提的。”[8]242可见,法官发现法律是以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没有矛盾作为前提的,而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也只是一种特殊情况。所以,从下位法中优先发现法律是法官发现法律的常态,而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只是发现法律的一种例外。
之所以需要优先从下位法中发现法律,是国家立法的客观要求。一般来说,高位阶的法律规范抽象化程度较高,外延比较大,而内涵比较小,由此带来的是法律概念的极端空洞,如《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低位阶的法律规范外延小,内涵比较丰富,规定明确具体,法官理应优先从低位阶的法律规范中发现法律。更为重要的是,“下位阶的法律文件本身主要是为了执行或者实施上位阶的法律文件而制定,下位法只是依照上位法的授权和确定的框架来进行具体与细化的工作,是上位阶法律规范的展开与具体化。”[6]242这样一来,优先从下位法中发现法律可以保证结果的可预测性和安全性,也可以减少司法机关由于裁量权过大而导致的对法律的误解与滥用。
下位法的优先适用有时也是基于以下原因:“如果下位法的制定是根据上位法的授权或下位法是对上位法的实施性规定并且没有违反上位法的规定。”根据上位法的授权制定下位法是国家立法机关考虑到一些地方的特殊性,给下位法主体一定程度的立法变通权,允许下位法主体根据当地情况制定符合上位法的变通规定。具体来说,“所谓变通规定,是指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授予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法律、行政法规授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立法权的情况下,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的、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适用并且与法律或行政法规有不相一致内容的规定。”[9]这种变通规定可以从《立法法》第81条中得到证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作变通规定的,本自治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当然,这种变通也不是毫无限制的,它不得对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作出变通规定。实施性规定是“为了贯彻上位法的规定而根据本区域实际情况所作的”规定。实施性规定主要是针对上位法的相应规定而作出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上位法更为详尽且易操作。按照《宪法》、《行政法》的规定,行政法规可以对法律,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实施性规定。
四、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特别法与一般法是以法的适用范围为标准而作的区分。按照法理学教材的说法,一般法指的是对一般主体、一般事项、一般时间、在一般空间范围内有效的法律。与此相对应,特别法指的就是对特殊主体、特定事项,或在特定区域、特定时间内有效的法律。在法律适用时,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主要是指“在具备特殊性的案件中,虽然两个互相竞合的事实构成都被满足,人们却能显而易见地得出应以特别规定为根据确定法律后果的结论。”[10]135-136该规则起源于罗马法的古典时期,是由罗马法学家伯比尼安提出的。应该说,在罗马法时期,没有明确的特别法与一般法的概念,主要用“个别法”与“共同法”来代替。如罗马法学家保罗认为:“个别法是立法当局为某些功利而引入的违背法的一般规则的法。”换言之,“公法权力主体在实施公权力行为中,当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不一致时,优先适用特别规定。”[11]我国《立法法》第83条对此也有说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可见,《立法法》中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主要指的是分属同一机关制定的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限于此。
对于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的认定,学界大致有以下几种分类:孔祥俊将其分为三种情形,即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之间的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之间的关系、变通规定与原规定的关系、下位法与上位法的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关系[8]。沈志先将其归结为两种情形,即同位法中的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异位法中的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10]142。笔者倾向于后一种分类。
首先,来分析同位法中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情况。前述的《立法法》中的规定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代表。这里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同一机关对一般情况制定了法律规范,对特别情况又另外制定了法律规范;二是同一机关在法律规范中规定了一般情况下的规范,在同一法律或另外一个法律的其他条文(条款)中规定了特别情况下的规范。”[12]202在这里,同位法中的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三种情形:一是同一法律文件中的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如《婚姻法》对离婚的一般规定与对现役军人离婚的特殊规定。二是一般法中的一般规定与特别法中的特别规定,如《反不当竞争法》与《烟草专卖法》之间的关系,前者调整市场经济中的一切行为,而后者只是针对烟草专卖领域。三是不同法律文件中的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两个法文件之间本身不构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但针对某一特定事项作出的规定不一致,其中一方规定比另一方更特别、更合适。”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特别法与一般法的适用模式只是存在于同位法中,如果下位法的特殊规定与上位法的一般规定不一致时,除非有规定,否则不能按此原则处理。另外,不是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虽说位阶可能一致,但是它们之间没有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区别,因此也不能武断地适用。
其次,异位法中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在这里主要是指下位法针对上位法的有关规定作出的特殊规定。这主要是指不同立法主体所制定的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在下位法实施性规定与上位法不相抵触的情况下,坚持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如《立法法》第56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再如,《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可见,无论是行政法规还是地方性法规,皆可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授权范围内针对特定事项作出特别规定,并且可以优先适用。这样一来,就可以做到对上位法内容的具体化,增加上位法的操作性。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下位法的制定一定要遵循上位法的规定,并且不能与之抵触,否则下位法就不能优先适用。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形,这种“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模式和前面提到的“下位法优于上位法”中的“变通规定”有类似之处。总之,特别法是否优于一般法的适用,主要取决于前者与后者是相符合还是相抵触,若特别法不符合上位法的规定,则其由于抵触上位法而不能适用。
综上所述,坚持法律发现的原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为法官发现法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准。毕竟在现代法治治理的系统中,规制和约束也具有现代法治的内涵[13]。
[1] 陈金钊.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发现 [J].中国法学,2002(1):49-60.
[2]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 王夏昊.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冲突之解决 [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7:41.
[4] 范立波.原则、规则与法律推理 [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4):47-60.
[5] 张文显.法理学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6] 陈金钊.法律方法论研究 [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7] 霍布斯.利维坦 [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8] 孔祥俊.法律方法论:第1卷 [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9] 汪全胜.“上位法优于下位法”适用规则刍议 [J].行政法学研究,2005(4):62-66.
[10]沈志先.法律方法论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11]顾建亚.“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适用难题解析 [J].学术论坛,2007(12):124-128.
[12]曹康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13]李岩松.论英国法官造法与地方自治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85-189.
Analysisoflegalfindingprinciples
ZHANG Zhi-wen
(Research Center of Transportation Law, Shandong Jiaotong University, Ji’nan 250357, China)
In the judge’s point of view, the source of law can not stay in the static state as the collection of various laws only.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it could only be manifested when combined with legal finding.Therefore, the source of law from judicial perspective becomes the “warehouse” of judges to seek rules of referee disputes.When finding law from the source of law, the judge should follow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the formal source of law is superior to informal source of law; the rules are superior to principles; the lower law is superior to the upper law; and the special law is superior to the general law.
legal finding; source of law; legal method; discretionary power
2013-11-18
张志文(1980-),男,山东临清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法理学、法律方法等方面的研究。
* 本文已于2014-03-12 19∶27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40312.1927.002.html
10.7688/j.issn.1674-0823.2014.03.14
D 903
A
1674-0823(2014)03-0273-06
(责任编辑:郭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