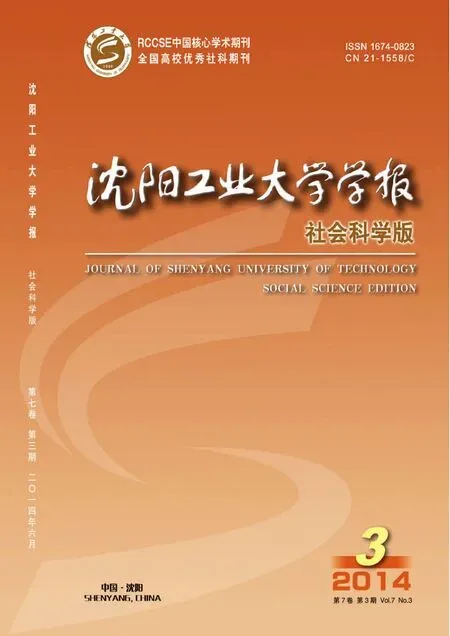城镇化背景下大遗址管理体制的突破与困境*
2014-04-03郭萍,刘洁
郭 萍, 刘 洁
(1.北京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北京 100021; 2.北京物资学院 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 北京 101149)
城镇化背景下大遗址管理体制的突破与困境*
郭 萍1, 刘 洁2
(1.北京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北京 100021; 2.北京物资学院 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 北京 101149)
对大遗址管理而言,我国正稳步推进的城镇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回应这些机遇或挑战,“十一五”前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寻求大遗址管理体制中管理架构和机构的部分突破。这些突破对大遗址保护已经或正在产生积极影响,但也面临着政策不具普适性、无法根除原管理框架痼疾等困境。促成大遗址保护需求与规划的衔接、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大遗址管理,是突破困境的重要手段。
城镇化; 遗址保护; 文物保护; 大遗址管理; 管理体制; 管理架构; 条块分割
对大遗址管理而言,我国正稳步推进的城镇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城镇化是本文的主要研究背景。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标准来看,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城镇常住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的提高[1],意味着农村往城镇迁移常住人口比重的提高,并会带来城镇人口、产业甚至城市本身面积规模的扩张,引发更大范围的城镇工矿建设、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需求①这一需求在2008年发布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第一章第二节中,即在土地需求层面得到明确预期。该节认为,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城镇工矿用地需求量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较高水平”,“区域性基础设施用地"将"进一步增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需要一定规模的新增建设用地周转支撑”。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通知》(国发〔2008〕33号)。。
一、缘起:城镇化之于大遗址的挑战与机遇
城镇化的全面展开,既对我国城乡格局完善、经济发展产生了正面影响,也给文物(尤其是大遗址)保护带来新的挑战——大范围建设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地上、地下空间的扩大与更新。由于与这些建设行为共享地下空间,且一旦建设即意味着对遗址的扰动,不少埋藏于地下且规模较大的大型古代遗址将不得不面临与各种建设“争空间”的命运。
基于这些遗址之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及保护紧迫性,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于2006年联合发布《“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以下简称《大遗址十一五规划》),并于2013年5月发布《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以下简称《大遗址十二五规划》),于开篇即明确其制定目的意在对抗“快速发展的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生产、生活”(或“大规模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等给大遗址带来的威胁及破坏,将城镇化发展中的建设行为列为大遗址遭受威胁或破坏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与这两部国家级行动计划配套,自2005年起财政部每年拨付2.5亿元资金,专项用于大遗址保护[2]。
大遗址保护究竟有何特殊性和紧迫性,使得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在每年已拨付数目可观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前提下,另外拨付如此大笔的经费专项用于特定类型文物(大遗址是否属于文物的一类尚存争议,为表述之便,这里姑且称之)的保护?城镇化背景下大遗址管理体制的突破及困境,由此进入笔者的研究视野。
二、大遗址管理体制的突破:从中央到地方
所谓“大遗址”*对于如何科学界定大遗址的内涵及外延,理论和实务界尚无定论。本文所提出的大遗址概念,主要源于《大遗址十一五规划》。参见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关于印发“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通知》(文物办发〔2006〕43号)。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因其“规模宏大”,且本体依附于土地而存在,具有较强的不可移动属性,大遗址保护工作面临保护范围大、所涉群体广、迁移异地保护难度极大且成本极高等其他较“小”的不可移动文物较少面临的问题*严格说来,根据《文物保护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某些地上的不可移动文物可能无法原址保护而必须异地保存,不可移动文物与环境的关联性被切断,其文物价值虽然减损但仍可部分保留。这一情况在我国和其他国家均有出现,前者如2012—2013年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舒坪刘氏节孝坊的异地保护(参见《自贡市首例文物异地保护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载自贡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zg.gov.cn/news/articles/2013/09/05/20130905112416-160976-00-000.asp),后者如20世纪50—60年代埃及为修建阿斯旺大坝迁移两座神庙,因而直接促成后来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诞生(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http://whc.unesco.org/en/convention)。,由此对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尤其在城镇化衍生的“地下空间争夺战”正如火如荼开展的当下,传统管理体制逐渐不再能完全满足新形势需要,并直接影响到大遗址的保存状况。
在这一情势下,从中央到地方层面,从国家文物局到其他相关部门,都在或主动或被动地探索大遗址管理体制方面的突破口,以顺应时势所需。其中,在原有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第一批重要大遗址名单公布时,仅有二处大遗址非国保单位,分别为:大辛庄遗址,第一批(1977年)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公布为第七批国保单位;丝绸之路新疆段,虽然该段并未整体公布为国保单位,但在该段上分布有十多处国保单位。因此,绝大部分大遗址兼具“大遗址”和“国保单位”的双重身份。管理方式之外,打破传统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管理格局的中央主导的“央地共建大遗址保护”项目库和地方层面各种形式综合性管理机构的设立,成为这一尝试中的代表。
1.管理体制突破前的“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方式及其“不适应症”
大部分大遗址本身即为国保单位,基于考古工作需要,加之国家文物局早在1991年即发布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敦促国保单位规范其管理,不少大遗址较早即建立了保护机构。如今,相当数量的遗址保护机构(或发展为管理机构)仍以文管所、博物馆以及由文物(文化)局或考古队、博物馆代管的过渡性管理机构三类形式[3]存在并运行,并以“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要求对大遗址进行管理,接受不同层级文物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其主要职责为文物的“调查征集、保护管理、维护修缮、藏品保管、宣传陈列和科学研究”*参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试行)》,1991年3月25日由国家文物局公布并施行。等工作。这几类管理形式基本以文物本体为中心开展工作,主要方式为在为文物保护单位划定边界(如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等)后进行相对封闭的管理。这种以文物本体为中心的封闭式管理方式,在“大遗址”这一概念提出并推行后产生了一系列“不适应症”。有研究已经留意到,因各部门多头管理而导致的决策分散、沟通不畅等问题以及对大遗址本体及管理方式不得不具有相对开放性这一特点的欠考虑,直接对遗址管理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4]。
与较易确定保护边界、面积相对较小、存在由文物管理机构进行封闭式管理可行性的地上文物保护单位不同,由于占地面积较广,许多大遗址与居民的生产、生活区域重叠,且其边界较难确定,难以进行封闭式保护,因此,以保留遗址区内的部分生产、生活为主要特征的开放式管理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也较为常见。开放式管理方式意味着遗址不再仅作为文物得到保护,而是需同时满足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等方面需求。
在中央层面,根据相关法律,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公安部等部门也和国家文物局一样拥有在大遗址区域范围内行使法律赋予的土地、建筑、农业、林业和治安等方面管理权的权能。“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省、市、县有三个以上层级的垂直序列”,中央级的行业主管部门主要承担业务指导和规划、监督、审查等专业职能[5]116-117。
而从地方决策者层面来看,根据《宪法》第107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而文物保护不过是该条所列举的7项事业中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因此,除文物部门外,工商、林业、公安、土地等部门也在这些区域内行使相应管理职权。例如,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金沙遗址已探明的遗址面积约3 km2[6],其中金沙遗址博物馆占地面积30万m2[7],其余面积则或将原规划为中高层住宅区的地区调整为低层住宅区(金山片区),或部分建成永久性绿地等[8]93-94。类似情况在其他大遗址中也属常见,即园林、工商、公安、国土等部门与文物部门一同在该遗址范围内各自行使日常管理权能。在地方一级,这些部门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业务部门,事权、财权均由地方政府统筹及解决。
综上可见,在出现新的管理体制方面的突破之前,在中央一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业务指导、规划、监督、审查等实现对地方一级行业内部门的管理,这一纵向分级管理方式,被业界称之为“条”状管理;在地方一级,大遗址多采属地管理,由当地政府统筹遗址内各项事务,这一横向分部门管理形式则被称之为“块”状管理。传统的以“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为代表的封闭式管理方式不适用于开放性较强的大遗址,并因其固有的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弊端[4],产生责权不对等、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目标多元化、市场寻租等问题[3],使得各地方职能部门在具体行使管理权时容易各自为政,割裂大遗址所涉事项的关联性;一旦管理事项产生冲突,即有可能因缺乏协调机制而导致问题被搁置、得不到及时解决。这被认为是形成大遗址保护现状的重要消极因素。
2.管理体制中央层面的突破:“央地共建大遗址保护”项目库
以大遗址保护片区为主要表现形式、“央(局)地(省)共建”为主要特点的“央地共建大遗址保护”项目库,虽然其本意未必如此,但却为克服上述为学者诟病的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弊端提供了解决思路[9]。根据《大遗址十一五规划》和《大遗址十二五规划》,目前我国已将陕西西安片区、河南洛阳片区、湖北荆州片区、四川成都片区、山东曲阜片区、河南郑州片区6个片区纳入“央地共建大遗址保护”项目库。虽然官方并未在任何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对何为大遗址保护中的“央地共建”、“片区”进行解释,但从已公布的上述大遗址片区来看,这些片区都具有覆盖面积较大、分布相对集中、文化发展脉络具有代表性、历史与文化渊源在我国人类文明和文化进程中具有较高地位等特点[10],“片区”的运作方式则主要是由国家文物局直接对片区给予经费、人员培训方面的倾斜,片区所处各级(主要是省级)人民政府承诺针对片区内大遗址主动开展保护工作[11]。笔者认为,大遗址保护片区这一管理方式至少能在如下两方面取得突破:
(1) 调动地方政府主动开展大遗址保护工作的积极性。由于只有在其本体和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或限制建设活动才能有效保护大遗址,身负完成“城镇化率”等各项指标任务的地方政府对于遗址保护的态度一直相对消极。这一态度由2012年因长沙古城墙被迁移异地保护事件而被舆论“一边倒”地指责的长沙市市长张剑飞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的回应可见一斑:“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确实是一对矛盾……在建设中,如果一开挖发现文物古迹就停住不建,对于长沙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可能就无法建设了。”一旦停止建设,可能动辄意味着“上亿元”甚至“140多个亿的损失”[12]。在笔者看来,上述观点颇具代表性,巨额的直接经济损失和看不见现实、眼前利益的遗址保护之间“孰轻孰重”其实是相对清晰的。
“央地共建大遗址保护”项目库的设立则多少减轻了地方政府对大遗址保护巨额投入的顾虑。一方面,根据与省政府签订的框架协议,国家文物局会承诺对片区给予项目实施、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倾斜[13],亦即地方政府能由项目中获得中央层面从财权到事权方面的优惠,且遗址等文化资源还因其文化底蕴成为“城市名片”*将大遗址作为“城市名片”或其他城市形象代表的说法,在多位参加大遗址保护西安、良渚、洛阳、荆州论坛的地方执政者讲话中均有提及,其中西安、洛阳、荆州论坛讲话已汇编成《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文集》(西安)、《大遗址保护洛阳高峰论坛文集》、《大遗址保护荆州高峰论坛文集》,分别于2009年、2010年、2013年由国家文物局出版。;另一方面,地方享受的上述优惠需以相关工作的开展为对价,由此推动地方由省一级支持遗址保护工作的开展,并承担具体协调和统筹工作。
(2) 有助于协调文物管理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关系。根据《宪法》第107条规定,省级人民政府是除中央以外的最高级别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全省行政区域内“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行政工作。因此,其有能力在较高层面有计划地协调大遗址保护工作开展中可能遇到的各部门职能交叉的状况,既有利于预防市、县级发生类似情况;其优先进行大遗址保护、主动开展大遗址相关项目建设的积极态度,也有利于在前述所涉部门发生管理职能冲突时作出有利于遗址保护的选择,由此多少破解前述条块分割中块状管理弊端。加之这一方式是由国家文物局与省级人民政府直接对话,即二者为“片区”框架协议的双方,不必由国家文物局将经费逐层分解到地方各级文物管理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将条状管理和块状管理结合起来,对于克服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的弊端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3.管理体制地方层面的突破:综合性遗址管理区、特区等的建立
如果说“央地共建大遗址保护”项目库是在国家(主要是中央)层面试图破解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那么遗址管理区、特区等综合性管理体制的建立则是地方层面克服这一管理方式弊端的尝试。就关涉群体如此之广、占地面积如此之大的遗址而言,首先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问题是:分别负责完成前述多重目标的文物、园林、工商、公安、国土等行政(管理)部门与上级业务指导部门之间、相互之间已形成条块分割的管理格局在先,如何统筹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管理行为,才能实现对遗址的科学管理?以遗址为要素或中心,建立综合性的管理机构,成为部分决策者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以笔者目力所及,目前此类管理机构的主要表现形式为遗址管理区或特区,其整体或部分为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行政府职能。例如,2008年设立的统筹瓶窑、良渚两镇的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良渚管理区”,后其权力被弱化至主要为遗址事务管理机构),统筹大明宫遗址保护、开发事宜的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办公室(以下简称“大明宫保护改造办”);2012年设立的汉长安城遗址保护特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汉长安城特区管委会”),等等。
就本文所述综合性的遗址管理区或遗址特区而言,由于其设立目的即在于统筹遗址所涉范围内事项,因此一般来说,其组织成员包括遗址范围内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主要部门,如前述良渚遗址管理区委员会在设立之初下设办公室、土地与规划建设处、文物管理局、综合发展处4个部门,另设余杭区财政局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分局和瑶山派出所,负责管理区范围的文物保护、城乡规划、经济开发、社会管理及其他工作的协调与监督等[14],实际上被赋予242 km2管理区域范围*有关良渚遗址管理区的区域范围,参见2001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的批复》(浙政函〔2001〕205号)。转引自余杭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发展规划的批复》(余政发〔2012〕11号),载余杭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s.zj.gov.cn/wse/temp/S1/MR/964ed699ea8e500d1e31a85dc6d48c91.mht.-955443135.htm.内的国土、规划、文物管理、财政、公安等主要行政权力,行使政府派出机构的职责。此外,为保证上述成员能达成一致意见,组织的领导层(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或特区)一般由主管其中所涉某项业务的高级别行政领导兼任。前述大明宫遗址、良渚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在其综合性管理机构设立之初均大致循此思路。
由于这些综合性管理机构的成立目标和管辖范围均较为明确,专司统筹和协调遗址保护及相关事务,且一般较全面地设立了遗址所涉事项的主要职能部门,因此在处理问题的及时和有效方面具有较明显的优势。
三、大遗址管理体制突破中的困境、原因与解决思路
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条块分割管理体制产生的部分问题,但是无论是大遗址保护片区抑或是遗址管理区、遗址特区,在其实现管理体制突破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境。
1.管理体制突破后的困境
大遗址片区推广的困境在于,这一管理方式不适用于所有的遗址类文物,不具备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可行性。首先,要成为片区,需满足前述所列遗址相对集中等诸多要求,而由我国大遗址的分布来看,显然并非所有行政区域都具备成为片区的条件。其次,地方乐于推进片区项目的动力在于中央所给予的事权、财权方面的倾斜,而这方面的倾斜往往需要较大数额的中央财政专项支出的支持,考虑到我国已提出将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大幅压缩1/3以上[15],获得大力度的中央财政支持绝非易事。
置诸地方层面,遗址管理区、特区管理方式的推行也并非毫无障碍。由于大遗址保护边界并非总与现有行政区划边界对应,因此在运作过程中,这些综合性遗址管理区、管理办公室、特区应如何与目前的行政区划进行衔接,将是管理者首先需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相关部门为这些机构的日常运转新增人员编制及日常经费;此外,一旦管理区、特区与其所处行政区域的行政级别相同(如良渚遗址管理区与其所处的余杭区同为正区级单位[15])或管理目标重合,则如何处理二者关系将成为新的协调需求。
2.管理体制困境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思路
笔者认为,撇除中央、地方决策者个人意志的影响,我国大遗址管理体制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大遗址保护需求与城市规划的衔接不畅、条块分割的管理格局无法从根本上打破等,也是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
(1) 大遗址保护需求与城市规划的衔接问题。大遗址保护需求与城市规划、尤其是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不畅,是造成地方决策层认为大遗址在与城市发展“争空间”的重要原因。这种衔接上的不畅通,使得大遗址没有在城市规划阶段得到合理定位,其保护需求也无法先期得到满足。之所以如张剑飞等地方决策层认为大遗址保护即意味着需付出较大代价,直接原因即在于大遗址对土地的限制、禁止建设需求未在城市规划中得以体现,而多是当开发商破土动工时,才发现其已支付巨额土地转让金(如根据前述南方周末所载张剑飞市长访谈,古城墙事件所涉开发商万达集团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为24.5亿元)的宗地地块内有遗址遗存。考虑到已付出的土地转让金、征拆成本及可预期的丰厚收益,遗址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自然往往居于不被选择的位置。因此,将大遗址保护需求与城市规划相衔接,能使文物或相关部门在规划阶段即获得遗址保护的主动权,预防各部门职能冲突状况的出现。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将大遗址保护需求纳入城市规划(尤其是土地利用规划)并非仅限于理论层面,而是已有十分成功的实践,如美国联邦土地管理局(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即在其管理手册中规定,根据不同用途,在规划土地范围内,应为已知(known)或已立项(projected)的蕴藏有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BLM所谓文化资源,包括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s),历史遗迹(historical sites)和具传统文化重要性的场所(place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importance)等。的区域预留一定的土地配额(allocation)[16]。这些预留配额体现于土地管理局的土地利用规划(land use plan)性质的“资源管理规划”(resource management plans)*RMPs主要用于评估并沟通公共用地方面的问题。参见The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Land use planning[EB/OL].[2013-01-11].http://www.blm.gov/co/st/en/BLM_Programs/land_use_planning.html.部分,为强制性规定。经由这一具有前瞻性的规定,联邦政府能先期保证文化资源用地不必与其他类型用地抢占配额;由于规划是面向全社会公开的,且一般会在土地使用权买卖时明示,土地买受人无法借口不知土地为文化资源用地而对其进行破坏。
进一步深究,如果我国如美国一般将大遗址保护需求纳入土地利用规划,则至少还需开展如下基础工作与其配套:勘定和划定遗址保护所需土地面积(以使国土部门明确遗址所需土地配额),精确测量遗址坐标并将其反映到城市规划中,在土地所有权、使用权证上载明遗址所处土地的使用限制事项等。
(2) 条块分割的管理格局问题。从前文有关中央和地方层面管理体制突破的论述不难看出,这些突破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消解条块分割管理格局的弊端,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且其日常工作仍处于这一管理格局内。
虽然诚如某几位学者的美好愿景,在中国建立类似美国的“国家公园体系”,以实现中央垂直管理(在地方层面表现为分片管理)能最终避免这一格局的弊端[5]4-125,但笔者认为,这一管理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且所涉甚广,要改变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不过,由中央正逐年将行政许可权限下放或取消的趋势来看,遗址管理也许能够跳出目前遗址保护仍以行政管理为主、为重的窠臼,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进而逐步在保护与利用中取得平衡,以另一种形式取得管理体制层面的突破。
[1]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 [EB/OL].[2013-04-15].http://www.stats.gov.cn/tjgz/tjdt/201304/t20130415_17743.html.
[2] 李韵.财政部设立每年2.5亿元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 [N].光明日报,2005-06-15(A1).
[3] 陈稳亮.大遗址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基于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J].旅游学刊,2009(9):79-84.
[4] 刘卫红.大遗址区土地利用管理分析 [J].中国土地,2011(9):5-8.
[5] 刘世锦.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3)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6] 朱章义,张擎,王方.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意义 [J].四川文物,2002(2):3-10.
[7] 金沙遗址博物馆.金沙遗址 [EB/OL].[2014-01-20].http://www.jinshasitemuseum.com/about.html.
[8] 王忠林.认真搞好金沙大遗址保护与利用 积极引领成都城市新发展 [C]//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洛阳高峰论坛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8-15.
[9] 郭萍.大遗址保护管理体制与机制研究综述 [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3(4):18-22.
[10]宋晓龙,王晓婷,孙霄.片区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方法初探:以《曲阜片区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为例 [J].北京规划建设,2011(5):94-97.
[11]刘冰雅.从累赘到名片:大遗址华丽转身之后的思考 [N].光明日报,2011-12-26(15).
[12]彭利国,鞠靖.“讲我不注重保护文物,我感到很委屈”:专访长沙市市长张剑飞 [N].南方周末,2012-02-23(5).
[13]滕敦斋,袁涛,汪海涛.国家文物局与省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EB/OL].[2011-03-17].http://www.dzwww.com/shandong/sdnews/201103/t20110317_6224410.html.
[14]余杭档案信息网.2001年余杭大事记 [EB/OL].[2006-09-08].http://daj.yuhang.gov.cn/zjyh/yhdsj/200609/t20060908_3307.htm.
[15]财政部.削减专项转移支付 有序推进预算公开 [N].政府采购信息报,2014-03-10(14).
[16]The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Land use planning [EB/OL].[2013-01-11].http://www.blm.gov/co/st/en/BLM_Programs/land_use_planning.html.
Breakthoughanddilemmaofmanagementsystemofbigarchaeologicalsiteunderbackgroudofurbanization
GUO Ping1, LIU Jie2
(1.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1, China; 2.School of Labor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Beijing 101149, China)
The steady urbanization in China is both an opportunity and a challenge to the management of big archaeological site (Dayizhi).A series of measures were adopted from the central goverment to local goverments around the “11th Five-year Plan” in responding to the opportunity or challenge, so as to seek some breakthroughs of management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big archaeological sites.The breakthroughs have had or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big archaeological sites, but they are still facing some predicaments of non-uniform policies and non-eradication of old management structure.To promote the linkage of demand and plan of big archaeological site protection and introduce social forces into big archaeological site management are important means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dilemma.
urbanization; archaeological site protection;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relics; big archaeological site (Dayizhi) management; management system; management structur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vision of management
2014-04-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26)。
基金项目:郭 萍(1983-),女,湖北嘉鱼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 本文已于2014-05-20 16∶52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40525.1242.003.html
10.7688/j.issn.1674-0823.2014.03.02
D 912.6
A
1674-0823(2014)03-0201-06
(责任编辑:郭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