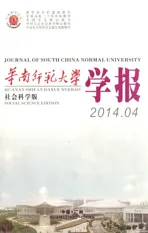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知识经验、理论模式与当代语境
2014-04-02段吉方
段吉方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段吉方(1975—),男,辽宁建平人,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曾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高度复杂的学科,其中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部分更是如此。”他并强调:“熟悉这门学科的读者会觉得是老生常谈,而对这门学科完全陌生的读者却感到困惑难解。”[1]伊格尔顿提出的问题在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那里曾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20世纪40年代,卢卡奇在为米·里弗什茨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和文学》一书写的序言中曾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最普遍的原则我们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中找到。”[2]他并认为:“如果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加以搜集和系统排列就可以产生一部美学,或者至少是构成美学的一个完整骨骼,只要加入连贯的说明性文字就能产生出一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那就完全是无稽之谈了。”[3]但也要看到,迄今为止,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分歧仍然鲜明可见。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并没有就文学与批评问题发表专门性的研究成果,在马克思关于文学研究的500页左右的文字中留下的是他对美学和文艺问题的“散见式”的思考;也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讨论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社会主义等问题时才涉及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相关问题的,他们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见解是一种“片段性阐发”的理论形态;更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全部的理论原则与方法观念更多地受限于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社会历史研究方法,意识形态理论遮蔽了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方法的具体形式,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系统性、统一性和连贯性。
一直以来,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特质、思想体系以及问题领域、理论品格的争论,都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的焦点和难点。特别是在当代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已经由一元走向了多元、由封闭走向了开放、由单一走向了综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面临着现实文化经验的洗礼和深度考验,同时也在学理层面上面临着把握现实的能力的挑战。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与建设所置身的历史语境。
在当前文化语境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其他文论研究一样处于一种多元化、多极化的文化生态和理论格局之中。这期间不仅充满希望,同时也是一个提出问题、面临挑战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当下仍然面临着不同理论传统的矛盾与冲突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也置身于不同理论话语趋同与求异的困难所带来的危机及挑战之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文学理论的大发展、当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不断涌现、种种思想裂变的冲击以及中国当下审美文化经验的复杂变化,都给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建设增加了更大的难度。在这种语境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亟待在问题意识和实践效应方面有所作为,特别是要在理论范式的凝练与发展上取得重要的理论突破。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理论学说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但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问题其实已经在文学发展的现实中得到了认可。综合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式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框架中确立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范式。由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十分复杂,相应地,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框架中确立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范式也就呈现出多种理论形态。特里·伊格尔顿在他和德雷·米尔恩于199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读本》中,曾根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各国的发展情况,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划分为四种理论模式,分别是人类学模式、政治学模式、意识形态论模式以及经济学模式。人类学模式以俄国早期民主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关注的是文学艺术产生和发展的人类学根源,探索文学艺术是如何与神话、仪式、宗教和语言问题联系起来的,并综合考察它们的功能。政治学模式以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乔治·卢卡奇为代表。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着重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及其意识形态的扭曲与虚幻化的内容。意识形态论模式以法国文艺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为代表。他强调意识形态是受经济基础、文化传统以及自身机制等因素“多元决定”的复杂现象,他提出的意识形态“主体垂询”功能、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念,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经济学模式以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雷蒙·威廉斯以及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为代表。他们重视大众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经验,强调工人阶级文化、青年亚文化、大众传媒等在社会文化构成中的意义与作用。特里·伊格尔顿提出,不同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回答现实文学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笔者认为,伊格尔顿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这四种理论模式大致能够概括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征。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并没有进入伊格尔顿的理论视野之中。并不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进入伊格尔顿的理论视野就代表多么大的理论成就,也不能单纯以国外哪一个理论家的观点来衡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但中国向来是文论研究的大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一直被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为什么在中国马克思文学批评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文学研究的全球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中国文学研究日益走到世界前台的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仍然在世界文化理论舞台上处于一种被忽略的状态呢?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以及不断丰富发展的审美文化现实往往最先表达并且在理论上转化为不同美学原则的论争。这也意味着,文学艺术创造的丰富性和实践性如果忽略了理论经验以及理论把握现实能力的有效性,便会带来文化创造力和思想竞争力的弱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就自身而言,并不着急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问题,只要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研究好就可以了。这也正呼应了那种一直以来流行甚广的“理论取消论”的观点。笔者认为,问题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一种反观传统、反思经验以及批判性的回溯性研究,往往会造成只围绕个别问题进行研究、忽略理论有效性的缺陷。而理论范式的研究正好可以从整体上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理论范式的研究本身就是从问题中来的。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历史走向更加复杂,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各种争论更加热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问题也更加难以把握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状况也不例外。笔者认为,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首先要回到它的历史语境中,这个历史语境就是文化多元化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现实。只有在理论把握现实的维度上体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才能体现理论范式研究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针对现实提问并不断融入现实文化经验的学说。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革命时期,还是在30年代的“左翼”时期以及4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理论飞跃时期、五六十年代的曲折发展时期以及新时期以来的整体创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直没有离开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而在如今,新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背景产生了各种新的文化思潮以及各种新的理论问题,这就更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的提问方式中,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不同方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内在的学理诉求。
其次,应该不断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经验和理论传统,在反思中不断总结理论经验,尽量在学理层面上深化发展我们固有的理论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恐怕一时很难有确定的答案,也不见得马上草率地给出答案。普列汉诺夫、卢卡奇、阿尔都塞、雷蒙·威廉斯等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理论模式都是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不断经受各种检验乃至多次遭受批评才建立起来的;甚至直到今天,有的理论模式还在接受人们的质疑。这也意味着,一种理论范式的形成一定是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的结果。同样道理,一个真正伟大的哲学家的出现,一个伟大诗人的诞生,甚至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诞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他们天才的自我才能,更需要几代人的文明发展与文化锤炼,需要文明传统、文化积淀以及哲学、历史、社会等多方面的思想氛围的培育和烘托。一种理论范式的建立也是如此。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现在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问题,一定要不断反省我们曾有的理论传统和经验。那么,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呢?就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范式的传统与经验而言,有的学者者指出,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确立的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模式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总结的。毛泽东的《讲话》从四个层面上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1)《讲话》总结和阐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知识经验问题,那就是来自底层的大众的文学生产和文化创造。(2)在《讲话》中,毛泽东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文艺实践出发,系统地提出了“文艺大众化”问题,表达了全新的理论观念和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追求。(3)在《讲话》中,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特殊的文学现实相呼应,从而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缔造了深刻的理论武器和斗争武器,而来自底层经验的“文艺大众化”方向则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拥有了“中国化”的理论形式。(4)“文艺大众化”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形态,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象化现实审美经验的有力方式。[4]确实,毛泽东的《讲话》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如何将中国审美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原则结合起来,真实地表征中国现代性社会发展中人们的情感和审美经验。为此,《讲话》着力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开始走出了理论创构的初期阶段,已经具备了理论范式层面上的理论条件;也说明“马克思主义观念已经作为一种整体精神契入中国审美文化现实,同时深刻贯穿于中国文学知识经验与理论研究的过程”[5]。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值得重视的传统。但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我们对毛泽东的《讲话》及其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形态与经验的总结,往往着眼于其意识形态话语层面的影响,忽略了学理层面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以后的发展中,“文艺大众化”的理论走向已经比较多元了,40年代延安与解放区的文艺实践与日常生活所置身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也发生了变化,这正是我们在学理层面上应该关注的内容。也就是说,《讲话》所确立的“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方向本身在学理上是有它的历史性的。虽然意识形态语境发生变化了,但学理层面上的功能与价值仍然会作为一种经验和传统留存下来,关键是今天我们如何继承和发展这种传统,如何将这种传统进一步与当代文艺现实结合起来,如何在学理层面加以深入地研究梳理。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性所在,也是理论反思的起点。
在当代,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仍然在重复卢卡奇的遗憾。他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发展水平相比,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正落得越来越远。”[6]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恐怕也是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仍然有很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其中,理论范式的建设仍然处于难题之中,也处于问题之中;但这并不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而是加重了问题意识的份量和责任。确实,像伊瑟尔说的那样,马克思“还没有讲清自己为什么依然喜爱希腊史诗这个棘手的问题就停了笔”[6]。但之所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有现实发展之必要,就是因为我们并不一定需要马克思一定要接着把希腊史诗问题讲清楚,我们需要的是他的哲学精神和学理价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从经典观念到多元主题,既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洪流,也是它的当代发展表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范式的完善就是要在发展中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呼应马克思主义面向现实文化经验的提问方式。这个过程的完善不单单是个别概念和理论学说的“照着搬”“顺着讲”,更没必要凡是谈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问题都要做那种马恩原著的“检索”和复述的工作。真正深入地探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问题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扎实地引向理论观念与思想精神的纵深发展,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学理精神贯穿于中国文学知识经验与理论研究的具体过程。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走向深入发展综合创新的过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与发展的系统工程。(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研究”(2009JJD750009)、2010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WYXM041)的阶段性成果)
[1]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
[2]卢卡奇.卢卡奇文学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275.
[3]卢卡奇.审美特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5.
[4]王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与理论模式.文艺研究,2008(1).
[5]王杰,段吉方.6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及其基本问题.社会科学家,2011(3).
[6]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