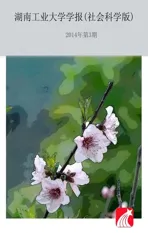空间置换中的女性成长
——析亨利·汉德尓·理查森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幸福的澳大利亚》
2014-04-01李玲玲
李玲玲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澳洲女作家亨利·汉德尔·理查森(Henry Handel Richardson 1870-1946),以罕见的勤奋与极其严谨的态度用了近20年的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三部曲《理查德·麦昂尼的命运》(The Fortunes of Richard Mahoney,1930)的创作。该三部曲由《幸福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Felix,1917)、《归途》(The Way Home,1925)和《最后的归宿》(Ultima Thule,1929)组成,为理查森赢得了193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使其成为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澳大利亚作家,同时也掀起了对理查森其人其作品的研究热潮。国外学者 Nettie Palmer,Edna Purdie,Olga M.Roncoroni,Vincent Buckley,DorothyGreen,Axel Clark等分别出版专著探讨理查森的生平,创作背景,也包括了对其作品的简单介绍。这些专著对三部曲的论述集中在作品的写作手法、叙述模式以及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体现的作者处世哲学等方面。国内相关研究论文均是从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切入,挖掘其性格缺陷和流散身份造成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对理查森的三部曲的研究多以男主人公理查德·麦昂尼为中心。Leonie Kramer在介绍三部曲时,甚至说道:“《理查德·麦昂尼的命运》是他的故事,主题是他的命运”[1]1至于理查德·麦昂尼的妻子玛丽·麦昂尼,目前的研究相当匮乏。值得一提的首先是巴塞罗纳大学的J·A·Hurtley发表的“The Fortunes of Polly Mahony—Henry Handel Richardson’s Woman in a Man’s World”。该论文探讨了三部曲所反映出的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指出理查森渴望建立男女平等的新的社会秩序。[2]玛丽·麦昂尼并不是一个平面的陪衬人物。整个三部曲见证了她从一个腼腆胆怯,需要保护的少女成长为独立勇敢,能支撑整个家庭的新女性。Catherine Cecilia Pratt在她的博士论文“Gender Ideology and Narrative Form in the Novels of Henry Handel Richardson”中提到:“如果非要说《理查德·麦昂尼的命运》三部曲中存在一位能成功适应环境,生存下来的英雄的话,那一定是玛丽·麦昂尼而不是理查德·麦昂尼。”[3]此外,学者对作家的生平研究发现理查森和妹妹艾达都对女权主义和妇女权利运动抱有很高的热情。[4]女性意识的觉醒亦是理查森作品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5]由此可见,如此关注女性的作家在她的扛鼎之作中所塑造的女主人公不可能只是一个陪衬人物。因而,三部曲中的女主人公玛丽·麦昂尼尤其值得研究。
细读文本,笔者发现玛丽·麦昂尼的成长变化和迁移有很大的联系。而迁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同空间的置换过程。以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幸福的澳大利亚》为例,玛丽的生活空间的三次变化,对应着她自我意识逐步完善,成长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过程。婚后被囿于卧室厨房的玛丽努力扮演着“家中天使”的角色,对丈夫唯命是从。流产之后的墨尔本之行开拓了玛丽的生活空间,为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契机。重回丈夫身边后,玛丽主动参与到丈夫的事业中,并扩大自己的社交范围,在这个过程中她的自我意识也随之增强。小说的最后,拥有独立房间的玛丽亦具备了完整的自我意识,敢于向丈夫的不公平待遇提出抗议。由此,笔者认为可以借用后现代空间理论分析玛丽·麦昂尼的成长过程。
一 公共/私人领域的划分
公共/私人领域的划分早已有之,英语中“公共的”(public)一词来自希腊语的“polis”,指的是“十八世纪时期以民主制度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该领域是属于一切人的,所有人都有权进入这里并发表自由言论、批评或讨论政府和社会。”[6]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讨论公共事物的地方。
与公共领域相对的私人领域则指每个人的家庭,即维持生存的地方。家庭是用来支持那个更高层次的公共领域的,而支撑家庭的则是女人和奴隶,家庭中的行事原则则是男人对女人及奴隶的权利和暴力。[7]“对家庭生活必需品的掌控是获得自由进入公共领域的条件,于是男人就有正当理由在该领域中使用权利和暴力,因为它们是获得这些必需品的唯一途径。”[8]
“18世纪以降,英国社会结构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推进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的改变就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工作/家庭)的分离。男子完全成为社会事务和公共领域的主宰,女子则日渐退缩到家庭的私人领域中。这种分离到维多利亚中期表现得尤其突出,出现了一批塑造和强化性别区分的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除了丁尼生(Alfred Tenyson)的《公主》(The Princess)组诗,还有诗人帕特默(Coventry Patmore)的长诗《家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和罗斯金的《皇后的花园》(Of Queen’s Garden’s)。”[9]
二 囿于私人领域,毫无自我意识
《幸福的澳大利亚》的背景是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据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所述,16岁的玛丽完全是应兄长约翰的要求辍学来到澳大利亚帮其打理家务。显然她所接受的教育来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被灌输的性别观念是“唯兄长之命是从”。玛丽的丈夫理查德·麦昂尼亦是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医学专业毕业生。他抱着发财致富的梦想加入到淘金的队伍中,以期挣得财富早日回到英国,他始终认为英国才是他真正的家。如此,刚刚移居到澳大利亚的玛丽和理查德奉行的一定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男主外女主内”“公私分明”的性别观念。“空间是性别的代码”,对于空间分配的不平等充分展示出两性世界中的不平等关系,并且“总的来说空间地理关系中总是男人占据主导”,男人对空间的控制权和所有权,象征着男人对女人的所有和支配权。[10]法国女性主义先锋人物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也认为,公与私、文化与自然等范畴不是相互定义的,而是公定义私,文化定义自然,男人定义女人,无论哪种情况,私、自然、女人都是他者。[7]
玛丽与理查德·麦昂尼结婚后,理查德为了迎接玛丽的到来对他原来的房间进行了改造,“他(理查德)在卧室和杂货店中间装上了隔板”。[11]74这个隔板隔开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清晰但不平等地划定了男性和女性各自的领地。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玛丽的活动空间都被限制在卧室厨房等狭小的私人领域。而丈夫理查德可以随意出入卧室厨房和杂货店。理查德的杂货店是淘金地的男性们商议讨论大事的地方,是象征权力权威的公共领域。玛丽被禁止进入象征男性权威的公共领域,亦不能参与杂货店内任何性质的谈话。淘金地发生动乱事件,玛丽的一个弟弟内德和理查德的最好的朋友普尔迪都被卷入其中。当无意中听到杂货店的男人们在谈论动乱事件时,玛丽迫切地想要询问亲人的安危。而丈夫注意到妻子的举动后,“拍了拍她的手,示意她回到厨房做分内的事情。因为丈夫的意愿在玛丽看来如同不可抗拒的命令,于是她顺从地回到厨房,继续洗碗”。[11]85婚后,丈夫主宰社会事务,占据公共领域,给妻子划定了卧室厨房等私人领域,并禁止她逾越界限。而妻子玛丽起初,对这种不合理的划分毫无怨言,绝对遵从。此时的玛丽毫无自我意识:“她确信丈夫理查德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丈夫看待事情的方式是唯一的最正确的方式。”[11]102所有事情以满足丈夫的意愿为标准,丝毫不能违背。她的主要职责就是照顾好丈夫的住行起居,为他营造一个舒适温暖的家。为了每顿都能给丈夫做出可口的饭菜,她托姐姐买来最好的烹饪书籍,一遍遍练习,无数次失败后,最后终于赢得丈夫的认可。每次丈夫出门后,她都费尽心思装扮房间,认真做家务,用心准备好晚餐后站在门口迎接他回家。回顾六个月的婚姻生活,“玛丽很高兴她已经完全搞清楚了丈夫的脾性,适应了丈夫的各种生活习惯。”[11]102婚后的玛丽就像一个快乐的“家中天使 ”,蜷缩在被给定的狭小的私人领域,生活完全以丈夫为中心,以丈夫的喜乐为自己的喜乐,毫无自我意识。由此,玛丽对英国当时父权制性别观念的顺从可见一斑。
三 涉足公共领域,自我意识初步觉醒
如果说亨利·汉德尔·理查森止于塑造这样一个毫无自我意识,效忠父权制的女性形象的话,那么她的三部曲绝不会成为经典。这个形象的独特之处在于,随着生活空间的拓展,人物内心的独立空间不断开阔,自我意识逐步增强,最终在获得独立生活空间的同时亦收获了完整的自我意识。
原本生活空间仅限于卧室厨房等狭小私人领域的玛丽,经历了痛苦的流产后,得到了丈夫的允许到墨尔本探望兄长约翰,顺便修养身体,调节心情。在墨尔本,玛丽结识了约翰的很多朋友,并有机会单独参加他们举办的一些社交聚会。因为当时正处于丧妻之痛中的约翰无暇陪同玛丽,而相对之前在巴拉腊特被限定的卧室厨房这一封闭狭小的私人领域,墨尔本的社交聚会场合是开放的公共领域。“开放的空间环境带来平等、狂欢的意义。”[10]夫权和兄权的暂时缺席也使玛丽有机会第一次真正体验这种平等。她写给丈夫的信中洋溢着对这种场合的享受和喜爱。在更广阔的新空间里,玛丽走出痛苦,获得了新生的机会。从墨尔本回到丈夫身边,她觉得自己“焕然一新,充满力量”,“这次回归对她来说是件大事”。[11]144因为这次生活空间的拓展让她获得了成长,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她内心的自我意识,她开始寻求改变,迈出了追求平等的第一步。
从墨尔本回来之后,玛丽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对事情的看法,甚至开始对丈夫的某些做法和决定提出质疑。但是自我意识尚未完全觉醒的玛丽在这个阶段发出的声音是微弱的。当看到丈夫在《圣经》上随意做批注时,虔诚的玛丽内心确信这种行为是罪恶的,不正确的。但是她鼓足了勇气,对丈夫做出的质疑依旧是微弱的:“她先是‘脸急的通红’然后‘握紧双手,鼓起勇气’,声音很低的问到:‘理查德,你认为那…那样…是…是…对的么?’”[11]145当丈夫告诉她回英国的决定时,“她放下手中的针线活,紧张的心砰砰跳:‘理查德,你有没有…我的意思是你曾经有没有想过…想过重新从事你以前的职业…我是说在这…重新在这开始?等一下。让我说完,我…我…哦…理查德—’不知道如何表达清楚她的想法,玛丽着急的紧紧扯着桌布,希望自己不要愚蠢的哭出来才是。站起身来,她轻轻跪在丈夫面前,手放在他的膝盖上:‘理查德,我希望你可以…我多么希望你可以(留下来)。’”[11]147墨尔本之行归来的玛丽不再像以前一样不假思索地答应丈夫的一切安排和要求,她已经开始试着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对丈夫的某些行为提出质疑。虽然自我意识初步觉醒的玛丽发出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是也起到了效果,为她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最终玛丽的意见被采纳,理查德决定留在澳大利亚,重操医业。他们搬离之前的住所,选址重新建造了新的房子。搬入新家后,理查德首先划定了自己的空间领域,并告诫玛丽没有允许不能私自进入。
但是此时的玛丽已经不能满足之前被划定的狭小私人领域,她的目光穿过卧室厨房投射到丈夫工作的诊疗室。“当家务活做完,孩子们也安顿好后,她(玛丽)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能够像以往一样,安静的做她的刺绣了……她不自觉的会用力的听一听有没有来看病的病人的脚步声或者敲门声……”玛丽甚至开始在头脑中颠覆之前所认同的性别观念,大胆的进行性别换位思考:“她会情不自禁的联想到如果自己是个男性,她对此会怎么做。她会在报纸上刊登她开始行医的消息。她会主动去和镇里的人们交往认识,让自己为人熟知。”[11]165思想上的越界促进了她行动上的改变。她开始主动结交朋友,扩大社交范围,逾越家庭/工作,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界限。在与格雷丁夫妇的交往过程中,使玛丽看到了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给女性造成的伤害和困扰,也学会了辩证地看待在父权制下所受的教育。格雷丁夫人最终因为无法忍受被丈夫控制压抑的悲惨生活与亨利发生了婚外情。而当玛丽得知这一情况时,她并没有立即给格雷丁夫人贴上罪恶的标签而是结合实际,进行了客观的思考和判断:“她从书中得知,这种事情确实时有发生,但是现实中似乎与书中非常的不同,甚至相差很远……因为书中出轨的女性都被当作坏女人,然而,现实中的格雷丁夫人确实不应该承受那么严厉的批评。”[11]183由此可见,玛丽的自我意识是随着她在公共领域中的历练一步步走向完善的,在历练的过程中她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摒弃陈旧错误的思想观念,确立新的正确的价值观。倘若永久蜗居在社会所设定的私人领域中,玛丽的成长成熟只能成为天方夜谭。
四 获得独立空间,自我意识完善
在《幸福的澳大利亚》的最后一部分,理查德股票赚钱,重新建了一所房子。搬往新住所后,玛丽拥有了一间可以容得下三个客人的房间。这个房间完全是由玛丽来支配的,是属于她的独立的空间。获得独立空间的玛丽此时也已经具备了完整的自我意识,对所遭受的不平待遇能够公然提出反抗。首先她向丈夫表示自己已经是个独立的成年人,拒绝丈夫仍然把自己当作小孩子看待。当丈夫反对她把名字由原来的波莉改为玛丽时,她反问到:“你不觉得波莉听起来太幼稚了么,我现在已经二十四岁了。”[11]238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耳特说过:“废弃名称和自我命名的行为是确立文化身份和申张自我的必要手段。[12]玛丽的自我命名行为标志着她在此时已经具备完整的自我意识,她要求丈夫把自己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平等相待。当丈夫因为朋友普尔迪对玛丽的冒犯而大发雷霆时,玛丽说到:“我必须说,理查德,在这整个事件中我认为你一点都没有考虑我的感受…事情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不是你,我觉得你至少应该表示一点关心。”[11]285玛丽已经可以义正言辞地要求丈夫考虑自己的感受。起初对丈夫提出质疑时,玛丽总是“脸急的通红”“握紧双手鼓足勇气”“声音低低地问到”,而此时的玛丽“语气中充满怀疑”“愤愤不平的问到”。她毫不避讳地对丈夫说:“我不像你想得那么愚蠢,我有自己的想法”。[11]286当理查德无视所有人的劝导,固执地决定要回英国时,玛丽同样大声地反抗丈夫的霸权:“你丝毫没有征询我的意见,理查德?”“这样太不公平。这里不只是你的家,也是我的家”[11]323在小说的最后,自我意识已然完善的玛丽要求平等的声音四处回响着,却未得到应有的回应。因为19世纪无论是英国还是澳大利亚,都是男性主导的世界。女性毫无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可言,男性总是充当发号施令的角色,而女性仅仅是命令的被动执行者。所以玛丽最终只能违背自己内心的意愿,抛开亲人朋友,离开她一直视为家园的澳大利亚。
《幸福的澳大利亚》发表于1917年,正值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中最著名的领导人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提出两性充分平等的要求,包括两性平等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而女性要获得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首先要具备的就是完整的自我意识,女性必须学会独立自主。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为女权辩护》一书中激情澎湃地说到:“我久已认为,独立乃是人生的最大幸福,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即使我生活在一片不毛之地,我也要减低我的需求以取得独立。”[13]而在理查森看来,女性要获得独立自我意识首先必须打破公/私领域的二分界限,走出将女性他者化的私人领域,勇敢步入公共领域,重新认识自我。理查森对此亦是身体力行。她选择写作作为她对抗这个男女不平等世界的武器,她的作品多表现女性特有的经历和经验、女性的疾苦和命运以及女性意识的觉醒。写作的成功更是她进入公共领域的标志。此外,她还于1916年亲自参加妇女权利运动,为女性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权利,进入公共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
[1]Krarner,Leonie.Introduction to The Fortunes of Richard Mahony[J].Australia Felix,London:Penguin Books,1977:1-3.
[2]Hurtley J A.The Fortunes of Polly Mahony-Henry Handel Richardson’s Woman in a Man’s World [J].Barcelona:University of Barcelona,1989:125 -137.
[3] Pratt,Catherine Cecilia.Gender Ideology and Narrative Form in the Novels of Henry Handel Richardson[J].New South Wales: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1994:14-15.
[4]Charles,Graeme.The Other Richardson Girl Ada Lillian(Lil)Richardson[J].Chicago:Lake View,2007:1 -7.
[5]朱新福,汪 卉.父权的解构:H·H·理查森短篇小说的女性解读[J].常熟高专学报,2004(3):72-75.
[6] Woolf,Virginial.Three Guineas[M].London:Hogarth Press,1966:6 -7.
[7]潘 建.公共/私人领域的纷争与和谐—记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的公共/私人空间[J].湖南大学学报,2006(1):110-114.
[8]Arendt,Hannah.The Human Condi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37 -38.
[9]周 颖.乡关何处是?谈<南与北>的家园意识[J].外国文学,2013(2):39-51.
[10]司文会.空间置换中的女性成长—<他们眼望上苍>中的成长主题的空间政治阐释[J].求索,2011(2):220-221.
[11] Richardson,Henry Handel.Australia Felix[M].Melbourne: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1960.
[12]Showalter,Elaine.Sister’s Choice: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M].Oxford:OxfordUP,1991:7.
[13] Wollstonecraft,Mary.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ith Strictures on Political andMoral Subjects[M].London:J Johnson,17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