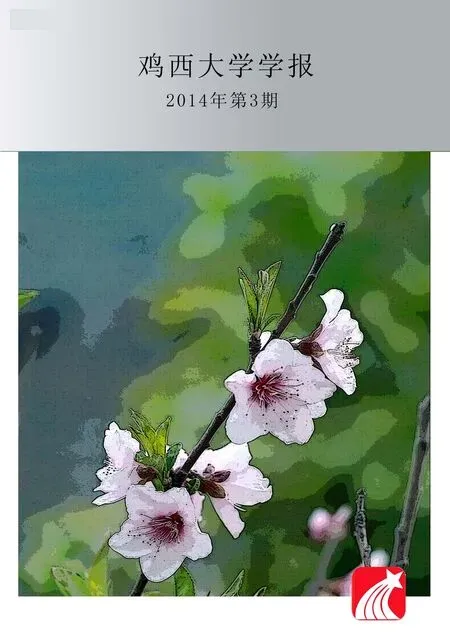全球化语境下文明与地方性文化的关系
——以电影《赛德克巴莱》为例
2014-03-31李伟长
李伟长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一 文明与文化的关系
要讨论这一关系,首先要在概念上弄清楚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化以及二者的关系。伊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对文明的概念有一个简单的表达:“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等等。”[1]
而后他指出“文明”一词在西方国家各民族中所指含义各不相同。“这个词在英、法两国和在德国的用法区别极大。如果说“文明”表现了殖民和扩张的倾向,那么“文化”则表现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文明”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有了某种程度的减少,因为它强调的是人类共同的东西,或者说,应该是共同的那些东西——至少对于那些已经“文明”了的人来说是这样。“文明”体现了某些民族的自我意识。对于这些民族来说,几百年来形成的民族界线和民族特性已无可置疑,因为这些东西早就通过他们的扩张和殖民完全确立了。”[2]
从埃利亚斯的论说中我们得出判断,文化是民族间差异性的东西,而文明表现的是普遍的同质化的东西;文化通过耳濡目染获得,而文明靠的是学习获得;文化是与传统有关的,具有稳定性,对于外来文化有抗拒性的,而文明表现出运动的扩张性。
但文明的内核仍是某些民族自我意识的体现,不过因为他们现阶段处于发达水平,先进于其他地方性文化,因而认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应成为其他文化学习的范式,这种对于文化间统治地位的争夺,恰构成了一个文化的场域。
根据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场域是为了争夺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领域,换言之,场域是争夺合法性的斗争领域。用布尔迪尔的话来说,即争夺实施“符号暴力”的垄断性权力的领域。场域是由在资本的数量与类型的基础上形成的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所组成的结构性空间。场域被看做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特定的要素(机构、组织、群体或个体)都是从其与别的要素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特点。”[3]在文化场域中,先进的西欧拥有更多的资本,处于统治者地位,称自己的文化为文明,落后的东方只有少量资本成为被统治者,其文化被界定为野蛮。但这种“高度配对”的结构性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稳定,被统治地位的文化为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就会抵制统治性文明的同化策略。“场域中的斗争使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相互对抗”。[4]
因此,文明对文化的同化,必定不会那么容易,同化中的碰撞在所难免。下面通过例证来具体看看这种关系。
二 现代性文明与地方性文化间的同化与冲突
电影《赛德克·巴莱》,是根据“雾社事件”改编而成,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后,日军侵入台湾。从此,日本对蕃族世代生活的地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文明开化,影片主要讲述了一曲当地原住民起而抗争最终悲壮失败的英雄史诗。电影的独特在于在一般意义的民族战争之上,赛德克族人更是为赢回他们的生命尊严、灵魂、生命价值和身份认同而战。影片正是写出了全球化时代一个明显的问题,现代性文明与地方性文化间的同化与碰撞,影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值得玩味的。
在《赛德克·巴莱》中,日本是作为一种文明存在的,他们有发达的科技:飞机、大炮、机关枪;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教育所、邮局、商店。在他们的权力话语之下,强力推销他们的文明,展现出普遍性的文明对于差异性的地方文化的强烈归化。赛德克族人被界定为一种野蛮的地方性文化与之对立。电影里面文明对于野蛮的界定在于其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上,即把赛德克族人视为最重要的猎场、出草(生活方式)和祖训(精神追求)视为野蛮落后。相比之下,原住民的存在,他们的贫穷成为先进文明的衬托。
在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以后,殖民者觊觎赛德克部落的森林、矿产,侵入原住民世代生活的领地,殖民者为了推行文明,建立起城镇,教育所、邮局、商店,与之相伴的是森林被砍伐,猎场被蚕食,猎物减少。赛德克人面临的是尘世家园与精神家园的双重危机,正如莫纳·鲁道所说“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的生活过得更好?反倒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多贫穷了!”赛德克族本有他们固有的骄傲,但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使他们失去了赋予他们的生存以意义的猎场,他们死后又要被祖灵遗弃,为了维护生存的权利,他们只有反抗。
正如莫那鲁道自己说的那样:“日本有军队,大炮和机关枪,飞机和大轮船。日本人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 反抗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地方性文化被同化吞噬于现代文明之中。然而在结尾的幻景中赛德克族人通过彩虹桥进入祖灵的猎场,实现了他们精神家园的复归,虽然这是更多象征意义的“大团圆”,但对于神话世界的展现是对这种地方性文化的留恋,纵观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一种强烈的张力跃然其间,正如花岗二郎纠结的肝肠,是趋向一体化、全球化的文明还是回归地方性、差异性的文化?影片对于这种冲突的表现是开放性的——文明和野蛮的角色互换。
运动会上日本人遭到杀戮后,日本军队进行了血腥报复,动用了各种武器,这时一向以文明教化野蛮的日本人完全是野蛮的。在这里,文明被用来制造杀人的先进武器,野蛮对于文明似乎是更根本的人性。就像电影里真实描述的那样,当日本人将先进的科技变成杀人的工具,美丽的家园成为焦土,族人被血腥宰杀,在遮天蔽日的炮弹下那个所谓的文明理想也化为齑粉随风消散了。当侵略者将满目疮痍的村落,称之为其文明同化的成果时,我们不仅要为之怀疑,这个文明化真的是普遍适用的美好理想吗?影片表现了对于现代性文明开放的反思姿态。影片结尾赛德克族人捐躯赴死,日本将领感慨久已失去的武士精神竟然在这蛮荒之地复活,这种精神正是现代文明所崇尚和缅怀的,在这里野蛮却又展现出了文明。这里我们感受到文明与野蛮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对立的,文明有它先进发达的优越性,地方性文化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存在价值。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文明和野蛮,每一种地方性文化都有其自身存在的意义,一种文化不能因为其先进性就自认具有普世意义,可以强制同化其他地方性文化。影片传递出的开放、多元共生的潜在意义对于全球一体化时代如何处理文化间统一与差异的关系具有不小的启发。
三 走向文化相对主义的“合唱”
文明代表着一种单一性的普遍方向和目的地,而地方性文化则是异质性多方向的,是走向单一还是多元共存是现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的话题。
从《文明的进程》中,我们看到文明其实是以近代以来西欧社会形成的先进成就以及一些核心观念,如民主、科学、自由、人权、博爱等等构成,其起源阶段也是众多地方性文化之一,是这些民族的自我意识体现。不过是因为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在全世界的扩张,从而取得了场域中的领导权,其文化也成了具有主导地位的文化,进而获得具有导向示范意义的文明地位,而其他文化则被界定为野蛮,处于被开化的地位。就像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表示的整个人类史的发展具有唯一正确的方向,他在书的代序中明确说到:“我阐述了一个热门话题,内容涉及到过去几百年中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在全球涌现的合法性,他为什么会战胜其他与之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近代的共产主义。不仅如此,我还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5]福山的终结观点有其特别的含义,“并不指一个个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而是指历史,指一种在所有时期在所有人的经历基础上被理解为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6]福山通过近代以来对主要政治经济制度各自发展进程的比较得出结论,西欧的民主文明政治,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是世界各个国家必将走向的目的地,世界历史潮流终将在这里汇合一处。这是一个宏大叙事的展现,西方文明的各种制度:经济、政治等,成为这个故事的唯一英雄。电影《赛德克·巴莱》里的日本正是西方文明的代表,演绎出一场普遍文明与地方性文化间的战争,差异性被同化为统一的伟大故事。
但是不要忘记文明具有的地方性文化内核,它不可避免遗传有产生这种文化的民族所携带的种种特征以及环境的特征。丹纳的《艺术哲学》通过大量的史实论证得出结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可见一种文明有产生它的特殊条件以及生存环境,被定义为唯一价值这本身就值得怀疑。伯克霍福在《超越伟大故事》中把这种宏大叙事称为伟大故事的讲述,通过捆绑历史事实,伟大故事成为一切历史(包括文本和话语事件的历史)的政治和伦理基础。后结构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通过拒绝观点与知识的普遍性,批判了传统历史叙述中的一致与全知立场,而主张性别、种族以及其他社会特征的多元化,从而实现“超越伟大故事”。就连福山也在《历史的终结》末尾表现出一种不确定性:当一群人被马车带到他们一心向往的那个城镇上,如果一些人发现周围的环境并不适合他们时,他们又将把目光投向新的、更远的征途。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环顾四周看到的正是他们事先预计的呢?对于这种普遍史的预测早有批判之声,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宗明义指出,“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7]“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8]
日本的文明侵入赛德克的野蛮后,赛德克族人变成了没有图腾的孩子,他们往日的骄傲不复存在了,带来的结局是花岗兄弟切开纠结的肝肠,更多的族人为了能通过彩虹桥进入祖灵慷慨赴死。西方文明也许不能被看成普世良药,而是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具有先进性的文化,其他地方性文化因为适应产生它的环境和民族,同样具有自身的价值。杰克·古迪在《偷窃历史》把这种现象称为“偷窃历史”,“指历史被西方接管,也就是说,历史被概念化,并已发生在偏狭的欧洲范围,通常是西欧范围內的事件加以呈现,继而,这种模式又被强加到世界其他地区。”古迪批判了西方历史著作中普遍盛行的欧洲中心论,亦即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进而批判了西方在创造“民主”“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爱情”等的过程中对其他文化成就的“偷窃”。古迪提倡一种新的比较的方法论,以进行跨文化分析。这种方法对评价不同的历史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据,取代了诸如“落后的东方”和“富有创造力的西方”那种简单的划分。
“是趋向一体化、全球化的文明还是回归地方性、差异性的文化”,这是目前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的一种伦理难题,也许选择权不在文明人和研究者那里,该把这个问题交给大山深处的人们。以一种“文化相对主义”视角来面对难题也许对我们会有一些启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怀着对种族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厌恶和对落后国家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建立了“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作为代表的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部落都有自己的逻辑、社会思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继博厄斯之后,许多文化人类学家都从文化和个性发展的角度阐发了文化相对主义观点。例如,露丝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各种文化同样都是有效的,现代文化和原始文化都是同样的实现人类潜力的方法,不能认为现代文化比原始文化更为先进高级,不同的文化并无优劣高低之分。而行为的是非标准也是相对的,被一种文化当作异常或病态的行为在另一特定文化体系内却具有特定价值。对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本性”,赫斯科维奇曾有一段精辟的描述:“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学术研究在面对全球化浪潮下地方性文化遭遇的命运时,其实该有着知识分子的伦理担当,对现代化过程中被撕碎的那些地方性文化应保持尊重,而不要加入指责地方性文化为“野蛮”的合唱中去。
全球化大趋势之下,文明与地方性文化的碰撞在所难免,关键在于我们应该破除自我中心论束缚,持有开放的心态,不同文化间展开平等对话兼收并蓄、借鉴彼此优秀成分,形成各种文化“复调的大合唱”也许是我们所希望的良性机制。
[1]伊利亚斯.文明的进程[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61.
[2]伊利亚斯.文明的进程[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63.
[3]斯沃茨.文化与权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42,143.
[4]斯沃茨.文化与权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44.
[5]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代序.
[6]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代序.
[7]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6.
[8]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