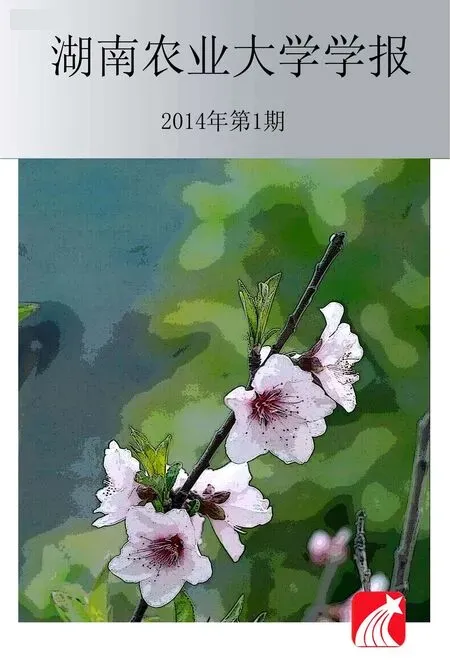中美农业科技合作:一个历史个案的经验与启示——基于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1925—1931)的考察
2014-03-31张瑞胜王思明
张瑞胜,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化的不断深入,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因生产效率低下逐渐衰落,而西方近代农业在科学理论和生产技术的装备下,迅速发展起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与西学东渐,西方近代农业科技便开始传入中国,开启了中国农业近代化进程。
中国近代与国外开展科技交流和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由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穆德于1988年组织发起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据统计,1888—
1918年,美国通过志愿运动派往国外的传教士共达8 000 多名,其中有2 500 左右派往中国,占总数的30%。他们包括司徒雷登、卜凯等。传教士在从事传教活动的同时也传播了一定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同时,许多开明的爱国人士也开始主动吸收和传播西方的先进农学技术与知识,但初期工作主要限于图书文献的译介和农业知识的传播。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便是罗振玉创办的《农学报》。《农学报》和后期的《农学丛书》、《申报》等的文章大多是来自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农书报刊的译文,大致反映了当时的各国农业科技水平。
中美两国之间农业科技交流占据十分重要地位。早期交流以教会传教士、商人和爱国士大夫等的民间交流为主,后期逐渐成立较为正式且有组织的交流合作项目,以研究机构、农业院校以及两国政府为主导。合作项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金陵大学、康奈尔大学及纽约洛氏教育基金世界教育会三方订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The Cornell-Nanking Story)。这个项目作为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示范性效果,洛夫和芮思娄对此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这次合作是最早的国际技术援助的模范”,并由此引出了中美两国政府、机构、学校的一系列农业科技合作,包括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农林部与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合作,两国联合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等。
对于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当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虽多有涉及却不尽完善。在计划结束后,美国康奈尔大学马雅思教授回国后不久就撰写了总结报告,详述合作的经过与成就。随后1964年康奈尔大农学院洛夫教授和原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思娄教授合著了《康奈尔大学与金陵大学作物改良合作计划》,也对这一合作项目进行了总结。这些文献为深入挖掘该项目的内容提供了美方视角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其所处立场不同,观点多有局限与片面。国内关于该计划的研究可分为三类。其一,国内当时参与计划的中方人员撰写的回忆录性质的书籍及论文,如著名育种专家沈宗瀚教授在台湾发表的多部作品,包括《沈宗瀚晚年文录》、《中华农业史论集》、《沈宗瀚自述》,曾任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的章之汶教授的论文《三十年来之金陵大学农学院》。其作为第一手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毋庸置疑,为后世研究提供了诸多线索素材,然而其对该计划的描述皆过于简略。其二,近年来集大成的农业科技史著作,如《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史》等。但由于其自身书籍类型的特点,对此项目描述也是一笔带过。其三,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重要,许多学者开始对中美近代农业科技交流领域加大研究力度,其中主要论著有王思明的《中美农业发展比较研究》、《中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等,曹幸穗的《我国近代农业科技的引进》以及沈志忠的《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这类研究文献很有参考价值,但受制于各方面因素,并没有对该计划进行细致、独立、翔实的个案研究。笔者试图结合前人资料,详细剖析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合作机制、效果、经验,以为当今国际农业科技交流合作提供借鉴。
一、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及其效果
1919年,华北大旱,受灾面积巨大,灾民人数激增,美国各界纷纷捐款赈灾。1922年,金陵大学农林科长芮思娄教授得知美国赈灾捐款尚余百万美元,便赴美请求委员会将余款用于华北农林改良事宜。芮思娄教授是世界著名的作物育种专家、康奈尔大学洛夫教授的学生,遂与之商议粮食作物改良合作事宜。1925年,芮思娄教授聘请洛夫教授担任金陵大学特约教授,随后金陵大学与康奈尔大学及纽约洛氏教育基金世界教育会三方订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
作物改良合作计划是中国官方机构第一次有组织有体系有规模的对外交流科技合作。它通过合适的方法组织并执行一项综合的作物改良计划,包括中国东部、中部、北部饥荒地区的主食作物如小麦、大麦、水稻等品种,并及时将优良品种进行推广。在中美两国改良人员的齐心努力下,培育出了一批高产的水稻、小麦、大豆、高粱、棉花、大麦等优良作物品种,并向农民分发。在当时粮食恐慌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作物改良合作计划以科学方法改良品种增进民食,颇著成效。[1]4
金陵大学稻作育种发韧于1924年,最初仅有品种比较试验,以后亦采用洛夫教授的穗行纯系育种法并育成改良水稻新品种“金大1386 号”。在南京实施的对水稻的选育工作成果突出。培育出的多个品种比农家优良品种产量高出14.6%至29.6%。改良水稻品种有“金大909 号”、“金大946 号”及“金大1386 号”,特别是“金大1386号”水稻平均亩产达300 斤左右,超出团稻白每亩107.4 斤。①
在小麦品种培育方面,1925年沈宗翰选取单穗小麦开展选育良种工作,1934年育成纯系新品种“金大2905 号”。通过与“金大26 号”的产量进行对比,“金大2905 号”小麦五年间的平均产量是30 蒲式耳每英亩,超过“金大26 号”平均6蒲式耳每英亩,约25%。[2]29鉴于“金大26 号”已经比普通农家品种高产7%,所以在同等的生长条件下,金大“小麦2905 号”比普通品种高产32%。同时该品种抗倒伏,成熟早,具有很强的抗锈病性,在长江流域获得大面积推广。在计划结束后也一直是作为当时中国粮食作物中推广面积最大的一个品种。在开封,农业合作推广站也培育出了高质量的新品种“金大开封124 号”。该品种比其对比品种的产量高出12.4%。在南宿州,农业合作推广站培育出了新品种“南宿州 61号”。通过将该品种与从美国进口并且在南宿州地区生长良好的品种“南宿州6 号”进行长达七年的对比,发现其产量比“南宿州6 号”增加了11.75%。并且经过三年的对比发现其产量较普通农家品种平均高出27.83%。
南京试验站的大豆选种工作始于1924年,当时金陵大学的育种人员王绥对比金陵大学试验田和附近农田里的不同品种大豆后,发现“金大大豆332 号”的品种统计数据非常抢眼。随后五年的测试数据表明,平均产量比对比品种高出5.46蒲式耳/英亩,平均增产达44.68%。[2]29而在“金大大豆332 号”与普通农家的两个品种的对比中,结果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增产83.1%和90.9%。
对高粱的选育工作主要是在南宿州农业合作站实施的。魏庚教授和时任金大农艺系主任的郝钦铭教授亲自赴绥远、济南、保定等地调研本地高粱与外国品种的特性。经过四年的测试发现,在同样的试验田内,这些新品种产量比普通农家品种的增幅在28%至48%之间。其中有两个优良品种产量增幅达到了47%至48%。
棉花的改良工作是郭仁风从中国棉花品种的选育开始的。他选育了大量的棉花品种,从产量和棉绒质量这两个方面来说,其中“百万华棉”品种远超其他品种。经过试纺试验鉴定“百万华棉”的质量等同于美国棉花。该品种被当时的棉农广泛接受,并视其是他们所世代种植品种的完美改良。随后,棉的培育工作被纳入到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范畴内,棉的品种试验开始在中国北方进行。经数年改良与试验结果,一些棉花品种在试验中成果突出。“脱字棉”宜于黄河流域,“斯字4 号棉”在北京地区和河北地区种植更为普遍,“爱字棉”宜于长江流域,“百万华棉”宜于江浙沿海一带,纱厂购买以上三种棉花,出价较普通棉多五六元,可见其品质之佳。[3]
4)根据煤矿安全知识规则体系,建立煤矿安全评估和推理的专家知识库,涵盖法律法规、行业规程规范、条例、手册、办法等,如煤矿安全规程、各工种操作规程、煤矿灾害防治与应急预案、重大危险源辨识标准、“三违行为”辨识标准、隐患界定标准、事故案例库等。
大麦的选育工作虽不是该计划的重点作物品种,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其选育工作主要在南京、南宿州、开封三个试验场开展。在南京试验场大麦的选育工作并不顺利。从1925 到1928年间,金陵大学的王绥试验了多个品种的大麦,包括来自得克萨斯和威斯康辛的美国大麦品种,但并没有发现其对比农家品种有足够优势。然而在大麦的育种过程中,王绥却深入进行了基因研究,特别是对麦芒性状的观测。虽然王绥最终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大麦品种,但他发现了当时欧美发达国家都未知的新麦芒,可以说是作物改良计划的另一种贡献。开封农业合作推广站试验人员则培育出了一个大麦新品种“开封313 号”。当年试验发现该品种比其对比品种平均产量高出7.27%,比普通农家品种产量高出21.28%。而随后到1938年经过数年的改良,该品种的产量达到了133 斤/谷堆,实际上超过对照品种44.9%,超过普通农家品种82.7%,远远超出了众人的预期。①
除了培育出优良品种外,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另一重要目标是对良种进行推广,使农民在不明显改变耕作方式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产量。事实上,除非良种被种植者接受并且保持其纯正,否则在培育良种阶段所做努力都是白费。这是整个计划中最困难的一部分,而在作物改良合作计划中都得以实现。随着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扩展,该良种繁育以及分配的计划也随之推进,甚至是在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棉花、小麦、玉米良种继续在不断通过各地农业试验场推广站大量向农民分发,很多农民从良种计划中受益。[1]2-3
二、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主要经验
在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开始之前,国人也对西方的一些农书进行了译介,并创办了一系列的农事试验场、农务学堂、农学会以及农业公司,但总体来说这一系列的中外科技交流都是民间的、零散的引进传播。翻译的农书多数不适合中国国情,聘请的外国教师授课也是生搬硬套不了解实际情况,对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作用不大。作物改良合作计划之所以能顺利实施并且成效卓著,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成功经验。
1.有良好的前期合作基础和运行机制保障
当时,金陵大学是在华注册的第一所美国教会捐款设立的大学,同时又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并获得国际认可,因而金陵大学农学院在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中自然处于国内大学中的优先地位。而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也是久负盛名。早在辛亥革命后,金邦正、秉志、邹树文、邹秉文、过探先、谢家声、钱天鹤、凌道扬、穆藕初等人先后自康奈尔大学农科学成回国。[4]这些农林科教事业的先行者无疑确定了康奈尔大学在当时国内农业科技领域的绝对影响力。金陵大学早在创立之初即与康奈尔大学结为姊妹大学并被康奈尔大学认可其颁发的学位。金陵大学农学院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合作交流的渊源始于1914年芮思娄教授自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毕业来到金陵大学教授农业课程。1916年前任金陵大学农科科长裴义礼辞职返美,芮氏继任为科长。在其任职期间,他聘请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邹树文、邹秉文、谢家声等人来校任教,努力打造一个研究中国农业与训练中国学生的农学院。[5]1281920年美籍棉作物专家郭仁风应邀来到金陵大学任棉作物改良部主任,后于1924年任金陵大学农业推广部主任。1921年康奈尔大学农科毕业的农业经济学家卜凯教授任职金陵大学农经系主任。这一系列前期的两校人员间的频繁流动为两校正式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合作方还建立了相关机制确保合作计划能有效运行。合作计划约定从1925 至1931年间,每年4月至9月从康奈尔大学的作物育种系选派一位教授来南京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实施作物育种改良,金陵大学负责提供研究设备和试验场,由世界教育会津贴康奈尔大学教授旅费。一方面康奈尔大学教授可以因地制宜切实地指导合作,另一方面在他回到康奈尔大学以后,也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和下一任访问教授讨论研究这个计划。合作期间,除因政治和战争因素1927年被部分打断、1928年全年暂停外,其它年份均有康奈尔大学教授来华进行指导。其中洛夫、马雅思、魏庚三位教授分别来华两次,在小粒谷类作物、生物统计学、天然授粉谷物、饲料谷物、蔬菜等领域进行了相关指导。作物品种改良是当时金陵大学农学院的中心工作,其经费由美国捐助华北赈灾余款内支付,每年约四万银元,为金陵大学最大的研究经费,以改良品种增加华北小麦、大麦、高粱、小米、黄豆、水稻等粮食产量,而以小麦高粱为主。[5]137
2.西方先进科技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结合
在作物改良合作计划中,康奈尔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为中方传授先进科技理论,并注意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1925年4月洛夫教授来华后,他提出了标准化的作物改良方法并准备了两份详细的备忘录交予各试验站(场)。一是对于选种测试的通用建议,二是秆行法。这些具体指导意见被译成中文并被广泛采纳。这是在中国作物改良工作中首次采用标准化的方法。洛夫教授还十分重视育种方法的科学化,认为以中国重要农作物而论,在同一范围内,如能科学运用改良方法,以谋品种之改进,则其产量品质必大有进步。[6]392洛夫教授提出的穗行纯系育种法为:单株选择(第一年)—单行试验(第二年)—二行试验(第三年)—五行试验(第四年)—十行试验(第五年)—高级试验(第六年)—繁殖推广(第七年)。这种方法在国内各地试验场获得显著成效,由此得到广泛应用并推广。[7]47这在当时中国粗放的农业科技领域无疑是新的起点。魏庚教授强调在育种过程中,作物分类学对于作物改良计划的系统性有重要意义。美国、英国、德国、荷兰等西方发达国家曾因未有作物品种分类而常常一种作物有数种名称或数品种冒用同一名称的现象,使得作物育种的科研和推广深受其害。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作物栽培历史悠久,分布尤广,加之从来无人整理分类,因此进行作物分类研究并予以应用尤为重要。[8]魏庚教授等人在金陵大学开设了作物分类学等课程,为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系统开展提供了全面的理论支持。
在康奈尔大学教授的指导下,各个试验站测试的农作物总量大幅增加,品种丰富,测试方法也逐渐专业化。在1927 至1928年间,只有8 个试验站总计试验46 229 株作物。而1929年到1930年间,试验站数量从8 个增加到13 个,总计测试作物数量也增加到96 799 株,达到前者的两倍之多。①而测试的农作物品种包括小麦、水稻、大豆、大麦、玉米、棉花、高粱、粟,共计八大类。测试作物的方法包括秆行试验、穗行试验、遗传研究等,足以体现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快速推进。
3.多途径开展农业科技人员培训
事实证明人员培训是作物改良合作计划成功的重要经验。在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还没有访华前,计划就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接受良好训练并且能够独立工作的专业人员在康奈尔大学的代表们离开后来继续这个计划,那培育良种便没有任何意义。”[2]40作物改良计划训练了一大批中国本土的农业科技人员,教会他们该计划的原理、方法、应用以及组织,使其在该计划正式结束后能够继续独立进行科研调查。
在合作计划开始后,金陵大学农林科早期师生包括沈宗瀚、王绥、郝钦铭、沈寿铨、常得仁等就参与了作物合作项目并赴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进修。回到金陵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后,他们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与康奈尔大学教授们的联系沟通,出国再深造,继续攻读相关农业领域的研究生以接受系统的农业科技知识。这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沈宗翰教授。沈宗翰当年硕士毕业于佐治亚大学并在1924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植物育种与遗传学的博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教授来华以后,他们发现迫切需要中国留学生回来帮助他们开展在华的工作,通过向世界教育会申请,同意资助沈宗翰来回的差旅费,于是沈宗翰在康奈尔大学读博期间便加入合作计划并跟随马雅思教授来华从事选种工作。沈宗翰教授1927年从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即回到金陵大学农学院教书并继续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其突出成就即为改良“金大2905 号”小麦,自民国十四年选穗到民国二十二年决定推广,历经八年时间。[5]140沈宗翰教授在南京太平门外金陵大学农场经过八年科学选种、田间试验,并在南京、南宿州等试验场试验了537 个外国小麦品种与之进行比较,终于在1933年夏决定“金大2905 号”小麦为推广品种。这是当时中国以纯系选种方法育成的最优越的第一个新品种。马雅思教授在计划结束后编写的最终报告中曾这样描述:“如果没有沈先生的帮助,这项计划是不完整的。他对中国的知识以及与教育领导人的熟识使我们的工作更顺利的开展。”[11]13
另外,选拔各地优秀农业教师及试验场工作人员参与一系列暑期研讨班培训也确保了计划的顺利实施。洛夫教授对人员的选拔十分重视,要求第一须有服务心,第二须对农业发生兴趣,第三须富有农业经验,及略知当地作物生长习性及栽培方法等等。[12]而严格的选拔之下,每次由各地前来参加作物改良讨论会的会员竟有九十余位之多,可见当时大家对农业研究的热忱与重视。计划期间一共举行了四次暑期研讨班,每次持续约三周,开展学院内正式学术演讲、试验田观测、非正式学术讨论和会议等各类形式的活动。主要涉及作物育种、遗传学、植物病理学等领域。研讨班共计包括五门课程:洛夫第一次来华时开设的试验方法论课程;沈宗瀚教授的初级作物育种课程;植物病理学部教授的植物疾病课程;马雅思教授的高级作物育种课程;洛夫第二次来华时教授的生物统计学课程。马雅思教授在1931年谈及研讨班的目的是“谋增进工作之效率,规定试验方法,交换试验材料,及增进各人研究之兴趣。”[13]他还概述了良种繁育以及分配的计划。他认为同一时间将大量的新品种投入繁育和分配既不可行也没有必要。他建议与其把少量的良种分配到广大的地区,还不如在一开始时就选定特定地区,选定那些有与良种计划合作愿望的地区。如果良种充足,就把大量的良种分配给当地农民。然后在种植结果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计划就可以扩展到最先分配地周围的一定范围内继续推广,直至几乎整个地区都种植新品种作物。通过研讨班的学习,一方面给予那些未有任何专业科学训练的中国同事们提供遗传学、植物育种等相关科目的强化课程,帮助他们补充学术理论知识以指导实际作物改良工作;另一方面把合作试验站的同事们聚集到一起讨论各个试验站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原因并给出解决措施。据统计,康奈尔大学与金陵大学正式合作接近尾声时,超过125 人从原先没有任何经验到训练成为能够独立完成作物改良试验的专业人员。[11]42通过计划中正式和非正式的训练,金陵大学农学院的专业作物育种人员和师资队伍在当时的中国遥遥领先。
在康奈尔大学教授们完成了在中国的任务以后,作物改良的工作仍然继续扩展。对农业科技人员的训练确保了作物改良计划的系统性延续。计划正式结束七年后,在中国一直遭受战乱的同时,作物改良工作却仍然在前所未有地扩大规模。总计改良培育出了小麦、棉花、水稻、大豆、高粱、大麦、玉米等35 种作物品种,其中25种已经分发配给农民,甚至有些已经种植了相当大的面积。如果没有大量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育种人员后续实地培育推广,这样的成绩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影响与启示
计划对双方后续工作有深远的影响。在后来的回忆录当中,康奈尔大学教授一致认为他们在中国的工作也拓宽了他们自身的技术和经验。前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院长梅尔斯教授曾在信中称赞道:“金陵大学与康奈尔大学的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成功是我们后来在洛斯巴尼奥斯与菲律宾大学农学院开展更为综合的类似合作计划的重要原因。我深信这个计划对于加强菲律宾的农业和经济是十分有益的,同样对于它对康奈尔大学、对农学院的利益,我也是一样自信。”[2]47同时,康奈尔大学教授们在农业教育、管理、科研等方面的先进方法对金陵大学其他院系也有积极的附带影响。中美合作进行作物改良引起了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大大刺激了官方在作物育种领域的工作投入。随着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推动,不仅金陵大学作物改良工作持续推广并日益正规化,还有包括中央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等一批院校的作物改良工作迅速扩张展开。同时民国政府在1931年计划结束后设立中央农业试验所,通过科学研究和农业推广服务继续提高农作物产量。而后来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也一度邀请洛夫教授作为顾问负责作物改良事宜。在抗日战争期间,南京的试验站和一些合作站仍继续生产良种供应本地的分配。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农林部与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合作、两国联合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等一系列官方组织的中美农业科技交流活动相继开展,有力促进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对当代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和中国农业推广工作亦有重要启示。在当时,“技术援助”这样的官方模式还并未出现,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至少包括:有良好的出发点并且可以达成互惠共赢的动态平衡;依据最迫切的国家需求建立一项可行的计划,并且技术知识转移地主国;贮备训练有素的本国人员,在外国专家撤离后,确保工作继续推进。这样看来用“技术援助”来形容这个计划是合适的。中美双方教授共同参与进行作物改良合作,付出很少的经费(大部分经费由纽约洛氏教育基金提供)却拥有这样丰富的成果,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创造了中外科技合作的典范。通过聘请外国专家学者来华、有针对性地公派留学生等方式将先进科技带进国门,从而引进近代先进的农业育种科技。更值得一提的是改良合作计划制定了一系列作物改良科技管理的政策体系。现代大多数科技交流引进多限于引进人才、品种、先进科技等,皆属于生产力范畴,但当今国内更缺乏的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要提高科技水平,必须实现科学技术引进和政策管理体制创新双管齐下,两者都不能偏废。
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在中国首次系统性地运用近代科学体系改造农业,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从事良种选育和对新的耕作方式试验研究,然后择优向农民推广,初步形成了近代中国教育、科研试验、推广结合的农业推广体系。在康奈尔大学教授的指导下,金陵大学和各地农业试验站效仿美国特别是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教学、科研、推广相辅相成的经验,金陵大学提供选育新种、试验方法、繁殖新种、人员培训,试验站负责品种具体试验及数据采集及部分作物的推广工作,在选育作物品种过程中训练专业育种人员。各中心试验场欲将优良结果推广于农民,必须推广人员作示范工作,及指导农民解决问题,推广范围可以县为单位,较小之县可以二三合并,推广人员在各县工作,必须与中心试验场时常联络,以便及时对优良品种进行推广。[6]394在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引导和启迪下,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近代中国农业推广体系初具雏形。
1925—1931年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不仅增强了中国经济实力,提高了粮食作物产量,改善了人民生活,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农业科技人才,同时也为后来中美两国一系列农业科技合作奠定了基础。合作计划也成为二战后杜鲁门总统开创的“技术援助项目”的蓝本,在1949年的就职演说中,他概述的“第四点计划”高度评价该合作是“一项能够援助贫困地区的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的项目”。[15]
注 释:
① 数据来自The Cornell-Nanking Story。
② 参与合作计划的13 个农业试验场包括:安徽省立农业试验站(安庆)、华中师范学院(武昌)、中央大学农学院(南京)、杰斐逊学院(唐山)、开封浸会学校(开封)、江苏省立第二农事试验场(徐州府)、南宿州长老会农事部(南宿州)、山西铭贤学校农事部(太谷)、山东农工学校(峄县)、圣保罗加拿大教会医院(归德,现名商丘)、沧州伦敦教会试验场(沧州)、潍县美国长老会宝业中学农事部(潍坊)、燕京大学农业试验站(北平)。
[1]沈宗翰.改良品种以增进中国之粮食[N].中华农学会报,1931(90):2-4.
[2]Harry H Love,John Henry Reisner.The Cornell-Nanking Story[M].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1964:5-47.
[3]沈宗翰.借用美棉兴推广改良棉种[N].农林新报,1931(285):280.
[4]沈志忠.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45.
[5]沈宗翰.中年自述[M].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56:128-140.
[6]洛夫.科学对于农业之重要续[N].农林新报,1931(255):391-394.
[7]白鹤文.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6-47.
[8]张家蔚.1930年双十节魏根博士演讲作物分类之要旨[N].农林新报,1931(233):70-71.
[9]洛夫.美麦作种问题[N].农林新报,1931(257):419.
[10]魏庚,沈宗翰.华北农业视察报告[N].农林新报,1931(229):2-5.
[11] C H Myers.Final Report of the Plant Improvement Project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Cornell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M]. University of Nanking,1934:13-42.
[12]洛夫.农业研究典示范[N].中华农学会报,1931(89):1-4.
[13]戴松恩.马雅思博士之演讲词[N].农林新报,1931(252):349-350.
[14]Linda McCandless.INTERNATIONAL PROGRAMS AT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N].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 at Cornell University,Winter 2004–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