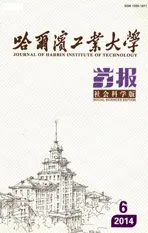罗马法中的贸易——以介于传统与变革中的要物消费借贷契约为例①
2014-03-31安东尼奥萨科乔
安东尼奥·萨科乔
(布雷西亚大学 法学院,意大利 布雷西亚25121)
翟远见 译
(中国政法大学 比较法学研究院,北京100088)
概 论
“消费借贷没有历史”[1],这是生活在十九、二十世纪的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西尔维奥·佩罗齐(Silvio Perozzi,1857-1931)的名言。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借贷活动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至古罗马建城之前。无独有偶,几乎同一时期的另外一位意 大利法 学家 卡 洛· 隆哥(Carlo Longo,1869-1938)也曾认为:“主要是罗马契约法体系的一般演进使我们相信消费借贷有其历史。”[2]
通过上述论断,19世纪的意大利罗马法学界力图说明,尽管事实上我们对该制度的古代阶段所知甚少,但是消费借贷对于任何共同体而言都至关重要。社会组织的历史有多悠久,该制度的历史就有多悠久。古罗马亦不例外的是,对于一个农牧社会来说,例如公元前七八世纪的古罗马,种子或者食物,甚至是小额金钱的转借,当是社会经济整体运转的枢纽,虽然在这一点上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痕迹。②V.Giuffré,Istituzioni di diritto romano.Corso,Napoli,2001,190:在古罗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消费借贷是最重要的交易形式。
古代罗马的经济主要以农耕和畜牧为基础,因此,也就经常发生以救助为目的的债权债务。若某人之犁锄损坏,或者其农作物收成欠佳,就需要向邻人求助;这些邻人会借给运气欠佳之人金钱、小麦或者酒油等必需品,以帮助他度过难关。
这是一种罗马法学将之界定为所谓的“非要式消费借贷”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消耗物的借贷,受领人(accipiens)取得交付给他的物的所有权,同时他负有在约定期限届满时返还“相同种类和 品 质 的 物”(tantundemeiusdemgeneriset qualitatis)的债务。
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已对消费借贷给出定义。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几乎全文照搬了盖尤斯的上述著作。有必要引述后书中的一段文字:“消费借贷之债以重量、数量或者尺寸计量的物为标的物,比如酒、油、小麦、钱币、铜、银或者金。这些物,通过丈量或者称量,我们给出它们的目的是使它们成为受领人的;而之后,受领人归还的不是原物,而是同一性质和同等品质的物。”(I.3,14pr.)
古罗马法学家认为,这类契约的基础是“信义”(fides)(即相信借用人会归还给我所借给他的全部东西)、“信任”(fiducia)和“友谊”(amicitia)的等价值。在公元2世纪,法学家杰尔苏在对规定了消费借贷、题为“Rescreditae”(相信会归还给我们的物)的裁判官告示的标题做说明时,他这样写道:“那么,由于裁判官在该标题之下规定了对与不同契约相关的多种权利的保护,故而,他将标题命名为‘人们相信会归还给我们的物’。的确,它囊括了所有我们基于对他人的信任而订立的契约。正如杰尔苏在其《问题集》第1卷中所言,‘相信某物会归还给我们’的表达具有一般意义。”(Ulp.26ad ed.D.12,1,1,1)
如此一来,便诞生了要物消费借贷。在要物消费借贷中,“给”(datio),即交付将被受领人使用、未来受领人以同量归还的替代物,是该契约成立的要素;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就像有些学者(如塞劳)所认为的那样,最初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了整个契约。
这一点古罗马法学家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对“mutuum”(消费借贷)一词所做的——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是错误的——词源学考察(消费借贷“mutuum”,正如拉丁语博学之士瓦罗所言,实际上来源于希腊单词“moiton”。该词表达了“变动”的思想,即金钱由一个人移转到了另一个人那里),很好地阐明了“给”这个要素的中心地位。例如,I.3,13,pr.:“故而称之为消费借贷,因为某物被我给了你,目的是使它由‘我的’变成‘你的’。”
此外,“消费借贷”这个称谓本身在罗马法原始文献中并不常见,常见的是“以消费借贷为目的的给付”(mutuidatio)。这恰恰是为了凸显要素“给”在此类契约中的中心地位。
最初,消费借贷被古罗马人放在了外延更广的概念“实物缔结的债”(recontrahere)之下。后一个概念的含义是,债乃由于债权人基于信任交给债务人的“物”(res)而生,同时该物也构成了所生之债的法律基础,且为债之量度,也就是说,债本身不能超出所交付的物的总量或者价值:债务人应当归还所交给他的那个物,或者与之相当的物,不多也不少。正因为如此,在《学说汇纂》第12卷的第1章中,像消费借贷、使用借贷、甚至非债清偿等这些事实或者关系才被共置一处。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给”这个要素,而绝非其理论架构。①对这一点的详细论述,参见我和我导师桑德罗·斯奇巴尼(Sandro Schipani)教授合写的《学说汇纂》第十二卷中译本的“序言”(《学说汇纂(第十二卷):请求返还之诉》=Digesta[liber 12:De condictionibus],北京,2012年版)。
因为正如上文所言,在古罗马的消费借贷制度中,“给”这个行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契约之全部,所以古罗马人不认为返还之物可以多于受领之物。②Ulp.26 ad ed.D.12,1,11,1:“普罗库勒正确地认为,如果我借给你了10(币),只要求你之后还我9(币),根据法律,你偿还的金钱不必超过9(币)。但是,如果我借给你了10(币),目的是使你还给我11(币),普罗库勒认为不能提起请求返还之诉以主张超出10(币)的那一部分。”这样一来,利息(当然,这里指的是所谓的“合意利息”或者说“作为报酬的利息”)就必须由另外一个专门的契约即所谓的“利息要式口约”(stipulatiousurarum)来规定。③单单一个简约是不够的。cfr.比如,P.S.2,14,1:“如果只是就利息的给付订立了一个裸体简约,那么该简约没有任何价值。”(“裸体简约”又译作“无形式简约”。——译者)
只是到了后来,由于自夏沃拉(Quinto Mucio Scevola,公元前1世纪)开始逐渐成熟的“实证法”上的契约概念,④主要参见Pomp.,4 ad Q.Muc.D.46,3,80.才发展出近代法学所熟知的理论,即认为在消费借贷中存在交付和合意两个要素。这是今天非常主流的观点,但是这很可能与消费借贷最初的混沌状态并不相符。
一、从起源到公元前3世纪
最初,很有可能通过对人誓金之诉(actio sacramentiinpersonam),来 惩罚不履行 债 务 的消费借贷借用人。后来,通过与该诉讼同样历史悠久的通知给 付 法 律 诉讼(legisactiopercondictionem),只要求返还曾经给出的物。后一诉讼,作为程式诉讼的请求返还之诉(condictio)的原型,是适用范围很广的严法诉讼的一种。①因此,完全可以说,主要是缘于技术程序原因(而非伦理道德原因)。消费借贷对于古罗马人而言,自诞生之始便基本上为无偿契约:在这一点上,继J.Michel,Gratuitéen droit romain.Études d’histoire et d’ethnologie juridique,Bruxelles,1963,303ss.之后,主要vd.C.A.Maschi,La gratuitàdel mutuo classico,in Studi in onore di Balladore Pallieri I,Milano,1978,pp.289ss.;关于罗马法中请求返还之诉(condictio)的起源及演进历史,参见拙著A.Saccoccio,Si certum petetur.Dallacondictio deiveteres allecondictiones giustinianee,Milano,2002.
除了最初的“友情”消费借贷外,很快就发展出另外一种借贷形式,因为朋友或者相识之人的圈子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借贷的需求,请求借贷之人必须向那些高于自己所属阶层的其他阶层的人求助,于是,消费借贷开始采用、或者至少借助“债务口约”(nexum)和“誓约”(sponsio)两种形式。毫无疑问,后者是一种“异质担保行为”。
关于“债务口约”,因为保存下来的原始文献非常有限,迄今为止我们对之还所知甚少。根据掌握的一点信息,我们知道,消费借贷的借用人,在金钱(这里指的是未铸造的铜块aesrude)被给付之时,要通过一个庄严的称铜式行为(peraes etlibram),将他自己交给贷与人,或者使自己处于后者的支配(potestas)之下,后者会让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劳作,直至债务完全被清偿。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主要来自李维的)历史资料,这些“债务人”(nexi)的处境极为悲惨,对于他们而言,返还所借金钱日益困难,于是,起义和暴动便不断发生。终于,在公元前326年(迄今确定的最有可能的年份),随着《博埃得利亚和帕皮里亚法》(lexPoetelia Papiria)的颁布,“债务口约”制度被废止。
在这个时期,人们所采用的另外一种借贷形式是“誓约”。在早期,誓约发挥着异质担保的功能:贷与人提供消费借贷,会要求有第三人的担保;第三人根据一个形式庄重的“誓约”,在债务人于约定期限内没有将受领的金钱归还的情况下,承担相应的责任。
大体而言,在古代晚期,多数以消费为目的的消费借贷,其形式有三种:要么是同一个社会阶层成员间金钱的简单给付;如果贷与人属于统治阶级(比如说贵族),而消费借贷的借用人所属的阶层等级较低,那么,后者要么通过“债务口约”使己身被押,要么找到一个提供要式“誓约”的担保人。
在消费借贷契约的历史中,真正意义的转折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通过前两次布匿战争(分别发生在公元前265—241年和公元前218—202年),战胜了迦太基,事实上取得了对几乎整个地中海的霸权。之前以农耕和畜牧为主的这座城邦,其商业贸易非常有限,而现在开始繁荣起来了。海上贸易逐渐兴盛,商品交换日趋频繁,奴隶经济得以推广,商业企业层出不穷,商业资本与日俱增。先前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现在被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之上的“庄园”(villa)所取代。庄园的生产具有工业性质,其产品主要面向市场。
消费借贷,被认为是“万民法”(iuris gentium)上的契约;作为这样的契约,它对异邦人(peregrini)也是开放的;在这个新的社会经济现实中,它是人们使用较多的一种契约。这一点,比如,在普拉图斯的戏剧中也有明确的反映。②在(公元前3世纪)普拉图斯的戏剧中,经常提到消费借贷契约。从这位剧作家常常描绘的奴隶或者自由人四处借钱无果的情景,我们可以想象在古罗马共和国中期,这种契约曾被广泛运用。对普拉图斯戏剧的罗马法研究,参见E.Costa,Il diritto privato romano nelle commedie di Plauto,Torino,1890(rist.Roma,1968);最近的研究,参见P.Leitner,Die plautinischen Komödien als Quellen des römischen Rechts,in Diritto e teatro in Grecia e a Roma,a cura di E.Cantarella e L.Gagliardi,Milano,2007,pp.69ss.
不过,在这个新的社会背景中,尽管借贷行为仍然以“信义”为中心来运转,但是此时物的返还要被其他形式要件所证实。这些要件以更加明晰的方式保证贷与人可以要回借出的物。
在这一点上,近些年的研究实际上超越了前人的理论。此前,人们低估了古罗马贸易的复杂与繁荣。
的确,根据一种最早由德国著名法学家、近代商法学的开创者莱温·戈尔德施密特(Levin Goldschmidt,1823-1897)倡导的旧有理论,在所谓的“第一帝国”罗马,意定债权也许很少发生[3][4]。该观点后来遭到了美国学者摩西·芬利(Moses Finley,1912-1986)的反对,后者认为意定债权在古代社会广泛存在(当然在古罗马亦是如此),只不过基本上都是以用于消费的意定债权的形式发生的罢了[5]。借助当代研究古代经济的史学家们(比如意大利的卡肖)的学术成果,人们才认识到,在古代社会里,“为了投资的意定债权”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钱借贷作为金融与商业间的纽带的例子不止一个,我们只需分析一下在波佐利(Pozzuoli)发现的历史文档,就可以一窥古罗马复杂的金融运作过程了。根据该文档,我们可以还原苏尔皮奇家族(Sulpici)所从事的金融活动的历史原貌。其中公元前40年3月13日至15日的三个文件(标号分别是TPSulp.53、46 和79)表明,银行家福斯托斯(Sulpicius Faustus)向小麦商优昆图斯(L.Marius Iucundus)提供了两万银币附有质押的消费借贷。优昆图斯用这些钱购买了一批小麦(此外,就以这批小麦作为这笔消费借贷的质物),再卖掉它们,并用出售所得的价金偿还借款。
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古罗马的企业,通过设立意定债权以及建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来募集经营所需的资本。这些金融机构运用的精致工具(证券、金钱过户、商业保险等形式),与近代银行所从事的活动相比,毫不逊色[6][7]。
基于以上所有原因,如果说古罗马人一方面极力维系着消费借贷的要物性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实践和经济生活需求的不断推动,①在古罗马,法律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关精辟的论述,参见A.Petrucci,L’organizzazione delle imprese bancarie alla luce della giurisprudenza romana del principato,in Credito e moneta nel mondo romano.Atti degli Incontri capresi di storia dell’economia antica(Capri 12-14 ottobre 2000),a cura di E.Lo Cascio,Bari 2003,p.129.他们试图构建其他模式,来超越前面所说的欲使消费借贷契约产生(债的)的效力,必须有物的给付(让渡“traditio”)这样的限制。他们通过一定的方式,围绕着同样的需求,力图达到完成我们可以称之为借贷的金融活动的目的。
二、要物与合意之间
(一)对要物性的确认
在罗马法中,消费借贷的要物性一直被古罗马法学认为是其不可动摇的基本特征;而且从注释法学派直至今天,对此也几乎听不到任何不同的学术声音。②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此仅提请参见C.A.Maschi,La categoria dei contratti reali.Corso di diritto romano,Milano,1973,partic.140ss.;M.Salazar Revuelta,La gratuidad del mutuum en el derecho romano,Jaén,1999;J.Byoung-Ho,Darlehensvalutierung im römischen Recht,Göttingen,2002.从合意视角对这种契约的不同解读,可参见U.von Lübtow,Die Entwicklung des Darlehensbegriffs im römischen und im geltenden Recht mit Beiträgen zur Delegation und Novation,Berlin,1965,21ss.,尤其是V.Giuffré,s.v.Mutuo(storia),in《ED》,XXVII,1977,414ss.;e Id.,La“datio mutui”.Prospettive romane e moderne,Napoli,1989.
消费借贷的要物性在优士丁尼的《国法大全》中多次被重申。作为范例,我们知道(公元2世纪的法学家)盖尤斯在其《法学阶梯》中说:“债可以通过实物(re)缔结,比如通过给付某物以提供消费借贷。”(Gai.,3,90)这一论断被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全文照搬,即“债可以通过实物(re)缔结,比如通过给付某物以提供消费借贷”。(I.3,14pr.)
基于同样的理由,(公元2世纪)比盖尤斯稍早些的法学家阿弗利卡努斯就曾说过:“通过裸体简约不可能设立债权。”(Afr.,8quaest.D.17,1,34pr.)
他的意思无疑是,一个裸体简约,即单纯的协议,尚不足以成立消费借贷;这个契约的成立,除了要有合意本身以外,还需满足金钱给付要件。
这些片段证实了上文的论述,即在古罗马的消费借贷中,物的给付是一个比单纯合意更为重要的要件,后者单独连成立利息之债的效力都没有,而必须采用我们前面所说的要式口约(stipulatio)的形式方可。
但是,在这一点上,即使抛开有关商业活动的历史文献不谈,法学原始文献本身,也还给我们呈现了下述紧张关系:一方面关于消费借贷要物性的理论建构,坚定地要求物的交付这个要件;另一方面,这一点又被认为过于繁缛,为了超越它,古罗马人不断探寻新的可能的法律制度。事实上,古罗马法学家时常充分借助要式口约的抽象性,在意定之债领域,提炼出了比伴随着返还等量物(tantundem)的合意的物之交付更为复杂的制度,目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开要物要件本身,尽管在抽象意义上他们从未将它抛弃。
实际上,鉴于前面所说的消费借贷对于一个相对发达和复杂的社会——比如公元前二三世纪以后的古罗马社会曾经应该具有的状况那样——的意义,如果说物的交付加上让渡这样的高度概括的规则,就能满足商业当事人在借贷活动中的一切需求,这似乎并不可信:倘若真是如此,我们不得不说,没有任何古罗马贷与人收取利息,或者对借出的钱财确定准确的归还期限,或者要求对做出的“给付物”的行为保留证据,或者要求为物的返还提供担保,等等。①关于此点,主要参见A.D’Ors,Ree t verbis,in 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diritto romano e di storia del diritto,III,Verona,27,28,29-IX-1948,a cura di G.Moschetti,1948,281;不过,A.Castresana,La estipulación,in Derecho romano de obligaciones.Homenaje al Profesor J.L.Murga Gener,a cura di J.Paricio,Madrid,1994,442,却说:“众所周知,以消费借贷为目的的给付,在共和时期的大部分阶段,并不能满足古罗马已经增长的大规模国际贸易的需求。”
古罗马法学家所做的理论模式构建似乎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这些模式越来越重视“消费借贷的合意”以及对于物之给付必要性(让渡)的超越。物的给付曾被认为是,为了使消费借贷产生(债的)效力,替代物从给付人(dans)到受领人(accipiens)的物理转移。
(二)让渡的去实物化
在这一点上,首先可以使人想到的是,针对消费借贷中的“让渡”要件不断地“去实物化”。这个结论被罗马法原始文献多次证明。比如,乌尔比安,超越先前法学家(尤其是尤里安和阿弗利卡努斯)在相关问题上的观点,②在这一点上,尤里安和阿弗利卡努斯的立场似乎比乌尔比安的立场要保守,他们否认在下述情况下有消费借贷的存在。cfr.Afr.,8 quaest.D.17,1,34pr.:“某人,作为代理人,管理鲁丘斯·提丘斯的事务,收到后者的债务人交来的一笔金钱,于是致信提丘斯,告诉他由于事务之管理,这笔钱现在在自己手中,且对于这笔钱,(如果)借给他,他就是需要偿还百分之六利息的债务人。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基于该原因,是否可以将这笔钱作为借出的钱而提起诉讼,以及是否可以请求给付上述利息。(尤里安)解答说,这笔钱没有被借出,否则就必须认为,基于任何契约而欠的钱,都可以通过一个裸体简约而变成借出的钱。这与就寄存于你处的金钱达成借给你的合意不同,因为在后一情形中,这些金钱由我的变成了你的。”对此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拙著A.Saccoccio,Si certum petetur.Dallacondictio dei veteres alle condictiones giustinianee,Milano,2002,pp.392 ss.认为借用人可以以消费借贷的名义拥有原来基于委托而持有的金钱。“在金钱消费借贷之债领域,引进了一些特别规则。的确,如果我吩咐我的债务人交给你一笔钱,你将向我负有债务,尽管你收到的不是我的钱。”(Ulp.,31aded.D.12,1,15)
比如允许以所谓的“短手”形式(brevimanu)进行让渡。这方面的例子是,若接受寄存之人被许可使用寄存的金钱,则视为存在一个消费借贷:“我在你处寄存了10(币),之后我允许你使用它们:涅尔瓦和普罗库勒认为,我可以向你提起请求返还之诉索回(这笔钱),就好像是借贷给你的一样,即使是在你使用它们之前。确实,正如马尔切罗也认为的那样……”(Ulp.,26aded.D.12,1,9,9)
另外,在“委托清偿”(delegatiosolvendi)中,债权人为了建立一个消费借贷关系,要求自己的债务人向借用人提供金钱:“尤里安……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以你的名义并根据你的意愿,借出我的一笔金钱,该债权由你取得,因为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在我们提供消费借贷之前,先向另一个人请求转借,使此债权人以我们的名义给我们未来的债务人一笔现金。”(Ulp.,26ad ed.D.12,1,9,8)
(三)在确定归还日期或地点时,合意(conventio)的意义
合意要件相对于要物要件越来越重要,也可以从下述方面看出这一点,即当事人得以合意确定返还以消费借贷形式借出的金钱之地点或日期。“在以消费借贷的名义给付金钱,并且有于特定地点返还之约定条款的情况下,(可以提起仲裁诉讼)。”(Pomp.,22adSab.D.13,4,6)
最终上面提到的“给出的物”(resdata)构成消费借贷所生之债的基础和量度的规则甚至也被超越,开始承认可以对返还物的质量和数量进行约定,比如可以约定返还的数量少于实际交付的量,实际交付的量只是构成返还之债的最大上限。“以消费借贷的形式给出了一些酒,之后就此提起了诉讼。这样的问题被提出,即应以何时为标准确定这些酒的价格……萨宾给出了这样的解答,即如果曾说过应何时还酒,则当以那一时间为标准确定诉讼标的物的价值……”(Iul.,4exMin.D.12,1,22)“普罗库勒正确地认为,如果我借给你了10(币),只要求你之后还我9(币),根据法律,你偿还的金钱不必超过9(币)。但是,如果我借给你了10(币),目的是使你还给我11(币),普罗库勒认为不能提起请求返还之诉以主张超出10(币)的那一部分。”(Ulp.,26aded.D.12,1,11,1)
“合意”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它还可以决定向何人返还以消费借贷的形式借出的金钱,此人可以不同于实际“数出”(numeratio)金钱之人,即用于消费借贷的金钱的真正所有人。“……毫无疑问,如果我以你的名义并根据你的意愿,借出我的一笔金钱,该债权由你取得……”(Ulp.,26aded.D.12,1,9,8)
(四)以消费借贷之名义而为的物的交付与要式口约并存
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在实践中,越来越普遍的是,伴随着以消费借贷为目的的金钱给付,受领人还要再做出一个允诺,即以要式口约的庄重形式承诺返还受领的金钱。
在原始文献的一些表述的基础上,学界将这种情况称之为“附有要式口约的消费借贷”(mutuacumstipulatione)。德国学说为之创造的一个很准确的术语就是“Stipulationsdarlehen”。
在这些“附有要式口约的消费借贷”中,消费借贷是根据一个要式口约这样的(口头)契约而提供的,消费借贷的借用人通常在要式口约中一并承诺返还本金和利息。
在这些情形中,法学家们有时只承认存在产生于口头契约的债。这样,消费借贷的要物要件就被最终超越了,因为通常情况下要式口约作为抽象行为,在金钱未被交付之前也产生债的效力。“如果某人未采用要式口约而提供了一笔金钱消费借贷,与此同时他又订立了一个要式口约,那么这里只有一个契约。”(Ulp.,46adSab.D.46,2,6,1)“只要我们以消费借贷的名义给出金钱,又使人通过要式口约承诺返还,不产生两个债,而只产生一个口头之债。”(Pap.,3quaest.D.45,1,126,2)
围绕这种类型的交易,古罗马法学家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没有数出的金钱”(nonnumeratapecunia)的问题,①在众多也许可以援引的片段中,管见以为,下述片段特别值得关注。Paul.,5 adP laut.D.12.1.30:“某人为了能够以消费借贷的形式拿到一笔钱,以要式口约向未来的债权人许诺返还这笔钱。他有权拒绝受领这笔钱,从而不向对方负有债务。”这个片段提到,以要式口约承诺返还的债务人,有拒绝受领消费借贷之可能;他,无论如何,先是受到“诈欺抗辩”(exceptio doli)的保护,后来受到“金钱未数出的抗辩”(exceptio non numeratae pecuniae)的保护(vd.Gai.,4,116a)。对此cfr.M.Cimma,De non numerata pecunia,Milano,1984;W.Litewski,Non numerata pecunia im klassischen römischen Recht,in SDHI,60,1994,405ss.或者所谓的“要物与口头结合”(reetverbis)的契约的问题,②关于此点的论述,笔者推荐至少应参见vd.M.Talamanca,‘Una verborum obligatio’e‘obligatio re et verbis contracta’,in IURA,50,1999(ma pubbl.2003),7ss.,此文准确梳理了关于这一点的学说发展史。最近,A.Petrucci,Applicazioni dellastipulatioin materia creditizia e problema della causa nel diritto romano classico,in Derecho civil y romano.Cultura y sistemas jurídicos comparados,a cura di J.A.Goddard,México,2006,237ss.,再次对此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等等。这些问题迄今也没有被罗马法学界完全解决。
(五)所谓的“以出售某物的价金而设立的消费借贷”(contractus mohatrae)
另外一个与要物性渐行渐远的例子是所谓的“以出售某物的价金而设立的消费借贷”。通过这样的行为,贷与人交给(未来的)消费借贷借用人一个实物(例如一件衣服、一个银盘子等),以使后者能够卖掉它,并将所得价金作为消费借贷之物而拥有。“你向我请求借一笔钱给你,由于当时我手头上没有,所以给你了一只盘子或一块金子,这样你可以卖掉它们以使用其价金。我认为,如果你将之出售,那么(我们之间)就缔结了一个金钱消费借贷契约。”(Ulp.,26aded.D.12,1,11pr.)③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片段,cfr.Afr.,8 quaest.D.17,1,34pr.:“有利的论据是,有意提供金钱消费借贷之人,交给(未来的债务人)一个银器让其出售,则贷与人同样可以正当地通过提起诉讼,像要回借出的金钱那样要求返还金钱。”Ulp.,31 ad ed.D.19,5,19 pr.:“你向我请求以消费借贷的形式借一笔钱给你;我,由于没有这笔钱,给你一个物让你卖掉它,这样你就可以使用其价金。”
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确实也存在一个物的交付行为,但是给付的标的物是一个与金钱不同的一般实物,而返还的标的物却是金钱。对于实物的出售,可以使债务人取得他要使用的价金,并在将来作为消费借贷而予以返还。但是,债务人要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六)承诺提供消费借贷的要式口约(stipulatio de mutuo dando)
在古罗马原始文献中,最能体现与要物消费借贷相分离的制度,是关于“承诺提供消费借贷的要式口约”的规定。在此情形中,债权人通过要式口约的形式,庄严地向未来的债务人承诺以消费借贷的名义提供一笔金钱给他。“如果我被要求以要式口约的形式承诺回答这样的问题,即‘你承诺借给我一笔金钱吗?’,那么,这是一个以不确定物为标的的要式口约,因为在要式口约中涉及到我(要回借出的金钱)的利益。”(Paul.,2aded.D.45,1,68)
上面提到的所有原始文献,尽管被有的学者评价为古罗马迈向承认消费借贷的纯粹合意性的第一步[8],但是它们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这种契约在古罗马法学中要物契约的定位,而顶多算是消费借贷的“特例”(singulariarecepta)。
在罗马法体系的整个历史长河中,这似乎构成了固守消费借贷要物性的主要理由。
三、从罗马法到当代法
(一)从注释法学派到19世纪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欧洲有关消费借贷契约的法学思想的几条演进脉络。
根据注释法学派的观点(这也是评注法学派的观点),毫无疑问,消费借贷是要物契约。不过,注释法学家们区分了“天然”消费借贷(mutuo‘naturale’)和“法定”消费借贷(mutuo‘civile’)。在前一种情形中,有物的给付发生;在后一种情形中,物的给付是拟制的,就如同在“没有数出金钱”的情形中,诉讼(querella)的两年时效已经届满将会发生的那样。
评注法学派法学家们的观点仍然受上述理论的左右。在消费借贷契约中,他们看到的仍然只是一个通过“实物”(re)而成立的契约。
但是进入16世纪以后,逐渐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因为合意主义是契约法的基础这样的思想已经在欧洲蔓延开来。
一方面,天主教法学家们强调,“协约须严守”(pactasuntservanda)原则是一个与良心相关的问题:因为言行不一有违对一个合格天主教徒的道德要求。结果就是,单纯的合意就可以构成应为一定行为的基础。
朝着相同的方向,自由主义理论似乎也接踵而至。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哲学领域,这些理论都确立了这样的原则:每个人都可以——哪怕只是通过与他人达成合意——自愿使自己受到约束。
“高卢风格”的人文主义法学家们之间也开始有了观点上的分歧。的确,如果说在库亚求斯(Cuiacio,1522-1590)看来,毋庸置疑,消费借贷是要物契约的一种,①十分重要的是,I.Cuiacius给消费借贷下的定义,即“mutuum est creditum quantitatae datae,ea lege,ut eadem ipsa quantitas reddatur in genere,non in speciem eadem.”参见氏著:Observationes et emendationes XI,37,in Opera omnia I,Prati,1836,c.509.那么他的一个弟子洛瓦塞(Loysel,1536-1617),借助重述在对《学说汇纂》的注释(Glossa)中业已出现的一句法谚,就已经认为,“牵牛牵牛角,信人信人言”,所以,一个简单的允诺或者合意,其效力绝不亚于罗马法中的“要式口约”。
所以,当看到同一历史时期的阿诺德·维尼乌斯(Arnold Vinnius,1588-1657)强调说,在消费借贷的要物和合意关系这一问题上,应该着重强调后者,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
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事实上,一方面,在欧洲,自然法和人文主义学说,大大激发了个体自由和私人意思自治,而单单有它们就可以导致任何契约的生效。另一方面,在“学说汇纂现代运用学派”的法学家那里——他们主要活跃于十七八世纪的德国和欧洲中部——我们看到,坚定支持此种契约的要物性理论的学者不止一个,比如德国的劳特巴赫(Lauterbach,1618-1687),以及其他一些不那么著名的法学家。
法国的多玛(Domat)②J.Domat,Le leggi civili nel lor ordine naturale II,Napoli,1788(trad.it.dall’ed.di Parigi del 1777),p.119:“消费借贷是一方据之向另一方给付一定量的物的契约。”和波蒂埃(Pothier),二人都在罗马法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极力重申消费借贷的要物性质。波蒂埃的一个理由是,一个人不能返还他没有收到的。这个理由并不充分,最终不免成为消费借贷要物性理论体系的致命弱点。
(二)欧洲各国民法典
像许多其他制度那样,1804年《法国民法典》在这一点上做出了与多玛和波蒂埃这两位法学家的理论完全一致的选择。该法典的第1892 条,沿袭古典罗马法的传统,将消费借贷清清楚楚地界定为要物契约的一种。③Art.1892:“消费借贷是当事人一方交付因使用而消费的物品的一定数量于他方,他方负返还同一种类、同一品质的同数量物品于贷与人的契约。”法国学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发出也要将诺成消费借贷制度这个“应然的法”(deiurecondendo)予以法典化的呼声。但是,对于这种呼声,理论界并非没有质疑[9],立法上更是毫无动静。
而另一种模式,即合意主义模式,几乎自然而然地在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ALR)中寻得一席之地。这部作为法学启蒙主义产物的法典,承认并规定了两种消费借贷: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Eigentliches Darlehen),以事先交付一定量的替代物、受领人负有返还它们的义务(vd.ALR,I,11,1§653)为特征;另一种消费借贷,我们可以称之为“非严格意义的”,其中某人负有向另一人提供借贷的义务(第654 条)。在纯粹诺成性的“非严格意义的”消费借贷中,不履行债务的一方可能会因不履行而被起诉,除非对方当事人更愿意解除契约,当然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不过,承诺提供消费借贷之人,在看到借用人的财产状况严重恶化(此时他也仍有义务受领金钱:第658条),以致于使人有理由怀疑他的偿债能力的情况下,有权不给付金钱(第655、656条)。
《普鲁士普通邦法》的新举措只是在潘德克吞法学内部辟开了一条裂隙,而整体而言,潘德克吞法学依旧根据波蒂埃所说的理由(即不能要求返还本未受领之物),固守着消费借贷的要物性,虽然普遍承认当事人可以订立消费借贷的预约合同(Vorvertrag)。显然,预约合同的结构是诺成性的。但是无论怎样,为了在一定意义上突破要物性的限制,消费借贷契约成了当时德国法学界激烈争论的一个话题。①Cfr.,比如,K.Adler,Realcontract und Vorvertrag,in Jahrbücher für die Dogmatik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un deutschen Privatrechts(Jhering’s Jahrbücher),31,1892,pp.190ss.在此翁看来,物的交付应被界定为消费借贷的“当然条件”(condicio iuris),因为要物是这类契约的性质而非本质要求;而对于G.Boehmer,Realverträge im heutigen Recht,in Archiv fur bürgerliches Recht,38,1913 314ss.而言,因为当事人可以订立“预约”,这似乎直接导致了对诺成消费借贷的承认。
在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中,尽管之前的准备性工作都指向确立消费借贷的诺成性,②Cfr.Die Vorentwürfe der Redaktoren zum BGB,a cura di F.P.von Kübel,Berlin-New York,1980,Schuldrecht 2,p.519.但是该法典最终还是采纳了部分德国法学家的观点,于第607条规定了要物消费借贷:实际上,尽管存在可就消费借贷订立预约合同(《Darlehenvorvertrag》:第610条)之可能,但是实质上仍维持了消费借贷的要物性。③Cfr.§607Abs.1:“受领金钱或者其他替代物作为消费借贷的人,有义务向贷与人偿还相同种类、品质和数量的物。”
对于该法典所选择的解决方案,德国有不少赞同者,但是力倡其诺成性的学者也不乏其人(von Lübtow,Larenz)。尽管司法界极力反对诺成消费借贷的方案,但是主张合意性的观点最终在2000年的法典修订中得到了采纳。修改后的民法典将消费借贷区分为金钱消费借贷(Gelddarlehen)和其他物的消费借贷(Sachendarlehen),二者都被作为诺成契约规定了下来。④Cfr.§488Abs.1:“因贷款契约,贷与人有义务向借用人提供约定金额的金钱。借用人有义务支付所欠的利息,并在清偿期到来时偿还向其提供的贷款。”§607Abs.1:根据物的消费借贷契约,贷与人有义务将约定的替代物交给借用人。借用人有义务支付消费借贷的报酬,并在清偿期到来时偿还相同种类、品质和数量的物。”
也是在20世纪,在欧洲,诺成消费借贷还曾被规定在1911年的《瑞士联邦债法典》中。尽管该债法典规定了一些要物契约(赠予、质押和铁路运输),但是,是把消费借贷作为纯粹诺成契约看待的(第312条)。⑤Art.312:“消费借贷契约是贷与人同意交付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者其他替代物于借用人,借用人同意返还同等数量的金钱或者同等同量的替代物的契约。”
意大利法在这一点上,尽管与德国法的演进路径完全不同,但是也是逐渐承认了诺成消费借贷的。
在意大利,《法国民法典》的选择(要物消费借贷),至少在立法目的上,被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所仿效。后一部民法典在消费借贷问题上所采用的模糊术语,⑥Cfr.art.1819:“为了消耗物品的消费借贷或者借入是一个契约,据此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一定量的物,后者负有返还相同种类和质量的等量的物。”尽管学说和司法不断将之解释为要物性的规定,但是毕竟为诺成理论的支持者们提供了解释的空间。⑦关于司法实践,首先参见Cass.civ.11.9.1895,尽管该判决指出了困惑的原因,但是最终还是将消费借贷定位为要物契约。关于理论学说,首先参见E.Pacifici-Mazzoni,Istituzioni di diritto civile V.2,Firenze,19275,p.399;近些年,对于该制度的“成因”分析,还可参见V.Giuffré,La《datio mutui》.Prospettive romane e moderne,Napoli,1989,p.17s.
1927年所谓的《法意债法典》,效仿《普鲁士普通邦法》,果断采纳了折中方案,规定当事人有两种选择:可以订立要物契约性质的,也可以订立诺成性质的消费借贷(第636条)。⑧Cfr.Progetto di Codice delle obbligazioni e dei contratti.Testo definitivo approvato a Parigi nell’Ottobre 1927- Anno VI,Roma,1928,art.636,p.294:“消费借贷是一种一方当事人给付某物或者负有义务给付某物的契约……”对此,cfr.R.Teti,Il mutuo,in Trattato di diritto privato diretto da P.Rescigno 12.IV,Torino,1985,p.660.
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的历史有些特别。在该法典的起草过程中,立法者意欲使之与前面提到的《法意债法典》的模式保持一致的意图非常明显,即将消费借贷规定为可以有两种性质的契约,根据当事人做出的意思表示不同,一种具有要物性,另外一种具有诺成性。①Cfr.l’art.615del Progetto preliminare del libro delle obbligazioni,in Lavori preparatori del Codice civile(anni 1939-1941),vol.II,Roma 1942,p.183:“消费借贷是一方据以向另一方给付物或者负有给付物的义务的契约……”;“草案说明”对此解释道:“在(消费借贷契约的)定义中,提到了要物消费借贷……以及单单产生债的效力的消费借贷。”(vd.Codice civile.Quarto libro.Obbligazioni e contratti.Progetto e relazione,Roma,1936,p.61)但是,在该法典获得立法通过之前的最后一次审读时,原有的制度安排被整个推翻了。最终,第1813 条的规定表明,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的立法者将消费借贷仍作要物契约看待,就像司法界②Cfr.,典型案例有,Cass.civ.num.1945 8.3.1999;Cass.civ.num.11116 12.10.1992;Cass.civ.12123del 21.12.1990.和部分学者(Forchielli,Messineo,Giampiccolo 等)也 认 为的那样。
在意大利,事实上,不乏有人(如塞劳、迪马约)认为,要物契约似乎被意大利的立法者自动排除了,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部民法典中,契约的概念本质上是建立在合意基础之上的(第1321条)[10][11];也有人认为,由于第1821条规定了“消费借贷的许诺”,立法者也许想为这种契约选择一个不同于要物性的模式(Carresi,Martorano,Giuffré)。③Cfr.,例如,F.Carresi,Il comodato.Il mutuo,Torino,UTET,1950–Trattato di diritto civile italiano diretto da F.Vassalli,vol.VIII,fasc.5e6,pp.99ss.;s根据Martorano,Il conto corrente bancario,Napoli,1955p.41之观点,第1813条是作为历史残余存于《意大利民法典》中的,之所以如此规定,只是为了尊重罗马法传统;在这一点上,还可参见V.Giuffré,Mutuo(storia),in ED,27,1977,pp.442ss.
实际上,在意大利正是司法实践孕育了诺成消费借贷这一类型;直到其诞生之时,学界亦未对这两种类型做出理论概括。之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理论界才总结出了“为了一定目的的消费借贷”。在这种消费借贷中,贷与人决定出借物应该用于何种目的;这种消费借贷一般用于修建建筑物,只需存在合意便可成立,对于作为消费借贷标的物的金钱的支付,一般根据工作的进展情况,发生在契约的履行阶段,而不再是订立阶段。④Cfr.,众多判例中,Cass.civ.7116del 21.7.1998;关于为了一定目的的消费借贷,vd.A.M.Giomaro-P.Morosini,s.v.Mutuo nel diritto romano,medioevale e moderno,in Digesto delle Discipline Privatistiche.Sezione Civile,11,19944.
如今,由于所谓的建筑消费借贷的广泛存在,意大利理论界已经顺理成章地既承认要物消费借贷,也承认诺成消费借贷,具体就要看当事人选择使用的是哪种模式。
(三)作为“软法”的欧洲各草案
如果考察一下欧洲合同法一体化进程中的各个草案,我们就会发现,诺成消费借贷似乎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模式。
的确,无论是1994年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⑤Cfr.art.3.2:“一个契约可以通过当事人间的简单协议而被订立、变更或者解除,不需要进一步的要件。”还是所谓的兰德“法典”(1996/2000),⑥Cfr.art.2:101:“契约在下述情况下订立:a)当事人表示出了受法律约束的意思,以及b)他们达成了一个充分的协议。不要求任何其他要件。”都采纳了诺成消费借贷模式。在兰德“法典”基础之上的《欧洲合同法原则》规定,契约仅因合意产生,“其他任何要件均不必要”。⑦事实上,PECL 的这一条完全是按照Lando教授本人的思路而设计的,目的是将“原因”(causa)或者“对价”(consideration)排除出契约的诸要素之外:cfr.C.Castronovo,Il contratto e l’idea di codificazione nei Principi di diritto europeo dei contratti,in Materiali e commenti al nuovo diritto dei contratti,a cura di G.Vettori,Padova,1999,pp.109ss.2008年的《共同参照框架草案》遵循的也是这一思路。这个文本与PECL的承继关系非常明显,构成了2008年发表的《欧洲民法典》的一个草案。该草案的起草工作由德国学者冯·巴尔(Christian von Bar)负责协调,来自欧洲这个古老大陆的不同国家的学者参与了起草工作。草案的II.4:101规定:“契约成立而无须其他要件,只要当事人:(a)旨在建立有拘束力的法律关系或者使其他法律效力产生;以及(b)充分达成了合意。”
为了消除可能的解释会带来的任何疑惑,《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的§3.2 的注释明确说道,这一规范恰恰正是为了“排除(契约的)缔结完成可能还要……取决于对某物的交付”。
与此不同的是,2002年的《欧洲契约法典高级草案》规定,要物契约可以跟与其相对应的(非典型的)诺成契约“并存”:⑧Cfr.art.34co.2:“要物契约经标的物之实际交付而成立,除非基于当事人之意思或者习惯,应认为当事人意欲订立非典型诺成契约。”依此逻辑,故而,消费借贷就应该被认为是一种要物契约,但是当事人也可以将之设计成诺成契约。
结 论
在结论部分,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一下至此所做的分析而呈现出来的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就是从法律传统的视角来看,消费借贷的要物性质或者诺成性质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如何对借贷活动(主要是金钱借贷)进行法学理论的构建问题。
从第一个(即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我们所引述的证据表明,在罗马法体系中并不存在一个整齐划一的消费借贷制度。特别是,在古典罗马法时期,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法学家所建构的理论中,还是在具体实践中,此种契约都被规定为要物契约。物的交付虽然被去实物化,但始终仍作为消费借贷的要件之一而存在。
不过,与此同时,古罗马人对于从事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更为复杂的活动现实需求,亦非视而不见。在这些活动中,物的交付也许被“观念化”,甚至完全不见其踪影。另外,前面提到的出土石碑的碑文也告诉我们,借用人的返还义务,愈发常见地被规定在“要式口约”中,而不是继物之交付而产生;于此方面,还要考虑到“没有数出的金钱”的问题,它蕴含了让一个人承担返还从未受领之物的义务的非正义性。在这些情形中,债权的设立完全建立在达成的合意的基础之上;或者顶多是,建立在以要式口约的形式所达成的合意的基础之上;要物性要件(即“让渡”),顶多只是使承诺人原本得向要式口约的恶意缔约人主张的(最初是“恶意”,后来是“没有数出的金钱”)抗辩不生效力。
我们还注意到,为了平衡上述规范,古罗马法学家认为,可以采用订立“承诺提供消费借贷的要式口约”的形式,来对提供消费借贷进行承诺。这种要式口约毫不约束要式口约的缔约人受领金钱,而总是使承诺提供消费借贷、却未履行债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vd.D.45,1,68)。
从第二个(即消费借贷的制度与法理)视角来看,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鉴于要物消费借贷和诺成消费借贷这两种制度构建在罗马法体系中都存在(无论是欧洲法,还是拉美法,在这些本文所关注的子体系中,均是如此),那么到底哪种模式更为可取。
管见以为,对于该问题,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答案,正如在罗马法系中不同模式所呈现的多样性那样:说要物消费借贷较诺成消费借贷更优、更安全,或者相反,皆为不妥之论。
在笔者看来,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的磋商活动,明智之举就是分别构建与之相应的制度,近乎于要为身材部分相似的模特裁量不同的服装,使得套套各具特色。
特别是,在金钱借贷活动中,如果借用人需要马上能够使用这笔金钱,比如说他要购买一栋房子,或者一辆汽车,或者任何其他的物,那么,毋庸置疑,要物消费借贷契约能更好地满足双方当事人(贷与人和借用人)的需求,因为物的让渡是契约本身成立的要件:没有物之交付,消费借贷便不成立,因为没有交付,促使借用人请求借贷及贷与人提供借贷的需求,亦即这笔金钱立即可供使用的需求,便没有被满足。
相反,近代的实践(其实,正如前文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古代的实践亦同)也要求“诺成”形式的借贷存在,这样可以“使借用人信任贷与人所做出的承诺”。
当只需借出这笔金钱的贷与人(通常是一家银行,或者任何其他“强势的”缔约方)做出承诺,对于借用人而言便为已足之时,即会产生上述需求。这是一个借贷活动,倘若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消费借贷”或者“待履行的消费借贷”(mutuo obbligatorio)。应该将它与单纯的消费借贷承诺严格区分开来,但是它与前面论述的要物契约也不同,因为金钱的实际交付在这种情形中是在契约的履行阶段,而不是订立阶段。
然而,窃以为,就像罗马法原始文献所启示的那样,这种诺成消费借贷,也许还需要附以两个矫正措施以使之平衡,其主要而非唯一的目的是,保护法律关系中“弱势的”缔约方。
第一个措施就是,如果借用人的财产状况发生重大变故,以致于可以使人合理怀疑其偿还借贷的能力,则有必要确保贷与人可以不必再提供之前承诺数额的借贷。①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第1822条在谈到消费借贷的承诺时,使用的是“显然难以返还”(notevole difficoltàdi restituzione)和“未提供相应担保”(mancanza di idonee garanzie)这样的表述。
第二个措施,依愚见便是,当借用人在合意达成后不再需要全部借贷时,应当允许他部分不受领,且并不因此承担任何责任。考虑到一家银行和消费借贷的债务人的缔约能力的悬殊,这是一项重新找回契约平衡的措施,它与在前文所引的罗马法原始文献中便已浮现的模式一脉相承。
[1]PEROZZI S.Istituzioni di Diritto Romano II[M].Milano,1928:251.
[2]LONGO C.Corso di Diritto Romano.Il Mutuo[M].Milano,1947:1.
[3]GOLDSCHMITH L.Premodern Financial Systems a Historical Comparative Study[M].Cambridge,1987.
[4]CIOCCA P.Moneta e Credito Nella Roma del Primo Impero[C].Atti Acc.Cost.,12,1998:25ss.
[5]FINLEY M I.The Ancient Economy[M].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1973:141ss.e 196ss.
[6]PETRUCCI A.Mensam Exercere.Studi Sull’Impresa Finanziaria Romana II sec.a.C.– metàdel III sec.d.C.[M].Napoli,1991.
[7]PETRUCCI A.Prime Riflessioni su Banca e Interessi Nell’Esperienza Romana[C].Atti del Congresso“L’usura ieri e oggi”,a cura di TAFARO S.,Bari,1997.
[8]ZIMMERMANN R.The Law of Obligation.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M].Oxford,1996:159.
[9]JOBARD-BACHELLIER M N.Existe-t-il Encore des Contrats Réels en Droit Français?Ou la Valeur Des Promesses de Contrat Réels en Droit Positif[J].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1985:1ss.
[10]BIONDI B.Contratto e Stipulatio[M].Milano,1953:231ss.
[11]SACCO R.Il Contratto[M].Trattato di Diritto Civile Diretto da VASSALLI,VI/2,Torino,1975:613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