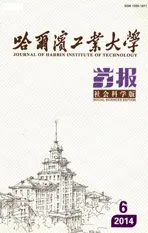平易叙事与哲学的真实:星云大师《合掌人生》真实性的构建
2014-03-31陈星宇
陈 星 宇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430072)
中国传统史学重视从客观的历史材料本身出发去梳理历史的脉络、探讨历史的真相,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是应有的基本态度。随着历史学材料范围由考古事物、正史记录扩展到地区史、专门史、家族史,更进一步到野史、个人回忆,甚至参考文学性叙事,史学研究成果呈现出侧重点不同、结论各异的面貌。原因之一在于随着史学材料范围的扩展,材料的叙事主体特征越来越明显。尽管史学工作者严格秉持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的态度,仍然无法排除历史材料本身带有的主观因素的渗透。这种渗透并非有意干扰史学研究,而是基于叙事者本身的自主与能动性,而呈现出的与叙事者的经验、心态等密切相关的侧重。历史材料中主体意识的存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一部个人史,由于叙事者的知识基础、独有的生活经历、情感意志、性格气质等特殊素质以及哲学观、政治立场、价值取向等精神形态,叙事体现与具有固定的价值取向和书写模式的正史相比较,必然呈现出更高的动态性和个人特征,也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史叙事与网状历史之间的断裂。
具有强烈个体色彩的历史叙事之所以有意义、能够可靠地补充宏观历史叙事,根本在于个人历史的叙事经历了个人回忆的重整,当它们再被表达出来的时候,实际上获得了新的诠释,已经经个人之手放置于宏观历史的脉络之中了。个人史对历史的细致化作用首先表现在叙事者的语言运用上。叙事者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回忆时的心态、对往事价值的判断,都可以通过叙事语言风格中蕴含的情感来做初步的体会。不同于宏观历史记事语言讲究语法、用词精确、逻辑严密、臧否有度,个人史的书写渗透了更多的个体性色彩,叙述者个人的出身、教育、社会阶级、性别等社会因素,以及精神因素,都可以表达感情倾向于或潜或隐的主体意识。同时,叙事者与宏观历史的深刻关系,也可以通过他的个人史书写而体现,他可以传递宏观历史记录中视角所不及、甚至不能明载的种种人际互动的细节,包括社会交往、家庭生活等涉及人们的感情波动以及属于隐私领域等一些感性问题。而这些补充往往对我们研究历史动力学帮助很大。
在上面的认识下,我们来考察星云包括散文、回忆录在内的作品,可以体会到一种个人史与佛教史交接的意味,尤其是《合掌人生》和《百年佛缘》中蕴含的家国情怀更是加重了这一意味。星云的“人间佛教”理念对人本性和社会性的强调渗透在其包括散文和回忆录在内的文字作品之中,而且随着他的宗教角色和宗教职责的一步步转变、“人间佛教”理念的践行与光大,文学作品也呈现出在越来越宽广的层面上对此理念的呼应。
一、身份意识与历史感
《合掌人生》作为一种回忆性的文本,大历史与个人史交接,尤其适合我们藉助其去了解历史动力所在。1995年,符芝瑛著《传灯:星云大师传》出版[1],2002年,林清玄著《浩瀚星云》出版[2]。这两部传记都是撰者以星云弟子的身份完成的。前者勾勒星云出生至于“人间佛教”大弘于世的过程中,星云本人和佛光山文化表现出的状态,多有在第三者的角度上宏观而定性的叙述和评论。1994年,佛光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二十册的《星云日记》,首次系统提供关于星云生平的一手数据[3]。2008年,现代出版社出版包含星云自述内容的《往事百语》[4]。在《星云日记》、《传灯》、《浩瀚星云》以及《往事百语》四部著作中,《星云日记》的史料价值是无可置疑的。《日记》跨度从1989年7月至1996年12月,历时七年有余,尽管有时间局限,但皆是星云自陈的弘法相关的事实、人物以及体悟。而《往事百语》也提供了一些星云的原始回忆数据。2011年,星云自传《合掌人生》出版,这部作品是首部出于星云个人真实视角的回忆性作品。这部作品与前期的《日记》、《百语》等构成了回应,也与星云著作中的精神内涵构成呼应,让我们从多种文本的对读中了解到一位宗教领袖活动的精神主线所在,同时也了解到在其宗教身份下的叙事稳定的叙事中心。
稳定性首先体现在统摄全篇的身份意识。从叙事者的角度来讲,《合掌人生》中星云本人是唯一的叙事者,对读者来说这样就排除了他传的撰者视角的干扰。叙事开始的时候,讲述者便已经具有在现在的时间点上的身份体认,以一种身份的意识来开展叙事,在这种意识下,叙事者对人生展开了回顾与审视。
我曾经把自己的一生规划为八个时期,以每十年为一时期,第一个十年是“成长时期”,第二个十年是“阅读时期”,第三个十年是“参学时期”,之后依次是“弘法时期”、“历史时期”、“哲学时期”、“伦理时期”、“佛学时期”。[5]1
作者在回忆中概述人生规划的阶段,即是一种事实回顾,同时也呈现了一种时间感。在人类学的口述历史材料中我们会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叙述者对生活的叙述和对生命的叙述,在时间感上是不一致的。在叙述生活的时候,叙述者采用循环的时间季节与年月来表达时间感受,而在叙述生命历程的时候,叙述者多以标志性、转折性的事件来作为时间标识。星云对自己人生有“八个阶段”的感受,实际上也是对生命历程的定性,它给出了一种不可逆的时空与历史感,而对每阶段规划都不脱离修行与弘法,这便是叙事者身份意识的体现。
《合掌人生》全文讲述着尘世中的历练、对至亲的回忆、教内修行、弘法因缘等。《合掌人生》虽是自传,但星云身为一位宗教和精神导师,自觉地承担着教导之责,即使在一部自传,亦是希望有益众生。星云倡“人间佛教”,在佛教济世观的指引下,基于“善”而细化了道德条目,令其变得明白可行,对尘世生活颇具有指导意义。它很好地填埋了大众出于对佛教出世性的经验的畏惧而形成的当代佛教与大众之间沟通的鸿沟。这种关照影响了《合掌人生》叙事的组织和措辞,使得它在以一种超越的视角来回顾往事时,所超越的是对烦琐的苦难的沉溺与深陷,而不是忽视与不理解它们,因此叙事并没有令读者产生立论过高的疏离感。这种超越的视角的建立根植于二者,一是叙述者的宗教身份及身份所约定的导师内涵,二是与宗教身份相匹配的稳定的叙事情绪。所以“人间佛教”在根植于普遍性的道德直觉之外,又在佛教这一独特场域中获得了另外一种带有佛教特点的宗教型道德直觉。回忆叙事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展开,“善”的生存感也在对人际和伦理的叙述中贯穿全书。每遇难堪之事,大师皆以自然天性与忍辱观念一一化解,并且总结道:
回首自己这一生当中,虽然经常遭受别人的讥讽、毁谤、批评、打击,但是多次的忍辱,对我的修行,何止增长数十年甚至百年。[5]42-43
这是生存人格的圆满,同时也是叙事人格的完成。在读者一方看来,叙事者是站在叙事当时描述他人生的河流的怎样流过那些平原深谷,也是在回答他何以站在当下,成为一个“当下之人”的问题。由“当下之人”主导的回忆和相应的叙事是具有时间性的,因为当“当下”随着时间流逝而动态变化的时候,“当下之人”也有可能因为新的经历和体悟而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回忆叙事。所以通常会认为,自传性的回忆叙事中会存在一个叙事人格,正是这种人格主导了叙事,传达叙事者所欲传达之事。然而“叙事人格”的说法天然地有着一个缺陷:叙事人格与生存人格如果不完全一致的话,那么由叙事人格主导的回忆叙事所反映出的是否可信?与虚构的区别何在?而且,叙事人格仅在叙事当时出现,它具有暂时性,而生存人格则是在时空维度中发生着变化的,以叙事人格去观照往事,文字呈现给我们的是否诚实?如果诚实,是怎样一种意义下的诚实?
实际上,叙事人格是基于生存人格而发生,甚至可以认为它是生存人格的一部分,它带有对人生的角色和责任的体认,它不仅在自传中,在其他回忆文章中,甚至在回忆发生而未形诸于文的时候,就可以发生,由其修整之后所呈现的事件内容与回忆者的价值观念息息相关。正因为有这样的主观性,所以自述、自传类的材料有可能触及宏大叙事所不及的历史深度和细节。星云认为,“人生好比一条路”,“人生的路,要靠自己走出来,自己走不出自己的路,总是没有把人生活得淋漓尽致”,人生与路之间的比喻关系本身就暗含着经历、路径、方向的意味,“人生路”这个比喻在体现经历性的同时,也在传达一种向前的一贯性,甚至某种程度上的不可逆性。《合掌人生》的叙事是流畅而一往无前的,它整体上透露着“命”的观念,“命”意味着对生命经历的认同,对角色和责任的主动担当,以及对生活状态的意味与哲学意义的阐发。在讲到包括佛光山在内的弘法事业的时候,星云往往体现着一种责无旁贷的积极精神。
对超越者的信任,是一位宗教徒应有的态度,“佛缘安排”的说法,并不是在论证超越者的实体性,而是透露了一种对人生经历的哲学化理解,所经历的事件的前后、因果、影响,无一不在此理解中有其合理的秩序,对此合理性的认同也是对人生经历的认同,实际上也完成了一个从生存中提炼哲学态度,又以哲学态度指导生存的过程。
二、佛教的人间性与“善”的生存
符芝瑛、林清玄为大师所作的传记囿于弟子和第三者的立场,对人间佛教和星云本人的解读近于宣传手法,近年邓子美、毛勇强先生的《星云大师新传》带有学者之风,使著作带有史料特色。与这几类著作相比,《合掌人生》所提供的回忆者主体思想方面的信息始终无可替代。《合掌人生》中渗透着一种基于身份的责任感,在叙事开始的时候,叙述者因此身份,明确了他的叙事选择;也是基于身份认识,行云流水的叙事依然有迹可循,它始终依循着道德空间中的方向感。
星云理解的佛陀“出生在世间,成道在世间,度化终生也以世间本怀为重,如果离开世间,则佛道不易成就。……佛陀应化世间,为一大事因缘,此一因缘即开始人间大众,悟入佛的知见。”[7]36“佛陀在世间”是星云“人间佛教”的认知起点,佛陀的人间性与“佛缘安排”的说法相映成趣。在其他作品中,星云屡屡讲到佛光山有人间、大众的性格,也自云自己的性格是“近于人间”。[5]111“性格”一词在星云这里,蕴涵着秉性与后天之性的意思,它所引导的是“性格”承担者与世间的相处之道。星云一“路”走来,持其秉性,修其心性,利生宏愿之下,不辞辗转世间而至其实现,身份——道德方向感贯穿始终。星云“八个时期”的自我规划,即是对这种方向感和责任感的自觉领悟,《合掌人生》的叙事安排是其宗教认知和宗教体验的反映,也是受宗教塑型的人格的体现。《人生路》的开篇说:
我最感激的是,父母生养我,不但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给我一个影响一生一世的性格。所谓“性格”,我生性勤劳,从小就喜欢帮助做家务,举凡扫地、洗碗、擦桌子,我都会主动去做。再者,就是我有一颗“仁慈”的心。[5]2这种似乎“性格先于经历”的说法,实际上是叙事者本人以回忆的当时的目光来观照的结果。与之相似的,是在回忆所敬重的外婆时感到外婆跪拜神明、吟唱经文的时候声音“比河流更悦耳。她虔诚的身影,散发的光彩,就像肃穆的神明,就像慈悲的观音。”[5]46从人物虔诚、慈悲的形象中时时可读到叙事者最为认可的人性特质。此外还有《母亲》一章,同样的脉络细腻、情感充实,人物身上也在体现着安贫、知足、坚韧与宽大等美德。从对这些重要品德的提举之中,我们读到叙事者所重的人间伦理的内容。书中《道情法爱》一章,更是提出一种基于信仰、理念的共通而发生的惺惺相惜、相互提携的同窗、同道之谊。这些充满人伦温暖的“善”同时也在一个侧面呼应着佛教“人间性”的特质。
《合掌人生》中屡次提到人间佛教“国际化、人间化、生活化、艺文化”的特质,也曾作简短总结:“人间佛教就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之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要有人间的性格、人间的伦理、人间的秩序;人间佛教要从‘人’做起,甚至要从‘自己’做起,凡事不要求别人。”[5]11这一种道德、有序、慈善、自立的生存方式,也是“善”的生存方式。回忆中星云亦不回避自身经历的如饥饿这样的事件所引发的生理和心理活动,甚至不避讳自陈境界:
空空虚虚地念佛,使我体会到忘却时空、身心脱落的快乐;从老老实实的参禅里,我也有过“身心俱泯,大地空旷”,乃至“时间、空间、天地万物都为之一空”的修行体验。不过说来惭愧,我没有开悟,也没有证果,直到今天,我只是安分地吃饭,安分地睡觉,安分地做佛事,所谓“心怀度众慈悲愿,身如法海不系舟;问我平生何所似,佛光普照五大洲”。这是我一生念兹在兹的愿心。[5]78
这一段现实的、抛却神圣化光彩的自我陈述,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展示一位有血有肉和光同尘的大师形象,更在于它避免了一种“圣徒化”的叙述,展示了一种人生的真实。这种真实在本质上是与“人间性”一脉相承的。
星云对文学艺术的专注也是他建立“善”的生存模式的途径之一。星云本人很早就体会到文艺之美与教育作用,对运用文学形式弘扬佛法有着强烈的自觉,这种自觉根植于其少年时代从通俗文学读物中受到教育的经验,以及他自己的阅读体验。①在《合掌人生》“人生路”和“道情法爱”章节中,星云回忆了自己从通俗文学作品得到启蒙教育的往事,以及成为佛教徒之后以文学弘法的经历,并且在《百年佛缘》“我与文学的关系”一章中,星云说:“因为我一生没有进过学校,也没有受过老师特殊的训练,除了寺院的教育,让我获得佛学的一些知识以外,应该就是我个人喜欢阅读文学的著作了。之所以启蒙我喜欢文学,还是由于佛教的经书比较深奥,读起来不甚了解,而民间的文学小说不但看得懂,并且趣味横生,所以我就这样深深地爱上了文学。”从题材上分类,星云的文学作品包括佛弟子传记、佛学内容的散文小品、自传与回忆录几大类。星云进入台湾,在文学方面雏声新啼的第一批文章是收于《无声息的歌唱》中的二十篇“物语”式散文[6]。文章以法物自语的方式介绍了大钟、木鱼、大磬、签筒、香炉、蒲团、烛台、牌位、戒牒、文疏、纸箔、佛珠、海青、袈裟、香板、僧鞋、钵盂、经橱、宝塔等二十种法物的仪制和功能,因为在文章以法物的口吻,揭露当时台湾佛教中的一些不如法不如仪的现象,也揭露了佛教寺院生活和教团组织的一些弊端,所以引起的反响并不止于文学层面。据星云自述,文章刊发之后,曾收到批评,指责他披露佛教“内幕”[7]1-7。这一批文章中牵涉佛教事实、表达呼吁和革新的情感,俱是文章立意所致,星云写“物语”的本怀,是“希望我们佛教徒革除这些陋习”。这种革新佛教的意识是应时因事而发,但在精神上有所承继。虽然《无声息的歌唱》更大程度上是一部散文集,但是其中所蕴含的宗教革新意识实可以远溯。
三、哲学的真实:宗教身份下对超自然经验的回忆
尽管对回忆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存在着争论,但是我们注意到,对“真实性”的争论并非针对回忆所涉及的事件的真假——人类的记忆是有误差存在的,在不带刻意欺骗意味的前提下误差是被容忍的;这种争论着眼在对回忆文本的解读上,在叙事者所布置的能指与所指、读者所感受到的能指与所指这两套系统之间的统一与矛盾性。这种争论的发生扎根于“文本自证”方法的不可靠,因为不经过诠释的文本是无法实现自证的,而一旦经过了诠释,“自证”性又何以谈起呢?回忆叙事因为强烈的主观体验性,似乎应当以一种“忘我”的状态来阅读,这种阅读状态的意义在于消除阅读的预设立场,避免对叙事者做出不当的怀疑。但是实际上,纯粹的阅读的“忘我”状态和“文本自证”一样是无法彻底实现的,我们作为阅读者所能做的,就是在努力地靠近叙事者经历状态的同时,实现对叙事者的叙事状态的挖掘。
对真实自我的角色有清晰的认同、在道德空间中具有明确的方向感,这样的叙事者在建构以自身经历为素材的文字作品的时候是有可能将个人的价值观念渗透其中,这样的叙事者本身就是一面棱镜,当回忆投射进镜面,它所反射的光辉因叙事者叙事当时的状态而异;而回忆事件本身在我们回忆的时候就已经区别于真实的发生和存在,而成为镜花水月,只可观望与念想而已。回忆要实现真实,或者说尽量实现真实,在叙事中设置真实可信的历史时间坐标之外,只能是叙事者努力重演当时的状态,之后再将个体化的体验叙述出来。在阅读的时候我感觉到,星云大师不仅重演了当年的自己,在述及他人他事的时候,也一次次代入理解,于是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体恤而慈悲的叙述氛围。
有一些来自回忆者个人的特征,譬如宗教身份,以及带有灵异特征的叙事可能会引发对真实性的怀疑,要指出的是,这种叙事的意义并不在于历史空间真实的发生和物理世界中的科学逻辑,而在于事件背后它向我们透露的叙事者的意念、哲学化的世界。作为一种非虚构性的文学,它之所以是文学而非社会学,便在于它不是社会现象的罗列,也不是由群体而普遍化的经验和规律,而是极为个体的人性叙事,是对规律的例证和对群体经验的分解。《合掌人生》的“真实”意义在于对个人哲学世界的呈现。在一个哲学的世界里,日常生存中的种种存在仅仅是哲学存在的基底,是哲学解释发生的可能的土壤,哲学的“真实”并不一定与日常真实是一致的。例如,宗教所崇拜的“神”大多数是在观念里被认识,尽管屡有关于救主降临的奇迹的记载,但对神圣人物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植于感受。
宗教与哲学是相通的,它们都有着看不见的秩序和看不见的实在。在某种视角下,历史上的僧传与回忆文学有着相似的特质——它们模仿史书笔法,时间脉络清晰,分部别类,同时也用了正史极少用到的生动叙述,屡见毫厘必现的叙事,宛如其所见,这很自然地会让人意识到其中的文学性。不仅如此,僧传中存在着不少超自然的故事和情节,历代沿革,颇可见固定的原型与母题。这些原型与母题屡见于书写而几成惯例,颇可令人回味。僧传在史料中的地位,是正史史料缺失下或不完善的补充,或者正史史料存在的前提下的参考。僧传并不等同正史,并非因为僧传的包括虚构性在内的文学性特征影响了叙述的严肃程度,而在于二者各有面向。同样是记录存在,正史记录的是物理空间中发生与发展,而僧传虽然也遵从叙事逻辑,却有着世俗与精神的双重面向,事件的本体发生在世俗之中,但是在利用叙述引导读者发掘事件内涵方面,僧传依从看不见的实在,遵守着看不见的秩序。我们处理其虚构色彩强烈的材料比较理想的方法,应该不是去伪存真地落实其在物理世界中的可能性,而是将这些材料做类型化的归纳,并在精神史的层面上为它们找到一席之地。
《合掌人生》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僧传,在本质上是一位老人在一种“知命”的哲学状态下,对往事的脉络所做的梳理和对曾有过的心路历程的交代。它将个人命运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将家国情怀、命运感、历史感贯穿全书,同时剥离了传统僧传的神圣化叙事,而替换以一种平实的书写,并且灌注了对人性的宽容与理解,以及与“人间佛教”相符合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因而展现的是一种“善”的生存模式。这种模式因为其“人间性”,而并不因作者的宗教身份而显得遗世独立,反而对读者来说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1]符芝瑛.传灯:星云大师传[M].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5.
[2]林清玄.浩瀚星云[M].台北:圆神出版社,2002.
[3]星云.星云日记[M].台北:佛光文化出版社,1994.
[4]星云.往事百语[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8.
[5]星云大师.合掌人生[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6]星云大师.无声息的歌唱[M].北京:中华书局,2012.
[7]星云大师.安住我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