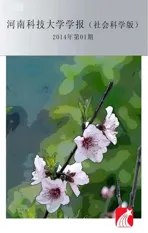论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之关系
2014-03-31王东洋
王东洋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史学新探】
论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之关系
王东洋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的关系,本质上是门阀制度与皇权政治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能够起到某种形式的考课作用,对于皇权政治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皇权政治的恢复能有效制约地方的分裂倾向,有利于国家的再统一。
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考课制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项重要选举制度,不仅对未入仕的士人进行品评,也对在职官员定期品评,对官员升降赏罚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魏晋南北朝的考课制度,不能不考虑九品中正制度的影响。有关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的关系,学界仅在论述九品中正制时偶有涉及,虽有学者提出九品中正制能起到考课职能,但缺乏有力的论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九品中正制与考课之关系,以及通过九品中正制所实施的考课与国家统一的关系。
一、中正定品与官员考课
(一)清议降品与官职变动
《三国志·刘廙传》注引《廙别传》载刘廙议政曰:“今之所以为黜陟者,近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耳……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而长吏执之不已,于治虽得计,其声誉未为美;屈而从人,于治虽失计,其声誉必集也。”刘廙认为,地方官的治理内容,如奉法、忧公、恤民等,一般会触及地方大族的利益,因此有的地方官虽治理较好但名声往往不好。地方官为求仕途升迁,必然要博取乡党名声,乡党的评价实际上成了地方官政绩的标准,对其升降产生重要影响。九品中正制正式运行后,昔日乡党的评价就转化为中正作出的清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正品第与官职高低相适应。唐长孺先生曾说,“中正品第并非只是一种褒贬虚名,而是和入仕途径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官位必须和品第相当,降品等于免官”,历史上所见明注降品的例子并不多,“但是不明说降品而实系降品的就很多,这些大概以犯乡议、清议,或者诏付乡议、清议来表示”。[1]116可见,中正品第的变动与官职升降有着互动关系。
时至东晋南朝,中正清议的范围更大,对官员职务升降也起到更大作用。东晋祖纳曾问梅陶有关“月旦评”之事,梅陶认为“善褒恶贬,则佳法也”。王隐问:“《尚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贬!”梅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2]1699在东晋时人看来,月旦评行“褒贬”就是某种形式的考课。九品中正制(公法)就是由国家将民间清议(私法)纳入国家控制的轨道而来,并保持了清议遗风。在职官员若违犯礼仪,其中正品第不被通过,即实施清议惩罚。《世说新语·尤悔篇》:“温公初受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驻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毎爵皆发诏。”注引吴承仕曰:“乡评不与,而发诏特进之。然则平人进爵,必先检乡评矣。”[3]温峤乡品(即中正品第)不被通过,进爵时需皇帝诏书特批,一般官员一旦乡品通不过,只能降职或禁锢。东晋孝武帝时,范宁上疏方镇去官时,“宜验其乡党,考其业尚,试其能否,然后升进”,“帝善之”。[2]1987所谓“验其乡党”,即考察其中正品第或听取中正评价。地方官或秩满离任或临时调离,都要对其综合考核,而考核品行时需听取中正的意见。以决其升降。
南朝对于遭受中正清议的官员,其官职或降或免。齐明帝建武元年十二月,“宣德太仆刘朗之、游击将军刘璩之子,坐不赡给兄子,致使随母他嫁,免官,禁锢终身,付之乡论”;[4]142萧梁后期,“(萧)斅时居母服,清谈所贬”。[4]1050此清谈即清议。南朝还将清议纳入律令,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法令。梁武帝天监元年规定:“士人有禁锢之科,亦有轻重为差。其犯清议,则终身不齿。”陈朝修订律令,“其制唯重清议禁锢之科”。[5]702张旭华先生认为,南朝中正仍然主持清议,且清议范围更广,处罚更重,威力更大,自刘宋以后,清议被逐步纳入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来。[6]206
南朝新皇帝登基,对先前遭受清议之人,一般会下诏予以荡除。宋武帝诏“其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7]齐高帝下诏“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先注,与之更始”。[8]梁武帝和陈高祖亦有类似诏书。周一良先生认为:“南朝清议倚靠王权,王权支持并可左右清议。但清议内容的标准和权威性,士大夫之不得违犯清议,则南朝与两晋没有很大差别。”[9]清议一方面是官职升降的依据,另一方面可起到震慑作用,使官员加强自身修养。从这个角度上说,东晋门阀政治已不可动摇,“九品中正制的考课作用也就无以体现了”[10]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北朝亦存在中正主持的清议。宣武帝景明年间,王温“寻简乡望,补燕国乐浪中正。品裁人物,升降有序,邦邑缙绅,比之水镜”。[11]北齐陈元康“不能平心处物,溺于财利,受纳金帛,不可胜纪,放责交易,遍于州郡,为清论所讥”。[12]343与东晋南朝相比,其清议力度和范围较小。
(二)中正参与谥号的评定
谥号是对去世官员的盖棺定论,好的谥号是极高的精神鼓励,并能给亲属带来相应的物质利益,对在世官员也能起到榜样作用。北魏中正参与谥号的拟定过程,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甄琛传》:
凡薨亡者,属所即言大鸿胪,移本郡大中正,条其行迹功过,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评议,为谥列上。谥不应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以实论。若行状失实,中正坐如博士。
此事发生在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由吏部郎袁翻提出。北魏议定谥号的一般过程是,属所将官员去世消息告诉大鸿胪,然后由中正提供死者行迹功过,再付太常审议,最后由博士评议定谥。太常博士所拟谥号若有异议需要重新拟定,有时甚至由皇帝下诏廷议才最终确定。其间,中正应提供去世官员的“行状”,即对已故官员“行迹功过”所作的总评价(考状)。6]291周一良先生认为,行状不仅序本人,而且需序三代。[13]可见,“行状”是官员一生治绩和品行的总概括,也从侧面反映了中正兼有考课的职能。
(三)中正参与武官军簿的管理
中正参与军簿的管理,南北朝都有相关记载。就北朝而言,《魏书·卢同传》载卢同向北魏孝明帝上奏云:“请自今为始,诸有勋簿已经奏赏者,即广下远近,云某处勋判,咸令知闻……或遭穷难,州无中正者,不在此限。”武官将士之军功记录在案,是谓军功文书。因战争频发和不可预见的原因,诸多军功文书得不到及时整理和保存,立功将士得不到及时封赏,出现了军功作弊等一系列问题。张旭华先生认为,北魏中正负有考察军功、校订勋簿和打击假冒军功等相关责任。[6]292南朝时,据《南齐书·高帝纪下》载建元元年十月诏曰:“……若四州士庶,本乡沦陷,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可听州郡保押,从实除奏。荒远阙中正者,特许据军簿奏除。”对于无中正的荒远之地,朝廷准许吏部根据军簿授官,而对于设置中正的州郡之地,则由中正提供品簿或类似材料,以便对武官考课。可见,中正官在武官考课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二、中正与吏部对考课权的争夺
吏部为考课主管部门,中正为官员中正品第的评定机关。中正与吏部的关系,从侧面反映了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的关系。两者之间的争论在魏晋南北朝不绝于耳。透过争论可以看出九品中正制在考课官员过程中的作用。
(一)魏晋时期
魏明帝时,傅嘏责难刘劭考课法时说:“方今九州之民……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才。”[14]此处“品状”指中正品第,“薄伐”指家世。所云“专任吏部”即吏部与中正分离,至少说明吏部在履职时没有参考中正品第,因此出现了品状和簿伐脱节的现象。至曹魏齐王芳时,有人则批评中正侵夺了吏部的职权。《三国志·夏侯尚传附子玄传》载齐王芳正始年间,夏侯玄议曰:
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
夏侯玄认为,原先尚书台和乡闾分掌铨衡和孝行,上下有序,但渊源于乡党评论的九品中正制度实施后,造成上下交涉,影响到台阁铨选;中正定品引起官员的职务升降,侵夺了吏部的铨选权。针对“吏部”与“中正”职权相侵现象,夏侯玄主张长官考课下属之才干,中正品评官员之德行,台阁汇总该官员才干和德行后,再决定升降赏罚。
针对曹魏中正与吏部相互侵权现象,吕思勉先生认为:“中正之弊,实由台阁不听官长考功校否之谈,而凭闾阎以意裁处之议也。”[15]钱穆先生认为:“中正评语,连做官人未做官人通体要评,而吏部凭此升黜,如是则官吏升降,其权操之中正,而不操于本官之上司。”[16]中正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侵夺了吏部铨选权,而这从反面证明,中正对官员的品评能够起到考课官员的作用。
西晋时期,规定吏部与中正共同完成选署任务。《册府元龟·铨选部》“条制一”条:“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若吏部所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这种制度设计相当好,在实际执行中却弊端重重。
晋武帝时期,刘毅对九品中正制的猛烈批评,多涉及中正与吏部的关系。《晋书·刘毅传》载刘毅主张废九品:
(九品)既无乡老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遂使进官之人,弃近求远,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党誉虚妄。损政五也。
所谓“品不校功”,即中正品第不能反映官员的治绩和德行,所定品第有悖考课之精神。刘毅接着说:
既以在官,职有大小,事有剧易,各有功报,此人才之实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则反之,于限当报,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损政六也。
刘毅认为中正品第与官员治绩相脱节有损考绩,助长浮华。从“上夺天朝考绩”看出,中正品第在西晋能起到某种形式的考课作用。
针对刘毅九品八损之论,元代史家马端临说:“品则中正可得而定,状则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为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状著于九品,则宜其难凭。要知既入仕之后,朝廷自合别有考课之法,而复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拘矣。况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当乎。”[17]在马端临看来,所谓“品”是未入仕者的品行评价,应由中正负责,“状”是已经入仕者的治绩表现,应由朝廷考课部门负责,而魏晋时期中正将官员治绩优劣纳入“品”“第其升沉”,在一定程度上侵夺了朝廷的“考课之法”,承担了部分考课职能。
(二)南朝时期
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遭到有识之士的猛烈批评,但东晋以降,批评之声大为减少。因为九品中正制实行了某种程度的变革,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东晋以降的九品中正制更倾向于对官员“品行”的评价,而对“治状”评论较少,便于与吏部配合。南朝由州中正或直接间接迁为吏部尚书(或吏部郎)的现象较为普遍,即使非直接迁转,担任州中正的经历对于吏部官员更好地履行选署职责,定有帮助的,更利于二者的相互配合。
《梁书·敬帝纪》载太平二年春正月诏:“诸州各置中正,依旧访举。不得辄承单状序官,皆须中正押上,然后量授……其选中正,每求耆德该悉,以他官领之。”经侯景之乱等几次动乱后,萧梁制度多有停废,故梁敬帝要恢复旧制。梁敬帝诏令诸州置中正,并规定必须有中正的画押,吏部才能授官,这反映了萧梁中正参与了吏部选署标准的制订。不过“中正押上”制度需要皇权下诏规定,或许可以从反面证明,萧梁中正职权有所下降,需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来保障中正的权力。这与魏晋时期中正侵夺吏部职权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北朝时期
北魏中正与吏部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中正参与吏部铨选、吏部与中正分工到“专归吏部”等过程。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七月诏曰:“自今选举,每以季月,本曹与吏部铨简。”[18]170北魏中正既以“季月”参与吏部铨选,则中正的意见对官员考课有着重要影响。
中正官与吏部官员相互兼职,反映了中正与吏部关系的协调。州中正兼任吏部尚书者,如北齐后主时,袁聿修“寻除都官尚书,仍领本州中正,转兼吏部尚书”。[12]565考功郎中兼任中正更能说明问题,如北魏宣武帝时期,裴佗身兼考功郎中和郡中正。即使不兼任,由考功郎直接迁转中正,也能说明二者的密切关系,如宣武帝时,封轨不辱使命,“转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18]765
北魏后期,中正定品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吏部职权进一步扩大。孝明帝时,刘景安与崔亮书信中说:“魏晋因循,又置中正……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业,空辨氏姓高下。”崔亮答书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18]1480可见,时至北魏后期,中正定品标准不再是士人或在职官员的德行而是门第,九品中正制已经成为门阀士族垄断其地位的工具。由崔亮所言可知,北魏后期吏部权限极大,中正侵夺吏部职权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到了隋朝,官员选举任命考课全归吏部,两者矛盾最终以中正的退出而得到解决。
由上观之,中正与吏部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分工不明、相互侵夺对方职权时期(魏晋);其二,中正与吏部逐渐相互兼容、参与配合时期(南北朝);其三,选署专任吏部、中正逐渐退出时期(隋朝)。中正所起的考课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官员“品行”的评定上,“政绩”由吏部负责考核。吏部与中正由冲突走向融合,共同完成了对官员“政绩”与“品行”的评定。
三、九品中正制与汉唐考课制
探讨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的关系,亦可从汉唐考课制着眼,考察汉代考课制对九品中正制度的影响,及九品中正制对隋唐考课制的影响。
(一)汉代考课制对九品中正制的影响
中正品第分为九等受到汉代考课的影响。唐长孺先生认为:“品分为九等也由来已久……这在两汉大概是流行的办法,”[1]109廖伯源先生进一步认为,九品中正制度的操作办法受到汉代考课制度的启发和影响,两者都分为九等。[19]
此外,中正定品时提供的“状”亦与汉代考课评语有关。唐长孺先生认为,中正之“状”是一种总的评语,其渊源是出于汉末名士的名目或题目,而非源于比较具体的“行状”。[1]107廖伯源进一步认为,九品品评人物之“状”渊源于汉末名士的标榜语,名士标榜语则溯源于汉代考课的评语。[19]
九品中正制既受到汉代考课制的深刻影响,则其暗含考课的精神当是势所必然。
(二)九品中正制对隋唐考课制的影响
隋唐时期,考课实践中出现新的评语方式——“考词”。隋文帝开皇年间,卢昌衡“出为徐州总管长史,甚有能名。吏部尚书苏威考之曰:‘德为人表,行为士则。’论者以为美谈”。[5]1404苏威亲自考课官员,考语简洁明了涵盖了官员的政绩和德行,与魏晋中正评语非常相似。隋炀帝时,敬肃迁颖川郡丞,“大业五年,朝东都,帝令司隶大夫薛道衡为天下群官之状。道衡状称肃曰:‘心如铁石,老而弥笃。’”[5]1685司隶大夫对郡丞评价,包含着上司对下官考课的意味,可视同于考词。
唐代皇帝常为重臣书写考词以定考第。唐太宗曾为大理卿唐临书写考词曰:“形若死灰,心如铁石。”[20]唐玄宗为中书令张说写考词曰:“动惟直道,累闻献替之诚。言则不谀,自得谋猷之体。政令必俟其增损,图书又藉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21]可见唐代某些考词,略同于汉末名士的题目,更可能受到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之“状”的影响。
汉唐考课制度相对完善,处于期间的魏晋南北朝,其考课制度却由于皇权相对弱小而被有些学者认为不复存在,此误。研究发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与汉唐考课制有着密切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九品中正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考课的功能。
四、结语
从中正的职能看,中正对违犯清议的官员进行降品,伴随而来的是降职或免职,中正品第在官职变动中发挥了考课作用;中正参与去世官员谥号的评定和武官军簿的管理,均发挥了某种形式的考课作用。从中正与吏部的关系看,在门阀士族居于主导地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吏部职权降低甚至被虚化是客观事实。由中正对官员进行定品以对官员黜陟产生影响,表面上看是侵夺吏部的职权,但本质上仍是某种形式的考课,从长远看来有利于吏部职权的恢复和强化。或许更进一步说,中正侵夺吏部的铨选职权,对在职官员定品以决定升降赏罚,正是九品中正制发挥考课作用的表现形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使没有中正侵夺吏部职权,吏部也不能独立地行使对门阀士族为官者的考课权。当皇权重振时,国家必然强化对官员的管理,选举与考课的大权专归吏部也是势所必然。
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的关系,本质上反映的是门阀制度与皇权政治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大族垄断选举的时代,地方大族通过乡论控制地方选举,并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显著优势,形成与皇权相抗衡的力量。地方大族起家官品较高,升迁较快,多担任高级官职,对其如何考课,是皇权必须解决的问题。九品中正制对于士族门阀的“品行”评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因门阀士族强大而造成的皇权考课的缺失。九品中正制能起到某种形式的考课作用,正是门阀制度下考课制度所具有的特征之一,对于皇权政治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中央皇权政治的恢复又能有效制约地方的分裂倾向,有利于国家的再统一。
[1]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M]//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2]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902.
[4]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7]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52.
[8]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32.
[9]周一良.两晋南朝的清议[M]//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43.
[10]杨普罗.关于魏晋官吏考课制度研究的两个问题[J].甘肃社会科学,1995,(2):80-82.
[11]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5:134.
[12]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3]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366.
[1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623.
[15]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931.
[1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3.
[17]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342.
[18]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9]廖伯源.汉代考课制度杂考[J].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2002,(42):1-20.
[20]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54.
[21]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504.
A Discussion on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ine-rank System and the M erit System in W 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ANG Dong-yang
(Humanities Institute,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23,China)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ine-rank system and the merit system essentially reflected the linkage between powerful Family System and Imperial Power Politics.In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the Nine-rank Appraisal System played some role ofmeirt system and improved the recovery of imperial power which not only restricted local division but also benefited re-unity of the country.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the Nine-rank System;the Merit System
K235
:A
:1672-3910(2014)00-0020-05
2013-01-21
2013年度洛阳社科规划项目(2013B200)
王东洋(1977-),男,河南鹿邑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