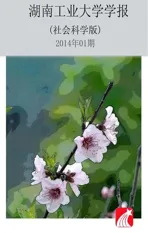对“嫖宿幼女罪是恶法”的一点思考*
2014-03-31宁利昂
宁利昂
(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对“嫖宿幼女罪是恶法”的一点思考*
宁利昂
(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嫖宿幼女罪最富争议之处在于其刑罚配置。相对强奸罪而言,该罪没有设置无期徒刑、死刑,因而给人以刑罚力度不够之感而受到强烈的批判。如细究之,该罪与强奸罪本来就存在构成要件的差异,并且,该罪的基本犯和加重犯可以在设定的刑罚区间内得到相应的匹配。因此,嫖宿幼女罪并不需要通过法条竞合等解释来适用强奸罪之加重犯的刑罚,其现行刑罚配置完全能够在罪刑均衡的评判下获得解释论上的足够合理性。
嫖宿幼女罪;刑罚配置;强奸罪;解释论
近年来贵州习水等地陆续发生的嫖宿幼女事件,引发了刑法学界沉寂已久的关于嫖宿幼女罪的集中讨论,其涉及到对构成要件的理解、对刑罚配置的衡量以及对此罪彼罪关系的考察等诸多方面。在这场讨论中,最为热闹的也许要算“嫖宿幼女罪是否为恶法”的争论了,在下文中,笔者争取通过对其中较为关键之处的把握,来做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一 恶在哪里?——对嫖宿幼女罪的初步考问
嫖宿幼女罪在近几年来受到异乎寻常的猛烈抨击与鞭挞,以至于被冠上了“恶法”的名头。这种认识,不仅在普通百姓中散播开来,也在不少刑法学者的论文当中有所体现。那么,嫖宿幼女罪到底是不是恶法,相应的认识又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呢?对此,笔者就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
其一,关于嫖宿幼女罪的相关刑罚打击力度不够的说法。对于嫖宿幼女罪的反对,主要是对其刑罚配置的反对。我国刑法规定,嫖宿幼女罪的相关刑罚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为罪不至死,也没有无期徒刑的设定,使得嫖宿幼女罪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反观奸淫幼女型强奸罪,其刑罚以一般强奸罪的刑罚为参照,从重处罚。并且,在强奸罪的刑罚设置中,既有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又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覆盖范围甚广。因而,嫖宿幼女罪在奸淫幼女型强奸罪面前,既失之于刑罚幅度偏窄,又失之于更重刑罚的缺乏,难免给人以一种打击力度不够、有放纵犯罪之嫌的直观感觉。但是,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卖淫、嫖娼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 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如将嫖宿幼女罪与一般的嫖娼行为的相关处罚进行比较,一个最少5年以上有期徒刑,一个最高15日的拘留,这其中的时间跨度是相当巨大的。如以此比较为观察对象,便可得出与前述比较完全不同的认识,即对嫖宿幼女罪的刑罚打击力度因显著强于对一般嫖娼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而不能不谓之为一种严厉的处罚。因此,对于嫖宿幼女罪的刑罚配置及其打击力度的非议,企图从其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相关刑罚的简单比较中得到绝对的说服力,在笔者看来是一种片面之词,其实质是重刑主义思想在作祟。
其二,关于嫖宿幼女罪有污名化被害人的可能的说法。对于嫖宿幼女罪的另一微词,即其字面本身含有贬低、折损作为被害人的幼女的人格及尊严的倾向。换言之,存在这样一种社会认知的假设,即,尽管同为被害人,被嫖的幼女和被奸的幼女遭遇的社会评价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相对后者而言更不受待见,而后者相对前者而言更值得同情,因而该罪名并没有尽到对被嫖的幼女的彻底保护。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笔者并不否认社会中存在这样的情形,即忽视或无视幼女相对于妇女更应值得保护和关爱的特殊性而将卖淫的幼女与卖淫的妇女予以同一性歧视。但是,笔者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缺乏人文关怀的认识绝不是作为整体之社会的基本认知,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会愈来愈少。其次,嫖宿幼女罪的“嫖宿”二字确实对人们认识相关案件中幼女行为的基本内容具有提示意义,但是,对于该罪名的司法认定是在特殊的场所和流程中进行的,现有制度完全可以给予案中被害人以足够的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3条规定,有关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在实践中,对诸如嫖宿幼女罪、强奸罪等牵涉到个人隐私或未成年人的案件,司法机关依法不公开审理的做法实属常见。因此,除非出现类似办案人员渎职、媒体越界报道等非正常情形,嫖宿幼女罪使具体个案中的被害人名誉受损的说辞只能是没有事实基础的揣测和想象。再次,就嫖宿幼女罪本身而言,对于“嫖宿”的理解也应当在事实陈述的层面上进行,而不能以带有歧视性、侮辱性的价值评判观之。如果遵从价值评判而非事实陈述的逻辑,那么所谓的“嫖娼”也要改名换姓,因为女性权利的维护在妇女这里与在幼女之处同样具有必要性,程度的不同不足以撼动这种必要性。由此可见,对嫖宿幼女罪之罪名污名化被害人的指责,尽管是出于真诚的呐喊,但并非理性的思考,实属牵强而不能成立。
其三,关于嫖宿幼女罪的体系定位不具有适法性的说法。对嫖宿幼女罪法律定位不准确的批评,主要来自于从事刑法研究的学者。我国有刑法学者指出,现行刑法将嫖宿幼女的行为归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明显不妥,因为嫖宿幼女行为侵犯的主要法益是幼女的身心健康而非社会管理秩序。[1]此外,也有刑法学者指出,我国刑法将对幼儿的性剥削和性侵犯移到刑法分则第6章第8节,说明风化管理秩序优先而非幼儿的性心理、性生理健康权益优先的立法取向,有悖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优先保护原则。[2]对于上述关于嫖宿幼女罪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位置不具有合适性的论断,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笔者是基本赞同的。因为,从犯罪分类的条理化和有序化来看,将有关行为侵犯的法益或侵犯的主要法益作为区分不同犯罪的标准,既有助于避免立法上的含混不清与歧义丛生,又对司法上的准确认定具有较大指导作用,作为刑事立法的努力方向之一是值得肯定的。以此观之,现行刑法对于嫖宿幼女罪的归类,确实给人们带来了理解上的困扰,存在将相关秩序而非幼女的身心健康作为优先法益的误导可能,因而是应当予以批判的。然则,理想的立法并非现实的立法。立法活动的复杂性、运动性和可能存在的便宜性以及各种未知因素,共同形塑了现实中的法律,因而又必然决定了上述取向无法完全和绝对的实现。事实上,我国刑法中还存在其他的类似情况。比如,我国有刑法学者指出,尽管走私淫秽物品罪被放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但不能认为其侵害的法益是经济秩序而应当是社会的性风尚;走私毒品罪曾与普通走私罪一同规定在单行刑法中,在九七刑法后又被纳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这种归类的变化并不能证明某种犯罪侵害的法益也发生了变化。[3]对此,笔者也认为解释得当。由此,以刑法分则的宏观视野观之,嫖宿幼女罪侵犯的法益与其本身在刑法中的体系定位的不适恰,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问题,遭受基于理想立法论的批判是应当也是必然的,但是,相关问题所带来的实际危害并非就真正如其批评者所描述的那般巨大,通过成本更低的解释论上的审查后,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得到有效化解的。
至此,可以归纳如下:在法定刑上,嫖宿幼女罪固然缺少无期徒刑、死刑的设置而轻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但并非意味着其就一定属于轻法的范畴,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论证来予以明晰;在罪名的指示意义上,对嫖宿幼女罪污名化被害人的非难,由于相关保护机制的现实存在及论者本身就存有价值预判的倾向,而只能视为真诚的关怀而非理性的结论;在罪名的体系定位上,相关批判能够取得理想立法论的支持,但在解释论的帮助下又可以暂时搁置一旁。由此,关于“嫖宿幼女罪是恶法”的论断在上述理由中并未得到强有力的证明,加之其并非没有承担打击相关犯罪的功能负载,也与其他罪名的设置一样内在地具有保护法益的价值追求,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嫖宿幼女罪并非是十恶不赦和一无是处的。
二 刑罚轻吗?——对嫖宿幼女罪的进一步考问
经过前述对嫖宿幼女罪的思考,若干认识及其合理性程度得到了初步的呈现。然则,倘若讨论停留于此,有关嫖宿幼女罪的困惑仍未得以真正和彻底的解决。因为,针对“嫖宿幼女罪是恶法”的观点持有者的第一个非难而言,尽管可以反驳说嫖宿幼女罪之刑罚力度不够的认识是受到了重刑主义非理性冲动的驱使,但直至目前为止,还未从正面来直接说明嫖宿幼女罪的刑罚配置是恰当与合适的,因而也就不能对嫖宿幼女罪是否为恶法的疑问做出确切的解答。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讨论。
在方法论上,对嫖宿幼女罪刑罚配置适恰性的探讨大多遵从了这样一种路径,即将其放置于我国刑法的整体架构中来予以评判。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梳理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关系,来比照各自的刑罚适用,评价其合理程度,并做出可能的调整。这些工作,都是在解释论的范畴中来进行的。在相关研究中,大致形成了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其一,两罪互斥论。其论者认为,通过区分同意能力的有无(或同意有效与否)来区分作为不同对象的幼女进而区分不同犯罪(嫖宿幼女罪或强奸罪),有利于保护幼女和保障人权的平衡,也使得两罪无法形成竞合关系而导致有关刑罚失衡的问题不再成为关键。[4]申言之,该论者主张两种犯罪的对象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决定了两种犯罪完全是相互隔离、各自独立的,需要关心的应当是构成要件的符合性问题而非两罪刑罚轻重的问题。应当说,两罪互斥论的提出是有其意义所在的,即作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的真伪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并且不难看出,该主张实际上蕴涵了贯彻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精神。然而,这种主张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暂且将来自其他学者在被害人同意与被害人过错等方面的异议搁置一旁,可以先提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嫖宿妇女是治安违法行为而嫖宿幼女构成犯罪?要知道,如果认为被嫖宿的幼女具有同意的能力或者其同意是有效的,那么结合被嫖宿的妇女同样也具有同意的能力或其同意也是有效的这一情形,应当认为嫖宿妇女的行为相比奸淫幼女型强奸罪而言更具有与嫖宿幼女罪的性质类同性,因为被奸淫的幼女无论是在通说中还是该论中都被认为是无同意能力或者说其同意是无效的。以此推之,嫖宿妇女的行为应当以犯罪论处,而不应视为一般的违法行为。事实却与此相反,嫖宿妇女的行为不是犯罪,而奸淫幼女的行为是犯罪,后者相比前者更具有与嫖宿幼女罪的性质类同性,即都为犯罪。这样的划分,根本就是由国家保护幼女身心健康而以14周岁划线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两罪互斥论尽管在部分的逻辑论证上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在整体的逻辑论证上难以做到周全。不得不说,就解释论而言,该论绕过刑罚适恰性问题的努力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
其二,法条竞合论。反对两罪互斥论的学者,基本都赞同嫖宿幼女罪和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立法沿革上,嫖宿幼女罪曾经是作为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当然内容来予以处理的。其次,嫖宿幼女罪可以解读为卖淫的幼女这一要素加上挖去幼女这个部分的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其他要素,亦即嫖宿幼女的行为可视为特殊的奸淫幼女的行为。应当说,两罪之间是法条竞合关系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实际上,也正是由于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这种关系,给许多人的两罪刑罚亦当基本类同的心理认识提供了生长空间。不过,在两罪关系上达成了基本共识的法条竞合论的主张者们,在进入具体理解后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样本。有论者明确指出:“《刑法》第360条第2款规定的嫖宿幼女罪,明显只能理解为236条第2款强奸(幼女)罪的特别条款,而不是整个强奸罪或第236条的特别条款”。[5]以此为基础,该论者在处断上采取了这样一种策略,在适用5年以上有期徒刑还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场合,因为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构成了法条竞合关系,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完全能够以嫖宿幼女罪定罪处罚,此时对应的刑罚也是相对偏重的;而在适用5年以上有期徒刑还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场合,“既然嫖宿幼女罪只是与第236条第2款存在法条竞合,则一旦出现第236条第3款所规定的加重情节,对嫖宿人就能够也应当根据该款以强奸罪进行处罚”。[5]若只看整体效果,对嫖宿幼女罪的处罚形成了从5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死刑的这么一个跨度,显然足以反驳有关嫖宿幼女罪的刑罚相对过轻而属于恶法的说辞。但是,不能不说这种看似有效解决了问题的处断策略的理由是存在重大纰漏的。因为,刑法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实质上是关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基本犯的规定,只是对于这种基本犯应当比对一般强奸罪的基本犯来从重处罚,而在刑法第236条第3款中,同样存在关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规定,并且属于加重犯的规定。申言之,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奸淫幼女多人的、二人以上轮奸幼女的及致使作为幼女的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都应当构成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加重犯,比对一般强奸罪的加重犯从重处罚。由此,如若在基本面上肯定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就应当逻辑一致地肯定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加重犯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而非只是片面地承认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基本犯之间的法条竞合关系。可见,采取前述策略固然让人眼前一亮,但其依据在经过推敲之后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对于上述策略合理性的补救性说明,或许可以尝试采取另一种方法。首先,既肯定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基本犯之间的法条竞合关系,也肯定前罪与后罪的加重犯之间的法条竞合关系。其次,在处断原则的运用上,遵循“重法优先于轻法”的原则。如此一来,在适用5年以上有期徒刑还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场合,采重法以嫖宿幼女罪进行处罚;在适用5年以上有期徒刑还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场合,采重法而以奸淫幼女型强奸罪进行处罚。有论者便是以这样的路径来支持前述的组合配刑策略的,其核心理由为:“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按普通条款规定定罪量刑,但对此也没作禁止性规定,而且按特别条款定罪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时,按照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定罪量刑”。[6]应当说,这样的逻辑解释更能自圆其说。但,即便如此,也并非毫无可商榷之处。第一,法条竞合中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之适用原则的确立是有其特殊使命的。可以做如下分析:若普通法轻于特别法,此时特别法为重法,适用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之原则的结果(采用特别法)与适用重法优先于轻法之原则的结果(采用重法)是同一的;若普通法重于特别法,此时特别法为轻法,适用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之原则的结果(采用特别法)与适用重法优先于轻法之原则的结果(采用重法)是相悖的。可见,只有在后项情形中,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适用原则才体现出其存在意义,否则,根本没有确立该原则的必要而一律适用重法即可。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法条竞合中除非出现法律明文规定按照重罪处罚的情形,否则应当严格遵守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第二,在法条出现竞合而刑法又没有明确如何处罚的情形下,如若认为重法优先于轻法的原则与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能够并存而无论如何选择适用都为可行的话,那么,将导致法官获得一种事实上的责任豁免,使其有机会来实施以纯粹为了取悦舆论或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的裁判行为,有引发司法道德风险的可能。
至此,相关探讨已经在此罪彼罪关系之梳理的道路上走得颇久了,而从中得到的反馈也大多为嫖宿幼女罪的现有刑罚配置不足以应对一些较为严重或特别严重的情形,而需要通过解释论上的相关策略来进行一定的调整。然而,笔者并不这么认为。嫖宿幼女罪的刑罚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则最高刑罚可以达至15年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嫖宿幼女罪的最轻情形与最重情形之间的刑罚跨度可以达到10年!的确,这个刑罚跨度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刑罚跨度即3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跨度比起来是绝对缩窄的,但是,要知道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基本犯的刑罚区间也就在3年至10年有期徒刑之间,并且因为其要相对一般强奸罪从重处罚,则其基本犯的刑罚跨度就更少于7年了。用10年的跨度来比对少于7年的跨度,笔者只能认为嫖宿幼女罪的现行刑罚配置不仅包括了基本犯的对应部分,更包括了加重犯的对应部分。因此,“嫖宿幼女罪是恶法”之观点的持有者所说的刑罚过轻的理由,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是简单的直观感觉而非慎重的理性思考。也正因为此,尽管笔者不敢断言嫖宿幼女罪的刑罚配置在立法论上是无可挑剔的,但笔者相当肯定嫖宿幼女罪的刑罚配置在解释论上是可以立足的,因而笔者又走向了组合刑罚策略主张者的对立面。
三 回到问题之初——考问之后的一点反思
在两次考问之后,笔者的观点已经很清楚,即在解释论上,嫖宿幼女罪的现行刑罚配置不必进行重构,亦无需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刑罚形成组合,其具有相当程度的适恰性。当然,解释论上的认识是一个方面,并不排斥其在立法论上进行修改,但是,这种修改的原因要么是前文中谈到的犯罪分类的立法技术问题,要么是压力型立法的又一个示例,而绝非实质意义上的刑罚力度不够或者说刑罚轻重失序,因此,尽管笔者与两罪互斥论者得到的结论具有很大相似性,但内在的推理逻辑则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在经过两次考问之后,笔者也不禁想回到相关问题的起点,来重新审视一下讨论是如何开始的。
对嫖宿幼女罪的诸多非议,最主要的是对其刑罚配置相对过轻的指责,应当是无疑问的。假如其规定了死刑或无期徒刑,或许当前的这场讨论根本就不会发生(又或者,讨论完全调转了方向,而变成了对于嫖宿幼女罪的刑罚设置是否过重的思考。当然,在当前境况下,这种情形是难以发生的)。那么,究竟是何种内在的运作力造就了嫖宿幼女罪的当前立法?在嫖宿幼女罪的刑罚配置的表象下,蕴涵了怎样的价值追求呢?众所周知,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究其根源,可归结为法律父爱主义的适用与体现。我国有法理学者指出,西方的法律父爱主义理论主张政府可以在某些领域为了公民自身的利益而不顾后者意志来限制其自由,并且该理论已经在合同法、行政法和宪法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7]实际上,法律父爱主义在我国刑法领域也同样发挥了较大的影响,例证之一,便是将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一并规定为犯罪。在这两处,刑法以类似父亲的角色将未满14周岁的幼女定位为了需要关爱的女儿,通过刑罚打击侵害幼女的行为来实现类似父亲对女儿应尽的责任。另一方面,刑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罪刑均衡原则的确立。在自愿的前提下,嫖宿幼女罪中的幼女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是建立在交易基础之上的,而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中的幼女则是基于情感或生理的需要,不以获得金钱或其他财物为目的。如果说,因为幼女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性质不一,造成了不同行为人相关行为严重性程度的大小不同,进而导致对不同行为人相关行为的处罚严厉性大小的区别,应当认为是没有违背罪刑均衡原则的基本逻辑的。因此,法律父爱主义与罪刑均衡原则共同赋予了当前嫖宿幼女罪的刑罚配置以解释论上的合理性。
然则,正是这样的立法,被许多人认为是实行了区别性对待,亦即对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中的幼女实行的是严格保护,而对嫖宿幼女罪中的幼女实行的却是有限保护。如有论者指出:“从是否承认幼女性自主权和性决定权来看,强奸罪一律否定,而嫖宿幼女罪却予之肯定,态度前后冲突、自相矛盾,严重损害了刑法的严谨性和权威性”。[8]笔者深切地体会到这些论断、见地和认识的出发点是良好、善意而无可诟病的。但是,这些对当前嫖宿幼女罪相关规定的反对、批评与痛斥,究其本质而言,是属于不同立场的表达,也就是说,是对刑法父爱到底要关怀到何种程度的不同理解,是对罪刑均衡原则到底要落实到何种情形的不同意见。于此,笔者也就不再多言了。因为,价值立场不同的问题,已超出了解释论评判孰优孰劣的范畴,而只能留待立法论去予以抉择了。
[1]张永红,吴茵.论嫖宿幼女行为的刑法规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11):46-49.
[2]屈学武.关于取消嫖宿幼女罪的立法反思[J]法治研究,2012(8):60-64.
[3]刘明祥.嫖宿幼女行为适用法条新论[J].法学,2012(12):134-142.
[4]车浩.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的关系[J].法学研究,2010(2):136-155.
[5]劳东燕.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的关系新论[J]清华法学,2011(2):33-47.
[6]张明楷.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关系[J].人民检察,2009(17):8-12.
[7]孙笑侠,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J]中国社会科学,2006(1):47-58.
[8]但未丽.嫖宿幼女罪存废之再思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12):32-37.
责任编辑:黄声波
Thoughts on the Saying“Crime of Prostituting Girls under the Age of 14 is an Evil Law”
NING Li'ang
(School of Law,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 China)
The penalty configuration is themost controversial topic in the crime of prostituting girls under the age of14.Compared with the crime of rape,no life imprisonmentand death penalty are set.So itseems that the punishment of this crime is not severe enough,and thus leads to strong criticism by some people.If take a closer look,however,we will fi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crime and the crime of rape in constituentelements.Besides,both basic crime and aggravated crime can get corresponding punishment in this punishment range.Thus,there is no need tomatch the punishment of aggravated crime of rape with the crime of prostituting girls under the age of 14.The existing penalty configuration can obtain enough rationality from the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 between crime and punishment.
crime of prostituting girlsunder the age of14;penalty configuration;crime of rape;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D924.34
A
1674-117X(2014)01-0087-05
10.3969/j.issn.1674-117X.2014.02.016
2013-10-18
宁利昂(1983-),男,湖南湘潭人,湖南大学教师,博士,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刑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