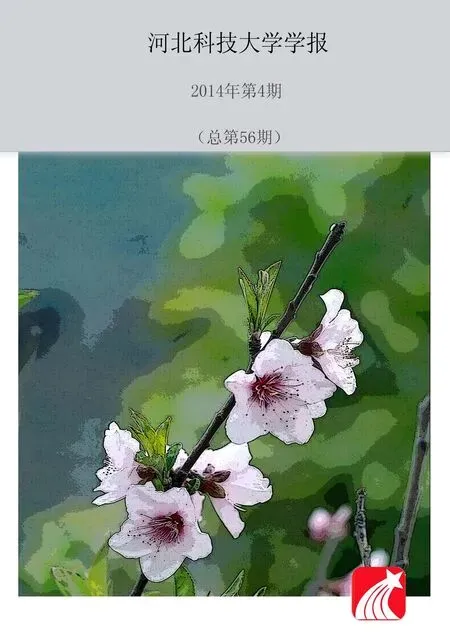论清代女词人赵我佩的“病、瘦”言说
2014-03-30骆新泉
骆 新 泉
(徐州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一 、赵我佩《碧桃仙馆词》简介
20世纪学术界对清代女性词的研究,源于徐乃昌在19至20世纪之交所做的对明清女性词文献的整理工作。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宣统元年(1909),历经15载,徐乃昌共辑录明末至清代闺秀词100家,汇编成《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以下简称《汇刻》)十集。《汇刻》中除了沈宜修、叶纨纨、叶小鸾母女三人系明末清初闺秀词人外,其他97位皆为清代闺秀词人,所以,《汇刻》实则是一部清代闺秀词的大型丛刻。《汇刻》存词多达5 100余首,数量是《全宋词》中宋代女性词作总量的近30倍,成就更远超前者,但至今为止,学界对后者的研究可谓应有尽有,而对前者的研究却远不够重视,仅涉及徐灿、吴藻、贺双卿、席佩兰、沈宜修等29人有专文讨论,且多数是仅有1或2篇论文涉及,而绝大部分词人及词作尚无人问津,这其中就包括词作数量可观的赵我佩、李佩金、苏穆、关锳、吴尚熹、吴绡、邓瑜、刘琬怀、张玉珍、俞庆曾等人。在众多无人问津的清代闺秀词人中,赵我佩更是词作数量多达173首且成就很高的一位女词人,词集名《碧桃仙馆词》(以下简称《仙馆词》)。
《汇刻》言赵氏夫名砺轩,而不知姓氏:“赵我佩,字君兰,仁和人。赵庆熺女,□砺轩室。”[1]谭正璧先生编写的通代女性词史话《女性词话》有所补充:“赵我佩……赵秋舲的女儿,家学渊源,亦工词令。所著《碧桃仙馆》词,以轻圆流丽,传诵一时。”[2](P98)清同治年中程秉钊清写底稿本《仙馆词》扉页中交代赵氏丈夫姓张:“我佩字君兰,适同里张氏,工于词,五律亦饶有中唐风味,据程秉钊氏序,称其‘体至孱弱,工愁善病,然饮酒至豪,言论磊落,有不可一世之概,人恒怪之,殆非凡女子’云。……其词清丽婉约,弥足珍视。”[3]据此我们得知赵我佩嫁给同乡人张砺轩为妻,赵氏体弱多病,善长短句,工愁善病,饮酒至豪,言论磊落。然我们今天已无法考证赵我佩的生卒年代,也无法确定其是否因“体至孱弱”而英年早逝。依照常理,倘若张砺轩先于赵氏离世,而赵氏又是一位以词传世的作者,理应在其《仙馆词》中保留一些悼亡夫的词作,但事实却是一首也没有,故推知赵氏实际先于丈夫离世;“工愁善病”言其因体质的至弱多病而导致其词作的内容多言及自身的疾病愁苦,故赵氏词作中多用“病、瘦、慵、懒、憔悴”等意象来言说自己的“愁、伤、恨、独、断肠”情怀,也就不足为怪了。据笔者统计,《仙馆词》中有大量疾病言说,具体数据如下:“病”—33、“瘦”—42、“慵”—12、“懒”—13等,其他还有“憔悴”—12、“倦”—18、“无力”—14等,合计高达144次,占全部词作的83.24%。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仙馆词》的绝大部分词作皆言病、言愁,少部分的词作中虽然没有出现“病、瘦”等字句和意象,但其内容仍在言病、言愁,难怪程秉钊要称其“体至孱弱,工愁善病”了。赵氏不仅在其词集中大量运用这类字句和意象,更因能巧妙运用这些词句及意象表情达意,达到极高的境界。《仙馆词》中的“病、瘦”不但记录了赵氏受苦受难的身体感受,也记录了赵氏受苦受难的心灵感受。她通过疾病所导致的苦难和情感上的残缺来唤醒自己及同时代的女性长期以来对疾病苦痛煎熬及夫妻离居造成的情感缺失的麻木,使时人在病与瘦、愁与恨中找寻迷失的自己,并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可以说赵氏词以自己独特的“病、瘦”言说参与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来,为后世读者竖起了一座“病、瘦”词的丰碑。
二、赵我佩词中的“病、瘦”言说
作为人类不可避免的生理现象,疾病始终是古今中外文学表现的必然主题,疾病和疗救疾病的主题“成为仅次于爱与死的文学永恒主题。”[4](P80~87)在诗词中言说“病、瘦”并非赵氏独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似乎对身体从来就是使用文化态度对待的。”[5](P49~50)杜甫客居成都期间,约270首草堂诗充斥着“病”意象,仅以“病”为题的诗就有《病柏》、《病桔》、《枯棕》、《枯楠》等。南宋吴梦窗晚年贫病交加,又兼失去爱妾,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挤压使他形销骨立,词中“瘦”意象颇丰。宋代及以后,诗词中充斥着“病、瘦”意象,尤其对“瘦”情有独钟:人瘦、物瘦、春瘦、天瘦等。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指出,“意象真正的功用是:它可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6](P57)古代文学中的这些“病、瘦”字句和意象,或以人比拟物之病瘦,或借物之病瘦喻示人之病瘦,或通过景物情境的层层铺垫和渲染突出人之病瘦,总之,“藉人与物‘瘦’的意象,强烈、深刻地抒写词人的愁苦之情。”[7](P121~126)男性文人如此,女性文人亦不例外,李清照就很善言瘦:“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点绛唇》);“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等,由伤嗟红瘦、花瘦、人瘦,隐喻人生短暂、形体消瘦。其实,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物象未必就是“瘦”,但词人心中之“愁”使得其在观照自然景物时,因系“以我观物”,故易安词中之景瘦、人瘦归根结底源于词人心之“愁”,花之“瘦”在于“愁”人之观感。由此可见,女性文人的“病、瘦”言说亦普遍存在且由来已久,只是学界对其长期忽视而导致研究的滞后罢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当代女评论家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一书发表,才真正开启了关于疾病隐喻的研究大门。
所谓“疾病的隐喻”,首先强调的是疾病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学概念,更是一个与社会、文化和文学种种语境相关联的概念。这样,疾病不但是作者个性的象征,而且成为“一种强烈展现内心世界的语言,即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桑塔格认为,疾病本身就是一种诉说欲望的表达:“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表述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8](P41)长期以来,学者一直注重于疾病隐喻的社会与文化内涵,而忽略了它与性别文化象征之间的必然且复杂的关联。事实上,疾病隐喻一直就有性别化的倾向,这一点在女性书写上体现得尤其明显。首先,女性的弱势身份与疾病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其次,在女性作家笔下,疾病参与建构了女性的自我主体,是一种身体欲望的表达方式;再次,同一类发生在男女两性身上的疾病,会获得不同的隐喻内涵。
赵我佩的疾病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真实的疾病言说,如因病后体弱而“病余怕倚回廊”(《清平乐》);因“病魔不肯随春去。抵死缠绵住”而“半晌起来无力、整花钿”(《虞美人·寄外》);“病中心绪厌喧哗”本是病中人之常情,也是“低语小鬟帘外、步轻些”(《虞美人》)的个中原委,“掩湘奁,笼翠袖。病到春分,病到春分后”(《苏幕遮》),是言说身体的疾病自冬至春一直未见好转,也是词人在“风雨连宵又”、“红染飞花瘦”、“百折回阑□倚久”的百无聊赖中的真实写照,“病余鸾镜掩青铜”(《鹧鸪天》)是在“眉敛翠,颊销红”的疾病折磨下爱美女性的必然行为。《百字令》则直接用“病中有感”为词题,并且点明是肝病。词人还有2首以“瘦”为题的词:《菩萨蛮·瘦》与《沁园春·瘦》,分别有“病余何事眉峰削,珊珊锁骨衣棱弱”和“怅年来病减,丰姿顿改”句,显然,这两首以“瘦”为题的词皆系疾病词。值得玩味的是,病中的赵氏以“肩如削玉,云样衣裳水样绡”、“意态犹娇”来告知自己(包括读者),即便身处病中,自己仍然是一位美人。词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是“美人消瘦”(《点绛唇·对镜》),同时暗示那位没有出场的丈夫:黄昏后,灯前月下,词人顾影魂销,丈夫若顾己病中之影,亦当魂销。李蓉言:在晚清至“五四”以来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女性疾病被赋予了非常浓厚的国家、民族及阶级特征,当女性在她们的文学创作中主动言说自身疾病时,“疾病就不再是一种社会、文化强加到她们身上并且要摆脱的命运,而是她们不得不领受的生命处境。”[9](P9~15)赵氏虽然并非处在晚清至“五四”那个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但词人有意识地在词作中反复强调自身的病瘦形象和愁苦情绪,理应是有意无意地表现这种不得不领受的疾病处境。
另一类可能是因长期“体至孱弱”造成的身体不适而产生的介于真实与拟想之间的疾病言说。对于这类疾病,我们应该作如是理解:疾病首先是一种身体语言,更深层次而言,疾病还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词人痛苦地审视自己的人生现实,发现了现实生活中弱势女性生命的无奈和挣扎,而又渴望把自己从不堪忍受的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却又没有自我拯救的力量,于是只好心造一个“疾病”幻影来自我慰藉。也就是说,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疾病主题并不一定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疾病的客观反映,它往往超越了疾病的医学意义,而具有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文化意义及美学意义。赵氏的这类词作很多,当超过第一类疾病词的数量。如“病过重阳候”(《虞美人》)很可能是因“题遍相思稿”而生的相思病,“似天公、付我伤心病”(《月上海棠》)难说是否身体上的病,更可能是“离愁”所致之病,“惜春人病,燕归时节”(《忆秦娥》)是因“天涯客去音书绝”而起,“奈赢得清愁,幻成新病”(《台城路》)是因“秋夜不寐,有怀昔游”而生。这个事实表明,“人们在表达疾病感觉时通常不分生理与心理,任何一方面出现不适感觉即可认为自己生病”[10](P276~284),杜甫草堂诗中大量的衰病意象,就是由于生活所迫而造成的内心紧张和压抑,因此诗人在诗歌创作时,“或选取病态物征的意象以自喻,或以衰弱老迈以自命,闲适的情感背后却是内在的矛盾与沉重,启示着后期夔州诗歌的内在脉络。”[11](P49~50)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先生在分析易卜生作品时曾说:“悲剧之产生主要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12](P108)所以,我佩词中出现数量如此多的疾病意象,根本原因在于表达个人与疾病抗争和希望得到来自丈夫的情感慰藉的无能为力,这对于身处医学不发达、理学桎梏酷烈的清代,这种疾病言说无疑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伴随疾病而来的往往是身体的消瘦,所以词人的“瘦”字“瘦”句极多:“镜里韶颜还更瘦”(《雨中花·癸丑七月海陵舟次,闷填此解》);“人瘦比花黄”(《南乡子》);“个人几日瘦纤腰”(《浪淘沙》);“瘦腰怯似柳枝柔”(《江梅引·寄采湘》);“瘦骨弱难支”(《南乡子·寄采湘》);“藕臂鬆金肩削玉”(《百字令·病中有感》)等。词人在两首以“瘦”为题的词作中,前者言其“珊珊锁骨衣棱弱”、“镜里浑难认”(《菩萨蛮·瘦》)的瘦形,后者言其“臂欲鬆金,肩如削玉……黄昏后,怕灯前月下,顾影魂销”(《沁园春·瘦》)的瘦态,可谓瘦人瘦语。正“因为自己瘦,才对周围瘦弱的事物同病相怜。”[13](P73~79)所以词人由己之病、瘦而连带出花病、蝶病、春瘦、花瘦、月瘦等等。对于赵氏而言,“病”、“瘦”已然成为她对周围事物同病相怜的体现,并已成为不堪重负的肉体和精神隐喻,作者重笔渲染身体之病瘦、之丑陋,“已经将人物与这个世界完全隔离,更让她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生存的悲剧真相。”[14](P84~86)
词人因疾病而生出种种苦痛厌烦心绪和种种慵懒行为,故而词中与“病、瘦”并存的还有“慵”、“懒”、“倦”、“无力”、“憔悴”等语词和意象。如“晴雪满阶慵不扫”(《清平乐·雪霁》);“侍儿扶起懒梳头”(《虞美人》);“懒启湘奁,慵抛画谱,闲却纱窗绣。晚妆无力,泪痕界破眉柳”(《百字令·病中有感》)等。赵氏的慵、懒、倦、无力、憔悴多是因丈夫长期离家在外,夫妻情感不能满足而起:“妆台和泪倚。镇日慵梳洗”是因丈夫“归期未有期”(《菩萨蛮》);“画屏香冷懒调笙”是因“人去也……镇日数行程”(《忆江南·寄外》之七);“晚妆无力”是因“云痴雨怨,都把良宵负”(《百字令·病中有感》);“眉慵扫”是因为“思君别后,碧天云杳”(《钗头凤》);“怅天涯、目断鸿”根源在于“信难通”,以至于“湿罗巾、别泪浓”(《江城梅花引》)。显然,当这些与疾病有关的词句及意象通过作者的反复强调从而牵动起作者和读者头脑中关于疾病的想象,以达到引导自己和读者认识抽象的事物和隐秘的主题,此时,“它就再也不是简单的生老病死层面上的疾病了,而成为通向深层主题的重要隐喻。”[15](P119~123)这提醒我们,作为生理学层面上的疾病,它仅是一个自然事件,但作为文化层面上的疾病,它又是荷载着价值判断的。即赵氏词中的病、瘦意象,实则就是清代病态社会中女性文人的病态生活写照,“人物的病体正是千疮百孔的病态社会的象征,因生病导致的死亡正隐喻旧的制度的崩溃、旧的文化精神的衰落。”[16](P34~36)
赵氏集中笔墨言说“病”、“瘦”的词有10余首,如《鬓云鬆令·新病初痊,鬓发半脱,晨状梳掠,忽忽自怜》、《百字令·病中有感》、《菩萨蛮·瘦》、《沁园春·瘦》、《虞美人》(连朝风雨黄花瘦)等。下面拈出两首略作分析,以求“通过疾病来观察女性的命运和生存状态。”[9](P9~15)
百字令·病中有感
重帘皱影,卷流苏百结,帐绡凉透。翠被轻寒浑似水,又是点灯时候。鸟妒花愁,云痴雨怨,都把良宵负。连朝倚枕,熏笼偎暖罗袖。
因甚终日恹恹,只缘肝病,不为伤春瘦。藕臂鬆金肩削玉,腮际红霞非旧。懒启湘奁,慵抛画谱,闲却纱窗绣。晚妆无力,泪痕界破眉柳。
词题已然交代是“病中有感”,并在词中点明是“不为伤春瘦”的“肝病”。长期罹病的赵氏的此次患肝病当属大病,以至于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多日不能起床,终日病情恹恹。词中既有对病体“藕臂鬆金肩削玉,腮际红霞非旧”之形销骨立的外形描写,又有对“终日恹恹”、“晚妆无力,泪痕界破眉柳”之病中情态的述说;既有“懒启湘奁,慵抛画谱”之病中慵懒的动作刻画,又有因病导致的“帐绡凉透。翠被轻寒浑似水,又是点灯时候”、“鸟妒花愁,云痴雨怨”的怨天尤人。词人在词中无涉丈夫的言行,更无涉丈夫的关怀体贴,只一味地独自咀嚼疾病的折磨。她对自己“体至孱弱”的病弱之躯与“工愁善病”的敏感气质毫不隐讳,甚至有自负之意,并且在两者间建立了一种因果关系,即天生的弱质多病导致了她的多情善感,多情善感的气质又增加了她柔弱之美和愁伤倾向。
这类词中,词人多是有意或无意地带出丈夫的身影,如《虞美人·寄外》,以“病魔不肯随春去。抵死缠绵住。恼人情绪困人天。半响起来无力、整花钿”向丈夫述说疾病带来的痛苦无助,且后悔自己“那回应悔轻离别”,并因此产生“何事音书绝。怜它燕子也怀归。难道天涯羁客、不相思”的恶情怀。再如:
虞美人
连朝风雨黄花瘦。病过重阳候。侍儿扶起懒梳头。谩说日高犹自、掩妆楼。
琉璃格子文窗小。题遍相思稿。伤秋情绪怕逢秋。道是纤腰如柳、恁禁愁。
虽然词中有“病过重阳候。侍儿扶起懒梳头”之“懒”,但更有可能是词人“题遍相思稿”而夫君不还家所致,以致于词人亦如“连朝风雨黄花瘦”、“伤秋情绪怕逢秋”、“纤腰如柳、恁禁愁”了。词人还有送别丈夫时的难舍难分,从而使其“晓妆人倦,懒画眉梢”(《湘春夜月·舟泊长安送砺轩返杭》)芳心寸乱。这与易安《凤凰台上忆吹箫》之“新来瘦”毫无二致,这样的“愁”又岂是“三杯两盏淡酒”能消解得了的?反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罢了。难怪赵氏最初将词集命名为《红豆词》,我们不能不说,赵氏的“病”、“瘦”,有很大成分是因对丈夫的思念造成的相思愁。
三、结论
封建时代的女性“拥有的唯一资本便是自己的身体,当语言变成空白和虚无,身体的出场便成为必然。”[17](P15)所以,赵氏疾病词中,身体的出场总是伴随病体出现的,有身体的整体呈现,如“人瘦比花黄”(《南乡子》);有身体的局部特写,如“瘦腰怯似柳枝柔”(《江梅引·寄采湘》);有体态与情态的精描细画,如“含颦独倚”(《清平乐》)、“闷拥香衾睡”(《菩萨蛮》)、“珊珊锁骨衣棱弱”(《菩萨蛮·瘦》)等。以“病、瘦”为主要美学特征的赵氏词,一是多用“病、瘦”语词和意象,二是多绘“病、瘦”形态,三是多构“病、瘦”意境。这些疾病词似乎告诉我们,赵氏谙熟于用传统诗歌描写女性的病弱之美。她对自己“体至孱弱”的病弱之躯与“工愁善病”的敏感气质显然毫不隐讳,甚至有自负之意,并且在两者间建立了一种因果关系,即天生的弱质多病导致了她的多情善感,多情善感的气质又增加了她柔弱之美及愁伤倾向。它“不单是显示了作者的才华与锤炼之功,更重要的是作者个性精神、审美追求的载体与象征。这才是‘瘦’的深层次、高品级的意义所在。”[18](P68~72)
作为清代才女之一的赵我佩,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中,以中国女性特有的天然禀赋、坚忍不拔和聪明颖悟,以及对文学的爱好,在清代文坛上竖立起一道明丽的风景。赵氏因“体至孱弱”而创作大量工愁善病的“病、瘦”词,因“言辞磊落”而创作大量直抒胸臆的愁苦词,这种鲜明的词作内容和艺术特色,成就了赵氏在清代词史上的突出地位。她“强烈地感受到男权体制下的自身角色的卑微,体味到自我生命价值的缺失”[19](P35~38),以独特的方式书写自己的病瘦感受,将疾病作为生命的一种状态,用来隐喻自己不断受挫的敏感的心灵和女性的身份焦虑,反映出那个时代女性的现实处境和心灵痛楚,这无疑是有着时代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徐乃昌,辑.小檀栾室闺秀词[M].清光绪刻本.
[2]谭正璧.女性词话[M].上海:上海中央书店印行,1934.
[3](清)赵我佩.碧桃仙馆词[M].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同治中程秉钊钞本.
[4]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J].文艺研究,1988,(6).
[5]王 菊.鲁迅小说“疾病意象”的文化指向[J].理论与当代,2007,(10).
[6][美]苏珊·朗格.刘大基,等,译.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7]陶文鹏.拟人拟物“瘦”字俱妙[J].古典文学知识,2010,(5).
[8][美]苏珊·桑塔格.程 巍,译.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9]李 蓉.性别视角下的疾病隐喻[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10]吕小康,汪新建.意象思维与躯体化症状:疾病表达的文化心理学途径[J].心理学报,2012,(2).
[11]钟继刚,姚小波.杜甫草堂诗的衰病形象[J].文教资料,2006,(34).
[1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3]陈昌宁.梦窗词“瘦”意象的美学意蕴[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14]张江元.张爱玲小说疾病的隐喻意义[J].名作欣赏,2010,(6).
[15]丁 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意象”探析[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5).
[16]任葆华.论郁达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J].电影评介,2007,(18).
[17]王冬梅.疾病隐喻与女性书写——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意象探析[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7.
[18]崔际银.“瘦”:李清照词的美学特征[J].名作欣赏,2001,(3).
[19]段继红,高剑华.清代才女结社拜师风气及女性意识的觉醒[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