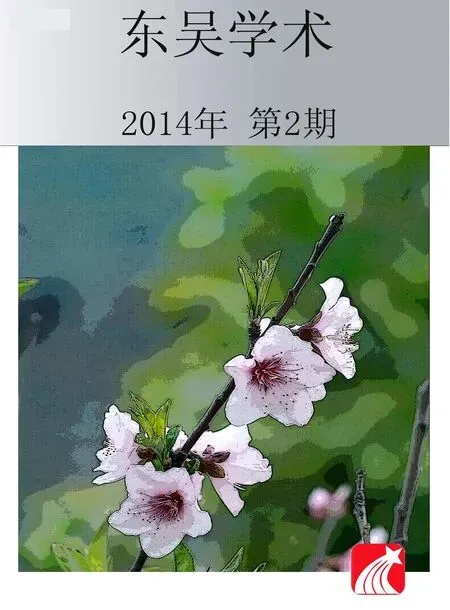冯积岐,一个背石头上山的人
2014-03-29方宁
方 宁
看着眼前的这部《冯积岐评论集》,总觉得这是来得太迟的关于一个人和一段历史的记录。但令人欣慰的是,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尽管感觉有些晚。
与希腊神话故事中那位推石头上山的西绪弗斯不同,想起冯积岐,我一直有个摆脱不掉的幻觉,总觉得眼前的这位以九部长篇、二百多个中短篇小说著称的作家,自己就是个可以被写进故事里的角色。这不仅因为论写作的勤奋,估计他算得上当代中国作家中单篇创作产量最多的作者(或许都无须用“之一”这样的字眼来限定),论写作的实力,他在小说中对于多种文学表现手法的尝试和运用也有着相当程度的自觉和近似炉火纯青的功底;若论阅读的丰富,冯积岐也许更出人意料,他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足以和那些在大学里教授同一专业的行家相抗衡,只要你提得出哪位世界文学排行中的作家或并非见于经传的作品,他都能立即进入文本分析的状态,如数家珍如叙家常,其感受之细,用心之深,解铃系铃,洞烛幽微;这也许恰好证明了他在小说中能用多种手法娴熟塑造人物的原因。当然,这些其实都还不足以构成冯积岐所独有的价值,因为就作家的身份和具有相当专业的鉴赏力而言,他所表现出的都还是在正常值的范围之内。谁不知道,一旦儒林序齿,虽说古往今来自有排行与定论,但那无疑都是些人中之精英、世间之龙凤。用曹子建的话说: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哪个不是读书万卷下笔有神的稀罕物呢!
而我想要说的是,冯积岐属于另类,正是在另类的意义上,他自己也许更适合成为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物。
我在二〇一二年夏天第一次和冯积岐相见的时候,他的形象和他的小说一样让我印象深刻。深棕色的皮肤,偏瘦弱的身体,沉静木讷,不擅言词,眼神也似乎习惯性地向侧面滑落,像是在谦卑状态下养成的一种习惯,尽管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柔弱谦卑的表情里其实隐藏着坚硬的力量,那似乎是陕西人性格里特有的执拗。说来惭愧,我平生第一次到西安,已经是五十多岁的年纪,陕西之行,虽说有诸多愿望,但最主要的还是想去拜访这个叫冯积岐的人。老冯如约而至,陪同他的,还有我的两位多年不见的朋友,一位是《小说评论》的主编李国平,一位是陕西师大的教授李继凯 (国平和继凯还是这本评论集最积极的助推者)。回想着和老冯的初次会面,就有彼此相识了几辈子那样的感觉。才一落座,我迫不及待地说起读他的小说时的那些感想,听我讲述着,老冯依旧像他的性格那样沉静,似在听我聊着他太熟悉的一件农具或一桩农活,他谦虚地笑着,偶尔还会显得有点无奈和感伤。后来聊多了,渐渐地知道老冯的骨子里其实还是个对世界、对社会有着很强烈看法的人,这和他的小说里所表达出来的“悲观情绪”多多少少有些关联。在我看来,他太擅长写那些挣扎在传统观念与现代生活中的农民身上发生的悲情和悲剧,尤其是那些喷薄而出的情感,最后都如烟花散去落得苍凉的结局,读了会让人五内如焚、坐立不安。
但是想想,如果一个作家心里只怀有对于人性的美好的认识,显然也是成不了什么事的。在老冯的作品中,我越来越相信,对世间美好事物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悲剧的认识所能达到的深度。身为作家,他必须能狠下心去表现生活中的悲剧——记得好像是前辈夏衍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个杰出的作家必须是能够狠得下心来的人,那样的人才能写出大东西、大悲剧。他还列举过很多的人,说他们作品的伟大就在于他们的心狠(大意)。依我看,冯积岐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性不仅有着天生敏感的触角,还有着足以形诸笔墨的能力和承担悲剧重量的勇气。他常说自己就是陕西岐山的一个农民,从小在地里头长大,家里成分高,“土改”的时候被划成了“地主”,由于出身不好,在他成长的年份里,遇到的各种坎坷就像影子一样地跟从着、牵绊着,好像至今都还是比别人多着一些无辜与不顺。而正是这些不顺,让他发奋去写作,想着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说自己因为出身的原因,从记事的时候起就一直和苦难相伴。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苦难也许更多地来自他的性格,源于他的天性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悲观心结。这些年,他对于自己,似乎越来越强化着宿命般的认识,无论写出多少文字,都不要想着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种附着在当代一些作家身上的大红大紫,虽然也令人羡慕,但是那些都不属于冯积岐命里所有的东西。
与其说冯积岐是个作家,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个不断地把生活锻造成为文学的修行者;他的修行课程包括用石头般的文字垒起社会精神的形象历史,表达着他对于历史中沉重悲剧的感悟。在我看来,三十多年,冯积岐像个每天按时出工的农民,背石上山,负重前行,他除了吸烟,并无其他的嗜好,在兀坐读书写作之外,全无娱己娱人之乐。他的小说中有着太多的场面,或描摹人性之善美,令人心向往之;或呈现贪吏之邪恶,足以令人扼腕。其写男女之情性,虽然或俗或艳,颦笑之间妖娆万千,但在背后丝毫掩饰不住作者对于生活中巨大的悲剧性的透彻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些敢写爱恨、敢触现实、洞达历史、直面悲剧的文字,使他的长篇小说《村子》能够在网络上获得了数以千万计的点击率。他的其他几部长篇也同样拥有众多的读者。
在今天的社会,许多聪明的作家,已经不再把“历史”、“责任”与“良知”视为写作的底线,与时俱进的社会心理,似乎也昭示着审美与文学的趋时逐利的方向。大家操练着同一类语言,追逐着同一种欲望。而那种热闹从来不属于冯积岐。从这个意义上看,他肯定不是一个懂得迎合时代的角色,面对五光十色的社会,冯积岐依旧像每天出工的农夫,与三十多年前从田垄里出发一样,依旧背负着沉重的石头,只管向高处行走,用文字的块石去垒就他心里的精神长城。
读英国小说家毛姆晚年写的随笔,常常会有感于他说过的几句话:“尽管整个世界、其中的每个人、每处风景和每个事件都是你的素材,你自己也只能处理与自己天性中的秘密涌泉相呼应的部分。”他还说:“艺术家,特别是作家,是在自己思想的孤独中建造一个不同于他人的世界。”对冯积岐而言,他太熟悉和了解当初给了他生命的土地,同时也给了他历史创痛的乡村,这些都构成了他与生俱来的生命的印记,也是他不断写作不断拿出力作的源泉。他的笔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他用文学思考着人的命运,这是他身为作家所能讲述出来的打动人心的故事。
我敢说,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他所写的每一段历史,都有着石头一般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