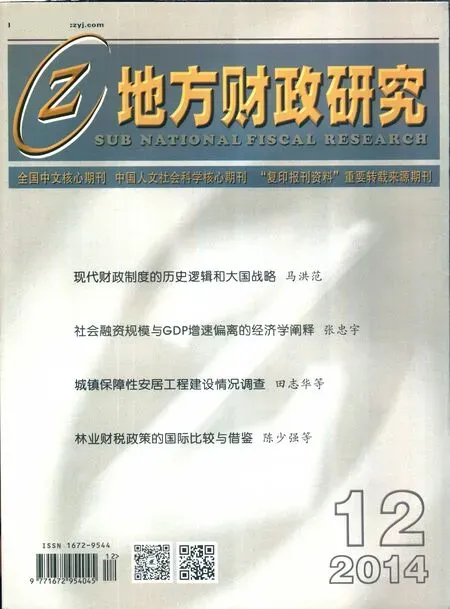地方官员行为与地方政府债务:一个基于文献的分析框架
2014-03-29肖坤彭坤
肖坤 彭坤
(1.辽宁广播电视大学,沈阳 110034;2.辽宁省委党校,沈阳 110004)
地方官员行为与地方政府债务:一个基于文献的分析框架
肖坤1彭坤2
(1.辽宁广播电视大学,沈阳 110034;2.辽宁省委党校,沈阳 110004)
政府债务是衡量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执政水平的重要部分,学术界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视角是多方面的。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和现实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地方官员在其中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而政治晋升、财政分权和软预算约束是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构造了考虑三因素的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债务关系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对文献进行了重新梳理,并用以往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框架的解释能力进行了证实。
地方官员 地方政府债务 分析框架
一、引言
近年来,特别是在2007年—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之后,地方政府债务受到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研究表明,在这些危机中,转型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比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受的影响更大(World Bank,2008),因此,经济学家提醒地方政府如果要进入金融市场应该事先做好风险评估(Bailey et al.,2009)
尽管中国国家债务问题依然在掌控之中,然而,目前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也已经达到了持续关注的范围。Shih(2010)估计认为截至2009年年底,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为11.4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银监会、高盛、财政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国社科院等从2009年5月到2011年12月分别进行了测算。多数部门的统计数据在6-8万亿之间,中国社科院2011年12月得到的数据是至2011年,地方债务规模将达10-12万亿,而高盛集团2009年12月测算的数据显示,中国政府负债余额已经高达15.7万亿元,占GDP的48%(李永刚,2011)。按照国家审计署《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我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加上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为6.75万亿元人民币,总计17.5万亿元人民币,约占GDP总量(39.7万亿人民币)的44%,尽管这一数据低于欧洲1992年制定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盟国家债务率60%的上限,但是根据审计署的报告,2010年底,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高于100%(巴曙松,2011),而且2011年以来,一些地方的机构,如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申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及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都爆出了债务危机的消息。尽管经过适当的协调,上述风险得以化解,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仅从这些部门给出的数据就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依然惊人。
早在2004年,21世纪经济报道就指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公共财政危机应该值得特别关注,而县作为一个行为主体也正是张五常特别推崇的县级政府间竞争的主角。其得出的结论是,金融风险曾经是威胁中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原因,而目前这一威胁变成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现有的文献表明导致地方政府举债融扩张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即财政支出压力(Bird,1992;Inman&Rubinfeld,1996;Wildasin,1996;de Mello,2000;刘尚希、赵全厚,2002)和财政收入紧张(Dafflon&Beer-Toth,2009;Cepiku&Mussari,2010;刘尚希、于国安,2002;杨志勇、杨之刚,2008)。
国内的一些研究大多将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是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央经济政策(肖耿等,2009;魏加宁,2010;周其仁,2011;Azuma&Kurihara,2011)。如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空前繁荣。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带动下,2009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继续快速增长。除此之外,中央还打破了中央对地方政府举债保持了16年的禁令,在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每年代发2000亿元地方债。
而其中的一个主要政策就是设立地方融资平台,很多研究认为地方融资平台作为地方政府借债的实际媒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秦德安和田靖宇,2010;贾康、孟艳,2009;封北麟,2010)。其实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地方投资公司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金融创新工具(Azuma&Kurihara,2011),然而随后出现了大量违规操作、不够谨慎而且低效率的投资行为(魏加宁,2010;张艳花,2010;张国云,2011),从而存在着很高的偿付风险(肖耿等,2009;刘煜辉、张榉成,2010)和资金贷后管理困难(沈明高、彭程,2010)。而且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和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金融创新和证券化(许成钢,2010),以及欧洲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沈明高、彭程,2010)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政策代价则是大同小异。
然而,这些“宏观的外部”政策不能解释全部的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因为地方政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造成的债务规模已经超出了“宏观的外部”政策发动者(即中央政府)的预期范围。在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投资比例和中央的计划偏差很多,例如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资金不足30%(刘煜辉,2010),而且在原计划两年各地需要配套的资金只有1.2万亿至1.3万亿元,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仅在2009年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就达5万多亿元(时红秀,2010c)。因此,地方债务的大量出现已经不再是地方政府收入不够的问题,而是因为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出了问题。因此,应该将目标转向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微观的内部”因素,如张艳花(2010)就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行为激励是互为因果的。
二、研究框架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学者对地方官员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地位的重要性已经达成共识,很多研究发现,在我国特殊的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对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都产生着重大影响(郭广珍,2009;郭广珍等,2011)。Li(2003)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关键是‘征得地方政府的同意和支持’”。然而,North(1981)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因此,全面地弄清楚政府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不仅是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且对今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因此,尽管影响地方政府债务的因素很多,但从理论上看,其中最主要和最本质的因素必须通过地方政府,也就是地方官员的行为发生作用。我们认为影响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因素是通过多个途径实现的。因此,如果仅仅从一个角度对其行为进行研究应该是不全面的。按照这一思路,主要的因素可以抽象归纳为三个,即政治晋升、财政分权和软预算约束。
这三个因素都直接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它们也影响着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和结构,更重要的是,这几个因素已经被大量的相关研究应用,并得到了初步的证实,将其放在一个模型中的相关研究还较少。为此,我们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的梳理,试图将其放入一个统一框架内,以对该问题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假设存在两个地方政府并处于核心地位。从财政分权的角度看,在税率一定时,地方政府会从中央政府那里分得一部分财政收入;从政治晋升的角度看,两个地方政府(官员)付出努力和当地基础建设水平都影响各地方的产出,而基础建设水平又受负债水平程度的影响,并通过政治锦标赛影响晋升。在财政收入和基础建设等支出确定以后,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也就确定了,进而我们构造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决定模型。
三、该框架在国内外研究中的体现
如上所述,我们认为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和软预算约束,其实巴曙松(2011)将地方政府债务形成原因归结为三个原因,即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间事权和财权高度不匹配、不恰当的政绩观和地方财政制度不健全,在理论上看,这三条恰恰就是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和软预算约束的具体表现。
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三个方面与地方政府债务的关系进行文献综述,又因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数据质量过低,而且存在严重缺失,使得对相关数据的处理变成本项目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对数据估计方面的文献也进行了简单的梳理。
(一)政治晋升与地方政府债务
晋升激励(Promotion Incentive)是企业领导将员工从低一级的职位提升到新的更高的职务,同时赋予与新职务一致的责、权、利的过程。黄亚生(1995)指出中国官员是向上负责的,这种方式即不同于企业的提拔等手段,也不同于民主国家的选拔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采用了上级任命、异地任职、异地交流和晋升等制度安排,实现了对各个层级政府官员的治理。因此,在这种政绩考核和官员提拔的制度下,地方官员会积极寻找经济增长机会来谋求晋升,这其实就是政治激励,它与财政激励是完全不同的(Blanchard和Shleifer,2000)。而随后的研究更加清晰,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经济绩效指标,尤其是当地GDP增长率,替代了过去的纯政治指标,变成了中国地方官员的选拔和提升的标准。Guo(2009)从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来为这种思路提供理论的佐证,他认为“资源密集型”工程就是基层官员发出有关自己政绩信号的主要载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在实现了自己政治目标的同时,也恰好实现了国家的经济增长目标。在这一思路下,学者们通过构造锦标赛模型,讨论了政治晋升对经济影响(Li and Zhou,2005;周黎安,2004;周黎安,2008)。和这种思路类似,张五常(2008)通过自身的观察,发现分权在县级层面的实施使得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进而把县际之间的竞争视为中国经济制度的核心,而该理论也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张军、高远,2007;徐现祥、李郇、王美今,2007)。
然而这种政治晋升机制对地方政府债务会产生什么影响呢?Breton(1998)也认为政府本质上是具有竞争性的,这些竞争可能发生在资源和控制权的争夺上,也可能发生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上。这类竞争不仅有助于政治体制的均衡,而且也能够实现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与税收价格的有机结合。周雪光(2005)则认为只有有能力动员足够的资源,突破已有的预算约束,才能在短期内做出引人注目的政绩。虽然摊派或加征税费不会产生政府债务,但会损害政府官员声誉,于是借债就成为最佳策略选择。陈本凤(2006)从干部的任命、任期制度存在缺陷角度论及地方债务,指出由于地方官员任用时间较短,导致其执政目标的短期化,所以官员考虑政府负债和使用财政资金的时候,很少考虑其长期后果。另外,地方官员并不对地区经济发展成本负有责任,但却间接享有经济发展的收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助涨了地方政府债务的攀升。
所以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到在当前的制度框架下,地方官员具有债务扩张的天然动力(祝志勇、高扬志,2011),但是较少具有基于上述理论假设下的模型论证。
(二)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财政联邦理论是财政分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特别关心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效率问题,认为如果将中央政府对所有公共支出做出决策权分配给多层级的政府体系,会使得提供公共品的效率大大提高(Tiebout,1956;Musgrave,1959;Oates,1972)。一些文献则认为地方政府很像一个多部门的集团公司的总部一样管理着其辖区内的公有性质的乡镇企业,因而认为政府具有“地方政权公司主义”和“地方政府企业家精神”(Oi,1992;1995)。而Weingast(1995)正式提出了“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的概念,他们相信只有满足了5个特征就将形成有效的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①这五个特征分别是:(1)政府体系至少有两个层级,每级政府都有明确的权威范围(authority)或者自治权(autonomy);(2)下级政府对其辖区内的经济事务具有首要的管理责任;(3)中央政府保证国内市场统一;(4)地方政府硬预算约束;(5)这种权威和责任的划分能够自我实施。而一些中国的证据使得该理论变成了“中国式联邦主义”(Montinola et al.,1995)。
将这一思想应用到地方政府行为上,龚强等(2011)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得到了很多支持地方政府借债的理由:如,符合代际公平的原则;使公共服务的运营成本更低;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平滑暂时性收支缺口的方法;有助于促进对地方政府的问责(Swianiewicz,2004;World Bank,2004)。Dewatripont和Maskin(1995)也指出分权和辖区间竞争可以加快国企的民营化改革,迫使政府减少对无效率国企的补贴和救助,增加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其背后的原因是,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有了追求地方税收最大化的积极性,因为他们成了税收的“剩余索取者”(Qian and Xu,1993)。而且,随后的实证研究也支持该理论的一些结论,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张晏和龚六堂(2006)分别利用不同时段的省级数据证实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是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公共支出成本等存在差异,加之财政分权的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的逻辑也不同,如果仅依靠本地税收为公共产品融资,会造成地区间的财政不平等(Martinez-Vazquez,2001),需要规范化转移支付进行矫正,但可能抑制地方政府提高效率和自食其力的积极性,产生预算软(逆)约束问题。然而也有研究认为,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合理、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地方税制不全等是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深层次原因(李永刚,2011)。
(三)(逆)软预算约束与地方政府债务
软预算约束被Kornai(1986)用于描述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缺乏硬性预算限制的特殊行为。具体而言,国有企业一旦出现亏损,不是自己通过提高绩效弥补损失,也不是通过破产终止企业行为,而是不断地向上级政府部门索取资源来进行弥补。这种预算软约束理论完全可以被运用到不完全财政联邦主义上,来说明地方政府债务攀升问题(Qian,1997;Wildasin,1997)。当我们把这一思想应用到地方政府债务上时,可以将地方政府类比于国有企业,各级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索取资源,如攫取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资源。这一以来就可以突破事先设定的预算限制,进而实现自己确定的目标。这些相关的行为都已经建立在这种预期之上而形成的,因而成为一种“逆向软预算约束”(周雪光,2005;时红秀,2007)。Nobue Akai&Motohiro Sato(2007)也指出,对于地方借债而言,事前激励一旦与中央政府的事后救助或者成本分担行为相结合,就有可能出于对其故意的扭曲而导致预算软约束。他们通过动态模型分析研究地方债务管理中的软约束问题,博弈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子博弈完美均衡是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
然而,预算软约束问题为什么能够持续存在,并能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就变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我国地方政府要实现债务扩张,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限制地方政府过度举债行为的法规还是相当丰富的。例如我国《预算法》的相关条款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担保法》的相关条款规定,“除了经国家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之外,对向国内债权人举借的债务,国家行政机关不能提供担保。”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可以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约束,例如即使中央必须对出现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进行援助,但是中央也完全可以在事后对当事的地方官员进行处罚。如果地方官员都有这种预期,也是可以遏止财政上的预算软约束问题的。
Wildasin(1997)、Inman(2001)认为在财政联邦制下,由于地方公共品投资一般具有外溢性,因此,激励联邦政府为地方公共支出提供援助,由此产生财政联邦制下的预算软约束问题。Persson&Tabellini(1996)、Bordignon et al.(2001)都证明了一个中央政府如果想要最大化社会福利,该政府就有激励对陷入财政危机的地区施以援助之手。从这一角度看,其实财政分权的体制本身就是导致预算软约束的原因(Raju&Plekhanov,2005)。而政策性负担说(林毅夫等,1999)对此的一个解释是,即使事后,中央因为信息的不完全问题,也无法判定地方的亏损是否出于地方政府官员的自利动机,因此出现预算软约束。而陈健(2007)通过构建一个预算软约束理论模型解释“多而不倒”的问题。虽然中央很强大,而且也能够在事后分清地方是否故意为之,但由于地方债务问题违犯者众多,也无法实施有效处罚。
四、该分析框架的应用
(一)理论模型构造
在该研究框架下,要将政治晋升、财政分权和软预算约束可以从多个角度研究,如果仅仅考虑博弈模型,依据行为主体的不同选择,我们可以构造出以下几类博弈模型。
首先,可以构造两个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行为,如晋升政策,分权政策就可以视为外生。其次,可以考虑一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这种情况下另一个地方政府行为可视为外生。再次,可以假设两个地方政府进行合谋,然后和中央政府进行博弈。这里的假设因为去掉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晋升激励可能会受到质疑,然而稍作分析就会发现,晋升激励是有范围的,而且其范围还相当有限。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晋升的官员毕竟是少数,如果地方官员认识到晋升无望,也许会放弃晋升,而且还有可能“破罐子破摔”,从援助之手变为掠夺之手(陈抗等,2002)。在这情况下,地方官员转而和邻近的官员进行合谋,以追求各自偏好的目标,也是很有可能的。最后,如果将模型做的足够贴近现实,可以构造两个地方政府和一个中央政府的三方博弈,当然,这时模型也是足够复杂的。以上模型在用于解释具体问题时,还可以对博弈信息、博弈顺序以及博弈次数进行相应的假设,进而构造出符合特定问题的模型。
(二)实证研究
要进行相关实证研究,就必须先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或者估算。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公开的时间比较短,公开的内容很少而且数据质量不高,所以目前的大部分研究还停留在描述分析上,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因为数据问题而无法开展,因而对数据的处理成了该领域的一项重要而急迫的任务。
在有限的相关文献中,Holackova(1998)的研究使得我们开始关注以前一直被忽略的隐性和或有负债问题。他们利用了财政风险矩阵来对地方债务进行分类,但是这个分类框架是一个技术性分类框架,因此他剔除了各种体制性因素。这意味着,要更好地解释地方政府累积负债的原因,仅仅运用这一框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利用新的分类方法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分类。Brixi(1998)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财政风险矩阵,刘尚希、赵全厚(2002)套用这一矩阵将我国的政府债务分为四类,显性的直接负债、显性的或有负债、隐性的直接负债、隐性的或有负债四类。顾建光(2006)也利用这种分类方法将各类地方债务区分为,中央政府债务转化为地方政府债务、财政体制因素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项目贷款、因承担道义义务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地方公共部门债务转化为地方政府债务(龚强等,2011)。
婆婆一听,急了。她一边哄着正在哭的当当,一边说:“为什么要做手术啊?不就是个结节吗?我问过启明那个学医的表弟了,他说结节没事,只要吃点中药调理就行。”
而Hana polakova Brixi(2000)指出,哥伦比亚政府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衡量债务利息支出和债务余额这两个指标上。这种方法虽然有利于从宏观上掌握债务的总量和发展趋势,但是这一信息只比较滞后,要想事先对风险做出的预测,则须建立更为精确的技术操作规范和衡量标准。Easterly& Yuravlivker(2003)为避免风险评估传统方法的局限性,运用会计方法模仿企业风险管理,测算政府偿债能力,通过建立政府资产负债表来考察财政可持续性,把政府负债和政府可用资产进行对比,对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案例分析,这是一个涵盖范围更广泛的分析方法。刘尚希(2004)通过建立政府债务与公共资源存量对比表、政府债务与公共资源流量对比表,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次对债务风险状况进行评价分析,这虽然不是严格意义的风险分析,却极大地拓展了债务风险评价的视野。而李扬(2012)运用资产负债表对债务风险评价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
五、结论性评述
影响地方政府债务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众多相关研究都持有这一观点,并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然而,这些文献大都是经验性的,它们虽然证明了地方政府债务和诸多因素之间的相关或因果关系,但并没有给出这种关系的内在机理,要分析这种内在机理需要借助于逻辑严密的理论模型,而理论模型的逻辑严密性却大大限定了其可以解释的范围,本文试图给出一个可能的范围,以为进一步理论模型的构造提供一些启发。
当然,将粗浅的理论框架转变为严谨的理论模型还需要大量的工作要做,一个容易遭到质疑的问题是,对三个因素的选择是否具有足够的合理性,这不仅要看理论模型的构造是否符合一般经济学的直觉,更需要实证分析的检验,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后的工作方向。
〔1〕Azuma,Y.and J.Kurihara,2011,“Examing China′s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Dynamics”,Politico-Economic Commentaries,No.5,January3.
〔2〕Bailey,S.J.,D.Asenova,and J.Hood,2009,“Making Widespread Use of Municipal Bonds in Scotland?”,Public Moneyand Management,Vol.29,pp.11-18.
〔3〕Cepiku,D.,R.Mussari,2010,“The Albanian Approach to Municipal Borrowing:From Centralized Control to Market Discipline”,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Vol.30,pp.313-327.
〔4〕Dafflon B.,K.Beer-Toth,2009,“Managing Local Public-
Debt in Transition Countries:an Issue of Self-control”,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Management,Vol.25,pp.277-366.
〔5〕Wildasin,D.,“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in the Current Crisis:Time for Emergency Federal Relief?”[R].IFIR WorkingPaper No.2009-07,January,2009.Unpublished manuscript.
〔6〕巴曙松.地方债务问题应当如何化解.西南金融,2011年第10期.
〔7〕封北麟.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财政风险研究.金融与经济,2009年第2期.
〔8〕龚强,王俊,贾珅.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7期.
〔9〕郭广珍.政治收益、经济贿赂与经济绩效.南方经济,2009年第11期
〔10〕郭广珍,李绍平,黄险峰.经济发展中的地方官员行为研究.经济评论,2011年第5期.
〔11〕贾康.关于中国地方财政现实问题的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12〕贾康,孟艳.运用长期建设国债资金规范和创新地方融资平台的可行思路探讨.前沿论坛,2009年第8期.
〔13〕李扬,张晓晶等.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及其风险评估.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
〔1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5〕林毅夫,刘志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责任编辑 寇明风】
F812.5/F812.7
A
1672-9544(2014)12-0069-05
2014-08-04
肖坤,校长,研究方向为规制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彭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生理论与实践。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0303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JL08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2YJC790046)、辽宁省教育厅项目(W2013004)和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L13DDJ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