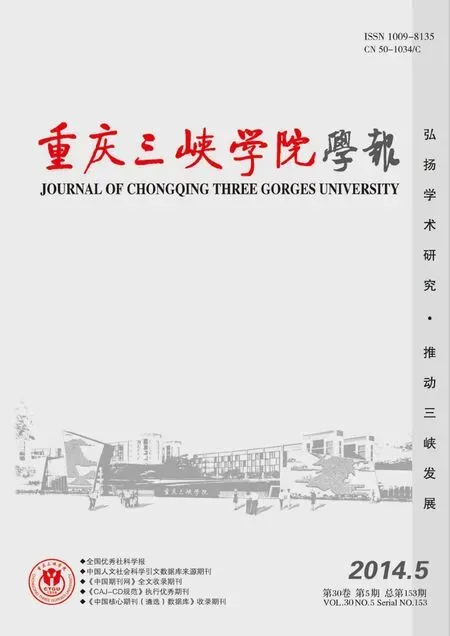柔软的黑人性与坚硬的主体性——解读《白宫管家》
2014-03-29何燕李
何燕李
柔软的黑人性与坚硬的主体性——解读《白宫管家》
何燕李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白宫管家》以交叉叙事的方式书写了西塞尔·盖恩斯在种族主义语境中的摇摆人生,以及与之相随的柔软黑人性和坚硬主体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棉花田里的舞勺之年,未谙世事的西塞尔以反抗彰显着其黑人性;第二,私刑下的而立与不惑,失去父亲的西塞尔用忍耐守望着自己的主体性,尽量不谈政治;第三,后政治秀的耄耋期颐,失去儿子的西塞尔凭反抗坚守着长期以来其族裔所需的黑人性。实际上,这三段从反抗→忍耐→反抗的人生,是当时黑人在“主人”宰制下的策略生存,旨在以迎合语境所允许个体“奴仆”承载的主体性的前提下守护集体的黑人性。
黑人性;主体性;西塞尔;家奴;白宫管家
黑暗不能驱走黑暗,只有光明可以。
——马丁·路德·金
在美国非裔族群内部,即使“在奴隶制时期,就开始出现一类‘拥有特权的’黑人”——“家奴”(house nigger),他们“拥有农奴(field nigger)从未享受过的权利”,同时除了自身“迅速被主人的思想和态度同化外,他们的孩子有时还被允许学习一些商贸知识和成为百工工匠”。[1]123这些特权是一把双刃剑,它们一方面让这类黑人过上了相对优越的生活,另一方面则使他们陷入了极为久远的身份困惑。因为在黑人只能被划分为农奴、家奴的黑色年代,他们如白人般歧视农奴的“白色化”使自身成为了后者的眼中钉,而那些比白人更能治理黑人的黑奴管家则变成了整个族裔的肉中刺。随后,这种身份困境在黑人能被划分为农奴、家奴、自由人的灰色年代得到流传,并延续到黑、白种族隔离时代,甚至蔓延至“黑人权力运动”之后。为此,“家奴”、“黑人管家”变成了族裔的特殊群体,承载了相应的身份之重,而这种重就体现在李·丹尼尔斯(Lee Daniels)的《白宫管家》(, 2013)之中,具体表现为男主角西塞尔·盖恩斯(Cecil Gaines,1912—2010)游走于黑人性与主体性文化夹缝中的三段摇摆人生:反抗→忍耐→反抗。
一、棉花田里的舞勺之年
对于深受双重殖民——奴隶贸易和种族主义的美国南方非裔而言,年幼时期大多并不懂得在白色语境中自己只是生如蝼蚁。于是,初遇“主人”宰制的他们会随本能奋起反抗,直到亲历前在的残忍结果,方而开始体会密不透风的种族主义和无法翻越的二元对立,并逐渐明白族裔长辈日日叮嘱的如雷贯耳的生存之道。西塞尔就是这类群体的典型表征,具体表现为如下两个阶段:首先,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西塞尔的童年驻足于乔治亚州梅肯区安娜贝丝(Annabeth Westfall)家的棉花田,因为14岁之前的他与父母艰苦而幸福地相伴。然而,这种幸福在1926年的某个阴天戛然而止,那时他目睹了年轻跛脚的男主人托马斯(Thomas Westfall)拉走母亲海蒂(Hattie Pearl)。于是,他焦急地追问父亲(Earl Gaines)有关母亲的去处,并开始一路狂奔追赶,却被父亲拦腰抱住。当母亲被白人带进棉花田边的破旧小木屋时,他大声地呼喊母亲,而父亲却用力地拉住他:“听我说,儿子,千万不能冲那个人发火,这是他的世界,我们只是寄居其中。”随后木屋传出母亲的惨叫和摔东西的声音,当跛脚主人边走出屋边整理衣裤时,父亲只是低头抹了一把眼泪。于是,西塞尔问父亲:“你要怎么做?”父亲看了看儿子,转过脸、低下头、再抬起来对着白人的背影说了一个字:“嘿”。白人随即转身、怒目、掏枪,就此截断了西父的生命线,逼走了西母的意识流,也撕碎了西塞尔的童年心。
西父被跛脚主人枪杀时,西塞尔吓得连打了几个寒颤,并在空白片刻之后才奔向倒地的亡父。此时,跛脚人挥舞着枪警告着任何可能反抗的在场黑人,而年迈的安娜贝丝夫人则一边告诉他们:“嘿,你们,挖个坑帮他埋了父亲,快点”;一边告诉瘫倒在地的西塞尔:“停止哭泣,现在我要带你到屋里去,我将教你如何做一个家奴。”为此,在经历了母亲被强奸、父亲被枪杀的代价之后,西塞尔的身份从农奴迈向了家奴,并自此开始自己的家奴人生。随后,安娜贝丝夫人教了西塞尔诸多家奴规则:端菜时双手举于胸前;走路时稳步小声;上菜时“不能有声音,甚至连呼吸声都不要让我听见,你在屋里时要安静得像空气一样”等。对于这种生活,西塞尔的评价是:“在屋里干活要比在地里好得多”,从而支撑他度过了艰难的舞勺岁月。
其次,苦不堪言的青年露宿。逐渐长大后,西塞尔意识到自己需要在被跛脚主人杀掉之前离开。于是,他拿着父亲的怀表,别过疯癫的母亲和垂老的安娜贝丝夫人,徒步离开了乔治亚,一路北上到北卡罗莱纳。整个“在路上”的旅程让他一方面感知了身为黑人的生存无助:“棉花田外的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没人给我工作,没人给我食物,没人给我栖息之所”。另一方面则使他再度目睹了反抗的结果:“白人可以随时随意杀掉我们,而不受惩罚”,因为“法律非但未保护我们,反而置我们于死地。”然而,长久的饥肠辘辘依旧令他徒手砸坏了某酒店放置蛋糕的橱窗,却不曾想遇到了好心的黑人管家梅拉德(Maynard),不仅给了他工作,还为其奠定了随后的白宫管家之路。
相较于白人安娜贝丝夫人的家奴规范,黑人管家教给西塞尔的是两样东西:其一,对“家奴”这个词的再认识。当他希望得到服务生的工作而提及自我能力(“我在梅肯是个家奴,做得还不错”)时,后者立即给了他一巴掌:“以后不准再用那个词,小子,那是白人用的词,词里满是仇恨,你爸爸没有教过你吗?”当然,作为农奴,西父教给儿子的只有饱满的棉花知识:“当花蕾裂开,花荚变成星型的时候,棉花就成熟了,就像天空中的大星星。”其二,对生存之道的再认识。关于生存,父亲教他不要招惹主人,安娜贝丝夫人教他如空气般服侍主人,而梅拉德则教他如何作为服务生自如地应对百态白人:“你要学会看他们的眼神,洞察他们的需求,学会预测,让你的客人眼中充满笑意。”因为“我们有两副面孔,摆给我们自己看的面孔和摆给白人看的面孔。想在他们主宰的世界混出名堂,就必须让他们感到你是无威胁性的。用我教你的腔调说话,北方白人喜欢有点抱负的黑人。”正是在梅拉德的悉心指导下,西塞尔掌握了精湛的黑人管家和服务技能,如调酒、擦鞋、擦灯、跑步、站姿等,随后又在其举荐下顺利进入华府的埃克斯塞尔(Excelsior)酒店工作,从而为他进入白宫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私刑下的而立与不惑
在白人政要和名流云集的埃克斯赛尔酒店,西塞尔维持了两种生存之道:第一,双重面孔和拿腔拿调:“两位从布法罗(Buffalo)远道而来,我为你们准备了一些烈酒,希望不会太冒昧。”第二,不闻政治和策略附和。当詹金斯(Jenkins)问他:“西塞尔,你如何看待黑鬼和白人小孩一起上学?”西:“老实说,我尽量不去关心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东西”。随后詹:“这就对了,西塞尔。政客都是罪犯,厄尔·沃伦(Earl Warren)(反对种族隔离的白人政治家和法学家)就该被千刀万剐,那个愚蠢的法官,居然想整合我们的学校。”西:“我认为沃伦法官不久就会发现那有多困难。”
对于华府的生活,西塞尔的评价是:“我从未想过自己这辈子能在这么富丽堂皇的地方工作,也从未想过自己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至此,西塞尔在族裔群体中率先步入了中产阶级行列。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历史语境中,这类美国非裔群体的特点是:“能够积攒一点钱,送孩子上学,拥有一个理想的住所”[1]123。对于自己的孩子,西塞尔的愿望是:“我发誓不会让他们经历棉花田里的苦难。”为此,为了保护儿子,他不希望他们做两件事:其一,去南方;其二,谈民权。这种由儿时棉花田阴影酿造成的坚固的南方情结导致了西塞尔不谈国事的态度和习惯,而这种态度和习惯对于他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助他赢得了白宫管家的席位。耳闻目睹了西塞尔与詹金斯对话的掌管整个白宫后勤运作的华纳(R.D.Warner),挑选他去弥补白宫管家的空缺。在白宫面试西塞尔的侍者总管(黑人)法洛斯(Freddie Fallows)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关心政治吗”,因为“在白宫不能有任何政治见解”。虽然对华纳单方面的挑选和西塞尔的兴奋表现颇为不满,但后者应对其不满的态度及专业的酒知识令他认定:“你会是个优秀的家奴”。另一方面让他与长子路易斯(Louis)日趋不和,细化为四个事件:
第一,玛米·提尔(Mamie Till Bradley)事件。1955年8月24日,14岁的提尔(Emmett Till)在密西西比梦林(Money)因与便利店的卡罗琳(Carolyn Bryant)搭讪而被其丈夫洛伊(Roy Bryant)及弟弟米纳姆(J.W.Milam)杀害。他们在塔拉哈切(Tallahatchie)河边“先用手枪抽打提尔,然后射击他的头部,再在其脖子上绑上一个75磅的石头,把他扔到河中”。整个案件的审判只持续了一小时,最终两人被判无罪,宣判那一刻法院内“响起了白人的掌声和欢呼声,布莱恩特和米纳姆甚至还以4 000美元的高价把他们的故事卖给了一个杂志——《看》”。[2]327
影片28:09-50:00处,西塞尔与儿子就提尔事件进行了争论。当儿子说自己想去参加提尔宣传会时,西塞尔强硬地进行了否决,因为它“一点好处都没有”、“这种破事只发生在南方”,因此当时“我离开那里就是为了我们能够活得更好”,而现在“我为白人工作,让我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白人。”话语间西塞尔耸耸肩充满自豪,而儿子却摇摇头满脸无奈。随后,父子间这种大相径庭的态度与相关矛盾成为整部影片的中轴线。相较于儿子对提尔事件的关注,西塞尔留意的是小石城(Little Rock)事件。1957年9月4日,联邦法院为9个黑人学生提供了一入小石城中心高中读书的机会。为对付这些黑人入学,阿肯色州州长福伯斯(Orval Faubus)宣布整个州进入紧急状态,启用国家安全部队确保入学变成骚动和暴乱。无法容忍阿肯色州政要无视美国宪法的行为,艾森豪威尔派遣联邦部队到南方,成为“自内战结束后、重建时期以来第一个动用军队保护黑人的总统”[2]330。对此,西塞尔评价道:“这是我首次目睹一个白人为黑人挺身而出”,于是“我告诉路易斯,总统一定会让我们的处境好起来的。”然而,即使“在新的黑白学生同校上课的制度下,种族依旧就像一件紧身的衣服。没有人会提到种族,但它始终存在于社会交往活动的界限之中。你可以远观,但不能触摸。”[3]92
第二,巴士被炸。出狱后,路易斯坐上了阿拉巴马伯明翰的自由巴士。当蜂拥而至的白人举着“阿拉巴马痛恨黑鬼”的牌子,吼着“黑鬼,滚回去”奔向巴士时,西塞尔正面带笑容耐心地为卡罗琳(Caroline Kennedy)讲故事。此事件极大地引起了肯尼迪总统的重视,也正是这位总统使西塞尔对儿子看法开始改变。当后者告诉他路易斯被关在监狱时,作为一个父亲,西鼓起勇气询问儿子的处境。当肯告诉西:“估计被打得不轻,但他应该习以为常了,因为在过去的两年他被捕16次”时,作为一个白宫的黑人管家,西只能:“是的,先生,还有别的吩咐吗”,然后在听到“没有”后转身离开,直到肯说:“我弟弟鲍比说这些孩子改变了他的内心,也改变了我的”时才再次转身。这种改变使肯发表了废除隔离的电视讲话,也使他在达拉斯机场被暗杀,而其不幸则粉碎了所有非洲裔“迈向大美国(AMERICA)”[4]69的愿望。
第三,路德·金随行。当路易斯与金博士在田纳西为黑人选举权斗争时,西塞尔与同事在华府家里玩纸牌。此时的西塞尔,对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满怀希望,然而这种乐观主义很快消失在无常的总统怒吼之中:“这个国家就是个装满了黑鬼怒火的马上要爆炸的火药桶……帮我把这群黑鬼赶回家。”与此同时,路易斯及民权者在塞尔玛(Selma)遭受了“血色星期天”,并与金博士等人就越战进行谈论,并谈及黑人帮佣。当路以父亲的职业为耻时,金却告诉他:“黑人帮佣在族裔历史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用“汗水和忠诚来抗争人们对这个种族的偏见”,用“过硬的职业道德和高贵的品格使种族仇恨慢慢消弭”,虽然他们“看上去卑躬屈膝,但在很多方面具有不为人知的抗争性。”
第四,黑豹党成员。当非暴力无法应对白人的暴力时,黑人需要新的维权形式。为此,路易斯加入了黑人武装组织——黑豹党(Black Panthers),当穿着花哨,带着梳着爆炸头的卡萝回到家后,久违的父子再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歌莉娅提到伯蒂埃(Sidney Poitier)主演的电影《炙热的午夜》(),并沉浸在对西德尼的喜爱时,路易斯打断她:“伯蒂埃是白人臆想中的黑人形象”。西:“但他的电影都是在为平等权利而战。”路:“仅仅是通过一种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而且“他的方法就是当白人狗,演白人狗。”随后,西塞尔起身怒吼冲向儿子,而路易斯也爆发了他对父亲的积怨:“对不起,管家先生,我不是故意要取笑你的英雄。”
此处,西塞尔与路易斯父子之间的矛盾浓缩了当时非洲裔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即以西为代表的中上层阶级所坚决反对的底、下层草根的种族自豪感运动——极力彰显黑色的自我,并高呼黑人的就是美的。因为这种“美即黑色”运动在“1960年代留下的后遗症是:魔镜,魔镜,谁最黑?”[5]127而这种毫无遮掩的“黑”全面暴露了族裔性,其中很多则是自殖民主义时期以来一直被白人所诟病的。因此,对于黑人中产阶级而言,相对富足而体面的生活使他们自奴隶制时期就“有一种日趋见长的情感——想进一步融入美国这个理想之地”[1]123。这也就是西塞尔支持查理去越南的根本原因。相反,以路易斯为代表的民权主义者则看穿了丑陋的美国现实:当它需要使用黑人时就呼吁平等,而不需要时则坚持隔离,并声称:“隔离但平等并没有暗示某个种族比其他种族低等”[2]203。
三、后政治秀的耄耋期颐
实际上,在如潮的黑色运动中,西塞尔也争取过权利,突出表现为二进华纳室。初进1968年,西塞尔恭恭敬敬地进去,犹豫良久后鼓起勇气告诉华纳:“由于有色(改口为)黑人员工与白人员工做同样多的工作,我认为我们的薪水应该与劳动成正比,先生。”华:“‘黑人’员工?”西:“我同时觉得我们应该有晋升的机会,黑人帮佣还从未被提升到技术员办公室。”华:“我们对你很满意,西塞尔,但如果你对你的薪水和职位不满意,那么我建议你另谋高就。”西:“恕我直言……”。华:“别被路德·金的扯淡蒙蔽了双眼,想想我是从哪里找到你的。”随后,西塞尔几度欲言又止,最终在蹦出“打扰了,先生”后离去。二进1986年,年迈的西塞尔从容进去,首先问:“我能坐下吗?”然后是:“我在这里二十多年了,一直以来黑人帮佣的薪水都比白人低,我觉得这不合理,华纳先生,一些黑人男佣现在都该当上技师了,多年前就该被晋升了。”华:“你这么觉得?”西:“我要求跟白人帮佣领相同的薪水,否则我就离开。”华:“那你只能离开了。”西:“我告诉过总统你会这么说,他让我告诉你把这话亲自说给他听,失陪了。”
促成这种转变的首要原因是查理的牺牲,1973年的生日那天,前一刻西塞尔还自豪地责问长子,下一刻则因为二子的离世开始迷茫地深思。相较于父亲的改变,不满以暴制暴的路易斯也在离开黑豹党之后就选择了返校,攻读了政治学硕士。只是他并未参加弟弟的葬礼,而父母亲身边那张空着的椅子再次点燃了父子矛盾。不同于二者之前绞缠于族裔整体、族裔阶层的矛盾,这次的矛盾从大家收缩为小家。为此,路易斯尊重了父亲的吩咐——离开。
1973年9月9日之后,西塞尔开始了诸多改变,突出表现就是为白宫黑人帮佣赢得了加薪和晋升,而此举使他得到了南茜·里根(Nancy Reagan)的邀请——“不是以管家,而是以客人的身份”带上妻子参加国宴。虽然国宴为两位老人带去了惊喜、实现了期盼,但也让他们重识了自我:歌莉娅整理略显暴露的礼物;西塞尔:“被服侍和服侍人的感觉很不一样,可以说截然不同,我能看到管家们为生存而练就的两副面孔,而我的一生也不过是活在这两副面孔之间”;直指了真相:“我希望我们能被真正接纳,而不是政治作秀。”
为此,西塞尔辗转反侧:“那次国宴之后,一切都变得不对劲了。”于是,他梦到了棉花田里的父亲;翻开了尘封已久的儿子的东西;瓦解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成见:“路易斯从来就不是什么罪犯,他是个英雄,为拯救国家的灵魂而战”;(对自己):“我一直喜欢服务,现在感觉不了”;改变了新的观点(对国家):“美国人总是对我们对自己人做了什么视而不见,而对外面的世界指指点点。我们听说过集中营的事,而两百年来这种集中营就发生在美国土地上。”随后,西塞尔甚至带上妻子驱车返回了棉花田,当年他奋起反抗的地方。回华府后,他提出了辞职,面对里根的挽留与感谢,他只是淡淡的:“我只是想第一个告诉您,仅此而已。”当里根试图谈心:“西塞尔,关于公民权利什么的,我有时会害怕自己站在了错误的一边,怕自己做错了。”西:“有时我会被它的真实含义吓到,但是我正在努力让自己不再恐惧。”至此,西塞尔彻底摆脱了棉花田的阴影,重拾了童年的自己。于是,他找到正在南非大使馆前要求里根政府释放曼德拉的儿子,张开双臂拥抱了儿子,并与他一起抗议和入狱。为此,西塞尔的人生从忍耐又摆回为反抗,正如他说:“进过监狱之后,我似乎全看透了。”然而,不曾想在迟暮之年还能“看到一个黑人真正地去竞选美国总统”,并赢得了胜利,从而在那一刻与儿子紧紧相拥、热泪盈眶。确实,奥巴马的上台令黑人振奋,因为他代表了族裔完胜,把400多年的黑/白关系整整旋转了一周,这种逆转对于服侍过8届白人总统的西塞尔具有别样意味,因此他戴上肯尼迪夫人赠送的领带和约翰逊总统赠送的领带夹,昂扬阔步走向了奥巴马。然而,即使高为总统,奥巴马也并不能真正带给其族裔多大切实利益,因为就其个体而言,他“不仅仅是小团体和国家溶解力的敌人,还是自由的敌人”,[6]而就集体而言,他依旧无法实现下层黑人大众的脱贫。毕竟,即使抛开个体性,作为黑人精英中的精英,奥巴马代表的只能是上层黑人的族裔性。
综上可知,导致西塞尔与路易斯激烈矛盾的根源是黑人管家这个身份本身的尴尬——在族裔民权运动中携带的是坚硬的自我主体性。路易斯认为父亲的这种主体性为满足白人的预设而淹没了黑人应该拥有的真正的黑色,因为白色语境为非洲裔家奴预设了一张黑色的脸,这张脸需要保持沉默,而这种沉默说明“黑人性是一个缺场符号——有关脸和声音的显著的终极缺场符号。”[7]137然而,实际上西塞尔及同事也以其力所能及的方式呈现了柔软的黑人性。换句话说,不同类型的黑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彰显着相应的黑人性/族裔性,正如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说的:“美国黑人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实体存在”,相反,他们“从来到这个国家的第一天就开始表述他们的不同观点”,甚至其“自由之路也并不一致”,而是“像充满回路和涡流的河流”,[8]因此族裔性在凝固如一之前还需要趟过很多河流,而且这些河流或许永远都不会有尽头。
[1]LeRoi Jones. Blues People: Negro Music in White America[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2.
[2]Henry Louis Gates, Jr.. Life Upon These Shores: Looking at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1513-2008[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1.
[3]Henry Louis Gates, Jr. Colored People: A Memoir[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4]Houston A. Baker, Jr. Blues, Ideology, and Afro-American Literature: A Vernacular Theory[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5]Henry Louis Gates, Jr.. Loose Canons: Notes on the Culture War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6]Henry Louis Gates, Jr.. Tradition and the Black Atlantic: Critical Theory in the African Diaspora[M]. New York: Basic Civitas Books, 2010. xiii.
[7]Henry Louis Gates, Jr.. The 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8]Henry Louis Gates, Jr., Donald Yacovone. The African Americans: Many River to Cross[M]. Stonesong Press, LLC, 2013, xi.
(责任编辑:张新玲)
Flexible Blackness and Rigid Subjectiv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HE Yanli
is a gorgeous film about the life story of Cecil Gaine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is the miserable childhood and his visible blackness when he worked with his parents in the field as a young man, until the young master raped his mother and killed his father. After that, he became a house nigger. The second is the invisible blackness and visible subjectivity in Cecil’s middle age life when he left George and went to North Carolina as an adult. There, he met a kind butler Maynard who taught him how to serve the White in a sly way. In this way, Cecil earned his subjectivity in North America, and changed his life conditions. The third is the elderly time of Cecil, and his fighting life when he lost his son, Cecil finally understood that the tru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hite and Black, ant that the real subjectivit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is his Blackness.
blackness; subjectivity; Cecil; house nigger;
I106
A
1009-8135(2014)05-0097-05
2014-06-02
何燕李(1984-),四川雅安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美国非裔文学理论和影视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