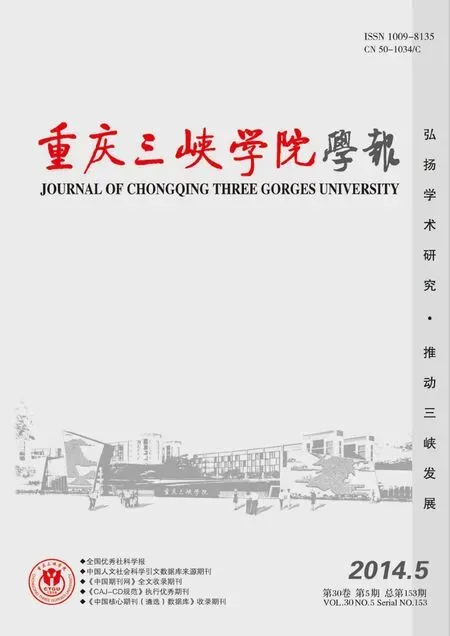析沈周文人山水画与汪野亭山水瓷板画异同
2014-03-29张丽娜
张丽娜
汪野亭研究 主持人:黄念然
主持人语:汪野亭作为近现代瓷绘艺术发展进程中革故鼎新的大师级人物,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对前辈大师创作理念及其审美精神的不懈学习与汲取。魏晋六朝之气韵生动,宋元山水画之俊逸,明代沈周之豪放,董其昌之以书入画,清代王石谷之清丽厚实,石涛之萧散狂放等等,均能入其彀中而赏其风格,悟其意境,师其技法,从而在博采众长之中自出机杼。本期开始将主要研讨汪氏创作理念及其技法对前辈大师的继承与创新,力图由此厘定汪氏瓷板画创作师古而自新的艺术历程。
析沈周文人山水画与汪野亭山水瓷板画异同
张丽娜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结合汪野亭与沈周的个人经历和心理历程,从创作风格、创作题材两方面比较沈周文人山水画和汪野亭山水瓷板画之间的异同,探寻沈周的创作对汪野亭的影响,以及汪野亭自身作品独有的特色,以期进一步认识汪野亭的瓷板画创作。
沈周;汪野亭;师古与求己;创作风格;创作题材
当代美术评论家陈传席曾精炼地概括了每一位艺术大师一生的经历,先“神于好”,再“精于勤”,最后“成于悟”。每个艺术家的创作之路都从仰慕前辈的优秀作品开始,但只停留在神往阶段而不付诸行动的话一辈子都只是一个空想家;心中有了目标就朝它前进,以勤补拙,慢慢完善自己向先贤靠近;当技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能否化蛹成蝶就在于最后一步——悟,这需要艺术家本身的天资禀赋和人生机缘。用马克思辩证主义哲学来阐释这段“成艺”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神于好”和“精于勤”是量的积累,它们如木之本、水之源;“悟”是由量变向质变飞跃的临界点,越过了它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中国传统文化璀璨辉煌,绘画艺术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每个时代绘画领域都不乏能人异士引领潮流,身为“珠山八友”之一的民国画家汪野亭就是这样的英才,他变革了墨彩山水,在陶瓷绘画中完美再现了中国画青绿山水的用笔设色,将中国绘画风骨与陶瓷工艺融为一体,开创出“汪派山水瓷画”的新格局。他的成就是师古与求己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明代画家沈周在其整个艺术创作的师古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沈周(1427—1509年),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世代隐居吴门。明代画坛人才辈出,“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却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沈周正是“明四家”的灵魂领袖。沈周开创了吴门画派,将宋院体与明浙派的硬度和力感融入元人的含蓄笔意,兼以吴镇墨色形成了磅礴而苍润、质朴而宏阔、平淡而悠远的“粗沈”风貌。他的学生文征明称赞他的作品为“风流文物,照映一时。百年来东南文物之盛,盖莫有过之者。”[1]24本文将结合二人的个人经历和心理历程比较沈周文人山水画和汪野亭山水瓷板画之间的异同。
一、取“粗沈”之貌画汪派山水
沈周的绘画经历了由“细沈”向“粗沈”蜕变的过程。画作由布局繁复曲折、结构严谨有序、笔法锐利细密、风格缜密细腻的细笔勾染逐渐脱胎为布局简疏明了、用笔雄浑苍劲、墨气淋漓老成、格调雄健宏阔的粗笔点簇。汪野亭早年即仰慕“粗沈”之豪健,汲取“粗沈”之豪逸天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汪派山水。
(一)布局用色
汪野亭的瓷板画和以往瓷板画之间在色彩的选择上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粉彩于康熙晚期创烧,雍正时期发展成熟并达到高峰,粉彩山水瓷画亦随之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粉彩山水瓷画逐渐由硬朗劲健、挥洒自如转为刻意雕琢、柔婉细腻。乾隆后至清末陷入程式化且缺少活力,用色俗艳秾丽,逐渐为大众所不喜。清末民初,一批文人画家迫于生计的压力加入陶瓷绘画创作,开始尝试以陶瓷作为载体表现传统国画的神韵,使瓷板画获得了新生,这种瓷画风格后人谓之“浅绛画派”。但因文人缺乏陶瓷工匠的技艺,这些制成品出现了“色阶少,光泽度差,颜色容易剥落等不足,还有待完善。”[2]汪野亭敏锐地感受到了传统粉彩山水瓷画和浅绛山水瓷画的优点和缺陷,决定将二者融为一体加以革新,创造有传统文人风韵的瓷板画作品,融合的关键就在于“粗沈”之豪健。
“粗沈”的风貌在其晚期画作《京江送别图》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画中主人乘舟远去,江面平远淡抹而出,几乎不着颜色,留出大片空白尽显水之浩淼悠远;群山以粗笔披麻皴法出之,墨色温厚圆润,更显山之苍茫高远,并以淡墨于群山间隙轻抹远山轮廓,远山更兼云雾掩映,墨色浓淡结合尽显山之苍秀飘渺。主体轮廓纯用墨色绘制,具体人、景、物的点染则采用各种颜色,以灰蓝、浅灰蓝、桔色制衣,以土黄色填山,以墨绿色点叶。沈周还娴熟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绘画“计白当黑”的手法,在画作上留下了二分之一左右的空白表示山之态、水之势。沈周晚期的画作墨与色、虚与实的交融互渗已至神境,画作整体清新淡雅而又不至于寡淡无味。汪野亭早年学习时就已醉心于“粗沈”之用笔老辣干练,着墨之氤氲淋漓,设色之清淡雅丽,决意将其运用于自己瓷板画创作中。
汪野亭的瓷板画《空山雨后》明显可见沈周画作中豪逸之气。这幅画作近景两岸的岩石以珠明料粗勾轮廓,烧成后成色为干灰色,类似于沈周画近山时的干笔皴擦,又在珠明料上覆盖蓝料凸显岩石的厚重冷硬;两岸间一泓清流延伸至远方,流水以一木桥相连,一村夫体态微蜷从桥上走过,步履轻松适意,与沈周《京江送别图》中那个持竿过桥的渔夫极为神似。中景采取“计白当黑”的手法设大片空白用以表现流水,在空白上覆盖厚薄程度不一的雪白料,表现出水流的流势和波澜,“产生了从平面走向空间的视觉效果。”[3]远景仅以寥寥数笔画出远山轮廓,留下大片空白覆以厚薄程度不一的雪白料,营造出山上云雾掩绕的空濛润泽之境,潺潺的流水和山中的云雾似乎自然连成一体,形成了水天一色的神妙韵致。据统计,汪野亭瓷板画中多有留白,一般留白占画作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占了画作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再覆以厚薄程度不一的雪白料妙显远山之轻烟淡峦、近山之苍劲有力、山间云雾之飞腾飘渺、山下流水之浩淼绵长。这种显山绘水之法与沈周晚年豪逸之风颇为神似,整幅画作空灵流动而又饱满充实。
(二)诗书画互溶
苏轼曾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诗书画三者本同根同源,诗的意境连缀起来就是一幅画,书画二者皆由毛笔所作,运笔时挥腕的力道、下笔时笔锋的选择、停顿时笔势的扭转等技巧本就相通,中国画是诗书画三者溶于一体的产物。汪野亭早年就已醉心于沈周放纵恣肆的书法,力仿沈字之洒脱奔放。汪野亭的字由此也逐渐发生了蜕变,由早期的清秀虚软走向古朴恣意,这个变化在他“汪”字的落款中清晰可见,开始“汪”的第二画和第三画一般是连在一起的,后来第三笔和第四笔连得很近,甚至有些直接就连在一起了,用笔愈发老辣潇洒,字体愈发自然随性。
书之随性恣肆与画之飘逸疏野间,气的连贯性或许让汪野亭进一步领会到了书画同源同体的真谛。原先瓷板画的书画是截然分开的,一般是一面作画,一面题诗,观者在欣赏时难免有断层之感。汪野亭大胆突破前人窠臼,率先运用“通景山水”章法装饰瓶类制品,绘画采用散点透视法,在圆柱式的器皿上展开一幅完整的画面构图,使连绵的群山、幻邈的烟云、苍润的岩石、缓静的流水、葱郁的树木连成一体,形成360度贯通不绝的完整构图,无一丝勉强刻意衔接的痕迹,欣赏者在任何角度都可以充分体味山之姿、水之味,“山水源头无觅处,游子信步山水中”的意境油然而生。同时,在画作中直接题诗、写字、落款、下印,真正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是文人画与瓷板画的完美融合。这种装饰风格开20世纪初景德镇粉彩山水装饰章法的新风,后人多沿袭此章法继续进行创作。
二、尽前人题材兼己意
“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高士逸人。”[4]75沈汪二人虽非衣冠贵胄,但皆可称得上是高士逸人。绘画题材上,沈周和汪野亭也多有相似之处,但汪野亭又有自己的特殊题材。中国的山水画并非对山水的纯粹客观描绘,而是要“胸中有丘壑”,将人事融贯于山水之中,于山水中展现某种精神,“山水以形媚道”、“圣人含道映物”,[5]22形成“有我之境”。因此,中国山水画中大多并不只有高山、流水、草木这种纯自然界的万物,一般还会点缀以茅屋、亭台、楼阁、行船、游人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点缀之物使原本沉寂的山水变得饶有生趣,形成情景交融之境,“情景者,境界也”。[6]113这些小的点缀物最能看出创作者的意趣,探寻创作者的心灵最宜从这些小处着手,以小观大。
(一)人迹点点品旨归
沈汪二人的相似之处在画中人物的刻画上可见一斑,画作中的人物一般体现了作画者的社会交往范围、日常生活活动、心中信仰偏好等。因此,人物的选择和表现中往往能窥探出创作者的人性之美、心灵之美,正如西晋顾恺之曾有言:“人最难,需形神俱得,次山水,次狗马,难成而易好,不待猜想妙得也。”每一个画家都会跟随着心灵的脚步在作品中表现不同类型的人物。沈周的画作中有雅会切磋的儒士,见《魏园雅集图》;有杖策寻隐的高士,见《山空无人图》;有依依话别的友人,见《京江送别图》;有徜徉山水的闲人,见《高木西风图》;有信步由缰的旅人,见《灞上风雪图》;有坐于堂屋的雅人,见《东庄图》;有辛勤劳作的农士,见《虎丘饯别图》。从这些人物中可以看出沈周平时的生活轨迹,他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士,既秉持着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准则,喜好与文人雅士结交,于绿水青山中谈诗论艺、共话世事;又向往着道家“无为而治”、“抱守虚静”的澄怀观道,孑然一身访名山,杖策披棘待古松,体味隐逸孤野之乐。汪野亭笔下也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或是论诗访友的文人雅士,见《修竹茅亭图》、《石岚飞瀑图》、《空山秋色图》、《携琴访友图》等;或是粗麻短褐的平民百姓,见《空山雨后图》、《溪山烟雨图》、《湖滨垂钓图》等;或是走山觅水的隐者高士,见《松林杖策图》、《山水图》、《长桥波影图》等。这些人物的刻画体现出沈汪二人作画旨趣的一致,这种一致性是他们为人处世态度的折射,他们都深受儒家“入世”之法影响,喜好广结各阶层好友,且坚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文人风骨;又沉醉于道家“出世”之清静无为,喜欢游历山水,春慕“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夏赏“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秋感“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冬守“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种题材的相似性源自于他们经历的一致性。
首先,沈汪二人皆社会交往广泛,他们结交的对象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些形形色色人物就是他们绘画的素材。沈周社会接触面之广在历代隐逸画人中是十分罕见的,使者、大夫、缙绅、好学者每天都到他家拜访,可以说是络绎不绝。从其墓志铭中可见沈周广泛地与自己同道中人交往,这些人物大抵具有文人的身分,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能够在雅集文会中舞文弄墨、共同参与文艺活动。除了与和自己有共同爱好的人交往之外,沈周还慷慨亲和地对待无甚学识的白丁,“贩夫牧竖”持纸来索画,亦“不见难色”,[1]18“下至舆皂贱夫有求辄应。”[1]24汪野亭亦好广泛交游,“月圆会”内八友自不必说,与瓷艺圈中的吴霭生、汪大沧、陈香生、余灶昌等也多有往来,还常与上层社会中爱好艺术的文人雅士赏瓷论画。这些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时,或围炉论经,或眠琴绿荫,或当窗吟诗,或品茗作画,极尽风雅淡泊之能势。对待贫苦百姓,汪野亭也十分仗义。卖菜为生的乐平同乡王荣初被指为地下党遭当局逮捕,他以身家性命将他保释;街坊或亲朋间发生纠纷,他必不偏不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解决纠纷,并自费赴茶馆调解的茶资;因此,他受到众人的敬仰,1942年辞世时,500多位各方人士护送其灵柩上船回乐平安葬。
其次,沈汪二人皆具文人风骨,虽与权贵交往,但并不屈膝阿附权贵为自己谋取利益。沈周15岁时就代父任粮长,赴南京接洽公事,那时的户部侍郎崔恭是名爱好文学的雅官,沈周作了一首百韵诗上拜,崔恭见了大为惊异并有些怀疑这是否出自15岁少年之手,因而面试一首凤凰台歌,沈周援笔成诗,作得十分精美工整,崔恭大喜赞其为王子安(唐代王勃,字子安,六岁能诗文,少年作《滕王阁序》名震寰宇,初唐四杰之一)复生;沈周后来因画艺卓绝、文采斐然、风骨高洁受到许多朝中重臣的青眼相待,如李相国、屠太宰、吴侍郎等皆倾心与之相交,声名不可谓不煊赫。但有一次他被误以为是卑贱的的画工而被派去绘察院的壁画,也是欣然前往。汪野亭也是这样的一个人,虽不排斥与权贵交往,但并不刻意讨好巴结,他1915年所作的墨彩瓷板《江山胜景图》就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当时已成为全国最著名的瓷画大师,作品供不应求。民国大总统曹锟曾派专人莅镇收购他的瓷板画,平日也会与杜重远之类的上层雅士坦诚相交。但对于他不愿结交的虚伪权贵,汪野亭不愿虚以委蛇,某专员五次求画未果,其警卫拔枪相逼,专员按住手枪并训斥手下休对先生无礼,汪野亭识破此双簧戏法,促其开枪,专员扫兴而去。
最后,沈汪二人皆好畅情于山水之中,或拄杖扣柴扉,或空山悟万籁,或溪畔聆群响,这些体验运用到山水画中不仅有利于描山绘水,尽显山姿水态,还有利于陶冶性情,更好地把握和表现人物的风韵。沈周一生极爱出游,有大量纪游感怀的诗作与画作为证。有人将沈周旅游的地点,分类整理为:僧寺游、南京游、杭州游、天台游、宜兴游、虞山游以及吴中游。倘若浏览《沈周年谱》,可以发现沈周于成化乙酉(1465年)游南京之后,几乎年年出游;直到正德己巳(1509年)逝世当年,83岁高龄的他,尚有宜兴善权洞之游。汪野亭亦是如此,他自谓“一生好入名山游”,一为体验,二为写生,常道“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足迹遍布景德镇及其邻近的祁门、婺源、黄山、乐平的名山古刹。
然而,与沈周不同的是,汪野亭画作中还有一类重要的人物——僧侣,《明月松间照》即是典范之作。画作采用平远式构图法,构图严谨有度,近景最显眼的位置伫立着三棵古松,运笔劲健有力,松树自古就与坚贞、隐忍、高洁等品质联系在一起,刘祯《赠从弟》一诗有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画者以树皮上密集额横点和突起的树瘤来表现树的风霜,最前面的古松态势尤为惊人,几乎与地面平行生长,但仍然生意盎然;这棵古松后站着一名僧侣,身着红色袈裟,脚踏纯黑僧鞋,双手藏于宽袖之中,身体微微向前倾倚靠在面前古松上,头部以45度角向上仰望,神情悠远平和,仿佛已与天地融为一体;画作中虽然并未绘出明月,但僧侣的意态、画上的题款及整幅画作笼罩的若有似无的清辉都间接表现出了明朗的月华,整个画作虚实相生完美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松下望月图,给人以静谧、安详、淡远之感。
那么汪野亭为何对僧侣这类人物如此偏爱呢?这和他醉心于佛教有莫大的关系。佛家宣扬万物皆空,以苦——人生皆苦、集——苦的原因、灭——超越苦难、道——脱苦之法为佛家“四谛”,即四大真理。汪野亭一生坎坷,佛家理念对其人生态度的构建、审美趣味的选择、摆脱尘世的纷扰有重要的意义。汪野亭晚年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瓷板画生意每况愈下,长子和幼子还险被抓去充军,这些都促使他多有出世之心,参惮悟道、诚心礼佛。这种禅意融贯于其山水瓷画中形成了孤远清寂、超凡脱俗的境界。同是“珠山八友”之一的王大凡为其作诗一首云:“烟水苍茫叠叠山,孤云未许俗人攀;闲中每喜寻僧语,静里常思学驻颜。”可以说是对其礼佛生活最好的刻画。
(二)船行悠悠有真意
除了人物,行船也是沈周和汪野亭山水画作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舟船虽是人造之物,但和自然界有着莫大的关系:首先,制作舟船的材料是取自自然界的林木;其次,舟船的制作是古人受自然的启发而得。《世本》中记载古人“观落叶因以为舟”,《淮南子·说山训》中也说“见簌木浮而知为舟”,最早的“船”是用许多根木椽或竹杆扎成的木筏或竹筏,继而是独木舟,“挎木为舟,刻木为楫。”因此,舟船可以说是陆地和流水的交融,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是自然的馈赠和人类智慧的结晶,沈汪二人的山水画作中多次出现的舟船正体现出他们已将己身融于万籁之中,达到了物我合一之境。但是仔细观察他们的画作,我们可以发现二人画的舟船有明显区别。沈周的画作中舟船一般为独木舟或乌篷船,以乌篷船居多,见《京江送别图》、《东庄图》、《独游孤山图》等。汪野亭的60幅画作中,舟船出现了26次,偶见独木舟(见《客路青山图》),但多是乌篷船和帆船同时出现在一幅画作中,且帆船占据着主要地位,见《长桥波影图》、《秋江帆影图》、《破浪乘风图》、《山川秀色图》、《桃园问津图》、《古刹钟声图》等。舟楫虽小,却可以反映出许多信息,从中可窥见沈汪二人人生轨迹的异同。
沈周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学底蕴渊博,从小接受的是正规的教育;15岁时接受父亲粮长一职开始受俗务缠身,但也并未遇过什么坎坷辛酸;45岁时即将家中事务交付长子,过上属于自己的闲云野鹤的生活,可以说沈周的一生是比较平顺适意的,尤其是晚年他已完全步入了“诗意的栖居”。因此,他画作中的舟船多是简单的一叶扁舟,或者带顶的乌篷船,这两种船都比较适合独自一人或邀朋携友来一场短途的旅行,乘船者既可独立于舟头极目眺望,感清风入怀,闻百鸟啼鸣;又可与几名友人藏于篷下,或躺或卧,品茗论诗,追古怀今。可见,沈周对现世生活基本是满意的,他从未想过要前往某个遥远的彼岸。
汪野亭则不同,他的求学和成艺之路一步步走下来充满了汗水和辛酸。汪野亭家庭贫困,父亲只是一个木匠,他自己开始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私塾先生。因醉心于绘画,他决定放弃教书这份稳定的工作去学习美术,好在他父亲和祖父都十分支持他的决定,他才得以考入江西省陶业学堂接受正规的教学、系统的培训,为以后创作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晚年经历日寇入侵、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之难,更加看淡世事。同时笃信佛教,佛家宣扬的来世、轮回、彼岸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渴望前往一个安静祥和没有纷争的彼岸。敦煌壁画、帛画、纸画中的“观音经变”里出现的舟船大多都是帆船,有个词叫“扬帆远航”,帆船似乎冥冥之中就给人一种可以将人带往遥远的极乐之土的感觉。除此之外,白色风帆在水中漂荡摇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上飘浮的白莲,佛教在很多地方都以莲为代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莲即是佛,佛即是莲。汪野亭在1942年创作的《古刹钟声图》上题诗曰:“古寺晨钟响入云,客帆风正洗潮平,林泉到处皆名胜,山水之间有妙人。”将帆船和古寺连在了一起,那客帆的归处正是古寺。帆船正是他用以表明自己身处此世,心向彼世的意象。
三、小 结
沈周和汪野亭都是各自时代中声名煊赫的杰出人物,汪野亭融“粗沈”之貌于己变革的“粉彩山水瓷画”,一扫前人瓷作之弊端,首创诗书画印于一体的“通景构图法”,成为瓷绘界竞相借鉴和模仿的典范,一直传承沿用至今。他们的创作题材也多有重合之处,但汪野亭在沈周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特色[7]。两代大师隔着数百年遥遥相望,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还未被发现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值得我们进一步探寻。
[1][元]马祖常.石田先生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汪雪媛,江葆华.汪派山水瓷画艺术[J].景德镇陶瓷,2008(3):15-16.
[3]刘静.从“雪白”的使用看汪野亭瓷画之艺术风格[J].艺术市场,2008(2):72-73.
[4]张建军.中国画论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5]潘运告.汉魏六朝书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6]杨大年.中国历代书画采英[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87.
[7]王小梅.论汪野亭瓷板画之渊源[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3(6):63-65.
(责任编辑:郑宗荣)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Shen’s Literati Landscape Painting and Wang ’s Porcelain Plate Painting of Landscapes
ZHANG L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Shen Zhou influences Wang Yet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tter’s works by means of comparing the drawing style and subject matter in Shen’s Literati landscape painting and Wang’s porcelain plate painting of landscap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 their mental course, so that Wang Yeting’s porcelain plate painting can be known by more people.
Shenzhou; Wang Yeting; learning from the past and creation; style; theme
J211
A
1009-8135(2014)05-0064-05
2014-05-10
张丽娜(1991-),女,江西南昌人,华中师范大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