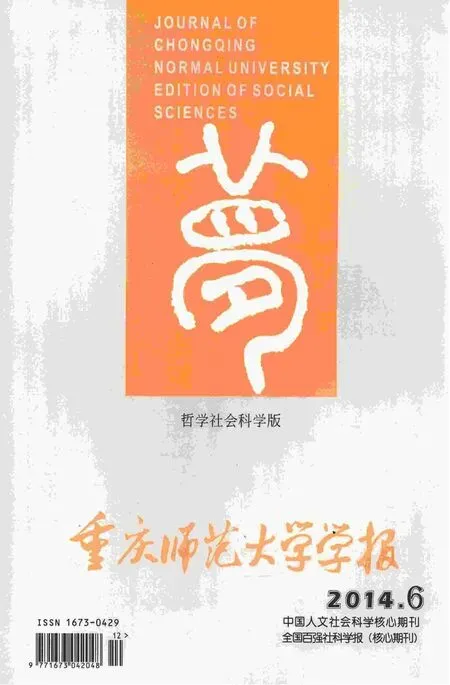中国传统美学话语方式探析
2014-03-29杨江涛
杨江涛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中,展示出了一种兴味盎然的审美经验。这种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审美经验,是古人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凝聚为蔚为大观的民族文艺传统,甚至还在民族的现代生活中滋生蔓延。处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当下社会,如何看待和言说这一民族遗存,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沿用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进行言说,是一条路径;运用现代美学理论话语解说民族审美经验,是又一条路径,这也是多年来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然而,循此路径和方法阐释过的民族审美经验是否是其本来面目?此一路径能否引导传统美学走向现代化?对此问题的质疑引发了本文重新对前一路径——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进行考察。在对民族审美经验进行自觉反思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美学形成一套独特的话语方式,这套话语方式是对中国传统审美经验的理性言说,是对其内在品性的如实展示。本文以为,这种言说民族审美经验的方式,不仅对如实了解民族审美经验意义重大,而且也对研究传统美学和传统文论以及其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故当详察。
一
中国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在言说民族审美经验的过程中,显示出了有别于现代美学理论话语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因循一种非对象化的体验世界的路子。传统美学在反思和言说民族审美经验的时候,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即就着审美经验的性质来言说,审美经验本来是什么样子,它就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示,这是一种就着审美经验的存在语境进行“非分别”言说的方式。这反映在传统美学的一系列经典命题中,比如“澄怀味象”和“一画论”。南朝的宗炳在《画山水序》开头一段云“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即道出了事物的“象”区别于“道”的独特审美价值所在。若按照现代美学的解释,主体首先在面对事物的时候要胸怀澄明,进而才能把握到对象事物的美。真的如此吗?“澄怀味象”没有提到“怀”是主体的,“象”是客体的,更没有说明哪怕是暗示二者是一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在这里,自然山水不是被观审的对象,而是与人唱酬互答的友好主体,“山水以形媚道”[1],开启了欣赏者超拔的精神境界,在这种人与世界交融一体的精神境界中,自然山水作为审美化的存在得以开显出来,此种存在是如此地饶有兴致,使人回味无穷。清初的石涛在言说绘画经验时提出的“一画论”,也是对艺术家体物方式的概括。[2]23根据石涛的看法,画家从世俗世界的关系限制中超脱出来,进入精神的澄明之境,方能体验到大千世界的鸢飞鱼跃。在这里,画家主体和自然世界之间从来都没有一个分明的界限,与此相反,画家审美胸怀的形成和精神境界的提升是要以大千世界的蒙养和陶冶为前提的。“一画”所示正是二者交融一体的状态。“一画论”和“澄怀味象”一样,展示出来的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品味、体悟和交融关系,而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审”与“被审”的关系。这在中国美学的一系列经典命题如“物化”、“情景交融”等之中,无不得以验证。
中国美学之所以会总结出诸如此类的命题,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事物不是简单的被认识的对象,而是体验的存在,只有在人与世界的交融一体状态中,只有当人在世界中品味、体验、一往情深地生活时,事物的美才能够巨细靡遗地显现出来。概言之,传统文化中的审美经验本身就是物我一体的黏着体,容不得半点罅隙,所以只有一种非对象化的、非分别的方式才能道出其本来面目。而以一种对象化思维为基础的现代理论来解说非对象化的传统经验,可谓缘木求鱼。
其次,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紧密关涉具体事物,以说明当下经验。即传统美学在言说审美经验的时候,一方面不离具体形象的事物,另一方面突出经验的当下品性。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总结性评价中,出现了不胜枚举的“诗话”、“词话”、“画品”、“书品”乃至“棋品”等著作,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用具体形象的事物来暗示、隐喻、点拨审美经验。以“诗品”为例,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可谓此代表,其中关于诗歌风格之一种“纤秾”的论述如下:“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3]显而易见,据现代理论,这种论说方式是非理论的,或者说得严格一点,不是一种理论表述。然而奇妙的是,古典美学中诸如此类的表述比比皆是。这种表述方式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在这个例子中,不管是“采采流水”还是“碧桃满树”,所涉尽是形象具体的事物,关于“纤秾”这种风格的理解,我们只能够通过这些具体形象事物的诗化表述切入其中。“纤秾”这种审美经验是如此地鲜活、朦胧,以致没有任何抽象的理论语言可以把它严格地界定下来,进而说清道明。这是一种具象的表达方式,它以具象代抽象,以具体的事物描述代替抽象的理论说明。
当然,以这种言说方式来展示审美经验也别有一番效果。具象的方式展示出来的审美经验是鲜活的,它虽缺乏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但却突显了其切己的当下性。“纤秾”的风格不仅仅是由一系列形象的事物点拨出来的经验,而且更是人在积极参与世界游戏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本真体验,“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即此谓也。如此一来,此种言说的方式就把抽象的风格点拨成了活泼泼的当下经验,从而也使言说本身带上了诗的色彩。根据现代观点,这些突显当下品性的诗性言说是前现代的,是非理论的,但在传统美学中,这种言说却是有效的、本真的。
最后,在语言符号领域,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诉诸具象语言,而非抽象语言。这一特点与上述第二个特点紧密相关,具象事物说理的方式,表现在语言符号层面,本身使用具象语言符号。上文所涉“纤秾”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这一点很好理解。更进一步的是,传统美学在对审美经验进行概括的时候,仍然循此路子。在此仍以“一画”为例试析。石涛云:“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夫画从于心者也。”[4]在这里,石涛展开了他关于绘画经验和绘画观念的论述,以为最根本的绘画之法在于心法,此“无画”应“万画”之心法,正是“乃自我立”的“一画之法”,此绘画的根本原则,石涛强为之名,名曰“一画”。显然,“一画”是一个概括性词汇,它高度概括了绘画艺术的指导原则和最高境界,是石涛乃至中国画史绘画经验的凝练和总结。然而吊诡的是,“一画”同样可以理解为画笔下的“一道”、“一条线”,这也正是“一画”的字面义,事实上现在也有一些研究者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要回到概括方式本身来考察。“一画”本来是画笔下的“一条线”,所有的画作都是由一条一条的线组成的,是绘画经验中再具体不过的事物了,现在石涛却赋予它新的含义,要用它来指称高度凝练的绘画经验。如此一来,具象语言“一画”就成了所指广阔幽深的概括性语言。传统美学通过具象语言的概括,道出了审美体验的真实。
在此过程中,现代美学理论那种条分缕析的理性精神没有了容身之所。据现代美学理论,作为对审美经验的反思,美学话语有一套逻辑严明的概念、范畴和体系,本应在一套抽象语言中进行归纳、概括、推理和演绎,然而传统美学对审美经验的自觉言说却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藉着具象语言进行概括。在这条道路上,传统美学话语符号之于民族审美经验,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
由以上对传统美学话语方式特点的考察,可以发现它是对民族审美经验的理性言说,但这种理性言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论言说,它不遵从现代理论体系的概念逻辑,是一种前现代的非理论言说,一种与现代美学理论迥然有别的话语方式。这种言说虽然缺乏理论的谨严,但仍然是理性的,它道出了民族审美经验的最高真实,展示了传统美学的独特价值所在。甚至在当下它还可以有效地参与到现代美学理论的建设中。
首先,把握传统美学话语方式的特点,是如实了解民族审美经验的前提条件,进而也是深切理解中国美学的必由之路。民族审美经验关涉的主要是事物在人与世界交融一体的存在境域中彰显出来的美,它是事物于人生在世中显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关于美的这种理解在现代美学语境中很容易受到曲解,很容易被曲解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感性把握。事实上,民族审美经验并不符合这种逻辑理性思维的解说方式,从根本上讲,它是在原初的生存境域中显现出来的,是与主客二元对立范式相悖的,所以它不可能从主客对立的现代逻辑话语阐释中得到如实了解。对现代美学至关重要的“主体”、“非功利”等概念,如果被用到对传统美学的解说中,就会产生很多误解。在中国古人看来,陶醉于世俗生活之中同样可以获得无上的乐感,入尘即出尘,其关键在于体验的程度和参悟的高度,美离不开沉浸于世的体验;若把它解说成是由于主体非功利的超越情怀而来的经验,可谓南辕而北辙。要想获得传统审美经验的本来面目,必须放下现代美学的理论成见,循着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对它做一番应有的体察和阐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对民族审美经验的性质,还是对其特有的言说方式,都会上升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简言之,传统美学对民族审美经验的言说,自成一完整的系统,它形象地彰显了传统审美的观念,本真地述说了民族审美经验的本来面目,传统审美活动的精神面貌需要藉此话语方式方能得以较好地还原。
其次,把握这种言说审美经验方式的特点,还有助于推进传统美学的现代化进程。传统美学在对民族审美经验进行分类、归纳、概括的时候,依据的不是逻辑思维,而仍然是经验——一种经过层进叠加、自觉反思的经验。一如《二十四诗品》对诗歌风格所做的纤秾、冲淡、高古、绮丽等划分,就是建立在司空图对诗歌反复吟咏和把玩的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品味和体悟等经验形式对风格和精神类型的划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民族审美经验不是按照理性逻辑的方式进行分门别类、排列组合的,故对它的言说就不需要遵循理性逻辑,毋宁说传统美学的言说方式遵循了一种经验的逻辑,并且这种经验的逻辑在具象事物和具象语言中得以展开。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经验的逻辑和具象言说方式对原发的审美经验所做的说明,是忠于其本来面目的,是富有成效的,这足以对当下的传统美学研究做出启示,即:传统美学不必跟着现代理论亦趋亦步,其话语方式本身就包蕴着超越现代科学理论的真理成分,诗化言说能够揭示出被理论语言遮蔽的真理。这种民族的言说方式虽然与现代理论思维相悖,但它却可以参与到现代化的进程中,进而发挥积极的作用。总之,在传统美学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用现代理论阐释传统陷入困境的时候,尤其要尊重这种经验的逻辑,要尊重这种非理论的、具象化的表达方式,传统的言说方式可以为现代理论提供有益的给养,这正是传统美学融入现代的重要契机。
最后,关于传统美学话语方式特点的考察,对现代美学理论研究也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现代美学理论主要是建立在西方古典美学的范式基础之上的,主客二元对立和对象化思维方式是这种美学话语的思维基础,所以这种话语采取了对象化的言说方式,这种方式在对审美现象进行说明时,总是竭力厘清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在此基础上对二者关系加以描述和分析。显而易见,这种话语方式的基础是主体哲学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现代美学的这种理论话语方式日益暴露出了其弊端,人生在世的繁多存在体验不是客体的形式引发了主体心意能力的协调而来的精神愉悦所能解释清楚的,审美经验作为一种人生在世的存在体验,是一种更加原发的经验,它应当在超越对象化思维的层面上给出解释。事实上,现代美学在20世纪的西方开辟出了现象学的新路向,这个新的路向以为,美不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审与被审的感性价值,而是一种人与世界共在的世界中显现出来的价值,是事物在世界中显出意义的一种本真存在。“审美经验不仅是一种与其他体验相并列的体验,而且代表了一般体验的本质类型,”[5](101)也就是说审美经验饱含着丰满的意义和无上的真理性。海德格尔的“诗思”业已昭示了这种言说审美体验的新方式。难能可贵的是,中国传统美学独有的话语方式与现象学的路向不谋而合。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秉持一种非分别的、非对象化的视域,描述了人生在世的审美存在体验,揭示了审美发生的原初奥妙,提供了一种迥异于现代理论的关于美的理解,即美是在人与世界交融一体的存在境域中,事物本身显发出来的一种价值。古典美学对人生在世存在体验的诗化言说,正是以一种“诗思”的方式证明了审美体验的真理性。这正是中国传统美学话语方式对现代美学理论研究的贡献和启示所在。
总之,中国传统美学拥有一套独特的话语方式,这套话语方式是对传统审美经验的本真言说,它与“现代美学”尤其是“西方美学”判然有别,本质上是一种非分别的言说方式,展现了非对象化地体验世界的路径的意义。藉此话语方式,可以对原发而富有价值的民族审美经验做出忠于其本来面目的理解,进而促进传统美学的现代转换,发掘其介入现代美学理论的潜在价值。
[1](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G]//周积寅编《中国历代画编》.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2]朱良志.石涛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O]//(清)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
[4](清)石涛.画语录·一画章[G]//周积寅编《中国历代画编》.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5](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卷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