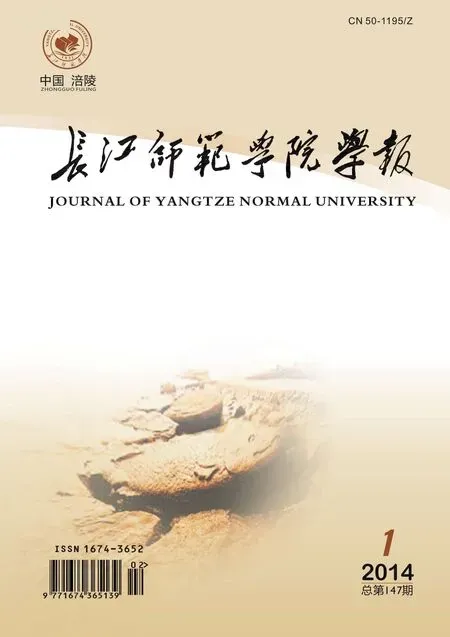论陈学昭早期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2014-03-29王俊虎郑莹莹
王俊虎,郑莹莹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论陈学昭早期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王俊虎,郑莹莹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陈学昭作为中国女性解放的先驱,她初登文坛就表现出了对女性命运的极大关注。她早期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做是 “五四”时期觉醒女性的悲鸣,她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为素材,塑造了众多在 “五四”时代精神的感召下追求独立自由,但最终却陷入苦闷、彷徨,甚至无路可走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女性形象群体,以此来批判和嘲讽腐朽堕落的男权社会,解构男权婚恋神话,揭露黑暗的社会对女性的禁锢和戕害,将鲜明的女性独立意识融入到自己早期的文学创作,为在男权、族权、夫权、父权、神权等压迫蹂躏下的众多女性喊出了获取解放、独立、自由的心声。
陈学昭;文学创作;女性意识;男权;时代女性
千百年来,在封建宗法制度相当完备的旧中国,女性一直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并非独立的个体存在,她们是被忽视、压迫、奴役的弱势群体。对于这样的境况与待遇,她们自身似乎已经习惯或者认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传统伦理道德让她们一生都致力于做一个 “贤妻良母”,将嫁人、生育作为自己最大的人生理想,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纵览中国古代文学史,不难发现,女性写作多是自我的倾诉和吟唱,抒发内心的闲愁哀怨。而 “五四”思想的启蒙,使女性从没有自我意识到发现自我,她们渴望摆脱旧礼教、旧道德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桎梏,渴望表现自我、实现自我。在这样的时代驱使下,一批受过正规教育的知识女性 “浮出了历史地表”,开始书写妇女在家庭、社会中所遭受的 “非人”待遇,以表达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憎恶,对男权中心主义的蔑视和抨击,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抗争和反叛。
陈学昭就是其中的一位,虽没有同时期的冰心、庐隐名气大,但在她的作品中所蕴含的女性意识却是大胆的、超前的,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也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陈学昭,原名淑英、淑章,1906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因家中藏书较多,她自小就阅读了 《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并在母亲的帮助下,偷偷阅读了 《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古典文学著作。也是因为喜欢学习 《昭明文选》,便有了后来的笔名 “学昭”。父亲在她七岁时便离世,哥哥们对她要求极严,动辄责罚打骂,母亲作为传统的家庭妇女生性懦弱,面对哥哥对她的欺辱与打骂,母亲只能偷偷地流泪。这样的生活环境塑造了陈学昭孤傲、倔强、清高的个性气质,而这样的性格对她后来的生活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2年,年仅17岁的她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开始了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孤旅漂泊生活。1923年冬,陈学昭以一篇名为《我所希望的新妇女》的文章受到时任 《时报》主笔的戈公振的青睐,并特地写信鼓励她多多地写作,至此陈学昭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
纵观陈学昭的文学创作生涯,其按照作品创作风格以陈学昭抵达延安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这里侧重从陈学昭到延安前的文学创作入手,探讨其中蕴含的女性意识。纵览她早期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她从初涉文坛就表现出了对女性生存现状及前途命运的极大关注,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对个性解放、独立自主的不懈追求,对封建男权、族权、夫权、父权、神权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并以独特的女性视觉与生命体验进行文学创作,表现出那个时代女性内心的苦闷、犹豫和彷徨。
一、现代新女性所应有的新品质
《我所希望的新妇女》是1924年元旦陈学昭发表在 《时报》增刊上的一篇散文,也是她的处女作。面对千百年来女性所处的受压迫、受奴役、被蹂躏的处境,陈学昭站在女性的立场,从个人修养和社会事业两个方面以阐述她对 “新妇女”的认识和思考。她认为新妇女应该在人格上 “了解这个变化不已的世界”[1]1,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不依附于男子,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情感和意识,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要 “拿道德的、公平的、明察的态度来对待外界。不为盲目者所称赞,但求同道者的同情,更具有不屈不挠的牺牲的博爱的精神”[1]1。中国封建社会,秉承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评判标准,女子从小只能在家专注女红 (工),嫁人后相夫教子,没有接受教育与参与社交、工作的权利。在这篇文章中,陈学昭认为女子应该具有和男人相同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她认为女子只有经济上独立才能在人格上独立。她在文章中要求女子 “要对于自己下一番苦功夫,得到深切的学问与经验”, “不以皮相、半解的知识来自欺欺人”[1]1。在她看来,很多女子之所以求学只在于想以此 “求得较高的配偶”[1]2,求得物质的报酬。在 《给女学校教师的公开信》中,她明确指出了女子自古以来在教育上被忽视的问题,并且严厉批评了有些女教师没有真才实学、思想渺茫、头脑空洞,她们只把教育工作看做获得劳动报酬的一种手段,对教育工作不热衷,得过且过;对学生不闻不问,漠不关心。这些观点都是陈学昭作为女性解放的先驱,站在现代女性的立场和角度,看到女性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女性在生活中所处的弱者地位的原因,具有鲜明的现代女性意识。
在中国旧礼教、旧道德的束缚下,中国的女子缺少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性,在封建神权、族权、父权、夫权的四重压力下逐渐具有了奴性的特征。她们习惯于固守家庭、相夫教子,做一个贤妻良母。在传统伦理道德中,“贤妻良母”是对一个女性最高的评价,而中国的妇女也在这样的评判标准下严格要求自己。在陈学昭看来,正是因为那些赋予女性的诸如无私奉献、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等 “传统美德”的枷锁才致使中国的女性一直处于 “非人”的地位。在传统社会,女子将美满婚姻当做自己毕生不断努力的事业,渴望通过嫁个好人家来使自己获得优厚的物质报酬,依靠自己的天然性别来获取生活的物资。甚至可以说,她们把婚姻当做事业,把嫁人和生育当做自己的 “天职”,而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嫁人,没有生育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会被人看不起,甚至遭到家人的唾弃。所以很多女性穷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做一个男权社会中有 “价值”的人。在 《我所希望的新妇女》中,作者认为女子的价值并不仅在于为人妻、为人母,还在于等同于男性的社会价值。她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去实现自己母性以外的价值。她认为女性要实现人格独立,最重要的就是自立,而自立就是要在经济上独立,要在经济上独立就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而不应固守于家庭,“一个独身的女子,对于社会上,一定会比家庭里的贤妻良母发展的多。”[1]2在 《给女学校教师的公开信》中,她也表现出了对女教师的希冀,希望她们能够认真对待教育事业,真正在教育上有一番作为,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不难看出,陈学昭对于女子的教育、职业、婚姻等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她眼中的新妇女就是应该在人格上独立、个性上解放、有学识、有自己的事业的新女性。她鼓励女子走出家庭的樊篱,打破传统伦理道德的神话,去从事适合自己的职业,不依附于男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女性。
二、抒写时代女性内心的苦闷
幼时坎坷的经历,形成了陈学昭敏感、多疑、倔强和反叛的性格,对家庭的失望和对自由、独立的追求,使她渴望去外面寻找自己的天地。她说:“我是一个流浪者,孤零漂泊的流浪者!天涯的游子,只有天涯的浪花是一生的快伴!”[2]50
作为被 “五四”文化激荡出历史地表的新女性,陈学昭敏感地感受到了来自家庭、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等带给女性的挤压、束缚和屈辱,她把自己的满腔悲愤都化作鲜活的文字,以此表达出时代女性觉醒后无路可走的内心苦闷和迷惘,同时也对黑暗的社会和传统伦理道德以及男权中心主义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和质疑。她以同情和悲悯、厌恶和讽刺的双重情感向读者形象、真实地描绘了 “五四”落潮期女性的生存现状和内心的焦灼、苦闷,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女性的悲凉生存境况。
《倦旅》是陈学昭的第一部散文集,在这部作品里,她化名 “逸樵”,将自己去安徽四师任教时的所见所闻所感用细腻的笔触向我们娓娓道来,缱绻缠绵,清新婉丽,近似于作者年轻心灵的内心独白,真挚、细腻,带有年轻女性对人生对命运的迷茫和感伤。正如她自己在 《关于 〈倦旅〉的写作》中所说,《倦旅》“记下了自己前一段的流浪生活,反映了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有时充满了悲哀凄怆,有时充满了愤怒激昂。”[8]298文中主人公面对美好的自然风光却无心欣赏,而是陷入了自己的思索当中,她认为人生就像 “浮萍浪花一样的漂泊着……”[3]14无处安身,只能随波逐流,充满着对前途命运的彷徨迷惘之感。“我顾视来路,又若是的隐约;我瞻望前途,又若是的渺茫。唉!我的心啊,将如何安放,在这样的旅途之上!”[3]14作者借主人公表达了自己的孤蓬漂泊的感伤和哀怨。在 《我的母亲》中,作者这样写道,“在这广大、空漠、扰杂的道路上,我踯躅着,我徘徊着,到处都是这不可扑灭的灰尘,到处都是难以选择的歧路。我空寂的心,我飘渺的魂,我失去了努力的目标,我憎恨着一切……”[4]51,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面对现实人生的前途命运和种种艰难险阻时内心痛苦的无奈和绝望,这也是处于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内心的真实写照。“我看破了!这梦幻的人生!这厌倦的生活!”[4]52我们看到了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女性内心的痛苦和焦灼,对生活的厌倦和对人生的绝望,这是那个时代追求自由进步的现代女性内心的共鸣。侧重抒写自然景物的散文集 《烟霞伴侣》表现出与作者平时创作不同的艺术风格,她自己在 《天涯归客》中说:“我并不很喜欢,这里面的好些散文是吟风弄月的”[6],但其实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描绘大自然的湖光山色的同时,也流露出作为女性所特有的情愫。虽在描绘风光万物,但郁积于心头的依然是一个新女性无尽的哀伤和纠结于内心深处的悲凉与迷茫。“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想耳边啼”的有家难归的无奈和感伤。在《如梦》中绿漪想 “求一个真理”[5],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无能为力,她犹疑、徘徊、失望。她认识到了这个社会的畸形,她渴望逃离,可走来走去还是走不出这个让她窒息的围城,最后她不禁感叹,这一切都如梦一般的飘渺!
在这些作品中,字里行间都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感伤情怀,寓于作者内心深处的是属于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感伤和苦闷。在这些散文里,人物有着趋同的共性,她们追求独立、自主,在 “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她们打破了传统伦理道德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桎梏,走向社会追求自己的理想,但黑暗的社会现实却阻碍了她们追求进步的步伐,她们变得焦灼不安、痛苦、迷茫甚至绝望。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建构文章,用自己手中之笔书写着时代女性的生存现状,表达了作者对觉醒了的新女性的生存现状的同情和怜悯以及对她们前途命运的担忧和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无情鞭挞,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陈学昭把追求进步自由的时代女性写进了中国文学史,是觉醒了的时代女性的代言人。
三、解构男权社会的婚恋神话
陈学昭是我国20世纪最早具有独立女性意识的时代女性之一,但她本人在经历一次次的突围、反叛和抗争后,最终还是陷入了无爱婚姻的泥淖中,她错失了两个挚爱她的男子,却和两个她不爱也不爱她的男子建立了恋爱、婚姻关系。陈学昭自身的婚恋悲剧就昭示了在这个受封建伦理道德影响颇深、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女性解放之路是何其艰难、曲折和漫长。
独立自主、个性解放的 “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典型就是女性摆脱传统的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的枷锁,追求婚姻、恋爱自由。一批自由意识觉醒、思想解放的新女性率先勇敢地向封建包办婚姻发起了挑战。正如陈学昭在 《南风的梦》中所说:“恋爱是不能奉命的,任凭是谁人的命都是不能奉行的。”[7]167在旧中国,女性一直过着 “顺从”的生活,依靠男性而活,她们把自己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男性身上,从父亲到丈夫再到儿子,而正是这种近似于奴性的依赖,使男性更加鄙视女性,使她们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低下。她们把婚姻看做自己谋生和获取生活之资的最有效途径,把嫁人、生育当做自己的 “天职”,而忽视了自己作为 “人”的价值。陈学昭在1927年1月的 《给男性》一文中,站在女性的角度,以女性的视角真实地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呼声,揭示了女性在爱情、婚姻和家庭所处的弱者地位,并对男权中心主义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批判。在 《他给她》中,作者以一个男性的口吻告诉恋爱的女友“恋爱并不是我们整个人生”[10],女性除恋爱外还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有自己的事业。这也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是站在一个男性的角度上来鼓励和劝告女性不要使自己陷入男权的婚恋神话。
《南风的梦》是作者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以作者自己和季志仁、蔡伯龄、孙福熙的友情和爱恋为素材,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克明的爱情悲剧,揭露了男性的暴虐、无耻和狭隘、贪婪、自私,颠覆了男权的婚恋神话。毛一波在《〈评南风的梦〉》中认为,“从 《南风的梦》我们看得见男性的偏狭、疑忌和残酷的劣根性来。”[8]323克明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女性,在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重重挤压之后,她依然保持着自己高洁、自尊、自主的品格,她宁可做一个跌倒在十字路口的饿殍,即便受到人们的讥笑和践踏,也不愿匍匐在男权的威势与玩弄下吃一口安稳饭。这些言论是作者借克明之口喊出的时代女性的最强音,表明了她们内心对独立自主的渴望和对男权的蔑视和讽刺。文中的人物是一群受 “五四”精神影响的青年男女,他们在面对感情时内心情绪的变化,反映出了在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禁锢和束缚下内心的矛盾和苦闷的情感。有论者认为:“《南风的梦》是一个失恋者的呼声,女性的灵魂的呻吟”[8]323。陈学昭是把自己写进了故事,用自己痛苦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生命体验来书写时代女性对理想、自由的追求。在文中,克明具有开放和超前的性爱观与藐视传统伦理道德的贞操观,她认为,男人多是用下半身思考男女关系的可怜生物,因为他们以为 “占有了一个女人的身体,便可以占有她们的灵魂”[7]第一卷,61。这些观点都源于她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立场,这些大胆的言论,是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的反叛,具有鲜明的性别意识。
在 《幸福》中,作者塑造了一个 “子君”式的人物 “郁芬”,她不顾父母反对勇敢和自己所爱的人结合在一起,她没有像子君那样婚后只把目光投注于个人生活的小天地,而是做一个独立的女性,坚持自己的工作。然而,在当时的黑暗的社会现实下,并没有一个宽松的可以任女性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氛围,面对工作的不顺和家庭中丈夫的不理解,她痛苦和迷茫。鲁迅说,出走的 “娜拉”,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而郁芬最终还是陷落在了婚姻的 “围城”中。我们看到,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个人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她们觉醒了,甚至有很大一部分人奋力地突出了封建的重围,大胆地反叛封建伦理道德,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在面对来自家庭、社会、传统文化的压力时,她们反抗、挣扎、左冲右突,渴望实现自己的价值。但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她们还是陷落了。“郁芬”式的女性在当时不是个例,作者用自己敏锐的观察、独特的视角,通过郁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黑暗的社会和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于女性的挤压和残害,表达出对女性的同情和对男权婚恋神话的质疑和反叛。
四、结语
陈学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她是在 “五四”时代精神的感召下走上女性解放之路的先驱。初涉文坛,就表现出了对女性命运的极大关注和思考。她早期的文本主要以散文为主,表达个人的情感,在感伤迷惘中带有不断向上的自强不息的力量。表现女性知识分子在当时对自由的渴望以及理想与现实社会之间发生矛盾时内心的无可奈何与彷徨迷茫之感。站在女性的视角,用自己细腻的笔触描摹她们的灵魂,抒写她们的情感。作品中饱含着抗争反叛、苦闷迷茫的情绪,向读者真实地刻画出了试图突出重围的时代女性不断的追求与抗争的心灵轨迹。
[1]陈学昭.我所希望的新妇女[A].陈学昭.海天寸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陈学昭.寸草心[A].陈学昭.海天寸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3]陈学昭.倦旅[A].陈学昭.海天寸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4]陈学昭.我的母亲[A].陈学昭.海天寸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5]陈学昭.如梦[A].陈学昭.海天寸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58.
[6]陈学昭.天涯归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26.
[7]陈学昭.陈学昭文集(第1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8]丁茂远.陈学昭研究专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9]单 元,万国庆.突围与陷落——陈学昭传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
[10]冯小青.陈学昭文学创作中性别意识的觉醒[J].学术探索(理论研究),2011(2):91.
[责任编辑:田 野]
I206.6
A
1674-3652(2014)01-0080-04
2013-11-2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陕西文学对延安文学的承传与发展研究”(12XZW020);延安市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规划项目“左翼知识分子与延安文学体制建构研究”(13BWXC30)。
王俊虎,男,陕西大荔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