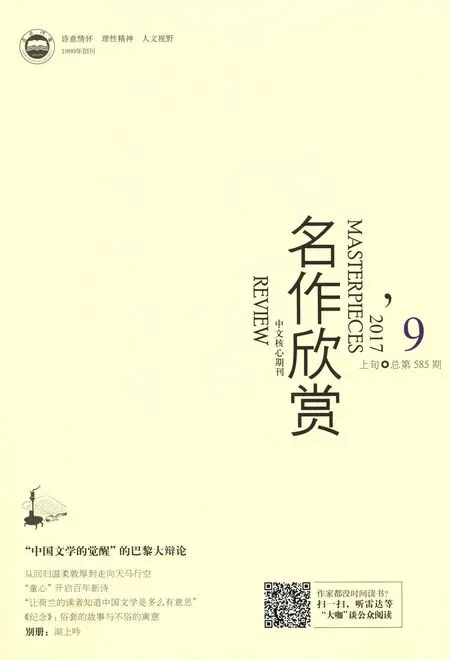“80后”的入城故事——读吕魁《火车要往哪里去》
2014-03-29李德南
文 / 李德南
一
来,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个故事:时间是农历六月初十,阴云密布的傍晚,热闹纷繁的大地突然变得沉闷而压抑,酝酿已久的大雷雨就要降临。接受过高中教育的知识青年高加林失掉了民办老师的职位,颓然回到家中,摆置在面前的,则是重又成为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身处厄境的他很快接受了巧珍,一个大字不识却美丽善良的姑娘的追求,个人的精神危机得以缓解。然而,当有机会进入城市并与美丽大方、见多识广的同学黄亚萍相遇时,高加林又发现,和巧珍的相爱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他们很难再有精神上的交流,更意味着他将一辈子被困在农村。尽管心里充满不安,高加林还是选择了与巧珍分手。就在对更大的城市南京生出向往时,高加林被告发是走了后门才谋得现在的职位,解雇后重又打回农村;而这时候,曾经深爱他的巧珍已嫁作他人妇……
这个故事出自路遥的小说《人生》。它“1981年夏天初稿于陕北甘泉,同年秋天改于西安、咸阳,冬天再改于北京”,发表后曾感动了无数高加林式的农村知识青年。而在三十年后,也就是2011年,吕魁在《大家》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火车要往哪里去》。后者可视为一位“80后”作家向一位20世纪80年代作家的致敬,两篇小说更形成了微妙的对话关系。《火车要往哪里去》的开篇是这样的:电视机里正播着巴西队和荷兰队的足球比赛,荷兰人的获胜使得叙述者马山“裤子口袋里那面值一百块钱的足球彩票转眼间成为废纸一张”。睡在身旁的,则是女友牛红红。他们此时所在之地是上海,尚在求学的马山邀约在县文化局上班的牛红红过来看世博会、逛周庄,并非出于爱,而是把这视为分手旅行,以消弭良心的不安。马山早已经爱上班花徐菲菲,其理由与高加林爱上黄亚萍相似——已有的恋人不够“洋气”,彼此无法再有心灵或精神上的交流。与高加林的遭遇一样,马山最终并没有能够和真正喜欢的人结为伴侣,甚至比高加林更不堪的是,徐菲菲从来没爱过马山,她喜欢的是富二代,马山对徐菲菲的好感不过是一场“意淫”。原本想着和牛红红分手的马山在失望之下,反讽地乘火车离开了上海,决意回那个小县城与牛红红结婚。
《火车要往哪里去》可视为对《人生》的“故事新编”——它所讲述的,同样是农村知识青年如何入城的故事,同样是以“爱情故事”作为架构。不同的是,高加林和马山的遭遇之间隔着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隔着中国开始走城市化道路的三十年。两个故事既有诸多相通之处,也有不少差异。《人生》中曾这样写到高加林进城的情景:“高加林进县城以后,情绪好几天都不能平静下来,一切都好像是做梦一样。他高兴得如狂似醉,但又有点惴惴不安。他从田野上再一次来到城市,不过,这一次进来非同以往。当年他来到县城,基本上还是个乡下孩子,在城市的面前胆怯而且惶恐。几年活跃的学校生活,使他渐渐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与城市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他很快把自己从里到外都变成了一个城里人。农村对他来说变得淡漠了。有时候成了生活舞台上的一道布景,他只有在寒暑假才重新领略一下其中的情趣。”这种对城市生活的迷恋,在《火车要往哪里去》中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山所置身其中的,是更现代、更“洋气”的上海。马山曾对牛红红起誓,毕业后一定回小县城与之结婚,“然而到上海没多久,我就轻易地背叛了我的誓言。与其说我意志不坚定,不如说身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确实有种魔力,她就像是位风姿绰约的美女,不管你什么身份地位,一旦遇见,就会被她吸引,为她所着迷。我仅用一年时间就适应了和我前十八年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两年不到我就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先前有关它的缺点在我眼中都成为无与伦比的优点,我发誓我要留在这里”。
吕魁曾经谈到,《火车要往哪里去》和《散伙饭》《朝九晚不归》是他个人心中的一组三部曲,“分别通过几件小事,记录了我及我身边朋友这一代大学生在本科、硕士及进入社会后的不同生存状态”。《散伙饭》与《朝九晚不归》也涉及凤凰男如何入城的故事,《散伙饭》中的一段话,堪称是对“80后”凤凰男经历的高度概括:“十八岁那年夏天,我以县文科状元的身份坐大巴,乘火车,来到千里之外的上海读大学。这之前,我对上海的概念仅局限于大白兔奶糖、回力球鞋,以及在电视上看到的外滩夜景。和我那干旱少雨的老家相比,我用了一个学期才适应上海温润潮湿的天气。又用了将近两年去了解这座城市的厚重历史,欣赏它如美人般绰约的风情。坦白讲,我人生中很多第一次都是在这里经历:第一次乘地铁、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吃西式快餐、第一次仰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第一次住五星级酒店。就这样,本科四年,我彻彻底底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会完成个人的现代化进程。不夸张地说,上海对我这种乡下穷学生的冲击丝毫不亚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到发达国家时的那种震撼。”在《朝九晚不归》中,同样的经历出现在主人公身上,他的名字同样叫马山,所不同的只是北京多了烤鸭、长城、故宫和北大、清华而已。这些细节的重复,用意似在强调这一代人命运的相似。
二
《人生》和《火车要往哪里去》都以入城作为主题,两者的叙事空间却不无差异。《人生》的主要叙事场景仍在农村,《火车要往哪里去》的叙事则主要是在高度发达的大都市上海中展开。也许是因为城市的肉身和精神都过于抽象,不好描述,路遥与吕魁都选择了让女性与城市相对应。城市的身体和美女的身体,城市的精神和美女的精神互为隐喻,构成解释学循环:对城市的迷恋可以转喻为对城市女性的迷恋;对城市女性的迷恋,则可以从对城市的迷恋中获得合法性。也正因如此,《火车要往哪里去》中的马山会像“爱上海一样爱着徐菲菲”,“像徐菲菲这样的美女就是我每天努力奋斗、争取留在上海的动力”。
《火车要往哪里去》中的火车、励志书籍与彩票这三个意象,也很值得注意。
在中国文学也包括西方城市文学中,火车是城市书写的核心意象。这在王蒙的小说《春之声》、铁凝的《哦,香雪》,以及路遥的《人生》等大批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中在在可见。现代化的先声,通往城市的路,通常离不开作为隐喻或意象的火车。西方城市文学中也同样如此。理查德·利罕在分析《嘉莉妹妹》时就谈到,这部小说中的主角来到城市往往是乘坐火车:“城市已经变得越来越像一台机器,人们进出城市,都依赖火车:其结果是,在工业城市中,很难说清楚这台机器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
在这一文学史和社会史的背景下,《火车要往哪里去》也可以视为对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重新发问。吕魁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有着如下遭遇:有知识,却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他们或可顺利进入某所著名大学读书,但随着高校不断扩招,考上大学已不能保证他们获得成功。尤其是在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形下,成功已成为无法企及的梦想。在想成功而不得的情形下,新一代的知识青年只好选择以反讽的态度来对待成功。马山们一再调侃各种成功人士,调侃那些试图教导当代大学生如何做人处事的励志书籍。这既是在反对励志读物的虚妄,也是因为看到了成功的虚妄。
在对前途不再抱有足够的希望与信心后,吕魁笔下这些一没钱二没社会关系的男女知识青年不再认同传统意义上的奋斗,而是“剑走偏锋”。“她们”大多是选择了以美丽的肉身作为交换资本;“他们”则往往是过着草根的生活,同时做着不切实际的梦。《火车要往哪里去》写到马山花巨额购买彩票,这并非是无意之举,而是将之视为通往城市、获得存在合法性的路径。马山吃苦耐劳,为省路费而很少回家,周末和寒暑假同时做多份兼职,什么工作都肯干,只要给钱就行。然而马山很明白,“即使我再辛苦十倍,像我这样的杯水车薪,除非有狗屎运中五百万大奖,否则上海的房子我几辈子也买不起。不过多赚一块距离我的梦想至少能近那么一点,虽然到头来交完学校、贴补家用后所剩无几,但即便是口袋空空,一无所有的我走在异国情调的淮海路,看着别人在高档酒楼、奢侈品牌店进进出出,身处其中的我也会有种参与感,莫名开心”。这里的参与感,不过是一种参与幻觉,最终当这些知识青年从幻觉中醒来,往往都会痛苦不堪。《火车要往哪里去》中的马山接受命运,带着落寞和失败回到县城,就不只是一种戏剧性转变,同时也是他的命定之途。
三
《人生》中所写到的城市,其实不过是小县城;而在吕魁的小说中,只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才称得上是城市,小县城已然成为乡土世界的构成部分。从这种变迁,可以看到中国在数十年城市化进程后的面貌。
费孝通曾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也一度成为我们理解传统中国的重要维度;然而,在经过几十年城市化运动后,仅是从乡土及其相关逻辑来理解中国,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2011年末,也就是吕魁写作《火车要往哪里去》的这一年,中国城镇人口在数量上已超过农村人口。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也意味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整个国家价值观念的转变。因此,年轻一辈的社会学家也开始越来越关注城市问题。陈映芳在《城市中国的逻辑》中就试图以上海作为田野调查的主要对象,系统地阐释、总结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呈现的特点,为理解今天的中国提供了非常好的视角。她特别注意到,“在今天中国的城市主义意识形态中,‘城市’被掺入了包括发展主义进化观、城市乌托邦等在内的各种想象要素。发展经济必须建设城市,对外开放必须依赖于城市,实现美好生活更有待于城市……伴随着现实中‘农业现代化’前景的暗淡和‘城市主义’被刻意渲染,城市象征了经济、科技、文化以及社会‘先进’‘发达’‘美好’的符号,也被理解为人类聚居的高级形态、生活空间的未来归宿。这样的城市想象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通过‘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样的主题,被中国的官方宣传机构表达、阐释得淋漓尽致”。
吕魁在《火车要往哪里去》里选择让马山领着牛红红看世博会绝非偶然,用意正在于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提出质疑。吕魁似乎对这种城市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有所反思,然而,就文本中所呈现的世界来说,这种反思和质疑的声音是微弱的。马山身边的朋友,无不认为马山应该离开牛红红;即便是牛红红,也不再如巧珍般纯真,而是变得无礼,贪小便宜。牛红红虽然在小县城生活,却早已为韩剧所同化,见到韩式衣裙便“瞬间失去理智”,“说话也开始故意嗲声嗲气”。高加林虽已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却多少还有依恋,生于斯的乡土世界也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复杂景象;而在《火车要往哪里去》里面,马山最后选择回到小县城,是在极其被动的情形下做出的,只是“被选择”而已。总之,已没有任何声音,在为乡村的存在意义提出申辩。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火车要往哪里去”这个题目是带着疑问的,也包含着杨庆祥所说的“80后,怎么办”这一问题。“80后”是既幸运又很不幸的一代。少数人在这个时代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由于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原因,绝大多数的“80后”所遇到的生存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小说中的结局,其实还是开放性的,吕魁的追问也持续延宕。在我看来,要改变“80后”的困境,首先必须期待并实现社会政治层面的变革,这最为关键。在现实面前,任何文学化的抒情或叙事都是无能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期待社会在价值层面变得更为多元。当今时代最麻烦的还不是贫富不均,而是在贫富不均的同时,我们都只认同富裕阶层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认为必须有足够的金钱、权力和财富才能幸福。其实不是。我们应该学会尊重他者的选择,多一些宽容,少一些攀比。同样不能忽略的是,“80后”应学会正视自己。一方面,这代人在现有的社会体制内很难获得上升渠道,大家都已不相信仅凭个人努力而不依赖社会关系依然能获得成功;另一方面,“80后”的主体膨胀也是前所未有的。读完《火车要往哪里去》,甚至也包括吕魁的小说集《所有的阳光扑向雪》就会发现,里面几乎所有男主人公都渴望过一种香车宝马、怀拥女神的生活,都希望能遇到范冰冰或李冰冰,要么是林志玲;女性则为一只LV包而欣喜若狂或哀愁万千。这反映了“80后”多数青年的普遍心理,也说明了消费社会对主体塑造力量之大。郭敬明的作品和电影之所以这么受欢迎,也与这种社会状况和主体的精神状况不无关系。事实上,哪怕叫冰冰的再多,也不可能人均一个;LV包若人人有份,其意义也就和蛇皮袋无异。这个主体之梦太富丽,太奢华,太不切实际,以致泡沫般一碰就碎。即使社会能有更多的公正,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也不可能让每个人幸福至此。如果不认识到这一梦想的虚幻性质,不能对消费主义的诡计有所识破,有所抵抗,那么这代人将永远活在痛苦的境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