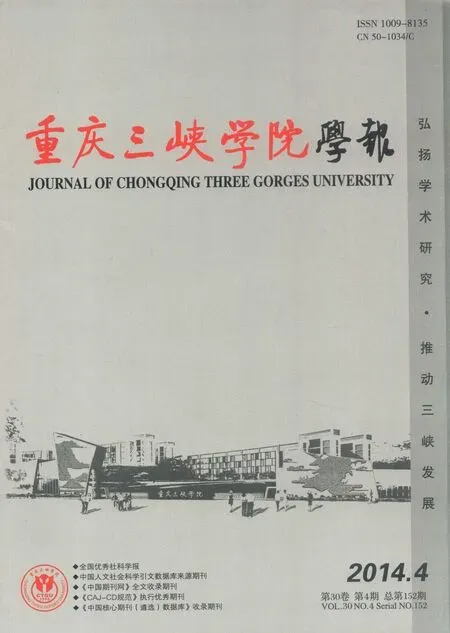三峡地区传统音乐的失守与拯救
2014-03-28叶培结万弋琳
叶培结 钱 洁 万弋琳
(1.蚌埠医学院艺术教研室,安徽蚌埠 233030)
(2.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一、三峡地区民间音乐概况
三峡地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量聚集之地,据考古资料现实,在距今201~204万年的早更新世时期,三峡地区就已经有人类——巫山猿人的生活足迹,这比“元谋人”还要早30万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三峡地区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不断丰富,三峡民间音乐也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形成中国大地上独树一帜的音乐品质,是三峡地区人民大众情感、精神、毅志、艺术的结晶。
(一)三峡地区传统音乐的产生与发展
三峡地区传统音乐主要包括巴蜀音乐和荆楚音乐,其产生历史久远,据历史文献现实,三峡地区的古代巴人,能歌善舞,却长期受到殷商的征伐,在武王伐纣时,他们踊跃加入伐纣大军,并把本民族别具一格的歌舞编排成战歌、战舞,鼓舞周军士气,震慑殷商,对讨伐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晋人常璩在其《华阳国志•巴志》中,对这一史事进行了描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1]这种“前歌后舞”的表演在当时并没有名称记载流传下来。《后汉书•南蛮列传》记载,在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刘邦命人在宫廷表演之,称其为“此武王伐封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2]于是,这种巴渝歌舞成了汉时宫廷歌舞的重要内容。这些传统音乐在三峡地区世代流传,影响至深,从未间断过,就连亲人丧葬时,都是“鼓盆而歌”,而且“其歌必狂,其众比跳。”[3]
三峡地区传统音乐可谓异彩纷呈,如长江上荡气回肠的《川江号子》、《乌江号子》、《清江号子》等;土家族的《梯玛神歌》、《摆手歌》、《龙船调》、《哭嫁歌》等;屈原故里秭归县的《祭江》、《招魂》等;还有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极为推崇的《竹枝词》。
(二)三峡地区传统音乐的重要特征
1.音声繁复多变。从三峡地区已出土的古乐器的整理和研究出发,并结合该地区现今的民间音乐(比如长短句的短歌,大型体裁形式的薅草歌、锣鼓歌等)来看,传统的“楚音”在乐律学上已相当发达,而且其音乐实践也相当丰富多变。例如兴山县的三度体系民歌,其音阶音列中总是包含着一种345音分左右的三度音程,这种介于大小三度之间的音程又不同于中立音(四分之三音),从而造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独特调式,十分怪异,为我国罕见,被称为巴楚古音乐的活化石。
2.领唱与合唱相结合。不管是先楚的古乐(如《下里》、《巴人》等),还是唐宋的竹枝词,以及今日的三峡民歌(如薅草歌、田秧歌、哭嫁歌等),无一不是采取的领唱与合唱相结合的方式,而且演唱者情绪热烈,极具感染力,声音穿透力极强。这种表演方式与北方地区的空旷、高远的独唱(如牧歌、信天游等)方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3.不断变化融合。音乐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总是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发展的。三峡地区的传统音乐也因为地区局部环境、民族关系等不同而不断变化发展。在变化过程中,这些传统音乐不断吸收各个地区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等,在继承中变化,在继承中发展。比如流行于三峡恩施地区的恩施杨琴。早起的恩施杨琴是从区外传播进入恩施的,表演上也是以外地声乐为主,恩施本地声乐为辅,但是,随着与恩施的地区文化、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表演上逐渐形成了以恩施本地声乐为主,外地声乐为辅的形式,声腔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有的板腔和曲牌,逐渐变化成极具恩施地方色彩的声腔,唱腔旋律流畅,人物情绪丰富,而且曲目也日渐增加,仅常用的唱腔曲牌就有20多首。还有一些三峡传统音乐与当今的世俗文化相融合,演变成适应当前居民文化的表演形式,比如土家族的摆手歌、摆手舞,就已经从原来的“战歌”、“战舞”、“祭祀歌”、“祭祀舞”演变成了现在的广场健身娱乐歌和健身舞。
4.区域性特征明显。历史上,由于陆路交通的不便,坐拥黄金水道的三峡地区一直是我国东西通道的交通要道,东进西出的各种物质、文化、人员等都要在这里汇集,所谓“万川毕汇、万商云集”是也。于是,三峡地区在东西两种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它兼具巴、楚文化的特点,又不失地方特色。其中,如三峡地区广泛流传的各种“号子”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楚帮号子”,就是湖北巴东的船工拉纤入三峡时的一种排号,采取领唱与合唱相结合的演唱形式,演唱效果极为粗犷、雄浑和高亢,这种排号主要分为拖杠、出艄、提缆、摇橹、撑篷、拉纤六种。另外,三峡地区传统音乐表演中某些动作,如“擦背换位”、“侧身”等,都与三峡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在三峡地区崎岖多山的地理环境里,劳动人民肩扛背驮,负重爬山时展现出来的肢体动作,潜移默化地移接到了歌舞表演中,打上了三峡地区的烙印。
5.群众自由参与性。三峡地区传统音乐的自由参与性是指当地民众可以自由地参与音乐和舞蹈的表演,并可以自由地退出,不受任何限制。这种参与的自由性,充分说明了三峡地区传统音乐的大众性和开放性特点,从而使这些传统音乐成为了当地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比如三峡地区土家族人的摆手歌、摆手舞和“撒尔嗬”就是群众性的娱乐项目,而且参与的人越多越好,气氛也越热闹。人们可以自由地跟着梯玛或歌师一起合唱吆喝,通常是通宵达旦地歌唱舞蹈。
二、三峡地区传统音乐的失守
(一)三峡地区传统音乐难抗流行音乐的入侵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文化市场也日益兴盛繁荣,各种音乐艺术百花争鸣,百花齐放。三峡地区也一改过去封闭状态,区内外的交流日渐活跃,各种外来音乐纷至沓来,对区内传统音乐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很多民间音乐艺人无法应对这些“通俗音乐”、“新潮音乐”的冲击,陷入了迷茫和困惑,而新一代的三峡年轻人也因为流行音乐的入侵和影响,对传统音乐不了解、不熟悉,更不会传唱传统音乐,他们身上仅存的一些传统音乐基因被一点点冲刷殆尽,传统音乐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无形中无情流失,更有甚者以继续传唱传统音乐为耻,认为那是一种落后的、保守的、老土的行为,由此一来,三峡地区的传统音乐逐渐被人们冷落和抛弃。
(二)三峡工程及三峡移民造成的三峡地区传统音乐的认为割裂
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经过了三峡工程建设及三峡移民的重要历史时期,这是与其他地区明显不同的。三峡工程建设及三峡移民对三峡地区传统音乐的影响甚大,一些传统音乐在三峡工程建设及三峡移民过程中被认为地割裂,这表现为:
1.由于诸如秭归、兴山、巴东、巫山、开县、奉节、大昌古镇等城镇因为全城淹没、全城搬迁,使得地区传统音乐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文化环境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2.伴随着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不少土生土长的三峡人迁徙到外地,从而导致三峡地区的传统音乐失去了固有的传播群体和传承人,从而逐渐被人们遗忘。
3.三峡工程的新建,筑坝拦水,使得长江河道上的许多浅滩支流也消失无踪,比如曾经水急滩浅的小三峡以及小小三峡,都因三峡工程的蓄水而一改往日模样,成为大型旅游船舶可以自由进入的优良河道,于是曾经在此活跃的三峡纤夫也逐渐转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生产力进步对拉纤劳动的自动抛弃),纤夫们曾经高亢雄浑的川江号子也随之沉入降低。现在要想听到这种古音,只有在当地的表演节目上,而这些表演节目由于缺乏川江号子的文化生态环境,以至于形神俱灭,徒有其表了。
(三)三峡地区传统音乐传承人的断代
传承人断代一直是困扰我国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三峡地区传统音乐上也是如此,一方面随着三峡地区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土生土长的三峡人开始走出峡谷、走出大山,同中国中西部其他地方一样,年轻人的外流和老弱病残的留守,是当前三峡地区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由于年轻人的外流,导致以“心传口授”为主要传承方式的传统音乐失去了新一代的传承人,许多传统音乐已经或者即将随着老一辈艺人的故去而消失在历史长空之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接受过现代音乐文化洗礼过的年轻一代,即便是回乡省亲、定居或创业,都热衷于享受现代音乐带来的精神麻痹、刺激,而不愿在传统音乐中寻找安慰、宁静,这种对传统音乐文化的无形抵制,也是造成三峡地区传统音乐传承后继乏人的重要原因。
(四)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三峡地区传统音乐的逐渐消亡
随着三峡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加重,水土流失、森林资源减少等问题对世代居住在三峡地区以农业耕种为生的原住民,特别是土家族、苗族等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以土地和耕种行为为基础的“山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日益破坏导致许多三峡地区原住民不得不离开祖辈们久居的三峡地区,外出谋职,这种一定程度上掐断了三峡地区传统音乐与三峡人的联系,从而导致传统音乐的逐渐衰微和消亡。
(五)三峡民间音乐的经济效益过低,社会效益被忽视
市场经济是以经济人为基本假设前提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体制,经济人最为重要的是就是一切以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这一共识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处于经济落后的三峡地区各级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也产生了行星撞地球般的强大冲击。于是,在当前看来那些没有或少有经济效益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音乐都被扔进了垃圾桶,而那些能够给地方政府和当地人带来经济效应的传统音乐则被进行重新包装,以便吸引外来游客的眼光,而完全不顾这些重新的包装已经完全破坏了传统音乐的灵魂,沦为了谋财获利的工具。这种短视的做法,根本谈不上对传统音乐的挖掘和保护,反而是加速了传统音乐的灭亡。比如土家族的哭嫁歌表演,就已经完全脱离了其最初的文化基础表演者既没有因为出嫁而不得不离开父母的那种悲痛,也没有初为新娘时候的喜悦与羞怯,而仅仅是为了表演节目来博人眼球、吸引观众。
三、三峡地区传统音乐的拯救
三峡地区传统文化灿若星辰,经过历史的打磨,更加异彩纷呈,但是,也正是因为它的“传统”和“古老”,才使其逐渐被现代社会遗忘。为了能使现代人认识了解并喜爱三峡地区的优秀民间音乐,也为了使我们的后代享受一片民间音乐的天空,拯救和保护三峡地区的传统音乐已迫在眉睫。不可否认,对于先辈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少三峡地区本土的和区外的专家学者、社会人士以及政府部门在全社会掀起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但是,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没有认识到,他们申报的所谓的“世界级”“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能真正代表整个三峡地区所有的非物质文化的,比如为了保护热带雨林,就不能仅仅保护几株具有代表性的植物;还有些人和政府部门太过“功利”,纯粹是为了“申遗”而“保护”,为了“经济效益”而“保护”,其行为就是“画个圈来收钱”,虽然短期内可能获得了经济收益,但却破坏了遗产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正是基于此,我们必须拨乱反正,正确处理拯救三峡地区传统音乐的方式和方法,努力保护传统音乐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使之沿着可持续的方向继续发展。
(一)“活态”拯救
三峡地区的传统音乐好比是滚滚长江中的鱼儿,正如为了保护江鱼,我们不能仅仅做一些鱼类标本一样,为了拯救和保护三峡地区传统音乐,我们也不能仅仅将传统音乐用单纯的文娱表演而留存下来,而要将传统音乐这条“江鱼”连同其赖以生存的“江水”一并保护下来。这就需要我们对三峡地区传统音乐采取“活态”拯救的方法,对某些传统音乐实施原样保护法,如摆手歌(舞)、薅草歌等与现代社会并不冲突的传统音乐;对某些传统音乐实施原样录像保护法,如川江号子、石匠号子等与现代生产力不想适应的传统音乐;对某些传统音乐实施仿真录像保护法,如“前歌后舞”这样的宫廷音乐;对某些传统音乐还可以采取多次录像的方式进行保护,如即兴创作的三峡民歌,多次录像法可以更为详细地记录其创作和演唱方面的变化规律。
(二)“教育”拯救
孔子云,“乐着,德之华也。”三峡传统音乐正是三峡地区千百年来人类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学习这些传统音乐不但可以提升其审美情趣、道德情操,跟可以了解并传承三峡地区的传统文化,正如匈牙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佐尔达•柯达伊(Kodaly Zoltan)所说,“民族传统有机的继承,唯有从我们的民间音乐中才能找到。”[4]由此可见,三峡地区传统音乐的继承和发展,必须依靠教育。但是,当前三峡地区传统音乐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缺乏完整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因此,尽快建立三峡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并编制相应的教材,是拯救三峡地区传统音乐的基础。在此,可以借鉴福建省的做法,不但在中小学课堂增加传统南音教育,举办南音比赛活动,还在泉州师范学院设立南音专业(本科),这些做法都极大地促进了福建地区传统南音的保护和发展。
(三)“人本”拯救
音乐说到底是关乎人的表达方式,它是对人的思想、情感、行为等综合的体现,因此,拯救三峡传统音乐最终还得落脚到人,做到以人为本。
1.要关注音乐受众,也就是对三峡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不管是老一辈的三峡原住民,还是新一代的“见过世面”的新三峡人,他们都对这块土地怀有深深的情感。如何使得三峡传统音乐不至于随着老一辈的三峡原住民的衰老而日渐老化、消弭?这就需要加强对新一代三峡人的音乐消费的关注,而这需要从政府的层面加以引导和强化。臧艺兵先生在其论文《音乐与八亿农民》中无不忧虑地指出,“官方的演出几乎不理睬”那些农民歌手、传统乐手,除非把他们和他们的音乐包装成具有“宫廷色彩”的样子。由此可见,官方的关注在“现代化”的今天已经严重“变味”,从而导致三峡传统音乐完全脱离了其“原生态”,沦为牟利的“伪传统”音乐,显然,这样的传统音乐虽然是“活的”,但其实它已经“死了”。因此,我们从根本出发,从人出发,才能真正拯救三峡地区的传统音乐。比如,巫山县著名的农村音乐人谭家兰女士,她首创了“巫山神女”网站,不仅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收益,更是广泛传播了三峡地区传统音乐,使三峡地区传统音乐不仅被世人了解、熟知,并演绎,还在一定程度上拯救和保护了三峡地区的这些传统音乐。
2.还需要充分关注传统音乐的表演艺人。三峡地区传统音乐的失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传统音乐是“心传口授”式的传承方式,在新一辈的表演艺人青黄不接的情况下,一旦老一辈的表演艺人故去,很多传统音乐也就随之消亡。因此,拯救三峡地区传统音乐,从人本角度出发就是要关心和关注表演艺人,对老一辈的表演艺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优越的待遇,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为其配备助手,以帮助他们把“心传口授”式的传统音乐用事物的方式记录下来,如纸质资料、电子资料、录音录像资料等,同时还要尽可能地组织老一辈的表演艺人培养新一辈的接班人,由于当前传统音乐的演出收益较低,所以还需对新一辈的接班人予以物质上的资助,使其在传承三峡地区传统文化的同时没有后顾之忧[5]。
3.要充分尊重三峡地区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三峡地区传统音乐之所以能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传承至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传统音乐根植于当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是其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家喻户晓的重庆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就是来自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啰儿调民歌,是当地土家族人民上山砍柴时的山歌,而《薅草歌》则反映了土家族人们在薅草过程中抖擞精神的民歌,曲风高亢、悠扬,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和感染力。这些反映三峡地区人民群众生活风貌的传统音乐,只有在当地人传统生活风貌中才能展现其生命活力。因此,我们不能人为主观地、强制地要求当地人移风易俗,这既是对他们的不尊重,也是对传统音乐的破坏。事物的发展总有其必然的规律,如果违反规律办事,结果只能适得其反[6]。
四、结 语
三峡地区是我国传统文化、传统音乐集结的重要区域,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品种繁多,表演形式丰富,是其他很多地区传统音乐所不具有的。但是,在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由于现代文化的不断侵蚀、加之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三峡地区传统音乐有的逐渐被人们遗忘,有的被人们重新包装,还有的正濒临消亡,文中提出的从“活态”、教育和“人本”出发对三峡地区传统音乐进行拯救的方法还有不足,也不尽全面,但却希望以此引发人们对三峡地区传统音乐保护和传承的强烈关注,使人们在机器轰鸣的工业社会能有一块打造传统音乐的静谧之地。
[1][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M].济南:齐鲁出版社,2010.
[2][南朝·宋]刘晔.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10册).
[3][民国]吕调元,刘承恩,张仲炘,杨承禧.湖北通志·风俗志(民国十年版影印本)[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4]杨立梅.柯达伊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5]熊晓辉.土家族土司音乐源流考略[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3(1).
[6]熊晓辉.土家族《上梁歌》的表现形式与音乐特征[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