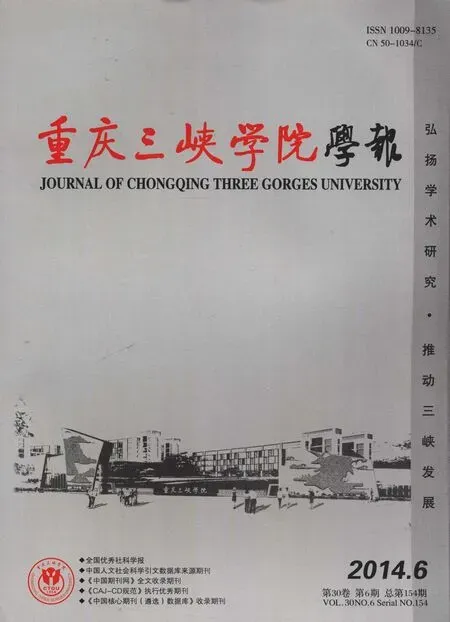扬雄《方言》词汇与汉代社会体系管窥
2014-03-28赖慧玲
郑 漫 赖慧玲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扬雄《方言》词汇与汉代社会体系管窥
郑 漫 赖慧玲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扬雄《方言》记载了众多的汉代方言词汇,这些宝贵的历史语料不仅反映了汉代各地方言分布情况,还为管窥整个汉代社会体系提供了相对详尽的资料。通过整理发现,《方言》一书中囊括了有关汉代政治和经济体系、社会阶级关系、生产力水平以及战事物质配备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且这些都是社会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要素。希望从以上几个方面着手,立足《方言》词汇,尽可能窥见汉代社会体系的轮廓。
《方言》;词汇;社会体系;史料
一、引 言
扬雄《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学著作,不仅开创了我国方言学研究的先河,还第一次以个人力量对全国大部分方言进行比较详尽的描写与比较,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占有卓越非凡的地位。罗常培先生在《方言校笺及通检·序》中,将扬雄的《方言》誉为“中国语言史上一部‘悬日月不刊的奇书’”[1],这不仅仅因为其在语言学、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还归功于它对汉代社会体系包括政治和经济体系、社会阶级关系、生产力水平以及战事物质配备等方面的宝贵记录。撒皮尔曾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2]通过对《方言》中词汇的整理,洞悉其语言后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可以为我们管窥整个汉代社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与平台。
二、扬雄《方言》中展示的汉代社会
了解一个社会最直接、最确切的信息来源,就是与当时人们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常用词语。扬雄《方言》一书共耗时二十七年,“常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这正如罗常培先生所说的:“《方言》是开始以人民口里的活语言作对象而不以有文字记载的语言作对象的。”[3]这种街头方言调查方式为我们研究汉代社会体系提供了丰富、可信的历史资料。
(一)《方言》中的汉代政治、经济制度与阶级关系
汉朝是我国封建王朝发展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瞥,汉代社会、政治制度大都承袭秦制,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较秦而言,汉初统治者重视发展农业经济,推行轻徭薄赋的赋税制度。同时,汉朝依旧崇尚重农抑商政策,对各阶级之间的等级制度也有严格的控制。《方言》是作者扬雄花时27年搜集整理而成的方言词书,其所收字词大都是对汉代社会面貌真实反映。正如布龙菲尔德所言:“每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4]探析扬子《方言》一书中所记载的字词,反思其背后的来由,对我们了解整个汉代社会是很有帮助的。
1.《方言》词汇与汉代政治制度
古来统治者就崇尚帝王之风,不止反映在绝对的政治统治秩序上,同时还要求其日常生活都具有皇室典范,其中高屋建瓴的宫室建筑就是一种体现。扬雄《方言》卷二中:“娃,嫷,窕,豔美也。吴楚衡淮之间曰娃,南楚之外曰嫷……故吴有馆娃之宫,秦有[木桼]娥之台。”郭璞注:“皆战国时诸侯所立也。”“娃”是吴人对美女的一种称呼,《资治通鉴》卷4胡三省注:“吴楚之间谓美女曰娃。”《御览》卷46引《越绝书》:“吴人於砚石置馆娃宫。”其中,“馆娃宫”原为吴宫名,为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宠幸美女西施而兴建。据《吴越春秋》载:宫内“铜勾玉槛,饰以珠玉”,楼阁玲珑,金碧辉煌。这些从某种程度都反映了古代帝王为博美人一笑的骄奢之风。
除此之外,《方言》中还有关于汉代官职的介绍,如“亭父”一职。《方言》卷三:“楚东海之间亭父谓之亭公。卒谓之弩父,或谓之褚。”郭璞注:“亭公,亭民也。弩父,主擔幔弩导憺因名云。”战国时,曾在临接他国之处设亭,并设置亭长,主担防御之责,出土于云梦的秦简上有“市南街亭”等语。《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十里为一亭,亭有亭长,掌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汉高祖刘邦就曾担任亭长一职。又《史记·高祖本纪》裴骃集解引应劭曰:“旧时亭有二卒,其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捉捕盗贼。”这里认为一亭长官由两人分别担任,亭父的主要工作是“开闭扫除”,治安警卫则为他职。
2.《方言》词汇与汉代阶级意识
纵观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人际社会关系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汉王朝也不例外。在这种等级深严的社会制度中,以地位低下的人为礼物相赠的旧俗,在古代并不鲜见。《方言》卷三中:“燕齐之间养马者谓之娠,官婢女廝谓之娠。”郭璞注:“女廝妇人给使者,亦名娠。”所谓“女廝”,是指送给使者的妇人,即“娠”,这种制度在汉代及汉以前都存在。《说文解字》:“娠,宫婢女隶谓之娠。”其中“娠”也就是女奴,也可作养马的人。女廝,《玉篇》:“使也,贱也。”《集韵》:“析薪养马者。”
汉代的阶级意识是比较强烈的,除了贵族不与平民、奴隶通婚之外,平民与奴隶通婚也有严格限制。同样在《方言》卷三中:“臧,甬,侮,獲,奴婢贱称也。荊淮海岱杂齐之间……凡民男而婿婢谓之臧,女而妇奴谓之獲。”我们可以看到凡平民与奴隶通婚,其社会地位也会随之降低。由此可看出汉朝对各阶级之间的通婚是有严格的控制的。
此外,汉代社会对农夫和商人是很轻视的。我们可以从对农夫和商人的称呼窥见一斑。例如:《方言》卷三:“儓,农夫之丑称也。南楚凡骂庸贱谓之田儓……或谓之辟。辟,商人丑称也。”“儓”是古代对低级奴隶的称呼,在汉代也作古代对农民的蔑称,这就说明汉代农民的地位是很低的,近乎奴隶。“辟,商人丑称也。”郭璞注:“僻僻便黠貌也。”“辟”,会意字,从卩,从辛,从口。“卩”,甲骨文象人曲膝而跪的样子。“辛”,甲骨文象古代酷刑用的一种刀具。称商人为“辟”,是对商人的一种歧视。
3.《方言》词汇与汉代经济制度
汉初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采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方言》卷七:“平均,赋也。燕之北鄙东齐北郊凡相赋敛谓之平均。”《广雅》:“平,均赋。”“均”,形声字。从土,匀声。匀者,帀也,“匀”亦兼表字义,合起来指土地分配均匀。《说文解字》:“均,平也”。《周礼·序官·均人》:“均,土均。”“均”特指古代的一种重量单位,古代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石。到汉代,一均等于二千五百石。《汉书》:“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据上所述,“平”、“均”都和“赋敛”有了联系。随着词汇意义和赋税制度的发展,语言对社会变化也适时做出反应,到了唐代,“平”、“均”发展为“均田”、“均平赋役”。明清时期,关于“均平”指称均赋税的情形就更多了。
关于汉初的赋税制度,有从汉高祖时起,实行“十五税一”的政策;及至汉文帝时期,又有“田租减半”之诏,也就是采取“三十税一”的政策,并有13年“除田之租税”。除此之外,汉初还有所谓“口赋”,也就是“人头税”,以及后来的“算赋”。但这些赋税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点——对商人与奴婢则加倍征收,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出汉代对商人的歧视,以及等级制度的深严。
(二)《方言》中的汉代的劳作工具
农耕文化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农业生产,在以农耕为主的汉代社会,劳作工具种类相对多样化。正如闵宗殿在《两汉农具及其在中国农具史上的地位》中所言:“两汉时期,是我国农具获得飞速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不论在材料上、动力上,还是在种类上、结构上,两汉农具都有突破性的发展,在我国农具发展史上,写下了十分辉煌的篇章。”[5]汉初的强盛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劳作工具的多样化是不可分割的。扬雄在《方言》中对此也有大花笔墨的介绍,其中包括粮食收割工具、收拢工具、加工工具以及织布的工具等,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汉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方言》中记载了一种收割庄稼的劳作工具,即现如今的“镰刀”。卷五:“刈鉤,江淮陈楚之间谓之鉊,或谓之鐹。自关而西或谓之鉤,或谓之鎌,或谓之鍥。”“刈鉤”是指镰刀一类的工具,多用于收割庄稼和割草。《说文解字》:“钩,曲也。”《玉篇》:“钩,曲也,所以钩悬物也。”从形状上来看,“刈鉤”是弯曲的,所以也可称为“鉤”。《说文解字》:“锲,镰也。”《六书故》:“刎镰,一曰小镰,南方用以乂谷。”由此看来,“刈鉤”、“鉊”、“鉤”、“鎌”和“鍥”都是汉代各地对“镰刀”这一收割工具的不同的称呼而已。
有收拢粮食的“杷”。《方言》卷五:“杷,宋魏之间谓之渠挐,或谓之渠疏。”郭璞注:“无齿为朳。”《说文解字》:“杷,收麦器。”“杷”是指一种有齿和长柄的农具,多用竹、木或铁等制成,用以把谷物等耙梳或聚拢起来。据此说来,王智群将“杷”归为“收割工具”[6]是有欠妥当的,我们窃以为应单独归为收拢粮食工具。
此外,还有对粮食进行加工的工具“臿”和“僉”。《方言》卷五:“臿……宋魏之间谓之铧,或谓之鍏。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臿。”“臿”本意是指舂去麦皮,引申为舂捣。《说文解字》:“臿,舂出麦皮也。”同样在卷五:“僉,宋魏之间谓之欇殳,或谓之度。自关而西谓之棓,或谓之柫。齐楚江淮之间谓之柍,或谓之桲。”郭璞注:“僉,今連架,所以打穀者。”僉,亦作“连耞”,或作“连枷”,是农民的手工脱粒农具,由竹柄及敲杆组成。原为农村手工脱粒农具,工作时上下挥动竹柄,使敲杆绕轴转动,敲打麦穗使表皮脱落。同理,我们以为王智群将“僉”也归入收割工具是不恰当的。
也有用来织布的工具。《方言》卷六:“杼,柚,作也。东齐土作谓之杼,木作谓之柚。”“杼”本义是指织布机的梭子。《说文解字》:“杼,机之持纬者。”注:今以梭为之。《后汉书·列女传》:“此织生自蚕茧,成于机杼。”机杼,后泛指织布的工具。杼柚也作“杼轴”,后作织布机上的两个部件,即用来持纬(横线)的梭子和用来承经(直线)的筘。亦代指织机。朱熹《集传》:“杼,持纬者也;柚,受经者也。”
刘君惠曾说过:“文化中最容易被人注意到的是一个社会中的物质设备。”[7]生产工具作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物质生产设备,其种类的多样化和广泛分布一方面体现了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
(三)《方言》中的汉代武器、战车、船等
汉初政权建立之后,强大的中央集权尚未形成,汉代统治者尤其以汉武帝为甚,都力图开疆扩土、征伐四方。刘军在《汉代军事后勤思想述要》一文中指出:“汉代是中国古代军事发展史上的丰碑,开创了古典军事作战的典范。”[8]我们认为这不仅要得益于强大的后勤物质储备,还要归功于统治阶层对军事武器设备发展的重视和大力扶持。《方言》中第九卷介绍了种类繁多的军事武器、车辆和船只,这也是汉代战事准备的一个写照。
1.《方言》中的军事武器
“戟”这种作战工具在汉代是很常见的,并且总类较多,连大小、曲直不同称呼也会随着改变。《方言》卷九:“戟,楚谓之[釒孑]。凡戟而无刃秦晋之间谓之[釒孑],或谓之鏔,吴扬之间谓之戈。”卷九:“三刃枝,南楚宛郢谓之匽戟。”郭璞:“今戟中有小孑刺者,所谓雄戟也。”《广雅》:“匽谓之雄戟。”三刃枝,这种兵器也是戟的一种。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戟出现于商代,戟是在戈和矛的基础上演进而成的。由于戟吸取了戈和矛的长处,在战场上也就更处于优势地位。西汉以后,戟由平直变为弧曲上翘,进一步增强了前刺的杀伤力,成为当时军队中的常备兵器。
“矛”,是古代用来刺杀敌人的进攻型格斗兵器,主要用于直刺和扎挑,是古代军队中大量装备和使用时间最长的冷兵器之一。《方言》卷九:“矛,吴扬江淮南楚五湖之间谓之鍦,或谓之鋋,或谓之鏦,其柄谓之矜。”《说文解字》:“矛,酋矛也。建于兵车,长二丈,象形。”“鍦”,《集韵》:“短矛也。”《左思·吴都赋》:“藏鍦于人。”注:鍦,矛也。“鋋”是指古代一种铁柄短矛,也泛指短矛。《说文解字》:“鋋,小矛也。”《史记·匈奴列传》:“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鏦”,古代一种小矛,也指古代一种有方形柄孔的斧子。《说文解字》:“鏦,矛也。”
除了进攻型格斗兵器,汉代军事战争中还有一种广泛应用的防御型武器“盾”。《方言》卷九:“盾自关而东或谓之瞂,或谓之干。关西谓之盾。”“瞂”,《说文》:“盾也。”《张衡·西京赋》:“植鎩悬瞂,用戒不虞。又通作伐。”“干”按其甲骨文字形,其形像叉子一类的猎具、武器,其本义是盾牌。《礼记·祭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注:“朱干,赤盾。”《礼记·檀弓下》:“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2.《方言》中的运输工具
汉代战车的结构构造比较成熟,关于汉代对车的组成部分的称呼,《方言》第九卷也有详细的记载。例如:“车下铁,陈宋淮楚之间谓之毕。”“毕”的本意是指打猎用的有长柄的网。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毕,田网也。”卷九“车枸簍,宋魏陈楚之间谓之[竹恢]……南楚之外谓之篷,或谓之隆屈。”“篷”古时一般指遮蔽风雨和阳光的设备,后也指帆。“轮,韩楚之间谓之轪,或谓之軝。”郭璞注:“轮,車輅也。”“轪”,按许慎《说文解字》:“轪,车輨也。”扬雄《甘泉赋》:“肆玉轪而下驰。”注:“车辖也。”
汉代的水上运输是比较发达的,舟因大小、长短、深浅不同而称呼各异,扬子《方言》中对这种情况的描述也极为细致,《方言》卷九:“舟……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小舸谓之艖……艇长而薄者谓之艜,短而深者谓之[舟符],小而深者谓之[楺,矛換巩]。”“舸”在楚方言多用来指大船。后来也可指小船,泛指一般的船。这些繁多复杂而又近乎详尽的区分,从侧面反映出汉朝船运之广泛,也为汉朝扩土开疆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三、小 结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方言》作为“中国语言史上一部‘悬日月不刊’的奇书”,不仅记录了相当数量的方言词汇,并指明各方言分布状况;还超出语言学的范畴,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体系包括政治和经济体系、社会阶级关系、生产力水平以及战事物质配备等方面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华学诚曾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方言》研究将面临着总结、加深、开拓三个方面的任务。”[9]从社会体系的角度来重新看待《方言》,也可以为我们研究《方言》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
[1]周祖谟,吴晓铃.方言校笺及通检·序[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2]撒皮尔.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周祖谟.方言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M].袁家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闵宗殿.两汉农具及其在中国农具史上的地位[J].中国农史,1996(2):29-33.
[6]王智群.扬雄《方言》词汇与汉代农牧业[J].台州学院学报,2011(2):41-43.
[7]刘君惠,李恕豪,杨钢,等.扬雄方言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92.
[8]刘军.汉代军事后勤思想述要[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4):115-118.
[9]华学诚.近15年来的扬雄《方言》研究与我们对《方言》的整理[J].南开语言学刊,2001(1):59-69.
(责任编辑:张新玲)
Dialectal Words in Yang Xiong’s Dialect and the Social System of Han Dynasty Reflected
ZHENG Man LAI Huil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Yang Xiong’s Dialect had recorded numerous dialectal words of Han Dynasty. Those precious recordings can not only reflect the dialectal atlas of Han Dynasty, but also provide detailed data to obtain a rough view of the social system of Han Dynasty. A sorting out reveals that Dialect includes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system, class relation, level of productivity and war equipment storage, which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the social system. Based on the dialectal words in Dialect, and from the aspects just mentioned, we attempt to obtain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 of Han Dynasty.
Dialect; words; social system; historical data
H172.3
A
1009-8135(2014)06-0117-04
2014-07-29
郑 漫(1989-),女,湖北天门人,西华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对外汉语方向。赖慧玲(1980-),女,四川成都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