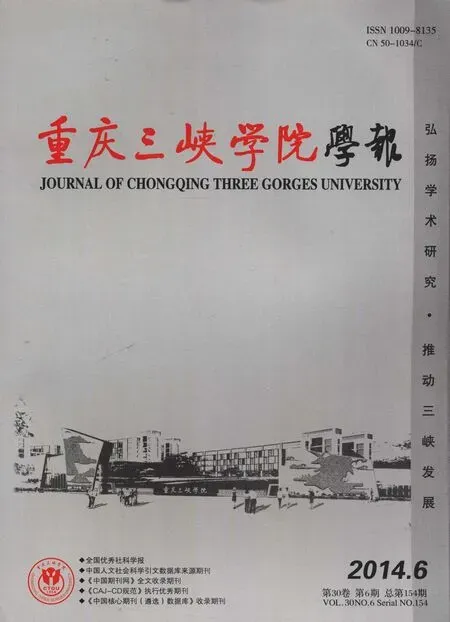《甩鞭》的生命意识
2014-03-28郑宗荣
郑宗荣 李 俊
(重庆三峡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甩鞭》的生命意识
郑宗荣 李 俊
(重庆三峡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甩鞭》写了土改前后山西山区农民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形态,主要以王引兰的生命历程为线索,展示一个普通女人活着的艰难。文本中蕴含着丰富的生命意识,表现为浓烈的生殖崇拜意识,王引兰童年愿望的满足、补偿心理的实现和性的满足。
《甩鞭》;葛水平;生殖崇拜;童年经验;补偿心理;性
“这个世界上,我用活来肯定他们的死,然而这活、这肯定,是怎样的一种疼![1]”这是葛水平在《甩鞭》里对王引兰生命的诠释。《甩鞭》描述了一个普通女人王引兰如何活着的故事。王引兰小时候因为父亲遭受意外的牢狱之灾,不得不和母亲背井离乡,十一岁时母亲三块大洋把她卖给李府当丫头。在李府长到十六岁,亭亭玉立,肤白貌美,被李府老爷看上。李府夫人想置她于死地,她只好求救于来李府送木炭的农村地主麻五,麻五乐颠颠地白捡了个“粉娘”,把王引兰带到乡村,过上了幸福生活。王引兰和麻五生了个女儿“新生”。好景不长,麻五在土地革命中被划为“地主”,家产被分光,挨批斗时,生殖器上被吊了秤砣蹊跷而死。为了自己和女儿能活下去,王引兰嫁给了第二任丈夫李三有,虽然贫穷,但还算安稳。没想到很快李三有意外地坠崖身亡。王引兰只好跟随麻五原来的长工铁孩回到过去的老窑,铁孩想和王引兰结合,王引兰说要等到女儿新生结婚以后,铁孩激动之下,说了自己害死麻五和李三有的事情。王引兰用铁孩杀羊的小刀插进了铁孩的身体。
《甩鞭》写了土改前后山西山区农民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形态,表现了这种生活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展现了传统文明的神韵,尽可能符合生活的真实。故事如流水一般缓缓流淌,没有大起大合的激动人心的情节,却有着丝丝入侵的力量,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动容,为王引兰无法反抗的命运感到悲伤,为人性中无法遏制的“恶”感到悲凉。葛水平在小说的字里行间运用了大量的隐喻、象征、意象,表现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性、梦想、生存与死亡。艰难的生活,渗透着顽强的生命意识。
一、生殖崇拜
《甩鞭》里展现了丰富的民俗文化,饮食服饰、民居建筑、婚丧习俗、岁时节日、方言俚语等无所不包,是人们生活状态及生命意识的折射。恩格斯说:“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2]”人类对“种的繁衍”非常关注,凝聚为骨子里的生殖崇拜。
“甩鞭呀,就是敲响冻地,告诉春天来了。”[1]甩鞭是山西农村迎接春天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仪式。“麻五拿了鞭走到大门外站到碾盘上,王引兰看到窑庄男男女女都站在碾盘周围,甩鞭人麻五张开了腕口,一条生命的弧线炸开了。”[1]
长形的鞭和圆形的碾的交融,也暗示天与地的交合,寄予着人民渴望粮食丰收、家畜繁殖、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在中国民间,鞭是对雄性动物生殖器的称呼,如牛鞭、马鞭、驴鞭、虎鞭、鹿鞭、羊鞭等。这里的鞭除了实写是一支牛皮鞭以外,更有文化上的寓意,象征着无穷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先民将对各种自然力的敬畏、依赖与神灵信仰观念相结合,产生了自然崇拜。做碾用的石头是“生命的本源,创世的母体”。人类的祖先在使用和征服石头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它的自然属性,在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对其产生了依赖和敬畏[3]。
小说中多处描写了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盛开的野菊花,散发出土地的静谧馨香和无边的大自然的生命信息。似乎王引兰每次性爱,都饱含着对油菜花的热爱与想象。“忽然一夜,油菜花开了,满坡耀眼的黄亮,花香把她拂闹得轻灵舒缓,差不多堵塞了对春天的其他想象。”[1]“那地方有丛野菊花生长着,花瓣很稠很浓,在太阳光下闪闪烁烁。山菊花的黄有点像油菜花,花朵在风的作用下不停地翻动。”[1]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调查材料证明,我国有许多地区还存留着以花卉植物象征女阴的痕迹。赵国华认为“从表象来看,花瓣、叶片可状女阴之形,从内涵来说,植物一年一度开花结果,叶片无数,具有无限的繁殖能力。所以,远古先民将花朵盛开、枝叶茂密、果实丰盈的植物作为女阴的象征,实行崇拜,以祈求自身生殖繁盛、繁衍不息。”[4]人类的生殖繁衍同植物的开花结果一样,都是自然界的生命延续。小说中还形象地描写了公鸡和母鸡调情,写出了大自然中生命繁衍的自然、淳朴、美好,寄托着人类追求生命繁衍茂盛的集体无意识。
小说人物的命名也颇有深意。王引兰可以看作是“引男”的谐音,与常见的“引弟”“招弟”异曲同工。王引兰给女儿起名叫“新生”,看似随心,却别有深意。新生是王引兰生活的升华和提高,是梦想和寄托,是凤凰涅磐。王引兰为了“新生”,自己的新生和女儿新生,改嫁给李三有。中国文化中一直注重生命的延续,不但帝王追求“长生不老”,普通人也得顽强地活下去。葛水平恰到好处地运用民间经验,选取了鞭、碾、花等意象揭示生殖崇拜,展示生命意识,赋予了作品新的精神个性。
二、王引兰的生命意识
王引兰美丽姣好的容颜,不是让她成为生活的宠儿,而是应了“红颜薄命”那句古话。她从城市逃到山西农村,甩鞭贺岁的习俗激发了她对大自然的亲近与对生命春天的盼望。她似乎找到了春天,找到了想要的幸福,看着半坡的油菜花,沉醉而忘记了一切。本来她只追求简单活着的本真,但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打破了她平静的幻想。失去丈夫,失去财产,不得不以柔弱的躯体和顽强的意志与磨难和考验对抗。
王引兰的一生是依附着一个又一个男人过活的,“小时候女人活娘,长大了活男人[1]”是她的信条。每每沉入命运深渊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男人出现。在李府中无路可走时,麻五出现了;麻五死了,孤儿寡母需要一个男人承担生活的重担时,改嫁给了李三有;李三有死了,跟随铁孩回到老窑。她无论怎样挣扎,最后都会成空,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力量在控制着她,真正主宰她的,也许是这种未知的心理力量。
用鞭声开启的春天,或许就是王引兰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来自生命的原点,或者来自童年的一种记忆。它沉寂在心灵深处,如同冬眠。惊蛰这一天,父亲的“鼓声敲响了冻土,把春天召唤来了。”[1]
“她和麻五结婚的时候,笼罩在她眼前的喜气如同贴在她前额的往事,让她想起童年时老财娶妾。从春天油菜花田里穿过的花轿忽闪闪的,忽闪起了她一个梦想:长大了也坐了花轿穿过油菜花田嫁人去。”[1]结婚,不过是满足童年愿望而已。“新人王引兰坐在花轿里,妖娆得很。她感觉到了幸福,也无异于投靠了幸福。得到幸福了吗,恍惚中又觉得这不是她要的幸福。”[1]到底要什么样的幸福?
弗洛伊德认为,凡一个姑娘去一家人家当侍女、伴读、保姆等,她就会不自觉地做着白日梦,即不管以什么方式,这一家的太太被除掉了,她自己取而代之,成为这家男主人的妻子[5]129-130。王引兰在李府当丫环时,看似被老爷逼迫,也许是她内心隐秘愿望的实现。所以当她到了麻五家,“王引兰来到窑庄第一天起就决定要用火盆来取暖。她不想生煤火,一来嫌煤脏;二来李府太太拢了袖管坐在火盆前的姿态很优雅,她从心里一直想着那个姿态。”[1]
弗洛伊德把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自我”是“一个可怜的、不安定的存在,它受到外部世界的打击,受到超我无情谴责的折磨,受到本能冲动贪得无厌的要求的困扰”。[6]232对应着“自我”的人格构成,“代表理智和常识,按照现实原则行事。它既以大部分的精力控制和压抑发自本我的非理性的冲动,又迂回地给予本我以适当的满足。”[7]124如果说在李府的时候王引兰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到了窑庄,她的自我觉醒了,想享受和李府太太一样的生活,满足了她一直缺失的“男主人妻子”的愿望,是一种补偿性满足。王引兰与麻五有了稳定的“婚姻”,性的欲望得到满足。麻五买了房子对面的一片坡地种上油菜,可以整天无所事事地看着满眼金黄享受着人生,所有年少的愿望都得到实现,她的“力比多”得到了释放,所以她真的安稳下来。
小说还原了女人的原始本性,赋予她们作为女人最重要的两点:性与爱。以性衍后,以爱泽人,生生不息。王引兰生命中的三个男人,以不同的方式爱过她,但也毁灭了她。最初麻五是她心中缺失的父亲,“爹啊,救救我吧,你不救我,我就没命了。”[1]渴望得到父亲一样的保护。走过年轻时的青涩,品尝了生活的艰辛,高大强壮的李三有在王引兰看来像一堵墙,他的高大让王引兰怦然心动,而脾气的温顺又让王引兰内心觉得很服帖。和李三有在高粱地的欢爱,终于得到一种平等的爱人的幸福。当作为性爱屏障的高粱被割倒时,她感到了深深的惆怅。性爱对这时的王引兰来说,是安稳生活与灵魂很重要的一部分。不管发生什么事,铁孩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这个一直陪着她的男人,和她之间却没有性爱关系,正因为没有得到,铁孩杀死了王引兰生命中的两个男人。当她认清铁孩是她不幸命运的始作俑者时,愤而举刀刺向铁孩。
死亡本是人人都想极力避开的,可在《甩鞭》里“死”不仅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脱离平庸进入崇高的方式,用“死亡”衬托活着的意义,就像铁孩所说:“人都想争活,其实活着的人哪有死了的人稳妥。”[1]“有些事情放不下,就得活。”[1]活着,是为了完成生命中未竟的愿望。作者用不可避免的死亡来促使人们反思活着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三、结 语
这篇小说,从死开始,到死结束,却讲的是活着的奔波与追求。生命完成了一个循环,梦想、希望,短暂的繁华之后,归于虚无。到文本结束,王引兰恍然发现,“她渴望的春天来了,春天美得没法言说,”[1]却又意识到,“她看到的依旧是一片暗,是一种没有半点生机的死亡颜色,一个聒噪的世界里,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已经离她而去。原来她的生命里没有春天的啊。她听到血流成阵,落地如鞭,干巴巴的成为绝响。”[1]《甩鞭》以乡俗中的甩鞭迎春隐含着人们对人生“春天”的渴望。在花开花落之中,是顽强的生命意识支撑着人艰难地活着,艰难,也是活着的意义吧。
[1]葛水平.甩鞭[J].黄河,2004(1):77-103.
[2]兰岗.主题与变奏——中国仕女画与西方女性裸体画的比较[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5(4):29-37.
[3]曹春茹.中国古代神话中石头的生殖崇拜[J].语文学刊:基础教育版,2006(8):69-70.
[4]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略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8(1).
[5]吴立昌.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转引自张永胜.《法国中尉的女人》人物形象体系的多重蕴涵[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
[6][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7]车文博.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张新玲)
Consciousness of Life in Whip Lashing
ZHENG Zongrong LI Jun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Wanzhou, Chongqing 404100)
Whip Lashing describes the living situation and forms of the farmers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in Shanxi Province at the turn of Land Revolution. Taking the life of Wang Yinlan as the clue, it demonstrates the hardship of an ordinary woman. The novel is filled with consciousness of life in the forms of strong sex worship,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wishes of Wang Yinlan’s childhood, the realization of compensation psychology and sex satisfaction.
Whip Lashing; Ge Shuiping; reproductive worship; childhood experience; compensation psychology; sex satisfaction
I206.7
A
1009-8135(2014)06-0092-03
2014-05-30
郑宗荣(1975-),女,重庆万州人,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学报编辑部编辑,主要研究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