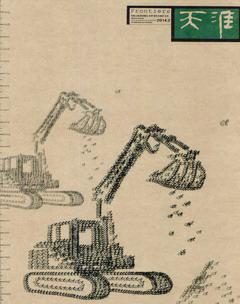作家在作品中的说者形象
2014-03-26王勇
王勇
近年来,在反复阅读巴赫金的论著时,他看待话语现象的一道独特目光,也引起了我格外关注。这就是在人们使用语言进行言谈的话语世界,究竟是“谁在说话和对谁说话。所有这一切决定着表述的体裁、语调和风格,如领袖话语、法官话语、老师话语、父亲话语等等”①。只是我们作为日常话语的说者,对此已经习焉而不察,所以就很少追问:比如在科学论文背后,是否含有一种学者的说者形象,在公文语言背后,是否含有一种官员的说者形象,在法律文书的背后,是否含有一种法官的说者形象。归根结底,这是一个话语世界中的“说话人以谁的面孔讲话,为何(即在何种情景中)讲话”②,这样一个十分复杂却饶有意思,值得我们深入揭示的说者形象的课题。
应该说,巴赫金早已揭示的说者形象这一研究对象,在汉语学界至今仍未引起足够关注。其实,说者的形象不仅是人类话语世界中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而且涉及人们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仅把视点聚焦在文学领域,侧重结合李娟散文写作这一典型文学个案,谈一下我对作家在作品中的说者形象形成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其中把李娟的写作和那些同属于汉语跨族际写作的作家相比,我们不难从中看出,一个作家在不同的作品中,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说者形象,不同的作家面对共同的言语对象时,也会呈现出相同或不同的说者形象,同一部作品的作者在不同的读者眼中,也可能会被解读出不同的说者形象,作家在作品中可能具有的说者形象问题,也是一个充满了多样性、独特性、复杂性的研究课题。
巴赫金很早就独具慧眼地指出:日常话语的说者和文学话语的作者(他扮演着整个作品的说者角色)虽然同属于话语的说者,但前者对自身的说者形象往往都会习以为常,因为说者的言语意识已经习惯于指物述事这一实用目的:“如果这时形成了说者形象和语言形象,那么这一点并不属于言语的任务。说者对这种形象既不感兴趣,也不想将之告诉听众(如果他不是矫揉造作,故作姿态的话)。”③但是在文学创作的作品中,“这里有许多个说话者,而同时却只有一个说话者(即作者)”④。这后一个层面的说者,即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与生活中的说者相比,恰恰具有着一个明显的特性所在:这一说者从事写作的一个自觉目的,正是塑造和描绘在言语谈吐上更加典型、生动、独特的说者形象。也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巴赫金也进一步提出了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作家在倾心描绘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时,他自身作为语言描绘者的说者形象,也会自觉不自觉,或明或暗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但是当我们带着这种目光,反观目前的汉语文学研究领域,却又不难发现,在文学研究者的常态视野中,谈到文学形象这类研究对象,主要还是指被作家描绘出来的各种文学形象,而作家作为文学话语的说者,他本身在文学作品中扮演着何种说者角色,呈现着什么样的说者形象,这类问题却被丢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长期以来成为一个文学研究的盲点。
谈到作者之我的说者形象,巴赫金格外提示:属于人的任何“形象”,都是被人创造的产物。这里当然不能把作者其人的相貌、品性、言谈之类的个人形象,与他在创作中扮演的某种说者形象混为一谈。因为那个伏案写作,原有着真实自然人身份,活在自己生活中的作者其人,原本就是生活中固有的,而不是通过文学方式被他创造的产物。所以这里所说的作者形象,借用巴赫金的术语表述,应该是由“第一性”的作者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某种“第二性”的作者形象,这个第一性的作者和他第二性的形象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属于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作品之外的作者和他在作品中投射的形象之间,的确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完全割断了这种血肉联系的作家,是一个只会用假嗓子说话的作家),但是,尽管有时候真像是文如其人一样,第一性的作者与其在创作中扮演的说者形象仿佛就要融为一体了,后者几乎成了创造者其人看似逼真的替身或化身,这也进一步巩固了一种错觉,即人们在谈论这一问题时,把二者混为一谈的现象总是屡见不鲜。
谈到作家在作品中留下的说者形象,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我们平常的文学阅读经验中,作家笔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似乎往往并不是作家本人的说者形象,而是被作家创造的那些谈吐各有特点的人物形象,这的确是我们不难碰到的一个文学事实。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这里至少有这样一种原由:从事文学写作的作家,也许具备创造生动人物形象的能力,还能讲出一些十分精彩的故事,但是这些作家中的不少人,却可能缺少典型的、独特的自我说者形象的文学原创力。所以他们作为作家之我的说者形象,也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在塑造形象的意义上可以说,作家近似于出色扮演各种人物形象的演员,但作家毕竟又不同于演员,演员虽能扮演不同的人物形象,自身却无法像作家那样,在创造不同形象的同时,也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形成自我的说者形象。只是由于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写人论事时,最终只能为读者呈现一个时代最通行的、最常见的、最盛行的一些说法、看法和写法,他们作为万事万物的描绘者,自身却扮演着乏善可陈的说者角色,因而这类作家之“我”在作品中的形象,也就成了“我们”眼中习以为常的,无需给予特别关注的,也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说者形象。
优秀的作家之所以优秀,不仅是因为这些作家创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而是由于作家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不仅富有作家之我深刻而独特的印记,又十分典型地体现了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时代、一个地方、一种文体、一种文学风格,某一类或某一代人富有着某种代表性的说者形象。这里仅举几例:1986年6月,博尔赫斯去世前六天,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前往日内瓦看望他,博尔赫斯的一句临终之言令她印象深刻,这句话就是:“作家以为自己在谈论很多事情,但他留下的东西,如果运气好的话,是一幅他自己的形象。”而以大写之我放声歌唱的美国著名作家惠特曼,他之所以成为改写美国文学史的一代经典作家,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言:“惠特曼出生前不到五十年,美国宣布独立。但是她虽然赢得了自由,却没有发掘出一个灵魂。心花怒放注视着这块领域的诗人,他们以外国的眼光观察,以过去的声音发言。”正是惠特曼跃然而出,在《草叶集》中一改往日的诗风,鲜明而深刻地展现了作家之“我”代表崭新的、现代的美国之我发言的说者形象。巴赫金之所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备加赞赏,这显然是因为陀氏是一位与所谓独白型作家明显有别,创造了“复调小说”这一独特文体的作家,这类小说中的说话人所说的话语,不仅在外在性,而且在内在性上都充满了你来我往的对话性基调。而且,这种对话性,同样也深刻体现在作家之我这一半隐半现的说者形象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作者讲到主人公,是把他当作在场的,能听到他(作者)的话,并能作答的人。”⑤这类作品的作者在讲到自身之我和他人之我时,毅然打破了那种独白性的牢固框架,他不是在“背靠背”地谈论对方,而是在与之进行着“面对面”的相互交谈。这的确是有关作家这类说者形象的流变史上独具魅力的一种形象。endprint
如果从中国叙事学的眼光来看,在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史上,就始终存在着一个昭然醒目的、脱胎于民间话本说话人的说者形象。但是正如浦安迪所说:“陈寿的《三国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无名氏的《全相三国志平话》都在叙述三国的故事,但谁也不会否认它们是三本截然不同的书。这不仅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哲学深度,显示了不同的艺术质量,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精神,而且更是因为它们代表三种不同的‘叙述人口吻;陈寿用的是史臣的口吻,罗贯中用的是文人小说家的口吻,而无名氏用的是说书艺人的口吻。”近代以降,受到西方小说家叙事风格的深刻影响,汉语小说作者那类传统的说者形象开始退出叙事舞台,“各位看官”、“却说”、“且说”这些作者用于自白的陈词套语渐被丢弃,正如人们常提及的:现代小说史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作者的隐退。尽量不要站出来说话,而是隐藏起自己的说者形象,这似乎成了当代小说家不约而同的一个潜规则。这时的作者竞相追求讲述的中立性,努力扮演着一种貌似客观,一言不发的说者角色。但是这不过是作者的修辞术给人造成的文学错觉。这只是一个作家的说者形象是否更加隐蔽的问题,而不是作家的说者形象是否有无的问题。因为面对任何所写的对象,作家总是一个有感而发的说话人,他不可能绝对做到无动于衷,不可能是一个毫无主体感应的“物自体”。在作者看似悄然无声的客观呈现中,正如巴赫金所言,这是客观描述背后隐含的“作者利用这种叙述,透过这种叙述,折射地讲自己的话”。所谓“‘客观再现的倾向,和‘客观描绘的不同手法,都只不过是构筑作者形象的一种特殊的相对原则”。
来自新疆的散文作者李娟,近年来开始引起文坛的关注。一位来自草根世界的文学写作者,之所以能够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显然是李娟的写作具有着某种引人关注的独特性。谈到这一点,我想到不少评论者不约而同的一种说法:这是因为李娟呈现了汉语读者鲜为知晓的世界一角,这就是新疆阿尔泰山一带哈萨克牧民的原生面貌。我也注意到,李娟在《阿勒泰的角落》一书的自序中,也有这类相似的自白:这本书“如果说有成书的必要,大约是因为它们所记录的这些与我自己有关的游牧地区生活景观,还算是少有人记录的”。但是在我看来,写作题材的新与旧,其实只是一个相对而言的问题,因为一个作家不论言说着什么样的对象,他在人类话语世界中,都不可能是谈论这一对象的第一位或唯一的作家。较早说明这一言语事实的学者也是巴赫金。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强调:“说者言语的对象(不管这一对象是什么东西),并不是第一次在该表述中成为言语的对象,也不是这个说者第一次讲到它。对象可以说早已为人所议论、争论,得到过不同的阐释和评价,围绕着它有过不同观点、世界观、流派,相合和相悖。说者——他不是《圣经》中的亚当,亚当只同尚无称名的原始事物打交道,第一次给它们起了名字。”
作家总是使用某一种语言描绘世界,提到李娟描绘的游牧世界,她在书中用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汉语感叹:“在这里,泥土还不熟悉粮食,道路还不熟悉脚印,水不熟悉井、火不熟悉煤。”但这个世界却早已经被多种语言照亮过。谈到哈萨克族的游牧世界,最地道、最本色地描绘这一世界的语言,理应属于这一世界的主人使用的母语哈萨克语。这一事实也提醒我们,李娟津津乐道的一些牧人故事,也许在众多哈萨克民族作家笔下,早已是习以为常、不足为奇的生活景观。顺便说一下,如果把李娟的散文翻译成哈语,她是否仍然能够获得不小的反响呢?李娟是使用汉语,主要面对着汉语读者写作的作者,有许多文学事实提示我们,她同样也不是首次或唯一用汉语描绘哈萨克族生活的作家。在本文中,我想把李娟的写作,归之于汉语世界源远流长的一条文脉,这就是汉语跨族际写作。对于汉语写作者而言,来自任何一个民族的作家之我,用汉语描绘任何异民族这类他者的作品,都不过是这类写作的不同变体而已。在我看来,与其说李娟的独特之处,来自她写作题材的新鲜或新颖,不如说在汉语跨族际写作这一背景下加以观照,她的散文独具一格的一个地方,也来自她作品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说者形象。
谈到汉语世界的说者之我对异民族这类他者的记述史,几乎和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其他民族相遇相交的历史一样久远。这无疑也是汉语写作史的研究者值得关注的一类写作。但是研究者同样也应该注意到,这一写作史也隐含着另一种历史,因为汉语跨族际写作史,不仅直接反映了不同时代被汉语描绘的不同民族的面貌,也同样呈现了不同时代的汉语描绘者作为说者留下的投影,这也是汉语跨族际写作中说者之我的形象此起彼伏的历史。
应该指出,跨族际写作中的说者形象,也像话语世界中其他说者形象一样,都不是说者个人杜撰的产物。它们是人们对世界的传统看法和说法,在言语活动中形象化的产物。“在每一时代里,在生活和活动的所有领域里,都存在着用语言表现和流传下来的一定的传统。”⑥有的要历经千百年时间的锤炼,才会在人们言语方式的习得中积淀或稳定下来。巴赫金还说道:“作者是自己时代的囚徒,是他当时生活的囚徒。”其实,没有哪一种语言,哪一个民族中谈论他者的说者,能完全超越时代和历史的局限而独善其身。这里也可以套用巴赫金文中的一种有意思的说法:包括司马迁在内的中国古代汉语跨族际写作中的说者,他们看不清自身历史局限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即不知道自己毕竟是活在古代的说者,因为他们不可能像今人一样,早已经历了从古代而现代这一巨大的“时间差”。用今人的眼光来打量古人扮演的所谓“夏夷之辨”的说者形象,这显然是古典的汉语世界里,局限于汉语和汉语所述内容的一种说者形象。
二十世纪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有的时间只有一百年,但是这百年之内中国作家之我的说者形象,却获得了全面的更新和改造。汉语跨族际写作者与古代相比,也形成了具有现代格调和崭新姿态的说者形象。如果说民国时期较早觉悟的一些民族学和历史学说者,已经发出了这类声音:“我们的边疆,是我国土地的一部分,我们边疆的民众,是我国人民的一部分。”那么体现了这类声音的说者形象,在范长江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就已经开始显露雏形。与后来的文学作品相比,他也许算不上“纯”文学的说者形象,但是回到当时的语境重读这一旧作,文中处处闪现的那个说者形象,还是会给人留下弥足珍贵的印象。这是一个对当时亦很通行,视边疆为荒蛮之地,视边疆民族为愚蛮之人的传统说者有所反省、有所启蒙的说者形象,是汉语世界的说者之我,重塑以中华民族的情怀和目光的说者形象。endprint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体和国情的重大转型,汉语跨族际写作开始在文学世界大放异彩。语言是人的第二形象,作家作为文学话语的说者,原本就是特别重视言语形象的说者,这类说者说什么和怎样说,为自身建构什么样的说者形象,这并非是一个纯粹个人化的言语行为,也是时代语境约定俗成的形成物。当代中国的边疆地带吸引着越来越多当代作家的目光,也形成了一批可圈可点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当然具有着不同的文学风貌,分别打上了作家文学个性的印记。但是这些作家在作品中呈现的形形色色的说者形象,仍然具有一些可以相互比较的共同点。这里仅举两类比较突出的类型,它们都是似曾相识,就像“原型”一样,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中重出复现的说者形象。其一就是充分体现了所谓“主旋律”声音的说者形象。任何一种语言形成的话语世界,都是不同说者形象相互角逐的舞台,总是会有某些说者的声音占上风,从而扮演着主流化、中心化、权威化的说者角色。正如巴赫金所言:“在每一时代里,在每一社会圈子里,在人们成长和生活的家庭、朋友、熟人、同志的每一个小天地里,总是存在着一些权威的、定调子的表述,艺术的、科学的、政论的作品;人们信赖它,引用它,摘录它,仿效它,追随它。”谈到不少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文艺作品,人们只看到它们是各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却没有看出这类作品也共有着一类不谋而合的说者特色。这是放声歌颂各民族翻身得解放和团结奋进,属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代言人的说者形象。比如在建国以后推出的那些经典电影文学作品中,这一点就体现得格外突出。
其二就是具有较高文学素养,在人文知识分子中属于作家这类典型文化精英的说者形象。近代具有现代知识分子身份和眼光的说者,在汉语世界出现以来,就开始扮演着这一话语世界中引人注目的一类说者角色。近些年学界一直在争议什么才算是知识分子,如何对其进行准确定位的问题。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原本作为话语世界中最善于,也最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说话人,他们理应持有什么样的立场、观点、看法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一个应该说什么和怎样说,究竟是在扮演何种说者形象的问题。任何对知识分子说者形象格式化的定义,都会被他们实际具有的“多面相”事实所打破。所以无论学界对于知识分子作为说者的形象有过何种充满期待的单一性描绘和定位,有一个事实却无法回避,现代知识分子作为说者的一个最典型的特性,恰恰就是他们可以按照多元的期待视野,扮演各类代言人的角色,这类言语主体的社会文化形象,原本就充满了可塑性。所以这类作家在汉语跨族际写作中呈现的说者形象,也自然会呈现出一些因人因时而异的变体。比如以藏地写作成名的马丽华,对自己作为边地和异族的说者形象,就有过这样的自我描述:“但西藏在想起我来的时候,我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是一个逗留得太久,热情也持续得太久的行吟诗人吧,是一个喜欢张望人家生活情景,喜欢打探人家人生之秘的好奇的旅人吧,是一个执迷投入但始终不彻不悟不知圣者为何物的朝香客吧。”
新时期以来,多元化的文学语境,为作家这类文化精英说者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广阔空间。这里试举一类,这就是汉语跨族际写作中所谓“伤逝者”的说者形象。一个新旧更替特别突出、普遍的时代,往往也是充满伤逝情怀的说者形象最容易滋生的时代。对日渐改观的民族人文传统情不自禁地感伤忧怀,也成为汉语跨族际写作中此出彼现的一类说者形象的原型。比如迟子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小说从头至尾的讲述者之“我”,自称“我是个鄂温克女人,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这个“我”在小说中出场的开场白是:“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迟子建在创作谈中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我满意的苍凉自述的开头。”其实,作家寻找自己称心如意的文学讲述风格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为自己的作品寻找心仪的说者形象的过程,也是作家为自身的说者形象“招魂”的过程。有的论者因为小说通篇出自那个鄂温克老人之口,便将这部小说称之为“独语体”小说。在我看来,这同样也是作家的叙事技巧给人带来的一种文学错觉。用巴赫金式的眼光来看,与其说这部小说是一种“独语体”,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仿格体”。这是来自汉族的作家之我,在感同身受地假托一位异族的老人说话。用巴赫金的话说,这里“仿格者是利用他人的视点做文章”。这里的“作者不仅描绘这一‘语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自己也用这一‘语言说话”。正如巴赫金所言:在研究小说中包括叙事人在内的说话人这一问题上,人们时常都没有廓清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在文学中建立说者形象和语言形象(言语形象)时,作取舍的不是说者本人,而是作者从说者本人的观点出发替他作的。”从表相上看,迟子建这部小说中的话语,显然都出自那个异族老人之口,都是她用来指物述事的语言,但同时这些话语的说者又是被作家深描细写的对象。借用巴赫金体味入微的一种形象说法,相对于以叙事人自居的那个异族老人而言,她深沉道出的“这种语言虽已成了描写的客体,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就好比一个人潜心干自己的事,而没发觉别人正在看着他”。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自始至终深情凝视着,并塑造出那个鄂温克老人说者形象的说者正是作家本人。如果说小说中的叙事人是在扮演一个部族衰落史的说者角色,那么站在其后的作家则是扮演着对这类行将远去的“逝者”一唱三叹、感怀不已的“伤逝者”的说者形象。谈到这一点,与古代汉语跨族际写作中文人之我的说者形象相比,当代文学中的这类说者形象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已经改写了那种传统的教化者和启蒙者的说者面貌。我发现,其实在最早开始从事汉语跨族际写作的艾芜等作家那里,就已经开始弹拨起这样一个文化基调,即不少汉族作家之所以倾心于边地异族的描写,他们几乎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心理动因,即寻找某种“我们”已经失去或“他们”正在逝去的东西。用迟子建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民族在精神上越来越萎缩,就是因为缺少了少数民族人身上那种可贵的血性的东西。”
回到李娟作品中的说者形象这一话题。李娟至今所有的文学写作,使用的都是散文这一文体。这里也会引出这样一个相关问题:小说和散文作为文学写作的两大文体,它们之间的区别究竟何在?散文这一文体的散文性特征是什么?这也是一个至今仍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问题。其实,以说者形象的眼光来看,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它们之间的区别并非在于虚构或非虚构,或是否注重写实感的问题,而是在于这两种文体作者的说者形象,在作品中往往具有着明显有别的存在方式。如果说小说这一文体的特性,往往体现在小说是作者之我的说者形象含而不露的文体;散文这一文体的特性,则更多体现在散文是作者的说者形象可见度最高,需要在文中亮相的文体。读小说的人时常会发现,小说的作者大都喜欢虚构出这样或那样的叙事者为自己扮演说者的角色,他自身的形象甚至会变得十分晦涩。而同样的作者一旦写起散文来,他们都会默守一个写作成规:不论说什么或怎样说,这都是作者之我在直接讲述我的事情,读者都会明显感到,仿佛作者之我直接走进了作品,面对读者扮演说者角色。所以史铁生才会在《我与地坛》这篇散文中开门见山:“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相对于小说而言,由于散文的作者卸掉了小说化的叙事伪装,散文也就成了作者这一说者形象的品性和特性,直接决定着作品魅力的文体。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