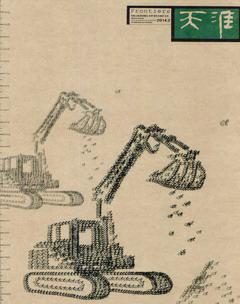驯化石狮子
2014-03-26韩振远
在中国境内旅游,不管去哪个地方,只要你参观的是人文景观,首先看到的肯定是一对石狮子。
狮子生长于非洲、南美等地,中国辽阔的疆域上,从来不出产这种重要的猫科动物,但中国大地上随处都可以看到用石材雕刻成的狮子,之所以如此,皆因狮子已然变作一种让人顶礼膜拜的图腾。
中国人的动物崇拜中有一种怪现象:越高贵的越怪异,往往是世间根本不存在或大家都没有见过的古怪,如龙、凤、麒麟,再一种就是狮子。这样做无非想制造出一种神秘感和威慑力。与龙、凤、麒麟相比,狮子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动物,其雄性体形矫健,头大脸阔,颈有髦毛,姿态甚是威猛,却生活在非洲、南美、印度等地,中国普通百姓不可能见过,多数帝王也不可能见过,雕凿石狮的工匠更不可能见过。封建社会里不可能有为大众开放的动物园,也没有摄影、摄像技术。然而,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狮子的艺术形象却在大众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小说、戏曲、杂技、民间节庆活动等艺术载体中,都可以看到狮子。狮子的艺术形象之多,存在周期之长,几乎成了除龙、凤之外的第三个图腾。
中国狮子艺术能有如此地位,与佛教传播有很大关系,佛经中称“佛为人中狮”,《灯下录》中云:佛祖释迦牟尼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因而佛教徒将狮子视为庄严吉祥的神灵之兽而备加崇拜。以后就把佛家说法音声震动世界、群兽慑服称之为“狮子吼”。狮子沾上佛光,自然身份非凡,令人起敬。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殊方异物纷纷来朝。古籍记载,汉章帝时月氏国(西域的一个小国)贡狮子,名为“狻猊”。从此狮子成为帝王专庞之物,一般人难见尊容。距离产生神秘,狮子虽是大型食肉动物,但毕竟鲜有人能“有幸”暴毙于其血盆大口之中,故无须对其抱有恐惧心理,反视为保护神有求于它,从而将狮子视为瑞兽,进而神圣化。就这样,产于异域的狮子在中国受到空前的礼遇。
石狮有一个从地下往地上发展的过程,最早出现的石狮是东汉时期的守墓狮,这一时期,狮子刚进入中国不久,中国文化还没来得及对其驯化,工匠手下的石狮亦属自然状态,抬头张嘴、挺胸收腹,作行走状,两颊带卷曲状鬃毛,肩两侧带翼翅,极富动感,威风凛凛,气势非凡,充满勃勃生机和大汉雄风。专家们把这种石狮称为走狮。
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艺术作品是社会形态的表现,石狮亦如此。战争、饥饿折磨着中土百姓,同时也折磨着中土石狮。百姓疲惫,石狮委顿,本来威风凛凛的石狮仿佛用肢体语言表露着当时的境况,再也看不出神兽的气势与威严,没有了汉朝石狮的神采飞扬。同为走狮,有的步履蹒跚,有的戛然而止,有的脚步沉重,尾巴有气无力地下垂,隐隐显露出战乱年代人们内心的彷徨、疲惫、无奈和恐惧。有些石狮伸长细脖,有些却紧缩下颌,有些还像狗一样伸出长舌。只有鬃毛增多,仿佛为掩饰内心的绝望,只好用鬓毛来虚张声势。
长时间的战乱,统治者累了,百姓累了,石狮好像也累了,不得不蹲下来喘口气,以便攒足力气,以图将来。人们把蹲下的石狮称为蹲狮,南北朝时期的蹲狮静中有动,给人以蓄势待发之感,下颌收紧,前腿前伸,后臀着地,还隐隐带有行走之状,造就了以后隋唐蹲狮的基本倾向。
从隋朝开始,与建筑相关的石狮逐步以蹲狮为主,在继承南北朝蹲狮特点的同时,石狮的两翼没有了,这种由外部引进的艺术形象开始走向民族化。造型更为丰满,细节更为写实,胸部显得宽大、厚实、壮硕,更显沉稳。而且有了公、母之分,公狮发型为卷发状,母狮发型为披发状。既有性别之分,站位也有区别,中国社会讲究“男左女右”,石狮则公左母右。蹲狮虽居多数,但走狮仍大量存在,唐朝的走狮造型与唐代的审美风格相一致,圆浑壮硕,沉稳有力,充分显示出帝国的强大与自信。
如果说,宋以前对石狮的驯化是环境所致,多是外形的改变,那么,自宋以后,则是人为地对石狮进行驯化,改变的是其精神。从宋朝开始,石狮进入精神驯化期,开始秀丽化、世俗化。受封建礼教影响,威武的石狮竟被人为地套上一个原来为狗所用的项圈,而且上面铃铛、缨绥俱全,生生把狮子的英武之气一股脑套没了。走狮的遭遇更加悲惨,除了扎眼的颈部项圈、铃铛、缨绥之外,还加了一条牵引链,像牲口般嘴里被勒上嚼子,把狮子弄得连犬也不如,使其从神圣化的高台直接走向世俗化的人间。好在从宋朝开始,石狮终于从阴气森森的陵墓、石窟中走出来,开始踞守于达官贵人的私宅前,矗立于官署衙门口,成为等级与权势的象征。从此,威风的石狮好像被人驯服,一步步走向世俗。
接下来,石狮就必须按照人类的意志做它该做的事了。
金元时期,石狮不再注重发型,不分公母,一概为螺旋状圆锥形,颇似佛祖发式。神圣化只通过一个符号而存在,没有了整体的神奇。性别由其所司之职来体现,中国人不是通过抛绣球求亲吗,那么,就让雄狮前爪下踩个绣球,雌狮的职责与世间女人一样是生儿育女,就让它前爪下有个小狮吧,这种拟人化手段的运用,体现出当时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把石狮的世俗化表现到极致。
明清两代是封建社会的衰落期,石狮艺术开始走向程式化,不仅没有了狞厉之美,而且逐渐有了喜庆吉祥色彩。连节日闹社火也举着个狮子,至此,这种来自遥远非洲的猫科动物,其实比任何一种动物都离百姓生活更近。狮子的形象更加充满臆测想象,对狮子的本来面目视而不见,我行我素。狮子的外在装饰更多,除了牲口一样的披挂外,嘴里还多了一颗珠子。据说,狮子爱玩“夜明珠”,所以嘴里要含一颗能活动的圆球。
明清以降,石狮更多地被请到大门前,与门神共同承担守户安宅之重任。因为,把这样的瑞兽雕刻成型请到大门前,会在人的心灵中产生安定感。民间流传门前石狮的作用多多,其一:避邪纳吉;其二,彰显权贵;其三,艺术装饰。有的地方还认为门前石狮能预卜洪灾,每当洪水来临之时,石狮的眼睛会变成红色或流血,人们看见后即可应急避难。但是,不管怎样,狮子都不得不蹲在大门前,履行着看家狗的职责。endprint
因为守门石狮在民间广泛应用,清政府认为有必要立一些规矩,以免已经走下神坛,但还余威尚存的狮子连仅有的象征意义也消失,影响统治者的尊严。清代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侧例》中对设置守门狮做出了相应规定:如:一品官门前的石狮头部要有十三个卷毛疙瘩,并随官职降低逐步减少其数量。犹如现在的军衔、警衔一般,官职大小一目了然。七品官以下不准在门前设立石狮,平头百姓更无此殊荣。但这种规定很快就有名无实,腐败的清政府连官职也能买卖,何况只有象征意义的狮子。
自汉代以来,经过两千年驯化,至清代,石狮完全异化成中国人自己的狮子,更加程式化,往往在一些小细节上做文章,威猛的狮子在工匠的雕琢下,更加没有个性,向吉祥喜庆造型靠拢,有些石狮甚至更像讨人喜欢、对人忠诚的卷毛狮子狗。从南北朝时期伸出长舌模仿狗的石狮,到宋代戴上狗用的项圈,直到晚清时期变成狮子狗,石狮已然名存实亡。这一时期出现的趴狮,四脚趴地,头部昂起,大嘴张开,形象简直连狗也不如,好像癞蛤蟆一般。在著名的晋中王家大院里,我就曾多次看到过这种蛤蟆一样的石狮。
在山西沁水县柳氏民居中,我曾看到多组石狮。令我没想到的是这里的石狮竟有教化作用,被称为教化狮,分别有“安分守己狮”、“金榜题名狮”、“寻求靠山狮”、“出人头地狮”,如此等等,而且教化的手段是那样的残忍。所有石狮嘴里都被勒上根粗粗的绳索,像羁勒牲口的嚼子一样,拖出口外,可以牵引。石狮表情凄厉痛苦,看后有一种莫名的恐怖感。加上被风化成白色,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我当时的感觉是看不下去,赶快逃离。
晋中灵石王家大院内,一对石狮也颇有意思。威武的狮子在工匠手里,好像变成了宠物,不光温驯可爱,而且被拴上缰绳,被人牵着。本来在母狮爪下的幼狮,像小猫一样,被人抱在怀里。
山西乡村普通人家门前的石狮形制都不大,多为清代到民国时期产物,雕刻并不精细,风格淳朴,民间气息很浓,看上去如同剪纸、泥塑一样憨厚可爱,无威武狞厉之势,多有喜庆吉祥之态。在碛口西湾村我曾看到两对石狮。其中一对俯卧在门墩之上,可称为卧狮。下面的门墩边缘用竹节围起,中间有莲花瓣。石狮嘴半张,口内衔着根粗粗的绳索,耳朵耷拉,雄狮爪下踩绣球,形象在狗与狮之间,与柳氏民居的石狮造型无异,却无恐怖之气,浑身透露着憨朴可爱。另一对石狮是门墩刻狮,形态为走狮。嘴里同样含有绳索,却没有被勒的神情,面部像个安详的孩子,头上有鬈毛,尾巴高高扬起,像个圆球一样,看上去同样拙朴可爱。我想,当年的民间工匠,可能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理解雕刻出这一对石狮,连神情也带有山民的痕迹。
乡村所有的艺术品都有民间特色,这种特色就是喜庆吉祥,剪纸如此,面塑如此,石狮亦如此。
我很喜欢这些农家宅院门前的石狮。因为,这些石狮分明就是农家愿望与追求的流露,有的像严肃的老人,有的像顽皮的孩子,有的像憨稚的布老虎,有的像逗人的小猫小狗;有的头大如斗,体小若雉,所谓“十斤狮子九斤头,一双眼睛一张口”。不管像不像狮子,都能带给人一种想象。这些石狮虽然制作不如官衙前的威猛精良,但个性十足,一家门前就是一种石狮,绝无雷同。无论它像什么,都是山村风情的体现,代表着农家的审美风格。即使像狗,也是狮子,是农家想象中的狮子。所以说,石狮是雕刻艺术,虽不复杂精妙,却一定是中国雕刻中最具想象力,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异化的一种石雕艺术形象。
近年来,曾经被凿去、推倒的石狮又大行其道,赫然站立在党政机关、公共场所门前。所以如此,一是因为石狮威猛尊贵的形象不可替代,两尊石狮雄踞大门前,比贴两张门神威武多了。二是石狮镇宅祛邪作用不可替代,只要崇信风水,讲究阴阳的地方,就有可能站立着两只石狮。这种地方的石狮往往异常高大威武,制作精良,价格不菲,却经不住推敲,程式化是其痼疾,若仔细体会,还会嗅到浓重的商业化气息,带着浮躁,再也不会像旧时的石狮那样,在威武中带着沉静。
有人说,几乎所有外来东西到中国后都会走样,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带上中国特色。石狮可能就是最好的证明。
韩振远,作家,现居山西临猗县。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家在黄河边》、《遥望远古》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