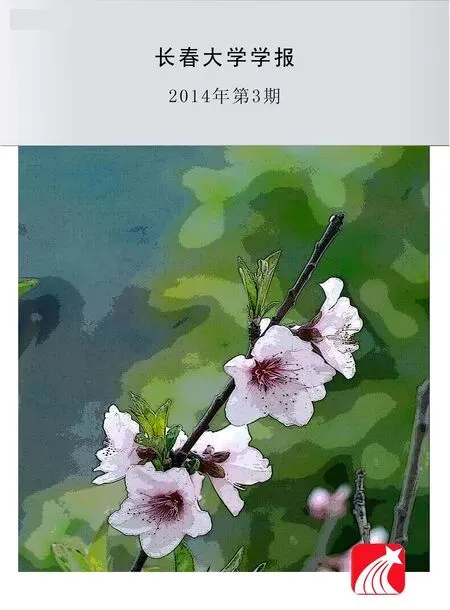失独体验下的身份与生命之思
——试论沈从文的小说《爹爹》
2014-03-26彭弥曾仲权
彭弥,曾仲权
(1.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2.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失独体验下的身份与生命之思
——试论沈从文的小说《爹爹》
彭弥1,曾仲权2
(1.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2.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沈从文在其小说《爹爹》中,以悲悯的笔调抒写了傩寿失去独子后的自虐回忆体验和孤独悲伤体验。这种失独体验的背后,一方面是傩寿作为“爹爹”的身份丧失后而感到焦虑和孤立,令其余生不知如何安放;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沈从文自身的创伤性经验以及他关于生命严肃性和文学意义的思考。
沈从文;爹爹;失独;身份;生命
1 傩寿的失独体验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爹爹》讲述的是湖南凤凰县城一位名叫吴成杰(又称傩寿先生)的外科医生,在遭遇老年丧子之痛后的生活境况和生存体验。从前的傩寿先生,阔额,双下巴,高身材,有一张“圆圆的和气脸儿”。凭着高超的医术,他开着一间“家传神方”的药铺,为县城里的百姓们解决各种疑难杂症。然而,当他步入知命之年时,其独生儿子却不幸在外地溺亡。痛失爱子的傩寿于是将牌匾摘了,生意不做了,逃到玉皇阁老和尚处,每日像孩子似的哭。
卡文纳夫在《面对死亡》一书中,对居丧者的悲哀反应分为了7个阶段:震惊,解组,反复无常,罪恶感,失落与寂寞,解脱和重组[1]。傩寿先生也经历了由精神崩溃、镇天痛哭到心酸回忆、逃避落寞,再到重回现实等艰难的“失独”体验阶段。所谓“失独体验”,是指独生子女意外亡故后,其父母所遭受的主观经验和心理体悟。独子死后,傩寿失掉了唯一的精神寄托和生存信念,他不仅外表颓唐不已,心理上也经历了多重折磨。
1.1 自虐回忆体验
儿子死后,傩寿先生因此“至少也死了一半”。他首先选择的是逃避到玉皇阁,与老和尚以及那些孤魂野鬼的牌位相依为伴。原来的环境、原来的邻里关系以及任何一件事物都会引起他的回忆和对比,痛苦的回忆始终纠缠着他,仿佛到处都是儿子生前的影子:同别人打架顽皮,打输了哭着要药,打赢了又讪讪地向爹爹讨药去给那伤者……而如今便是这昔日认为的麻烦也成了一种甜蜜却又痛苦的回忆。“这小孩的麻烦事情,这个时候哪里会再有?”“儿子那种羞愧感激的样子,这个时候也不能见了”,更不提在爹爹面前撒娇不想上学,或撒着天真的谎,或念自己作的诗与爹爹听……这全然都不会再有了。正如沈从文说的,“儿子把爹爹所有的快乐,以及一点小小脾气,也带到土里去了”。
这时傩寿先生就会自虐式地想象着“就是恨他,虐待他,假若是这样可以把那个儿子从死神的手上夺回来,他愿意。若是他一死,就可以使儿子活转来,也愿意”。所谓死者长已矣,又如何懂得活着的亲人的悲痛。傩寿先生“每日让一种从回想上得来的忧愁啮食着这颗衰败的心,不知道什么时候为止。”胡塞尔[2]认为,从价值论的角度看,时间并没有具体的现实性。只有当主体在意向着、直观着的时候,时间才成为现实性的。所以,重要的不是时间的现实性刻度,而是被主体体验着的时间,是意向活动中的时间体验,离开了人的体验,单纯谈实在之物的时间将毫无意义。正是儿子的死激活了时间在一个父亲生命中的意识,他感到度日如年所带来的折磨。“儿子在,医生实以为纵有六十岁也仍然是四十岁的心”,而如今五十岁的他,却似乎感到有七十岁——儿子的年龄似乎也加到他身上了,他正半死半活地承受着时间的凌迟。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也是一位“失独者”,她一遍遍地对人哭诉自家孩子被狼叼去的凄惨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祈求别人的多少怜悯,只是自虐似的在一遍遍讲述中强迫自己回忆,强迫自己不断感受那种刀绞般的失子之痛,这是一种变相地折磨惩罚自己。
1.2 孤独悲伤体验
当常人在同情别人时,总在潜意识里带着一种优胜庆幸的姿态,这让悲痛者的痛苦加重,无论怜悯还是关怀,于他们而言无疑只是二次伤害。傩寿一生行善,却遭遇如此恶果,但他并不怨天怨人,也不想要别人的怜悯。县城里的人也似乎只是怕少不得这样一个心地仁慈又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并没有人真正懂得他。因此,傩寿先生的悲痛并不被大家所理解,他们只是给予他无尽的怜悯。殊不知,正是这怜悯让他感到他与平常人家的不同,让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丧子的疼痛。当傩寿先生抑住悲伤替人诊治时,并不愿提及丧子之痛,而对方却偏偏又用看似极同情的话谈起,以为是好心,实则徒增了傩寿的凄楚;傩寿先生之子还活着时,有人劝他续弦的,也无不是贪医生的小康,想从亲戚中介绍相宜女子结亲,为自己今后若有个病痛作打算。而傩寿想的却是亡妻临终的遗言,想要给孩子全部的爱,免受后娘薄待;在为别家小孩施行手术时,如果小孩成了哭脸,作父母的就全然不顾傩寿先生,赶紧把孩子带走了;来参加傩寿儿子葬礼的,也是家中有病需有求于医生之人,无病无痛则医生很快就会被忘却;三个月后,傩寿先生又重新把铺柜门打开了,大家都以为他忘了丧子之痛,或视医生为治病救人才继续活着,全然不了解心死如灰的傩寿。他依旧微笑,却不似往日之笑,想必这微笑中有生活全部痛苦的印记,有对人生无常的深刻悲悯。但他人也全然不了解。傩寿的知音也许只有玉皇阁的那位老和尚——一位不矫情、不势利,也有过丧义子之痛的老者。只有遭遇过同样经历的同病相怜者方能站在同一维度上,互相体恤,互相安慰。小说末了,沈从文用轻描淡写的笔触描写了傩寿的死,没有渲染任何人的哀痛,甚至只表达“医生一死给了许多人不方便倒是真的”这一评价,在心酸的嘲讽中更为傩寿一生孤独而不被真正理解所感到悲哀。
“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乃人生三大不幸之事,傩寿先生竟就遭遇了两样,其悲可想而知。沈从文认为,悲哀像中毒。血气方刚的少年,或许过一会便复元,而老人虽并不显出中毒模样,但“身体内部为悲哀所蚀,精神为刺激所予的沉重打击,表面上即不露痕迹,中心全空了。老年人感情中毒,不发狂,不显现病状,却从此哀颓萎靡下去,无药可治。”傩寿先生初闻丧子噩耗时也曾大哭一阵,后来便不再去玉皇阁大钟下哭,且重新营业,外人看来以为全好,但实际上悲哀像一剂慢性毒药一样已经浸透了他的全身,这种潜伏的隐痛在他身上侵蚀着他的魂灵。“以前一颗心,像全寄存到儿子胸腔子里……如今儿子既不再到这世界上,这颗心,已不知要放到什么地方去了”,表达了傩寿对儿子深切的思念以及余生的无望。
2 “爹爹”身份的遗失之思
傩寿先生的死,除了前文提到的因自虐回忆和孤独寂寞造成的“失独”体验折磨外,还有一项重要原因,是他失子后作为“爹爹”身份的丢失而处于焦虑无措的状态中,这些使得他丧失掉生存的信念,使其感到余生无处安放。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身份”是指个人在社会上享有的法律规定的受他人尊重的价值、地位和重要性。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个体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具有不确定性,需要在他人的评价中完成对自我的定义[3]。傩寿在其子未死之前不仅是作为一个医生身份的存在,更是作为一个父亲(爹爹)身份的存在。正是这双重身份的和谐共存塑造了一个开朗善良的傩寿先生。而痛失独子后,傩寿作为父亲的身份被瓦解了。“爹爹”这重身份恰恰是傩寿最为在乎的,这一支架的坍塌使傩寿陷入丢失父亲身份的焦虑无措中。“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型形态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4]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族血缘关系伦理建构的社会,个体身份的确立是建立在家族伦常关系之中。由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5]所引申出来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确立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人的身份。事实上,自夏朝“家天下”以来所形成的家国同构关系中,“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6],君臣关系是父子伦理关系的延伸,“父子”的伦理身份是最为根本的。这一身份关系对于个人在封建家族宗法制社会中的身份确立至关重要。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向来有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7]的伦理警示。傩寿先生的“失独”使他违背了这一伦理规范,“爹爹”身份的消失使他无法在余生中体会一个父亲在父子伦理体系框架中所应享受的欢乐、地位和尊严。不仅如此,小说中的他还丧了妻,而且年事已高的他在“儿子一死,也成了与孤魂野鬼相近的一个人了”,可知其高堂父母亦不健在。因此,傩寿处在一种既不能成为“父”,也不能成为“子”,更不能成为“夫”的游离状态中。于是,他被乡土社会的典型形态抛弃在外,成为了一个孤独的、无身份的存在。
从中国传统的血缘社会角度来看,“失独者”傩寿的父亲身份已经遗失,他得以继续存活的是他作为医生的职业身份。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中国传统血缘关系型的伦理身份范式在伴随着自然经济逐渐瓦解的现代性进程中,逐渐被职业型的身份范式所取代。在小说中,医生的职业身份不仅让在血缘伦理关系中丢失了身份的傩寿寻找到了继续存在的希望,也使他作为服务于县城百姓需要的一种精神符号而存活着。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爹爹”的傩寿已经死了,傩寿的生存状态仅仅是“活着”——无目标、无信念地活着。正如余华在他的小说《活着》的韩文版自序中写道:“‘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8]傩寿先生“无法来抵抗这命运所加于其身的忧愁负荷”,也只能是忍受般地活着,“只有尽自己悲痛下来了”。
威廉·布洛姆认为:“身份确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安全感。”[9]傩寿先生在丢失父亲这一身份后,无意识地开始加强其仅有的医生身份。这令他只要是见了病人来求助的,尤其是哭泣的小孩,即便是在悲伤中也从不拒绝别人的请求。“一面是疯子一样怀恋着已经埋到异地土里了的儿子,一面又来为人看病敷药”。而傩寿先生作为“救人”的医者却无法“救己”,自身心病不知如何调理,这又导致了医者这一身份内部的自相矛盾。这种自相矛盾其实是中国近代社会现代性未完成的产物。妄图从职业关系中确立身份是徒劳的,传统的血缘关系型身份确立范式使得丢失“爹爹”身份的傩寿虽然在服务于县城百姓的需要中寻找到了继续存活的理由,但是却在情感上受着“爹爹”身份遗失的折磨。“医者”身份的继续存在非但没有使傩寿回到常态,反而使其在医治他人孩子的过程中,因不断被唤醒其“爹爹”身份遗失的焦虑而饱受情感折磨,“见到别的小孩子,心上载不住悲哀”,“常常把眼泪来当饭”。正是“爹爹”身份的丢失和“医者”身份内部的矛盾共同加速了傩寿的死亡。傩寿要想重获“爹爹”的身份,从“爹爹”身份遗失的焦虑和情感折磨中解脱,只有通过死亡在“地下”去重拾“爹爹”的身份。“这作爹爹的,就为了不能让儿子一人在地下寂寞,自己生着也寂寞,要儿子复活既不能,于是就终于死了。”
3 《爹爹》背后的生死之思
在沈从文的审美世界中,爱、美、死亡通常都是彼此联系,和谐共存的,对死亡的抒写是他思考生命的一种特殊文学方式。由于受童年时期对死亡认识的影响,沈从文对死亡的抒写大都呈现出自然性、客观性,虽以死亡意识为悲剧底色,但因糅合进牧歌情调,使得其小说呈现出哀而不伤的美学风格,克服了常人对死亡的恐惧与不安,令读者能够直面死亡。如《边城》中翠翠父母、爷爷、天保等的死亡,《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媚金与豹子的殉情,还有《月下小景》中寨主独子傩佑与心爱的女子为爱而死等等。而《爹爹》这篇小说却毫无牧歌田园诗情,让人读来凄恻悲悯不已。
《爹爹》这篇文章作于1928年初,此时沈从文由北京刚来到上海,租住在上海善钟路的一个小亭子里。从北京到上海,不仅仅是空间位置的迁移,更逼迫着沈从文身份的转换。一直伴随沈从文的自卑情结,造成他难以与其都市身份相认相容。都市的繁华喧嚣带给他的只有生活的困窘、身体的疾病和心理的压抑等创伤体验。“真正的创伤体验一般来自于没有防范的和突如其来的打击,来自于美好事物突然露出了狰狞面目,心理承受力在猝不及防的考验中濒于破碎、趋于崩溃。”[10]这些创伤体验使得沈从文将自身的孤寂、回忆和身份缺失的焦灼潜移默化地熔进了《爹爹》的抒写中。
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要表达的不仅是自身创伤性的日常经验,更探讨了摒弃死亡本身外,死亡于生者(居丧者)的影响,并隐含了其生死意识及朦胧的文学理想。最深的舐犊情却换来最浅的亲子缘,沈从文力求通过傩寿先生这个人物透射出的体验,去引导读者获得一种人生的严肃感。人永远无法体验和感知自身的死亡,只有从他者的死亡中来感知和体验死亡。如同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山鬼》里描写到的,当毛弟的爹在世时,癫子大哥曾聪明伶俐、快乐自如;毛弟的爹去世后,毛弟大哥疯了,毛弟的妈也必须承担起生活的艰辛。毛弟爹的死,使得家庭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中。无怪乎沈从文还在《爹爹》中半带愠怒与嗔怪地责备傩寿之子“把一个健壮有为的身体,毁灭到一件无意而得意外事上,这对生命仍然可以说是一种奢侈浪费。”这种对生命的不负责任导致“另外一个活着的人生活全变了”。这些均表达了沈从文对生命严肃性的推崇,他希望人是以一种自我负责、自我实现的态度去面对死亡,而不是挥霍消磨珍贵的生命。人怎样去张扬自己的生命力,如何在生命的燃烧中显示生命的意义,是沈从文礼赞生命、讴歌人性美的终极目的。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还回忆到,一个平时身体很壮的老同学陆弢,为了同一个朋友争口气,而在泅水中不幸被淹死。这件事让沈从文感慨到历史的无情,个人的悲欢全然不被历史所关注,渺小的人被卷入历史的洪波后,便消失殆尽,激不起一点浪花。于是沈从文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他认为个人的悲欢是很难被传递的,别人永远无法感同身受。沈从文曾说:“人间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11]但他觉得文学是有魔性的,只有通过它才能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康长福曾总结过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他认为沈从文一是想借助文学的手段来重造人性、生命、民族品德,进而实现重造社会、国家、民族的社会理想,这可称之为“重造的工具”;二是希冀通过文学的重造来实现重造文运、重造经典、抗争文学审美危机的艺术理想,即“工具的重造”[12]。沈从文便是用文学这支“魔笔”写出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用这种平易近人、润物无声的方式唤起了人的感觉和想象,使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阶级的人们都能够从这些故事中获得关于人生、生命和社会关系的重新体验和思考,进而达到对生命的明悟。他希望借助文学这座桥梁来重造人性和民族品德,进而实现重造社会、国家、民族的社会理想。
[1]汤笑.死亡心理探秘[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289.
[2]埃德蒙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80-85.
[3]樊朝刚.创伤体验与沈从文小说创作[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26.
[4]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
[5]论语:中华经典藏书[M].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77.
[6]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295.
[7]杨伯峻.孟子译注: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0:182.
[8]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5.
[9]莱恩·T·赛格尔斯.“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文学研究中的新视角[M]∥乐黛云,张辉.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28.
[10]贾振勇.掮住黑暗的闸门:创伤体验与鲁迅的自我救赎[J].鲁迅研究月刊,2010(2):25-31.
[1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90.
[12]康长福.沈从文文学理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
责任编辑:柳克
Thoughts of Identity and Life under the Experience of Losing Only Child—A Discussion on Shen Cong-wen's Novel Daddy
PENG Mi1,ZENG Zhong-quan2
(1.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2.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Shen Cong-wen,with a tone of compassion,describes themasochistic recall and lonely sad experience of Nuo Shou after losing his only son.Behind this experience of losing only child,on the one hand,this novel expresses Nuo Shou’s feeling of anxiety and isolation after losing the identity as“daddy”,making him not know how to spend the restof his life;on the other hand,it reflects Shen Cong-wen’s traumatic experience and his thinking about life seriousness and themeaning of literature.
Shen Cong-wen;daddy;losing only child;identity;life
I207.427
A
1009-3907(2014)03-0362-04
2013-11-11
彭弥(1989-),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研究;曾仲权(1987-),男(土家族),湖北咸丰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和美学研究。